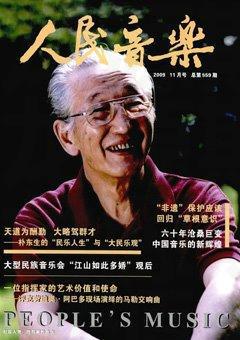不同时期土家族歌舞艺术的文化特征研究
土家族优秀的民间歌舞艺术记录了土家族民族文化发展的艰辛历程,其文化积淀十分丰厚,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这也是本文立意的初衷。
笔者认为要研究“歌舞文化”就必须正确理解“音乐文化”。正如露丝•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一书中提出“从未有人以原始的眼光看过这个世界”,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对音乐文化的研究局限在如爱德华•汉斯立克(E•Hanslick,1825—1904)或约翰•布莱金(John Blacking)对音乐的认识和界定上①,而是应该跳出音乐文化事项的文本,将其放入本文的环境下,以一种深远的视态和宽广的胸怀,接纳这种音乐及依附于它的相关文化现象。J•T•提顿、M•斯娄宾认为“音乐,尽管是一种普存的现象,但它是以文化获取其意义的”②,因此,他将音乐行为的四个组成部分(音乐、表演者、听众、时间与空间)演化为一种音乐文化模式:情感、表演、社区和历史。以此为参照,笔者认为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将本文中的歌舞文化研究范围界定为:内容、歌舞形式、歌舞行为者及对象、历史文化背景,本文旨在对这些因素在不同历史时期呈显出的特征元素进行提取和研究。
一、第一阶段:先秦时期
这一阶段主要指公元前316年秦灭巴国前,是土家族早期歌舞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时期。一方面,为了生存,土家族先民除了与自然抗争以外,还不断和异族发生战争,如巴族在廪君时代以后,势力迅速增长,战事日益增多,使其歌舞形式逐渐向“战舞”性质发展。《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周武王伐封,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歌舞行为中展示出巴人劲勇强悍、无所畏惧的民族精神。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力低下,土家族先民的生存条件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自然环境,由此产生了土家族先民特定的文化生态意识和图腾崇拜,这种意识突出地体现在当时的祭祀性歌舞行为中。
1.具有战斗性的特质
这一时期,土家族歌舞行为中体现出“战斗”、“奋斗”的特征。在《华阳国志•巴志》中描述的古代巴人“天性劲勇”、“前锋陷阵”、“锐气喜舞”,《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集解引郭璞称其:“皆刚勇好舞”,其歌舞御敌的场面壮大,开创了世界战争史上运用歌舞行为战胜敌人的先例。这个时期的歌舞行为在很大层面上展示了古代巴人勇猛好战、“锐气喜舞”的性格特征。
如早期巴渝舞。据史料记载,该舞是一组由古代巴人创造的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表现战争题材的大型歌舞,其舞大约分为六段,名六成。③所有表演者均“执杖而舞”,场面甚是浩大壮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左思的《蜀都赋》中曾描绘了巴渝舞演出时,其舞容矫健剽悍的生动写照。④再如摆手舞。据记载,土家族先民在渔猎时代就已会,其中的军事舞就是表演战阵舞的动作。伴随着一锣一鼓的伴奏,展现变化无穷的单摆、双摆、侧身摆、送摆、回旋摆等上百种摆式,其动律特点为:走动顺拐,重拍下沉,双腿屈膝,全身颤动④。可见其模仿古代战争动作的成分很大。其中被誉为“戏剧史上的活化石”的茅古斯是穿插在摆手舞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⑤,共由七部分组成,其中第一部分和第七部分都分别描绘了土家族先民们和野兽、自然、异族之间的搏斗,其舞蹈动作古朴、刚劲有力、粗犷豪放,从而进一步渲染了土家族先民勇猛善战、威武不屈的民族性格。
2.具有图腾崇拜和祭祀的特点
图腾、祭祀(宗教)性舞蹈是中国四大类民间舞蹈⑥中的一类。土家族先民信仰和祭拜多神及与他们生活相关的自然事物,其中尤其信仰太阳神和土地神,⑦土家族先民很早就懂得运用舞蹈形式来沟通神与人,并且认为只要神高兴了人才能愉快地劳动和生活,故在当时的许多民间歌舞艺术的内容中呈现了大量娱神和娱人的元素,深刻地体现了这一时期歌舞艺术的巫祭特征。
如虎舞通过模仿虎的动作而表现了土家族先民对白虎的崇拜;原始的摆手舞“排甲起堂”、“闯架进堂”、“纪念八部”、“迁徙定居”等内容⑧,表现了土家人敬畏祖先、娱悦神人的深度意识;跳丧舞则通过歌、舞、乐一体的民间歌舞形式,表达了土家族先民对生命的崇拜;而茅古斯和梯玛神歌中表达出的生殖崇拜内容也是土家族先民生命崇拜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礼记•周礼》和《诗经•小雅•甫田》中记载和描述了古代巴人有击鼓祭礼田祖的习俗⑦,薅草锣鼓歌便是这种祭祀“田祖”(土地神)的歌舞行为,常由小鼓、大锣、马锣、大钹互相配合进行演奏⑨,以达到娱神娱人的目的。
二、第二阶段:秦汉至南北朝时期
虽然在先秦时期巴族和周围族群的交往一直较为频繁,但秦灭巴后,随着各民族的交流日益增多,土家族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范围内族际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土家族歌舞艺术得到较大发展。至汉代,汉高祖将巴渝舞纳入宫廷歌舞文化,按照统治阶层意志进行继承和发展。此后至南北朝时期,虽战争不断,但由于历朝对宫廷歌舞文化的重视,以及土家族自身文化发展环境较为宽松,故这一时期土家族歌舞文化分别向宫廷歌舞和民间歌舞方向发展,而呈现如下特征。
1.作为统治阶级彰显功德的政治工具
鉴于古代巴人的歌舞行为在战场中的出色运用,它逐渐被统治阶级所关注。汉高祖将巴人在战场上大胜殷人而跳的巴渝舞正式纳入宫廷歌舞文化,并将之改编和发展。《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将晦涩难懂的古老巴族土语重新填词,《晋书•乐志》记载:“(巴渝)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召本歌曲》、《行辞本歌曲》,总四章。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读。魏初,乃使军谋祭酒王粲改创其词……而为之改为《矛渝新福歌曲》、《弩渝新福歌曲》……以述魏德。黄初三年,又改《巴渝舞》曰《昭武舞》。……据功象德,奏作《武始》、《咸熙》、《章斌》三舞,皆执羽龠。及晋又改《昭武舞》曰《宣武舞》,《羽龠舞》曰《宣文舞》”,同时也招募巴族乐人进宫为其服务,如《汉书》所载。由于长期于宫廷中表演,巴渝舞已丧失了以前“战舞”的功能,逐渐演变为朝廷为接待“四夷使者”而举行宣扬朝政的阅兵式性质的礼仪性歌舞,土家族民间歌舞艺术被作为统治阶级彰显功德的政治工具。
2.作为民间评论政治的有力武器
另一方面,继续流传于土家族民间的歌舞文化较好地保留了本族的民俗和民风,又由于发展环境较为宽松,民众间拥有一定自由的话语权,于是民间歌舞艺术又被作为品评朝政的有力武器。如《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土家族先民为称赞“巴郡陈纪山,为汉司隶校尉,严明正直”,以歌谣形式唱道“筑室载直梁,国人以贞真。邪娱不扬目,枉行不动身。奸轨辟乎远,理义协乎民”,而对汉武帝和孝桓帝时的巴郡太守则分别以歌谣形式予以讽刺“明明上天,下土是观。帝选元后,求定民安。孰可不念,祸福由人。愿君奉诏,惟德日亲”、“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应,府记欲得钱。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犬”。
三、第三阶段:唐宋至明清时期
这一时期,统治阶级继续加强其对土家族地区的政治统治。宋元时期实施了“相对独立于皇权直接管理体系之外的”⑩土司制度,原本自给自足的土家族先民被迫成为被土司进行剥削和压迫的“土民”;元明清时期施行了“改土归流”政策,废除“土司”,有效地解决了中央王权的统一和稳定;在清代,全国各地不少文官被朝廷派往土家族地区,带来了先进的外来文化{11},发展了这里的文化和经济。这个时期民间歌舞中大量反映了土家族人民的痛苦生活状况和对封建制度的憎恨和反抗;同时,土家族歌舞艺术中继续保留了原始的民俗民风,藉以保存自己的民族身份。
1.具有反映民间疾苦、抨击封建制度的内涵
由于汉族封建文化作为强势文化注入和溶解着土家族民族文化,使土家族的许多原始的民风民俗无可选择地背离了自己的传统,逐渐激发了土家族人民强烈的反抗意识,于是出现了以“哭嫁歌”为代表的,大胆、直接的表达自己内心感受,反抗封建制度的民间歌舞艺术。
哭嫁歌,也称“十姊妹歌”,是土家族一种非常有特色的歌舞艺术形式,它产生于封建统治阶级在土家族地区施行统治制度之后。早期土家族的婚俗非常自由,男女之间经过交往、对歌、赛歌、跳舞、吹木叶等方式接触,相爱之后,经过土老师作证即可成亲,不索取任何财物{12}。但在统治阶级逐渐加深对土家族的统治后,特别是在清雍正十三年(1735)实行“改土归流”制度之后,封建枷锁日益牢固,土家族妇女的自由婚姻状态不复存在,继而取代它的是如民国《永顺县志》记载的“坐床”、“填房”、“还骨种”等汉族封建婚姻礼俗制度,这种从自由到不自由的落差强烈地刺激了土家族妇女的民族灵魂,它实际上是改土归流后土家族普遍存在的女性婚姻悲剧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家庭悲剧的一个缩影{13}。哭嫁歌在形式上是以轮唱为主,节奏较为规整,由歌词的句式来划分乐句的句式,具有长短句特点,一般在每句称呼过后,即加紧把歌词唱完,最后的字句显得宽松,情绪中时而悲叹时而怒骂,其中“骂媒歌”更是表达了女性对命运的呐喊,表达了土家族妇女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强烈抨击。
2.作为一种确认民族身份和进行族际交流的艺术
土家族生活在山区和峡谷中,交通闭塞,虽历代统治者加强过这里的交通建设,但改观不大,加之离中央王朝远,经济非常落后。但正是这样的自然环境给土家族保留和恪守自己传统的民风民俗创造了条件,因此,即使在“蛮不出洞、汉不入境”和“改土归流”等管制制度的影响下,土家族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努力维系着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并且在与汉、苗等民族进行族际交流中举行形式多样的歌舞艺术行为,使其在确认民族身份和确立民族自我保护意识的同时,更是凸显了强烈的文化交流欲望。
如长久以来“本寨数十里外辄为足迹所不至”{14}的土家族人民一直拥有自己统一的活动中心——摆手堂,并定期在这里进行大型集体歌舞,维系着本民族的民族身份认同。同时,摆手舞还将周围苗、汉族人民吸引和聚集在摆手堂内外,使摆手堂成为族际交流与交往的活动中心。清朝彭施泽的竹枝词“福石城中锦作窝,土王宫畔水生波,红灯万盏人千迭,一片缠绵摆手歌”,就生动描绘了其载歌载舞的热闹场面,从这个意义上讲,摆手舞加强了本族人民之间的联系,促进了本族文化的发展。再如这一时期,薅草锣鼓歌被广泛参与,大家聚众而歌,为民族习俗的传递和族内教化创造条件;同时土家族民间戏剧(傩戏、阳戏、秀山花灯戏、土戏等)也在这一时期发展和繁荣起来,由于其内容多为表现本族或他族的各种俗事,加之也是聚众而观的形式,因此在潜移默化之中对本族传统文化的教化和传承以及外族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起的作用和效果是非常大的。
四、第四阶段:建国后——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1956年11月,土家族最终得到了党和国家的确认,土家族文化更受到国家的重视。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土家族地区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逐渐消解,地域差异性的逐渐消失使其民俗文化的地域性特征越来越模糊,民间音乐舞蹈资源作为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化功能变异和消失的成分越来越重。一方面,如土家族摆手舞因其运动特点,已演变为一种传统体育项目;“哭嫁歌”的文化内涵也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发生很大的变化{15}。另一方面,作为土家族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情歌,本是研究庙堂文学和封建士大夫文学创作的重要原始素材,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社会经济的冲击使如今会唱原始的土家情歌的人越来越少;在“文革”期间,像茅古斯、跳丧舞等因其带有封建迷信和神秘巫术色彩而被当作陋习禁止表演,直到今天,这种艺术形式由于传承问题也在人为地淡化和消亡。面对这些情况,在当今,土家族歌舞文化因其丰厚的民族和历史文化内涵而被赋予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身份,并正在被政府和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所共同关注,同时她也显得格外娇脆和珍贵。
当下,挖掘、传承、整理和研究土家族传统的歌舞文化事项便成为我们每个民族音乐工作者迫在眉睫的任务。近年来笔者欣喜地发现,研究土家族民间艺术的专家和学者大幅度增加,不少通过精心提取的优秀民间音乐舞蹈资源正被音乐舞蹈工作者重新创作、加工和表演,如《木叶情歌》、《摆手欢歌》等,从而创新地继承了这些优秀传统艺术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看到了土家族传统歌舞文化的生命系统得以延续的希望,我们更愿意看到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生命之树能在世界民族文化的大森林中得以长青。
①薛艺兵《音乐的文化模式》,《中国音乐》2008年第3期。
② J•T•提顿、M•斯娄宾《一种认识音乐世界的音乐模式》,管建华译,《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③左尚鸿《巴人军舞遗风与“泥神道”传承》,《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④陈廷亮、黄建新《摆手舞非巴渝舞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⑤李丹《浅谈毛古斯舞对人的发展的影响》,《前沿》2008年第6期。
⑥刘彦、全露《操化:土家族摆手舞的现代变异》,《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⑦熊晓辉《土家族栽秧薅草锣鼓歌的生态生成及其艺术特征》,《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⑧黄兆雪《摆手舞的社会功能及发展趋势》,《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6期。
⑨周兴茂《重庆土家族薅草锣鼓的现状与保护对策》,《铜仁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⑩张晓松《论元明清时期的西南少数民族土司土官制度与改土归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2期。
{11}陈素娥《论张家界阳戏的挖掘及现代发展》,《怀化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12}陈朝霞《土家族“哭嫁歌”的文化本源与艺术特征思考》,《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4期。
{13}曹毅《土家族哭嫁歌的悲剧性内涵》,《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
{14}黄兆雪《摆手舞的社会功能及发展趋势》,《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
{15}徐欣《对土家族“哭嫁歌”“哭”的探析》,《重庆社会科学》2006年第10期。
肖罡 长江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张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