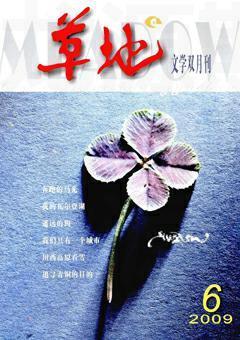雪地上的脚印
房 蒙
母亲生炉火的时候总会把柴火杂乱的丢在地上,起先是玉米芯,“哗”的一声从荆条筐里倾倒出来,之后是用斧头敲打酱渣块的声响。酱渣块是夏天里用花椒种子榨油后剩下来的,短圆柱体,颇像小码的磨盘,经了秋风的磨砺,变得坚硬无比。入冬了,先烧这些,再烧煤块。因为这时的我多半还在睡梦里,因此大多是一种潜意识的想象,掺杂着一些睡梦的飘渺,分不清到底如何。
母亲折柴草的声响清脆无比,这些被秋天的太阳晒得酥干的柴草被母亲粗糙的手掌所折服。与柴草同样酥干的还有火柴,“嗤”的声响过后,柴草燃烧着,骄傲的跳着舞蹈,然后被母亲塞进炉膛里,盖上炉盖。这时候,它们多半要沉默数秒,淡蓝色的烟从炉盖的罅隙里挤出来,顶在天棚上。几秒之后,我会听到它们像决堤的洪水,从烟囱里奔流而出。
柴草的烟气很淡,却仿佛怕冷一般不愿出门,只是贴在天棚上。天棚是用经年积攒的报纸糊的,久之泛出鲜艳的古铜色。我睁开眼睛,问母亲:“这烟也会看报纸?”母亲朝我笑一笑,并不马上回答,只是慢慢地说了一句:“夜里下雪了,快起来看。”我说:“是么?”于是光着身子坐起来看雪。
母亲把劈柴塞进炉膛里。火,像是勇敢的战士,在炉膛里左突右冲,发出隆隆的响声。顶在天棚上的烟渐渐淡去,屋子一点一点暖和起来。窗玻璃上的冰凌花,保存到现在,她们形态各异,而尤以菊花的造型最为常见,也最为经典。我伸出手去抚摸她们,从温润的厚度中散发出来的冰冷刺痛了我。
等母亲把酱渣块塞进炉膛里,生火的工序算是结束了。母亲站起身来,拍拍手,见我光着膀子,于是喊我披上被子。等到从外间里洗手回来,看我依旧如此,赶忙扯过被子把我包起来,最后狠狠地在我屁股上拍一巴掌,我回过头,看到母亲生气的样子,咯咯地笑出声来。
我舍不得将昨夜的冰凌花抹掉,尽管我知道它们终究是要融化殆尽的。我从融化了一点的地方望出去,整个世界成了白色的。窗台上已经有鸟儿光临过了,它们细密的足迹印在厚厚的雪里,使人颇觉意境深远,情趣盎然。煤棚子上的积雪像是新切的奶油蛋糕,与棚子里面煤炭的黑形成强烈的对比,从颜色里渗透出来的冷与热的感官的差别,会让人深思良久。伴随着将近年关的几声鞭炮声响,一些雪团寂寞地从树上落下,正好落在尿罐子里。我猜想尿罐子也一定结了冰,会在我的尿的冲击下不断变换声调,最后某处被刺出一个洞来,发出清脆的声响,冬天的早上便在这般的声响里变得鲜活且富有诗意起来。
于是,我想到例行的早晨的排尿。我拔开栓销,打开窗,冬天的冰冷毫不吝惜的将我的身体刺痛,甚至刺穿。我站到窗台上,我的头快要顶到窗户的上沿了,或许我就要长大了。我双手抓住窗棂,开始撒尿,冒着热气的尿液,带着一晚上的热量,冲破形同虚设的纱窗,将窗台上的雪融化,融出一条深深的沟壑来,四溅的尿液滴出大小不一的凹洞,参差错落。这让我尝到了其他季节里未尝经历过的快乐。
母亲将一壶烧开的水倒进暖水瓶里,躺在床上的我,因为这早上的雪而兴奋得难以入眠,于是决定起床。母亲将烧得通红的炉盖挪开来,炙热的火苗从我的倒提的棉裤里钻进去,将一切能及的线头烧焦,散发出一种好闻的味道来。于是,冬天的早上也跟着绘声绘色绘味起来。
我穿棉裤的过程简直像是繁文缛节,起先是趁着热气劲儿将棉裤套到我的腿上,然后抓着裤腰的两边整个的把我提起来,在空中短暂的几秒里,我的身体慢慢沉陷,沉在温暖的棉裤里,当然这时候还不算完,最复杂的是掏秋裤的裤脚。外祖母担心我冷,于是将棉裤的裤脚做得细而紧,于是掏裤脚也便成了一项漫长而繁杂的工作,回回都会在母亲的一声叹息里结束。等到这些都就绪,照例是比身高。母亲说:“麦收的时候还不如我高呢,如今竟然比我高了呢!”母亲说这“呢”字的声调拖得特别长,带着无尽的感慨。我低头瞅了一眼十公分厚的草褥子,没有说话,母亲也没有说话,那是用经年的麦秆填充起来的,至少从精神上支撑了我整个的孩提时代。
我推开门,先是爬到鸡舍顶上看我刚才的杰作。我想,从窗户之外去审视刚才的杰作,必然会有不同的感觉,然而结果却让人索然无味,似乎毫无新意可言。于是去看尿罐子是否如我想象般结了冰,当苹果树上一团雪花毫无顾及地从我的脖子里钻进去的时候,我终于还是会心地笑了。
村子里静极了,似乎听得到雪落的声响,甚至青烟从烟囱里逃走的声响都清晰可辨。在这种情况下,你能想象出一只鸡惊声的尖叫会有多么刺耳了。我瞥了一眼鸡舍,猜想又有呆鸡做梦的时候从鸡架上摔下来了,或者有老鼠偷吃鸡食,将它们吓着了。然而分明有一行模糊的脚印从院子门口一直延伸到鸡舍里去了。
“娘,有人偷鸡!”我瞬间做出了判断,并对着屋里喊了一声。
母亲淡淡地“嗯”了一声,拍打着手从屋里出来。她绝不相信会有人偷鸡,因为在这个山沟沟里,从来没有人偷鸡。即使谁家的鸡鸭鹅少了一只,也只会怪黄鼠狼或者鸡鸭鹅自己迷了路,断不会想到是被人偷走了,更何况在这个将近年关的雪天里。
“谁呀,快出来,里面多脏!”母亲弯下腰慢慢地问了一句。只见一个年岁与我相当的孩子从鸡舍里钻了出来,头上顶着几根干瘪的麦草。我躲在母亲身后,看到小家伙低着头摆弄着棉袄的一角,以及袄袖子上的鼻涕结成的痂,禁不住咯咯地笑出声来,因为我的袄袖子上也有同样的饹馇。
母亲进屋取来几个鸡蛋塞到小家伙的手里,小家伙迟疑了一下,最后抬头羞涩地看了母亲一眼。母亲说:“快回家吧,小心冻坏了。”小家伙这才讪讪地出了院门,三步一回头,直到转过牛大爷家的屋角走远了。
我问母亲那是谁,怎么没见过呢。母亲说,她也不认识,兴许不是我们村子的。我又问,那他为什么偷咱家的鸡蛋?母亲去关鸡舍的门,漫不经心地说道,谁知道呢?
嗯,谁知道呢。我也跟着诧诧地念叨起来。
等我和母亲进屋的时候,屋子里的烟已经不知去向了,炉膛里的火偃了声息,如人入中年,突然变得深沉且深刻起来。窗子上的冰凌花已然不见了,只留下一些细密的水珠挂在上面。窗外的风景渐渐清晰,阳光刺破云层,穿过玻璃,扑到墙上的旧报纸上,整个世界顿时万丈光芒。
雪地上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