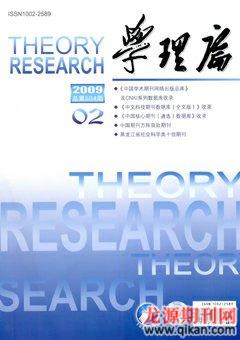论胎儿权利的立法保护
杨显滨 苏 喆
摘要:随着胎儿侵权事件的不断增多,法学界对胎儿权利的保护越来越关注,作为审判机关的法院对此类案件的裁判更是大相径庭。这反映了我国法律不承认胎儿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缺陷和不足。赋予胎儿特殊的民事权利能力,以强化对胎儿的保护是必要的。
关键词:胎儿;胎儿权力;民事权利能力;立法
中图分类号:DF5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02—49—02
一、 我国关于胎儿保护的立法现状
《民法通则》第九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从公民出生时起”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而对于成为自然人的必经阶段的胎儿还没有出生,当然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不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不享有民事权利,不承担民事义务。从生理上来说,胎儿具备了人的完整性,单纯以出生作为民事主体存在的起点是违反科学的。从人诞生的角度而言,胎儿是作为民事主体的自然人诞生的最初始阶段,如果自然人获得保护,那么作为初始阶段的胎儿也应该受到保护,否则,对于自然人的保护是不完全的、不充分的。[1]《继承法》第二十八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保留胎儿的应继承的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对于该条规定,学界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一方面,有学者认为《继承法》实际上承认了胎儿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因为有学者认为“无论是利益还是民事权利,只能为民事主体所享有,而要成為民事主体,必须具有民事权利能力。”[2]如果《继承法》不承认胎儿具有民事权利能力,那么胎儿就不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就不应该保护胎儿的利益或民事权利(应继承份额)。由此可见,与《民法通则》相比,《继承法》有了显著的进步,打破了《民法通则》的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承认胎儿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保留”胎儿的应有份额,并不是由胎儿即时取得。《继承法》虽然给胎儿保留了相应的份额,但胎儿只有出生时是活体才享有遗产权,是“留而不给”,事实上并不承认胎儿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不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3]
二、西方国家关于胎儿权利保护的规定
(一)个别保护主义
个别保护主义原则上不承认胎儿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允许有例外存在,即在某些例外情况下承认胎儿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如《日本民法典》第721条规定:“胎儿,就损害赔偿请求权,视为已出生。”《法国民法典》第1923条在继承制度中规定:“在继承开始时尚未出生,但已怀孕的胎儿,视为在继承开始前出生。”[4]《德国民法典》第1923条第2款规定:“在继承开始时尚未出生但是已经受孕者,视为在继承开始之前已出生;”第2108条第1项规定:“第1923条关于胎儿继承权的规定“对后位继承相应适用”;第844条第2项规定:“抚养人被杀时,其应受抚养之第三人,虽于其时尚为胎儿,对于加害人亦有赔偿请求权。”[5]但个别保护主义很难达到以点盖面的效果,个别列举保护终究不能穷尽,是否可行,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商榷。
(二)概括保护主义
概括保护主义认为,只要涉及胎儿利益保护的,视为胎儿已经出生。如《瑞士民法典》第31条第2款规定:“胎儿,只要其出生时尚生存,出生前即具有权利能力的条件。”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典第7条规定:“胎儿以将来非死产为限,关于其个人利益之保护,视为既已出生。”这种立法模式有很大的适用空间,但不加区分地赋予胎儿民事权利能力,又会衍生出一系列的社会和法律问题,比如:怀孕期间的胎儿权利由谁行使?是否应该附加义务及由谁履行?如何看待流产、堕胎的法律性质?胎儿出生后为死体时,其在受孕期间所得利益是否应当返还、消灭或继承、后续义务等等。因此,总括保护主义的适用仍然需要权衡利弊,同时也是一个价值取向问题,需要继续研究和完善。
三、 关于胎儿权利保护的立法建议
(一)赋予胎儿不附加义务的民事权利能力
胎儿虽然具有生理上的完整性,并且是作为民事主体的自然人的初始阶段,但胎儿与人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自然人是已经出生的人,而怀孕期间的胎儿尚未出生。因此,应当赋予胎儿民事权利能力,但不应当包括履行民事义务。因为胎儿尚未出生,无法履行起义务。这就是胎儿享有民事权利能力的特殊性,即不附带义务的民事权利能力。同时也有学者担心,如果赋予胎儿民事权利能力,会产生一系列问题,比如胎儿的受害人的地位问题、为了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而堕胎是否犯罪问题等。[6]基于此,有学者主张,对于胎儿的利益,只需法律明文规定就行了,没有必要赋予胎儿民事权利。如果赋予胎儿权利,流产和堕胎就等于杀人,要承担刑事责任,与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相矛盾,也不利于妇女的保护和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7]以上两种观点不无道理,但流产和堕胎是否违法甚至犯罪, 应该说是一个价值取向问题,各国依其社会政策自有不同的选择,我国完全可以根据本国的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政策,排除流产和堕胎违法或犯罪的可能性。曾世雄老师甚至一反传统的观点,旗帜鲜明地指出,民事权利能力的设置并非为民法上不可或缺的制度,但是否可行需要综合考虑。
(二)胎儿享有民事权利能力的时间应当从受孕时开始
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受孕是胎儿开始存在的标志,也是胎儿的原始状态。只有经过受孕阶段胎儿才能成形,具备生理上的人的完整性,为出生后顺利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然人,即民事主体做好准备,具备成为民事意义上的人的可能性。在受孕前胎儿是不存在的,根本不存在其权利被侵害的问题。只有在受孕后,胎儿可能会遭受到直接或间接的损害,那么从受孕时起赋予胎儿民事权利能力是正确的,也是绝对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保护胎儿的利益,为司法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三)母体在怀孕期间遭受不法侵害,导致流产、胎死腹中,应由孕妇即胎儿的母亲提起侵权之诉主张赔偿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孕妇在怀孕期间常常因遭受不法侵害,导致流产、胎死腹中或胎儿出生后为死体。这种情况下,胎儿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不是民事主体,没有损害赔偿请求权,不能向侵害人要求赔偿,应当把胎儿作为母体的一部分,由孕妇即胎儿母亲提起侵权之诉主张赔偿。原因在于此时侵害人侵犯的是孕妇的身体健康权,而不是胎儿的身体健康权。
(四)胎儿民事权利能力在出生时为死体,其权利能力视为自始不存在
胎儿虽然是人的初始阶段,但毕竟不是民法真正意义上的人。赋予胎儿特殊的民事权利能力,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胎儿出生后的利益。如果胎儿出生时为死体,不能成为真正的自然人,那么对于人的初始阶段即胎儿的保护也就失去了意义,成为胎儿继承人利益的保护,与法定解除条件说的原意相悖。当胎儿出生时为死体时,仍然承认其出生前的民事权利能力,在法理上是说不通的。既然胎儿出生时是死体,那么胎儿完全丧失了作为自然人所享有的民事主体的可能性,当然不可能在出生前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因为当胎儿出生为死体时,该民事主体是自始不存在的,那么既然作为民事权利能力载体的民事主体是自始不存在的,民事权利能力怎么能存在呢?德国、法国的理论、立法和司法实践都确定了一个基本的原则:胎儿在母体中受到侵权行为的侵害,身体、健康受到损害,有权在其出生后就其损害请求损害赔偿。[8]可见,西方一些国家也认为胎儿民事权利能力在出生时为死体时其权利能力溯及地取消,以出生时为活体作为先决条件。但也有人提出:“若在胎儿未出生前允许其行使权利,在其出生后为死体的情况下,某些权益的取得将失去意义。比如,胎儿受赠,但出生后为死体,若此时将受赠财产作为胎儿遗产被其继承人获得,则与赠与人将财产赠与胎儿的初衷完全背离。胎儿继承财产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9]从理论上来说,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依法定解除条件说,当胎儿为死体时,其民事权利能力溯及地取消,也就是说该赠与合同的受赠人自始不存在。既然不存在,赠与人可以从财产占有人那里以赠与合同无效为由行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不存在胎儿遗产由其继承人继承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朱俊,黄金波.试论胎儿人身损害赔偿权[oL].中国民商法网,2005-3-15.
[2]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78.
[3]梁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91.
[4]魏振瀛.民法[M].北京:北京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55-56
[5]尹田.论胎儿利益的民法保护[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2(2):49.
[6]张俊浩.民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101.
[7]刘心稳.中国民法学研究述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91-92.
[8]杨立新.胎儿受到侵害是否有权索赔[oL].中国民商法网,2003-11-22.
[9]杜雪明,黄斌.论胎儿权利的法律保护[oL].成都法院网,2008-4-15.
(责任编辑/王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