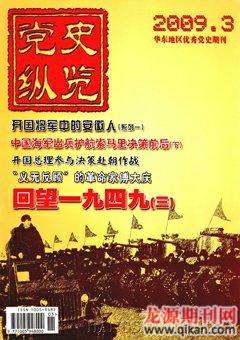“义无反顾”的革命家傅大庆
袁小伦
“我远远地望着他,只知他晚年非常寂寞……在一步步走向人生的尽头的那几年,似乎是,他漫长生命当中每一个片段,都在他的记忆里活了起来,弹拨起当年壮怀激烈戎马倥偬而来不及体味的一切……他的老友,包括我的母亲,终于得以去看他。那场面令人凄然——似乎谁都有话要说,而谁都说不出,只‘执手相看泪眼。……就是这时,他颤抖着为我的生父题写了那四个字:‘义无反顾。放下笔,已是泪流满面。”这是曾生活在叶剑英膝下的义女戴晴回忆暮年叶帅接见她的母亲,并为怀念她的生父傅大庆题词时的情景!笔者知道叶剑英有一个不幸牺牲的战友、老一辈革命家傅大庆,也知道叶剑英收养了傅大庆的女儿傅小庆(戴晴),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傅大庆仍然是一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人物,对于叶剑英与傅大庆的交往也知之不多。为了让革命先辈的事迹得以更好的流传,笔者将读到的相关史料敷陈如下,并期待知情者的补正。
一
傅大庆(1900~?)是江西临川上顿渡人,父亲不幸早逝,母亲李冰是一位小学教师,靠教学收入辛辛苦苦养活几个孩子,傅大庆是长子,他念了教会中学,英文学得不错。五四运动时,在北京师大读书的临川学生章涤昌受进步思想影响,接受了马列主义理论,定期给家乡青年寄《新青年》、《向导》、《每周评论》、《晨报副刊》等进步刊物阅读。傅大庆与同学傅烈等人一起,秘密阅读,深受影响。1920年,傅大庆为了继续求学,从江西来到上海,进一步接触新文化。他深深为《新青年》上陈独秀的文章所折服,便写了一封信给陈独秀,陈独秀便热情地复信并约他见面。见面之后,陈独秀要他住到新办的外国语学校,那是杨明斋新办的学校,表面上学俄文,事实上进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活动。其间,经陈独秀介绍,傅大庆到武昌,找到陈潭秋、包惠僧等人,不久便入了团。1921年初,傅大庆与刘少奇、萧劲光等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取俄文名费德洛夫。1924年1月,列宁逝世,傅大庆冒着寒风参加了葬礼。
关于傅大庆在莫斯科留学和回国参加革命的情况,郑超麟回忆说:“傅大庆不仅是我的同学,而且是我的朋友。‘同学是无所谓的,但在那时的环境下,我能交‘朋友,交真正的朋友,则是很不容易的。1923年春,我们一行十二人,从西欧来到莫斯科进东方大学。东方大学早已有中国班,中国学生是直接从中国来的……这两部分中国学生,无形中有隔阂,很久没有消除。我们从西欧来的人,相互间不仅是同志,而且是朋友,这人和那人,或深或浅总有私人的交情;可是,我们和他们(指原本就在东方大学的中国学生,编者注)无法结交为朋友,他们自己相互间也没有朋友的感情。当时的形势是这样的,从中国直接来到莫斯科的学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领导人,另一类是‘被领导人,‘领导人就是旅莫支部党和团的负责人。选举来,选举去总是那几个人轮流或永久当选。‘被领导人则是始终未曾当选为领导的人,他们只能听从前一部分人的安排,他们不敢同我们从西欧来的人亲近。对于这一部分人,我们无法交朋友,甚至无法说话。那几个‘领导人则常常找我们说话,但不是找我们交朋友,只是来‘了解的。傅大庆就是‘被领导人当中的一个……蒋光赤和抱朴,他们也是‘被领导人,即他们从来未曾当选为旅莫支部党或团的领导职位的,但他们‘不听话,即不是暗地反对,而是公然反对那几个领导人,有时发牢骚,甚至鼓动别人起来反对。这两个人不是同我们住在大学里,而是住在附近一个女修道院的一个房间,没有人去看望他们。我到莫斯科后即同这两个人交了朋友。……有人悄悄警告我:抱朴和蒋光赤是反对派,反对旅莫支部领导的,你不要同他们来往,但这警告太迟了,我已经不能断绝同他们的关系了。一天,我去看他们,意外地看见傅大庆在同他们谈话,我很惊讶,后来听他们说,傅大庆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看他们一次。原来并非无人敢去女修道院看他们。其实,旅莫支部并无明令禁止同他们往来,不过暗示而已。那些人为了避免麻烦,就不敢去看了。从此我就同傅大庆交了朋友,常常在大学本部同他在一起谈话,互相询问家庭情况和经历……我在西欧来的人中交了几个朋友,到莫斯科后,又交了三个朋友,傅大庆是其中的一个,自然,我不能说傅大庆是我的最亲密的朋友。我欣赏他不怕打击,敢于同领导所厌恶的人往来。1924年暑假前,回国革命已开始酝酿,旅莫支部派遣一大批同志回国工作,暑假前已经有一队出发了,暑假中又出发一队,人数可能比第一队更多,带队的人是陈延年,我被指定为庶务兼会计,傅大庆也在此队中……到了海参崴,但没有船去上海,只好住在海员俱乐部候船。等了好几天,有一条英国船来了,但这是货船,不是客船,水手是中国人,说能够用‘载黄鱼的办法载我们到上海去,不过只能载五六人去。我们商量先去几个人也是好的,于是一部分人,傅大庆在内,先回去,队长陈延年,会计郑超麟,以及其余的人,则等待以后俄国船开赴上海时再乘去。”
傅大庆回国后,被派到大革命的中心和策源地广州,也就是这个时候,时任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的叶剑英与他有了交往。傅大庆担任苏联代表团团长鲍罗廷和军事顾问加伦将军的翻译,受到宋庆龄的赞赏。据说,他在黄埔军校翻译时,曾一个人在台上,先将鲍罗廷的俄文译成国语,又将国语译成广东官话,然后再照样译回去。
关于大革命时期傅大庆在广州的情况,张太雷的夫人王一知回忆说:“我们住在鲍罗廷顾问的公馆里,鲍公馆坐落在广州东较场附近,是一所两层的花园洋房。鲍罗廷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儿子住在楼上,有时,有些苏联军事顾问也住在楼上。我们则住在楼下。楼下还有一个翻译室,有几名翻译人员,专门从事当天各地报纸的翻译工作,译稿经整理之后供鲍顾问参考之用。记得翻译室中的人员有李仲武、黄平、傅大庆、卜士奇等人,这个翻译室也归太雷领导,我协助太雷做日常的选材工作,常常是太雷和我两个人挑出要译的内容,分派有关人员去翻译。”包惠僧也回忆:“当时在苏俄代表团任翻译的人很多,如傅大庆、杨明斋、李仲武、卜士奇等。他们除了翻译工作之外,还要担任苏俄专家与各方面的联系和交往工作。”
1925年,傅大庆两次随国民革命军东征,讨伐军阀陈炯明。东征途中,傅大庆作为苏联军事顾问加仑的翻译,随叶剑英率领的部队一道打到梅县。1926年叶剑英和傅大庆都参加了北伐。傅大庆先在东线作战,后又随鲍罗廷、加仑调到武汉。其间,他不遗余力地贯彻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与汪精卫、陈独秀接触频繁。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傅大庆赶赴南昌,参加周恩来等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之后,在南下途中,他受党组织派遣回临川,对农民建国军首领孙牛仔、邓克中等人进行团结教育工作,取得成效,受到贺龙的鼓励。陈毅回忆说:“赣东有一股绿林武装,头子姓邓,就叫邓司令。这个邓司令通过一个后来成了翻译家叫傅大庆的和叶贺接头,愿意接受贺叶的委任。条件是发他几百条枪,我们可以派人去领导。这时候,朱培德的队伍紧跟在我们后边,我们考虑,朱培德迫近时,他又多少可以起一点牵制作用,所以就答应了他。党派我和肖劲同志到这个绿林部队去领导,我本不愿去,但肖劲同志觉得搞个绿林部队也不错,于是决定去了。便把我们交给傅大庆,由他介绍了去。”
同年底,傅大庆又参与了张太雷、叶挺和叶剑英等人领导的广州起义。起义前夕,他奉省委命令到宝安向县委传达省委指示,要求宝安工农革命军于12月13日前到罗湖车站会同铁路工人抢登火车,直趋广州,参加暴动。宝安县委接受任务后,随即从工农革命军中抽调骨干300余人,于12日集中在县委所在地的楼村待命,起义队伍编为两个大队。县委书记刘伯刚现场领导,工农革命军副总指挥郑式南直接指挥。12日夜两队同时出发,直扑深圳抢登火车,参加了广州起义。
二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剑英和傅大庆都转移到香港。1928年,叶剑英经上海赴苏联学习,傅大庆被广东区委派往新加坡活动,并担任中共南洋临时委员会常委兼宣传部长。先后在泰国、印度尼西亚、缅甸、菲律宾等国建立地委或支部,积极领导海外华人和当地群众开展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1930年5月,根据共产国际东方局的指示,马来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立,傅大庆当选为马共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负责组织、宣传工作,大力培养当地干部,发展党团组织,和胡志明一起,把东南亚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搞得如火如荼。他还主编和出版了《马来西亚工人》月刊。1931年6月,他以办“洋行”为掩护,负责建立东方局办事处,因叛徒告密,遭英国殖民当局逮捕被引渡回国(同案的胡志明也在香港被捕被引渡到广州),先后关押在上海,后又和国际友人牛兰夫妇一起,被解送到南京。
在上海狱中,傅大庆意外地见到郑超麟,并委托郑超麟设法营救被关在广州看守所的胡志明。郑超麟回忆:“在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我看见了傅大庆。那是在1931年夏秋之交,我已经被共产党开除了,我因托派活动罪被国民党逮捕,关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等待判决。我住在‘人字间,这条弄政治犯最多。一天,看守送进来一个犯人,是从广州押来的,就要解到南京去。我看见了,吓了一跳,原来是傅大庆,他看着走来走去的犯人,一个都不认识,忽然看到了我,马上走近我,悄悄地说:他有事情要报告中央。他自然不知道我已经不是共产党员;在此情形下,我也不必首先告诉他我是托派。我答应了他,他就说给我听。原来,他是在印度加尔各答办英文报纸,报馆被封,人被捕,他被引渡回国,要押去南京受审。他在广州看守所中遇见胡志明,胡请他设法通知中共中央营救他,傅大庆要我将胡的要求通知中共中央。我义不容辞,尤其因为胡志明也是我的熟人,但怎去通知中共中央呢?我想起,在龙华看守所一定有中共秘密支部,能够传达消息。但哪一个政治犯是支部负责人呢?在‘人字间的中共政治犯中,我只认识两个人:陈为人、关向应。我考虑结果,认为三条弄里的总负责人是陈为人。我直接找他。我说,刚才解来的犯人名傅大庆,是在印度被捕的要解到南京去。他有重要的话要报告中央,我现在要告诉你,陈为人立即严肃起来,不说一句话,听我说下去。我把傅大庆的话一字不漏地说给他听。他咬紧牙关听我说完,仍旧不说一句话。我明白,我的目的达到了。两三日后,傅大庆就解走了。”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傅大庆经宋庆龄营救出狱,先后在武汉十八集团军办事处、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工作。叶剑英和傅大庆,这对分别近十年的老战友又重逢了。在南方局军事组,叶剑英兼任组长,傅大庆任十八集团军军事翻译。傅大庆受叶剑英的直接领导,同时给崔可夫率领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当翻译。
当傅大庆得知毛泽东在延安召集一批专家,正研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但苦于没有好的译本时,立即主动请缨,根据《战争论》俄译本第三版作了重译,并以最快的速度于1940年11月由学术出版社出版发行。该译本分上、下两册,白话文体,直排本,大32开。该译本在学术出版社出版后托人送往延安,朱德、叶剑英将其誉为当时最好的《战争论》译本。
三
在埋头著译的日子里,经叶剑英的介绍,傅大庆结识了当时在苏联大使馆武官处工作的冯大璋(杨洁)。1941年元旦,周恩来为傅大庆和冯大璋主持了婚礼,婚礼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隆重举行。因为当时重庆政治气氛压抑,为了振奋士气,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周恩来和叶剑英决定把婚礼搞得热热闹闹的。南方局军事组的同仁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人向新郎新娘表示了热烈的祝贺。三楼会议室里,贴满了贺幛和贺词。周恩来的贺词非常醒目:“形式和内容统一,大庆和大璋同心”;紧挨着的是邓颖超的贺词:“相爱合作,善始善终”;叶剑英这位“红娘”赠送的条幅富于哲理:“爱是有条件的,只有在现有条件的基础上不断地发扬光大,创造更多更好的条件,才能得到爱的保障,这就是发展中求巩固。”傅大庆写了一首《新郎自题》:“郎才女貌两相忘,赢得倾心是庆璋,绝俗文章师马列,胡公超姊自高强。”叶剑英则在这首诗旁边题上“顽皮”的批语:“好不要脸!”
在婚礼进行中,周恩来首先举起酒杯祝贺新婚夫妻,然后环顾在座同志,又微笑着望了望坐在身旁的邓颖超,风趣地说:“在他们新婚的喜庆日子里,我还想再提一些想法。我以为,在结婚前要有正确的恋爱观,婚后要有正确的家庭观和生活观。”他又说:“我们有一个革命大家庭。在我们革命队伍里,除了夫妻关系以外,还有战友关系、同志关系。结婚以后理应把革命工作做得更好。生活方面要科学地处理、安排,过革命者紧张、活泼的战斗生活。我和小超同志从结婚以来,互敬互爱,互相帮助,幸福美满。还有一点,我的身体一直能保持得这样好,因为我从来没有自我摧残过。”说到这里,大家会意地笑了起来,为周恩来这番既风趣又富有哲理的话喝彩。周恩来最后又强调:“我和小超结婚后,十多年来,爱情是在上升和发展。在家里,我们是夫妻关系;从革命和政党来讲,是战友关系、同志关系。”邓颖超听后补充说:“我们还是师生关系。”叶剑英紧接着颇有诗意地评述道:“作之夫,作之友,作之师。相敬相爱,白头到老。”傅大庆钦佩而深情地望着周恩来和邓颖超:“胡公和超姐理应是当代夫妻的典范。”
为了表示祝贺,叶剑英还特地以诙谐幽默而又情真意切的笔调写了七联五言长诗《大璋大庆新婚志庆》:“一见即如故,合欢定百年。无劳蜂与蝶,采药遇良缘。小雀飞入海,玄蛤变未全。昨日王老五,今宵主盛筵。良朋欣满座,恼煞座中单。笑语频含谑,妙语落言诠。举杯何所颂,瓜瓞正绵延。”这首妙语横生的谐趣诗,首联开门见山,落笔定情,记叙这对新人,一见钟情,定下婚姻大事,百年合好。第二联写新人恋爱经过。两人相爱,本是诗人当“红娘”,牵针引线,却自谦“无劳蜂与蝶”;因为冯大璋曾在重庆国立药学院读书,专攻药学,是一位药剂师,后到南方局工作,所以是“采药遇良缘”,而“采药”来代替“采蜜”,颇有新意。第三联写新婚夫妇亲密之情。“小雀飞入海,玄蛤变未全。”典出《国语》:“雀入于海为蛤,雉入于海为蜃。”叶剑英用此典,引“雀”和“蛤”入诗,意思是,美丽的玄蛤本是“小雀”入海而变的。以此来喻指男女双方,如“雀”与“蛤”的合二为一,“小雀飞入海”,即变为“玄蛤”。两者结合,开始演变,尚未变全。 以下数联,描绘婚宴之盛况,“昨日王老五,今宵主盛筵。良朋欣满座,恼煞座中单。”接下去,“笑语颇含谑,妙语落言诠”。用夸张的笔法描绘参加喜筵的“良朋”们嬉闹笑谑之欢,但谈笑间又充满“妙语”、“言诠”,有情有理,寓情于理既渲染又含蓄,尤其“笑语”与“妙语”分寸把握得当,值得品味。“举杯何所颂?”良朋好友频频举杯相庆祝颂,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瓜瓞正绵延”,速结小瓜,早生贵子,子孙绵延。此句典出自《诗经•大雅》:“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这首诗情真意切饶有情趣,将一对革命伴侣的婚恋和婚宴刻画得淋漓尽致,读后令人回味无穷。
1941年10月,傅大庆夫妇奉命携带秘密资料和刚出世的女儿(即戴晴)前往北平,建立地下通讯机构,筹建秘密电台,以加强同第三国际的联系。本来他们是要去延安并且已经启程了,是在半路被追回来的。傅大庆和冯大璋在北平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的情况,在戴晴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他们受派遣回到外祖父的家所在的北平,以帮闲教授的身份周旋于汉奸、政客当中。我想他那时一定是非常紧张、非常寂寞的。‘他唯一的休息是抱你到北海去。他说小孩子常看水眼睛亮。妈妈说。……最特别的是他与我的外祖父的交往。老先生是清末翰林,顽固的保光绪派,出于联姻名门之固癖而把我的母亲嫁到湖南曾家。无奈母亲那时思想太新,自己逃婚到日本,数年后又携这样一名自己‘自由上的女婿归省,外祖父的怒气可想而知。但事情后来竟朝着人们预料的反面发展,这保皇老人不但接纳了他,居然还有一首七律写到他们翁婿间的关系:‘敢道滹沱麦汴香,臣惭仓卒帝难忘。艰难险阻亲尝尽,天使他年晋国强。蔼蔼苍松伴紫芝,颌眉妙墨出瑶池。朽株新被祥风拂,一夕青回两鬓丝。 广谋贤甥正 冯恕。亲友们吟咏玩味之余,一直以为这是马列主义的伟力:我的共产党父亲以主义征服了顽固的岳丈。……当父亲的传记作者召集家族座谈会广泛征集信息时,我才知道,原来他还懂藏文。外公之所以对他认可,是因为他能直接阅读藏经——老人只认藏喇嘛,其他所有汉传佛教高僧在他眼里都是野和尚。所有这些,他什么时候学的呢?或者说,以他的天分,几乎不用下工夫学?他们那一批共产党人都是这样的么?”
1944年7月23日深夜,正当傅大庆的助手汪青城在架设天线,准备用发报机向莫斯科发报时,埋伏在附近的日本兵破门而入,将汪逮捕,随后傅大庆与冯大璋亦遭逮捕。在狱中他们经受了严刑拷打,坚贞不屈。戴晴说:“在日本宪兵队的监狱里,他受了很重的刑——这是我的有充分依据的估计。因为,妈妈作为从犯,又有孕在身,还被抽打、灌凉水、过电——我的妹妹生下来的时候,小身子上一块紫一块青——对他就可想而知了。”傅大庆托看守转给妻子杨洁一张纸条:“我很好,不要惦记我。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若能出去,要教育好孩子,成为有用的人,吾愿足矣。”后来,怀孕的冯大璋,由父亲“保外分娩”,逃出虎口。过了几个月,孩子生下以后,她四处打听傅大庆下落,始终没有结果。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1月,叶剑英参加军调部工作来到北平,冯大璋去探望叶剑英,向他汇报了傅大庆的被捕情况。叶剑英立即布置李克农调查。李克农查遍敌伪档案,毫无线索;至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建交,中国政府要日本政府清查被抓往日本的劳工中有无傅大庆,等了许久,仍无音讯,这时才确证,傅大庆不知在何时何地,已被日本法西斯杀害。以后的岁月里,叶剑英对冯大璋及其女儿关怀备至,像对待自己亲人一样爱护她们。叶剑英见到冯大璋时,总是嘘唏不已地说:“大庆是个好同志,极好的同志!”
戴晴回忆叶剑英谈起傅大庆的情景:“当时我还只有5岁的时候,就在不是如今天这样四座联成一排,而是孑然傲立在王府井街口的老北京饭店——调处执行部办公地玩耍;后来又随着叶剑英元帅职务的变迁,到广州,到武汉,到北京;也曾随着他或开会,或视察,或遭软禁而到庐山,到大连,到湘潭。”“至于父亲,因为他的使命十分机密,则至今也没有弄清。我想他们的交往大约始自黄埔——叶伯伯当教官,我的父亲为鲍罗廷作翻译;而他们的交游恐怕主要缘于性情:两个人都随和、爱笑爱闹,口袋里没钱便罢,有了几个大子儿就琢磨着搞点什么打打牙祭。在由叶伯伯抚养的将近40年的时日中,他只有3次对我谈起父亲。一次是他们弄了一副熊掌,费了老大的劲也烧不透,最后还是吃了个大汗淋漓。再一次是我入共青团的时候。那是一个黄昏,叶伯伯从楼上下来,把他随身保留近二十年的父亲的译作《战争论》送给我。书上,除了他显然不止一次的圈点批注外,还郑重地写下了——庆儿:当你入团之际,将这本书送给你,不要辜负你父亲的牺牲。最后一次已是1982年。他应江西烈士博物馆之请为亡友题词。他题的是‘义无反顾,笔锋间已失去了往日的潇洒。我想这是指他们1941年底的最后一别。当时父亲正从赴延安的途中被召回,紧急派往北平。我想他出发时的心情,恐怕与易水畔的荆轲差不多。他不准备回来了,这大家都有预感,无论是送的一方,还是行的一方——他从此也就真的没有回来。”
“义无反顾”!叶剑英为亡友题词,悲凉慷慨,馀情不绝。傅大庆告别叶剑英,毅然北上,一去而不复返,其英烈壮气,千载犹生。此刻,笔者想起骆宾王《易水送别》末两句,“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