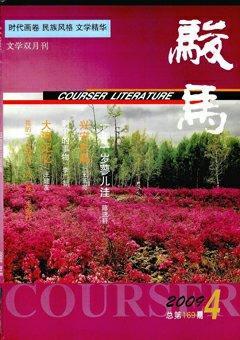那边那边的发廊
文星传
原名文兴传,自由撰稿人,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2000年开始文学创作。在《清明》《文学界》《北京文学》《莽原》《北方文学》《青年文学家》等杂志上发表中短篇小说一百多万字。长篇小说《昆明夜魅》被中国门户网站搜狐评为优秀军事题材长篇,出版有中篇小说集《天堂在左》、小说集《我的槐花巷》。
1
西妹是个发廊妹,十八九岁的样子。她总爱跷着二郎腿坐在发廊的门口。她旁边是一个巨型的大花篮,花篮上面是万紫千红的绢花,花篮后面便是发廊浅蓝色的玻璃大门。大门很新,银色的门框也很新,黄色瓷砖贴出一片光彩,在灰头灰脸的槐花巷里,发廊装修得富丽而又新潮。
西妹总是背靠着一把木椅,身子微微向上仰着,有时候嗑着瓜子,有时候和好几个发廊女凑在一起说说笑笑,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西妹第一次引起我注意不是因为她帮我老妈把花盆送到家,也不是因为她黄色的披肩长发,更不是因为她媚艳之极的口红、眼影和露脐装,而是因为她那双玲珑的小脚。在这里我要先强调我可不是什么嫖客,也不是什么喜好三寸金莲的腐朽。我之所以注意到她的小脚,责任完全不在我。西妹坐在发廊门口的时候,往往身子在门里,脚却在门外一晃一晃的,有时候是一双黑色的长筒靴,有时候是光光的戴着脚链的一双玲珑小脚,紫红色的脚趾甲格外醒目。槐花巷青石板的路面不是很宽,所以,那天我在夕阳的余辉里就看见了那双脚。当时夕阳的余辉是金黄金黄的,把什么都照得透明闪亮,那双玲珑又白嫩的小脚就让我的心颤了一下,我就记住了那双脚,并且在走过发廊的玻璃门时还不由自主地回了下头。西妹就在里面朝我一笑,说:“大哥,来耍一下嘛。”她的话让我心颤得更厉害了,应该承认,如果这家发廊不是坐落在槐花巷里,我几乎就要搭她的腔了。我知道这家发廊不光是给人美发按摩的,里面还有一些单间,有很多时候会给男人们一些更多的服务。
可我家就在槐花巷里,是许多老门老户中的一家,我哪里敢在这里唐突啊。虽然我下岗在家,但是巷子里人都知道我在考研,没准哪一天我就金榜题名,远走高飞了。有些人见了我的面就已经打趣地喊我“研究生”了。我只能一本正经目不斜视地从青石板的路面上走过,从这家“贝贝发廊”门前走过。
槐花巷曾经是烟花柳巷,很有名的烟花柳巷。小巷的老房屋中间至今还残留一座两层的小楼,虽然已经是灰头灰脸的了,可那白墙黑瓦,画栋雕栏,依稀透露着当年的繁华。听我爷爷说,在前清的时候,这小楼是有名有姓的,叫章台园,用柳永的两句词做了门联:“宴处能忘管弦,醉里不寻花柳”,横额是“浅斟低唱”。即便是如今,每遇良辰,这小楼的砖瓦间还散出淡淡的胭脂气,让整个小巷沉浸在一种淡香里。“贝贝发廊”就坐落在槐花巷的出口处,生意还不错,可来这里洗头按摩的都不是槐花巷的人。槐花巷从一九四九年起就不再是烟花柳巷了,这里的人都非常忌讳“烟花柳巷”这个词,如今大家都很正派,都和我一样目不斜视了。
2
我从没有主动和西妹接触过,我和她所有的接触都是很偶然的,我不是在表白自己,这是真的。
譬如那天就是因为我老妈,她老人家不知道怎么一时兴起,居然不顾自己年老体衰,一下子就买了四盆鲜花。那是个很晴好的日子,阳光穿过院子里的老槐树把我家的小院照得斑斑驳驳的,树上的喜鹊也在“唧唧喳喳”地叫。我还以为是有什么贵客要来呢,我站在院子里左顾右盼的时候,我老妈就把我们家小院的门撞开了。西妹就跟在她身后露着半边脸。老妈左右各抱了一个花盆,西妹也是抱着两个花盆。老妈朝我使了个眼色,我就赶紧去接西妹手中的那两盆花。西妹说:“莫管我莫管我,先把阿姨的盆接了,好重嘛,她一个人郎个拿得动嘛。”
西妹是自己弯着腰把花盆放下的,弯腰的时候她露脐装的背后露出了好白好嫩的一大块肌肤,那肌肤在阳光下像绸缎一般闪着光,真的很养眼。西妹把手中的花盆放在院子里最当阳的地方,放完后她还歪着脑袋看了看。
我客气地说:“进屋喝口茶吧。”
西妹摇了摇头,朝我一笑说:“蛮好看的花嘛,蛮香的。”说完就轻盈地跨出了我家的小院。
我原是准备追到门口再说一声谢谢的,可我的脚还没抬起来,老妈就一把扯住了我的衣服,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待西妹的脚步声在青石板的路面上消失后,妈才说:“多事。”我不知道老妈这话是在说我还是在说西妹,我没问,也不想问。自从我下岗在家,老妈总唉声叹气的,我不想自找没趣。
我知道巷子里的人对那边那家发廊和发廊里的发廊妹们一般都是斜视的,很不以为然的样子。我也只好做出一副很不在意的样子,不再往门外看。但我到现在还坚持认为西妹的那句话不正确,她说那两盆花蛮香,我一点儿也没嗅到,我倒是嗅到了西妹身上的香水味,那才是真香呢,直到她离开我们家很久,那香气依然在我家的院子里飘着。
3
你不能不承认这一切一切都来得很突然,没有一点儿预谋。我坐上公交车的时候天空还是一片晴朗,连半朵云彩都没有。想不到下车的时候,一阵狂风过来,倾盆大雨就跟着来了,很猛的雨,整个地面都溅起了雾一般的水花。西妹正好站在发廊的门前,看见我她就招手,很关切的样子。我无法选择,只好朝发廊奔了过去,一直奔到西妹跟前,奔到她的胭脂气里。西妹说:“大哥,赶快把身上的水擦擦。”说着她就拿起一条雪白的毛巾往我头上擦。
我说:“我自己来自己来……”
西妹就笑嘻嘻地把毛巾递给我,她笑的时候就没有这种行业女子的那种媚艳气了,很质朴的,那张圆圆的脸像苹果一样。
当时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我说:“这天,真他妈的!”
西妹就捂着嘴笑了起来。
我说:“你别笑,真是说下就下了,也不打声招呼。”
老板走过来殷勤地说:“先到里面躺躺,喝口水,按摩按摩?”
我摇了摇头,做出一副随时准备冲出去的样子。这时外面的雨越下越大,我也很想在这里站一会儿,雨要是想下就让它下去吧,谁能奈何老天爷。
西妹也在一边说:“坐一下子嘛,下雨天留客天,我不留你天留你。”我觉得西妹说的也有点儿道理,我是被雨困到这了,还怕谁说什么闲话不成。我就走到里面的一个单间里说:“休息一下也好,不过我只按摩,不搞那乱七八糟的名堂。”
单间里的气氛比较好,音箱里放着轻缓的音乐,好像是一首江南的老民歌,很缠绵。香水气也袭人,房间里的香水气和西妹身上的香水气是一样的,这让我也对这种香水气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好感。
西妹是跟在我身后进的单间,她在我身后说:“大哥,我来给你按?”
我故意冷冷地说:“随便吧,反正是躲雨,也没啥急事。”
我是在这次按摩时才知道她叫西妹的。她睁大眼睛,很认真地说:“搞我们这行的,一般对顾客说的都是假名字,我给你说的可是真名字。”
“为什么?”
“不晓得,想说了,觉得你这个人蛮好的。”
西妹的小手胖乎乎的,很柔软,按摩的力度也正好,这一点我很快就感觉到了。我原计划是合着眼一声不吭地让她去按,可西妹显然是个不甘寂寞的女孩,她并不在乎我的沉默,晃着圆圆的脑袋,嘴巴不停地嘀咕着一些顺口溜的小段子逗我。那些小段子从她那带着四川口音的嘴里吐出来,就让人觉得格外俏皮。譬如我刚躺好,她就说:“摸摸你的头好温柔,摸摸你的脸好阴险,摸摸你的腰好风骚,摸摸你的腿直流水。”这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西妹的顺口溜把我逗笑了。西妹好像并不知道我在笑,仰着脸看着天花板,继续着她的独角戏。应该承认中间有一段引起我的不小的警觉。那一段是这样的:“万水千山总是情,不给小费行不行?世间哪有真情在,赚得一块是一块。万水千山总是情,不给小费行不行?洒向人间都是爱,先生千万别耍赖。万水千山总是情,不给小费行不行?万里长城永不倒,小费一分不能少。”当时我想,别看这小女子表面上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其实是在向我暗示小费呢,反正我兜里就那么些钱,随她说去吧,我依然闭着眼。
在西妹一段接一段的顺口溜中,外面的风雨声渐渐小了,我也该走了。
我坐起来的时候,边往裤兜里掏钱,边笑着告诉她,不好意思本人的小费不是很多。没想到西妹就朝我努了下嘴,然后把她的兰花小手扬了扬,那意思是让我别出声,只管走人。
我还想再说什么,西妹就在我背上拍了拍,说:“好了,走吧!”她自己也径直离开了单间,去应酬别的客人去了。
我觉得有些发廊妹还是可以的,不像人们说的那么不地道,那么龌龊,譬如西妹吧。
4
我的观点首先受到邻家大姐的抨击。我一直都很仰慕这个邻家大姐,她是个很正统的公务员,一身板正的西装,爱把手背在身后,不苟言笑,比较爱关心我的个人生活和事业,总是谆谆教导我该如何如何立志做人,而且她还是一个有很高修养的老文学女青年,因为总是拒绝杂志社男编辑的“亲切指导”,所以在文学方面总是处在一种怀才不遇的状态。那天她正在撕一封某杂志的退稿信,手下雪花纷飞。我就把我憋在心里的话对她说了。我说得很小心,我低声说:“你也可以写写那些发廊妹,其实她们中间也有很不错的……”她听了我的话先是把眉头一皱,那双本来很大很亮的眼睛突然就眯了起来,然后就把嘴角一撇:“啊呸!我说呢,槐花巷的遗风到底在你这显出来了,是不是要做个新时期的柳永啊?哈哈……”
她的笑声很刻薄,像刀子一样刺得我难受。我赶紧从邻家大姐的房间里退出来。邻家大姐追到院子里,在我身后喊道:“哎,哎,我说,小弟,你也别考什么研究生了,‘且去填词吧……”
那天我似逃跑一般逃出邻家大姐的声音的。我就知道现在的槐花巷已经不是当年的槐花巷了,大家都是正人君子了,我这种思想只能惨遭奚落。以后每当我路过那家发廊的时候总觉得邻家大姐的眼睛就盯在我的脊背上,让我身体的每一处都有一种彻骨的感觉,我不得不目不斜视,好像我根本就不认识西妹一样。可以看出西妹有时也很想喊我一声,想再说一声:“大哥,来耍一下嘛。”可她没有说出口,她的声音往往会形成一声若有若无的叹息。其实我心里都听得到。
西妹依然是那副样子坐在发廊门口,跷着二郎腿,把那双玲珑的小脚伸在门外晃悠,或者嗑着瓜子,或者和别人说说笑笑。我只要一迈出家门,就可以远远地看见她。在这里我要交代一下,发廊在青石板路的最南边,我家在青石板路的最北边。虽然我可以远远地遥望到发廊,可距离还是太远了点儿。阳光总是要先照到发廊的大门,很明媚的阳光照在玻璃的门面上,照在门前的巨型花篮上,照在西妹圆圆的脸蛋和充满活力的身体上,把它们都照得格外亮丽鲜活。西妹似乎很爱晒太阳,她的身子在这个时候也愈发往后仰,好像整个人就躺在金色的阳光里。你不能不承认西妹和发廊那鲜亮的门面构成了槐花巷里最亮丽的一道风景。
5
那个手机短信是在上午发到我手机上的,那会儿我没看专业书,手里拿的是一本叫作《篮球》的杂志,杂志封面上有一个黑人球星正对着我很张扬地笑着。他的一只手抱着一个篮球,另一只手的食指笔直地指着我的鼻梁,让我有一种被人挑战的感觉。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短信。短信的内容是这样的:“大哥,愿意陪我坐一会儿吗?”
大概是受黑人球星的影响,我觉得这条短信也很富有挑战的意味,就回了一个短信:“怎么不可以,不过我要知道你是谁?”不一会儿短信就又来了。这回她告诉我说她是西妹,正一个人在湛河堤上。湛河是一条横贯我们这个城市的一条人工河流,两岸的河堤上满是草坪,那是情侣们常去的地方。
湛河离槐花巷比较远,槐花巷的居民基本上不到这里来休闲,所以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我的短信是这样回复的:“等着我,马上就到。”
远远地我就看见了西妹。她今天没抹口红眼影,也没穿露脐装,穿了件白色的大棉T恤,牛仔短裤,再往下就是雪白的袜子和耐克球鞋。她像个中学生一样盘腿坐在草坪上,看见我就把她胖胖的小手摆了摆,然后又指了指她旁边,那意思是让我坐在她旁边。
我还没有坐定西妹就说话了,她歪着脑袋有些调皮地说:“你猜我是怎么知道你手机号的?”
她的话我还真的无法回答,接电话时我就有些纳闷,她怎么会知道我的手机号呢。我说:“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西妹依然是很调皮的样子,歪着脑袋连说好几个我不告诉你。那天西妹表现得一直很调皮。她睁着大眼睛说:“我觉得你这个人不错,还是个研究生,才找你说话的。”
西妹的话让我笑了,我说:“你听谁胡诌?实话告诉你,我如今正倒着霉呢,连工作都丢了。”
“那有啥子哟,你们城里人郎个活也比我们乡下人活得好……”西妹一副什么都看得开的样子仰望着蓝天说。说实话,我觉得没心没肺的人也许会活得比别人更好,不像我老妈,一见到我就唉声叹气,也不像邻家大姐,一见到我就要“无微不至地关怀”。我认为和西妹这样的人在一起,你肯定会忘记一切苦恼的。西妹实在是被我看得不好意思了,头一次显出几分羞涩,她攘了我一把,说:“你莫要这样子看我嘛,防贼呀?我不会纠缠你的,在家里我耍的有男朋友,我们感情蛮好的。”
“他知道你在发廊干吗?”
“哪有不晓得的道理,你莫要瞪起眼珠子看我,有啥子奇怪的吗?你们城里人哪晓得我们乡下人,草民一个,哪有那么多好讲究的,有得钱挣就行,没得钱郎个活啥?”
“可是,可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
“又不偷不抢,有啥子不道的嘛,你看,我每个月都有得钱往家寄,他在广东打工,也有点儿把子积蓄。我们再干几年,以后也会有好日子过的。这才是道嘛,活人的道。”西妹说这话时,依然是大眼睛望着天空,一眨一眨的,很纯洁,像一个充满了憧憬的中学生。如果你在这个时候见到她,我想你怎么样也无法把她和媚艳的发廊妹联系在一起的。
整整一上午我们就像一对年轻的情侣一样依偎着说话。就在我几乎忘记她是个发廊妹的时候,西妹站了起来,她拍了拍屁股,突然说:“大哥,我知道你喜欢我的,我早就看出来了,可你不敢要我。其实嘛我也蛮喜欢你的,我喜欢你这样有学问的人,要不是我家供不起,我也要考大学,考研究生的。还好我也算见过研究生了。”
“呵呵,是吗?你这么看中我?”
“你不要不相信,你要是真想要我就去开个房吧,我不收你的费。你要是不打算要,我也该回发廊了。”
西妹的话来得太突然了,真让我有些手足无措。我看见一只青色的小鸟在我前面飞过,在蓝天上留下一道青色的轨迹。于是我便吹了声口哨,哨音追随着那只青色的小鸟而去。
我觉得我快乐。
6
西妹是通过发短信向我借钱的,她的短信是这样的:“我有要紧事,大哥,能借我点儿钞票吗?”说心里话我当时差点儿就动心了。我感觉西妹不是那种欺骗人的女子,是可以信任的。我认为有些人是不需要很深的了解的,是可以一见如故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一见钟情的时候有很深的了解吗?子期与伯牙成为知音前经过调研吗?起码连野史都没这样的记载过。
我当时很相信自己的感觉,我把我的存折揣到裤兜里,并且把两只手也揣在裤兜,做出一副悠哉悠哉的样子步出了我家的大门。我看见门前的老槐树上有一只不大的小鸟像个小人似的瞪着小眼睛在观察我,啊哈,你懂什么呀。
邻家大姐正站在小巷的青石板路上,以一种极其不屑的斜视看着远处的发廊,看着远处的西妹。说实在的邻家大姐也算得上是个美女了,她高高的个子,白嫩饱满的脸蛋,惟一美中不足的就是那对大眼睛有点儿凸,像是某个鱼缸里的金鱼眼,只要她的眼睛看着你,就会让你产生一种被逼视的感觉。看见了我,邻家大姐就说:“小弟,是不是又要去那边的发廊风流倜傥一番啊?”
我赶紧掩饰说:“大姐,你看我是那样的人吗?”
“怎么不是?一出门眼睛就往那边瞟,有勾魂的吧?婊子无情,你可别真的着迷了。”
“没有,没有,大姐……”
“你看那些女子个个都是什么样子,龌龊之极!败坏社会风气。我可告诉你啊,市政府马上就要扫黄了,她们统统都要被撵走的。你现在是失业在家,容易心闲生余事,要是出了啥事可别怪姐姐事先没给你打招呼啊。”
我说:“哪里哪里,我这不是学习累了嘛,累了就出门透透气,看看树呀鸟呀什么的。”
邻家大姐冷冷地一笑,说:“只要不看鸡就行。”然后她就大步地走开了,往巷子外面走的,经过发廊时也和我一样目不斜视,正气凛然。
邻家大姐虽然走了,可她的话犹如黄钟大吕,在我耳边响着。我这个时候才觉得我要把钱借给西妹实在是一种很欠考虑的行为,有时候能不能还钱不在于借债人的人品,而在于她的偿还能力,这个时代中国的哪个城市没有西妹这样的女孩?今天她匆匆地来了,来这个城市挣钱,明天她又匆匆地走了,甚至连挥一挥手都不挥,和某些诗人一样也是不带走一片云彩的。她们给城市留下的只是一道轨迹,而城市会给她们留下什么样的记忆呢?好像有个诗人说过——记忆是一种永远的失落。她连这个城市都可以失落,她欠我的钱能不失落吗?想到这些我决定捂紧自己的腰包。我当时对那边的发廊产生一种很遥远的感觉,它跟我仿佛就不在一个世界,我实在没有必要去为另一个世界做点儿什么。于是我又退回到屋里,也用短信的方式回了西妹,我说:“对不起,大哥这里也很拮据,恨不得去抢银行。”
过了好一会儿,西妹才又发来短信:“真不好意思,我怎么可以向你借钱呢?我只是一个外来妹,哪有这个资格嘛,真是急昏了脑壳,打扰大哥了。”
我又发短信回去:“没什么啊,我和你毕竟和别的外来妹不一样了,我是确实没有,有了一定借给你。”
第二天我再经过“贝贝发廊”时,西妹在我走近的时候就躲到阳光的后面去了,直到我走过发廊门前那块特别宽大又有些晃动的青石板后,她才又扭着身子坐到门口,坐到那片灿烂的阳光里,让阳光和花篮以及整个亮丽的发廊都做她的背景。她就坐在那片风景里,微微仰着身子,跷着她那玲珑的小脚,像以往一样没心没肺地嗑着瓜子,说笑着。我能感觉到那笑声里有一种别样的失落。
没办法,西妹,大哥只好对不住你了。
7
西妹走了,走得很突然,她是在我根本没有思想准备的时候离开槐花巷的。
上午我准备去新华书店买点儿考研的资料,我从小巷的青石板路面上走过,我头顶上是一些老槐树的枝枝叶叶,还有一些青色的藤蔓,纷纷扬扬地颤动着。那些藤蔓和绿叶在阳光的照耀下,绿得很透明,像是祖母绿的玛瑙一样。那天巷子里的那种胭脂气也格外得浓,轻轻地荡漾着,让人沉醉,让人想入非非。远远的我就看见了“贝贝发廊”亮丽的门面。有好几个发廊女就站在那里,她们中有的斜着身子倚在玻璃门上,什么也不做;也有的立在发廊的台阶上,很专注地修理着指甲。人群里就是没有西妹。我一开始以为西妹还在躲我,她正站在或者坐在发廊里面的某把椅子上等我过去。不过我的潜意识里还是产生了一种很特别的感觉,所以我走过发廊的时候,一改往日目不斜视的习惯,特意朝发廊里看了几眼。里面并没有西妹,没有她圆圆的脸,也没有她那带着四川口音的声音。
我想西妹也许去做别的什么了,也许正在里面的某个单间里,我耸了耸鼻子,就这样想着离开了槐花巷,离开了那飘着胭脂气的小巷。当我登上一辆蓝色的公交车后,我的手机就响了。是西妹的短信:“研究生大哥,我走了,我男朋友被车撞了,很重,怕是永远站不起来了,我不能不过去,还记得那天我向你借钱吗?就是为了去看他,一时兜里又没钱,急昏了脑壳,还是姐妹们给我凑了点儿路费。这下可好了,我要照料他龟儿子一辈子了。真不好意思,那天我打扰大哥了。”
我得承认这个短信让我心里一动了,而且多少有点儿不是滋味。我认为我其实并不是很看重钱的人,我赶紧拨打西妹的手机,我想告诉她我愿意把钱借给她了。我拨打了好几遍她的手机,西妹就是不接,只有她手机上的彩铃声一遍一遍地响着,那是一首当时很流行的歌曲,汤朝的《狼爱上了羊》
“狼爱上羊啊爱的疯狂
谁让他们真爱了一场
狼爱上羊啊并不荒唐
他们说有爱就有方向
狼爱上羊啊爱的风光
他们穿破世俗的城墙
狼爱上羊啊爱的疯狂
他们相互搀扶去远方……”
我好像今天才真正听明白这首歌,突然之间就被狼感动了,当然也被羊感动了,虽然它们也不是一个世界的。
(责任编辑 晋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