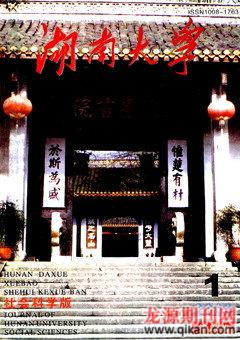19世纪英国历史小说简论
刘洪涛 谢丹凌
[摘要]历史小说是英国文学的一个重要门类,它萌芽于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时期,在19世纪迎来了它的辉煌时代。以人物与历史的关系为主线,19世纪英国历史小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在司各特的历史小说世界中,历史总是制约着人物的命运;雏多利亚早期历史小说中的人物试图摆脱历史羁绊,独立演绎自身命运;维多刺亚中晚期的历史小说中,“历史”开始被人物支配,它渗入人物内心的探索历程,成为个人精神结构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19世纪英国历史小说;司各特;维多利亚时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1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09)01-0076-05
英国哲学家柯林伍德(R.G collingwood,1889~1943)在谈到历史小说的定义时曾说道:“小说家们在虚拟的世界中以历史为素材建构起一座真实的大厦,当小说中的生活被置于历史背景下时,当小说中的人物与历史人物的处境不谋而合时,这就是一部历史小说。”概言之,历史小说是以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小说,它往往忠实于史实和细节,艺术地再现历史风俗、社会概况和人物的生存状态。
早在16世纪后期的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盛极一时的流浪汉小说里已经开始出现历史的痕迹。而流行于18世纪末l9世纪初的哥特式小说,“可以被认为是历史新态度在文学形式中的第一次体现”,“它是历史传奇的一种独特形式,一种关于过去历史与异域文化的幻想形式。”也就是说,哥特小说并不局限于表现恐怖的主题,还着力于“描绘出一幅封建时代家庭生活和风俗的图画”,由此唤起一种“令人快乐的惊恐”。这些令人惊恐与愉悦的图景孕育在历史的废墟中,暗示着小说中历史因素的萌发。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英国区域编年史热潮的兴起,历史小说的“史前史”阶段宣告终结。这一时期的一些小说受这股风潮的影响,以地方古志和历史记录为题材来展现一个逝去的时代,着力描绘了散发着乡土气息的历史、方言与生活习俗。此类“区域小说”的直接后果,是催化了历史小说的伟大天才司各特的诞生。
“19世纪是一个剧烈动荡的历史时期,这个世纪执著于对过去经验的研究,它渴望搜集历史的遗存和艺术,正如卡雷所说的,它醉心于被时代、过去、当下、未来所涵盖的思想。”当19世纪大多数欧洲小说家对自己的时代风尚质疑时,他们不愿在现实中寻找答案,而是将目光投向历史。于是有了司各特,有了司各特之后英国历史小说的异彩纷呈,高潮迭起,从而造就了历史小说发展的黄金时代。
一司各特小说王国:历史幕景下的人生百态
司各特不仅仅改变了小说,而且改变了书写历史的方式。他不断向拥有史诗创作经验的前辈学习,更为显著的是,他从莎士比亚的剧作中汲取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司各特的名字是一个跨时代的文化符号。他“以历史为媒介,完成了艺术与生活的完美结合”,“他的历史在对待某一特定时期内某一特定国家的风俗、习惯、情调和精神的关系上,比任何历史都更加翔实可靠”。司各特的小说超越了哥特小说中的奇思异想,超越了环境现实主义小说的最初形式,他通过艺术手段展现了真实的历史事件和时代精神,使欧洲小说超出了风俗小说的狭窄范围,进入了展现社会和历史的广阔领域,从而创造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小说。
历史,这个独特的角色,在哥特小说家霍勒斯·沃尔波(Horace Walpole,1717~1794)、拉德克利夫夫人(Ann Radcliffe,1764~1823)那里,不过是故事情节的点缀和陪衬,而从司各特1814年的成名作《威弗利》开始,到后来的《中洛辛郡的心脏》、《修墓老人》、《红酋罗伯》等等,它已经赢得了独有的“话语权”。司各特的小说犹如一幅幅巨大的历史画卷,把中世纪到资产阶段革命时期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社会生活包罗无遗。在司各特笔下,历史不再是铺设故事的道具,而以其不可替代的特质成为故事里一道最独特的“风景”。
与此同时,“个人”开始以独立的角色粉墨登场。“司各特小说不仅栩栩如生地描绘了过去时代的社会生活、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同时也形象而真实地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这些人物都是时代的人、阶段的人、社会的人。”在司各特的小说中,个人的命运开始与巨大的历史事件结合在一起。正如巴尔扎克称赞司各特时指出的那样:“(他)作品里的人物是从时代的五脏六腑里孕育出来的。”
在历史小说中,司各特细致地确立了一幅幅人物在历史环境中自然活动的图景,使历史与个人形成了默契的联结。这些人物不再身着哥特式小说中的奇装异服,他们与当时的物件、摆设和看法和谐共存。同时,司各特从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四世》、《亨利五世》中汲取养分,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大胆地运用了虚构与想象,勾勒出一个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并运用极富个性的私人生活场景和鲜活的小人物画廊,生动具体地描绘了当时的社会习俗。这些平凡的人物在历史的制约之下“戴着脚铐跳舞”,演绎着命运的故事,这不能不说是历史小说的一大突破。以《中洛辛郡的心脏》为例,这部作品完整地诠释了司各特对于历史小说中“个人”角色的独到见解。小说以苏格兰农民大卫·迪恩斯的两个女儿珍妮和爱菲为主要人物,并将这两个角色与苏格兰农民反对外来压迫的历史运动汇合起来。正如司各特曾对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提到的那样:“一个民族的性格,不是从它衣冠楚楚的绅士群那里可以了解到的。”于是,作家在《中洛辛郡的心脏》里便排斥了“衣冠楚楚的绅士群”,而让一群胼手胝足的劳动者占据了前台,让珍妮·迪恩斯在爱菲的悲剧里崭露头角,在历史的舞台上演绎着人生百态。珍妮和一般小说里浪漫动人的女主人公不同,她在独特历史环境的影响下形成了朴素的人生信条和道德原则。她在当时清教徒家庭的严格教育下,在法庭上坚定地说了真话,致使妹妹爱菲被判死刑,这体现了历史环境对个人行为强大的塑造作用;但在出庭作证后,坚信妹妹无罪的珍妮决定去伦敦面见国王,替妹妹申诉冤情,这体现了个人由于意识到了自己在历史语境中的地位,开始对强权进行反叛,人物与历史在一个广阔的背景中相联结。显然,司各特认为,人民能够很好地传达历史的雄浑回音,小说中历史的决定作用在底层人物的生命轨迹中得到彰显。
此外,历史中真实的帝王角色也是司各特笔下鲜明的历史人物,司各特丝毫不粉饰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展现的真实性情。《城堡风云》的故事情节设置15世纪的欧洲,中心人物法国国王路易十一在打击诸侯割据势力和加强中央集权的行动中将自私、迷信、残忍、狡诈的性格展示得淋漓尽致。在另两部小说《肯尼威斯城堡》和《奈杰尔的家产》中,英国历史人物伊丽莎白与詹姆士一世的形象在历史的日常语境中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这些帝王英雄在历史幕景的制约下形成了真实而独立的个性,他们的思想与行为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
由此而知,司各特不愧为欧洲历史小说的创始
人,他把人物设置在充分发展的历史关系中,把人物放置到具体的历史舞台上。但弗吉尼亚·伍尔夫谈到司各特时说:“他笔下的人物只有在谈话的时候才活着,他们不会思考。司各特既不探究他们的心理,也不尝试从他们的行为中推论出什么。”正如前文所说,司各特小说最大的特色还在于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他的历史小说侧重于对生活外部环境的描述,只把人物作为传达历史信息的“工具”。例如在司各特第一部长篇小说《威弗利》中,主人公爱德华·威弗利无非是一个透明的中介,是一个对詹姆斯二世党人的活动一无所知的英国青年。他只身来到苏格兰高地,睁着好奇的眼睛,持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把一切新奇的事物尽收眼底,同时把他的所见所闻通过历史感悟呈现出来,从而展现逼真的历史图景。同样,在《中洛辛郡的心脏》中,司各特虽然着力描述了个人遭际,但更多地是为了从个人的命运中折射出一个时代重大的历史矛盾。司各特并没有细腻地描写珍妮遭遇困难时的内心波澜,而是将她放置在一连串戏剧性矛盾中,让珍妮用具体的行动对困难处境做出回答,将人物的行动融入时代的背景。此外,司各特小说中的人物常常是平庸而无为的,他们仅仅生活在一个特定的时代,所知有限。不同时期的文化是通过一个全知叙述者来介绍的,这个全知者站在比小说人物更高的位置上比较过去与现在,归纳人物与历史的联结,这也进一步削弱了小说人物的地位。
虽然司各特小说中的人物“平庸、被动或摇摆不定”,但他笔下关于人物的描写却是历史小说史上个人“成长”历程的一道分水岭。从那时开始,个人开始不断在历史舞台上寻求自己的角色定位,在历史的支配下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演绎自己的人生悲喜剧。
二维多利亚时代早期:历史浪潮中的个体生存
作为“纷繁复杂”代名词,维多利亚时代孕育了文学史上罕见的辉煌,历史小说也在继承与创新的矛盾徘徊中迎来了丰收的黄金时期。维多利亚时期的历史小说家试图维系着与司各特历史世界的某种联系,但是他们开始体悟历史发展的整个进程,在当下和永恒之中抒写历史的瞬间。同时,莎士比亚在《亨利四世》中所描写的“大众生活”影响着维多利亚时代历史小说家们的创作。“仿佛约定俗成一般,这些小说不再沉溺于浪漫的历史片断,而是努力将社会与个人融入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历史小说赢得了这一时期小说中的桂冠。”
维多利亚早期的历史小说是从司各特时代缓慢过渡而来的,这是一个人物独立演绎命运的“历史”时代。早期的历史小说中充斥着各色各样的人物,有孤独的追寻者、哥特式的恶棍、寻求精神世界的英雄……他们在历史的框架之下开始了独立的追求。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影响深远的历史小说家,如威廉·安斯沃思(William Harrison Ainsworth,1805-1882)、吉姆(George Payne Rainsford James,1801-1860)、布尔维·利顿(Edward George Bulwer-Lyt-ton 1803~1873)等,还有许多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作家,如查理·狄更斯、威廉·萨克雷等,也积极地投身于历史小说的写作。
狄更斯一生写过两部历史小说,一部是《巴纳比·拉奇》,另一部是《双城记》。《巴纳比·拉奇》是以1780年“伦敦起义”为背景的,这是一次由清教徒领导的群众性暴动。中国读者熟知的《双城记》则描写了一个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在展现法国大革命宏大叙事的基础上刻画了英法两国的社会状况。对于小说中的英法社会,狄更斯并不是进行逐个的、细致的描绘,而是创造了一个连结的背景,将两个国家作为一个历史文化的集合体,从而展现波澜壮阔的历史。同时,狄更斯通过气氛紧张的社会背景,“成功地戏剧化了个人的困境与冲突,分裂和承诺”。他开始将个人纳入了历史的叙述之中,利用人物与环境的联系,细致敏锐地观察人物的外部特征。这部小说突出地刻画了查尔斯和卡顿两个人道主义的理想人物,狄更斯把他们放置在一个暴乱而残杀的年代,使他们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语境中诠释舍己为人的自我牺牲精神,从而折射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查尔斯是侯爵的儿子,他自动放弃贵族特权,到英国居住,和梅尼特医生的女儿结了婚。为了营救管家,他冒着生命危险回到法国,被革命者逮捕,并判处死刑。卡顿为了营救“情敌”查尔斯,混入监狱,顶替和他长得十分相似的查尔斯上了断头台。可以说,这是两个人物独立演绎的“英雄悲剧”。他们拥有自己的思想,并深刻地主宰自己的内心活动和外部行为。此外,在《双城记》中,狄更斯没有采用古典的历史阐释,将历史视为奔腾不息的河流,而是选择了“圣经”模式,将历史的进程演绎为一段“重获新生”和“自我救赎”的历程。卡顿代替查尔斯死去,查尔斯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卡顿,并带他回到法国,向他讲述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象征着人物的重生。然而,狄更斯并不仅仅赋予人物在煎熬、混乱、牺牲后的“复活”,他通过个人的“新生”展示了历史“死而复生”的发展模式——英法两国在死亡般的浩劫后一切恢复平静,预示着重获新生的潜力。这种将个人的经历融入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形成暗示作用,是继司各特之后维多利亚时代历史小说的新颖构思。
在众多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小说家中,萨克雷是一颗独特而耀眼的星。他对历史创作拥有独到的见解,认为“小说比历史史书更接近现实,同时认为,与常规的历史描写相比,小说家和画家所强调的艺术,能够为生活提供一个更真实的图景”。在1851至1852年间,他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部历史小说《亨利·艾斯芒德》,在其中,萨克雷带着或喜欢、或怨恨、或支持、或诋毁的态度审视小说中的个体,力图呈现一种真实的、浑然天成的历史图景。他把个人经历作为历史事件的重要部分来描述,使个人在历史的漫长叙事中拥有一席之地,作家的历史观点也在个人经历与人类经历的广阔联结中得到体现。与此同时,萨克雷认为小说人物比史传中的英雄更真实,他笔下的人物都是有缺陷的,比起司各特,他更加突出地展现了历史处境下的人性。《亨利·艾斯芒德》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下表现了英国17世纪末巨大的历史事件和参与其中的一些人物的生活和命运。小说里写到了帝王、贵族和率领千军万马的将领,但萨克雷却不用虚假的光彩去装点这些大人物。他曾说:“历史女神为什么要无尽期地跪着呢?我赞成请她站起来,恢复自然的姿态。”在主人公的从军经历以及7年战争的若干描写中,将领之间勾心斗角的行为和自私自利的性格暴露无疑。这种平等主义的表现手法使历史人物的自主性得到提升,人物已经具备了独立展现自己性格中善与恶、美与丑的“能力”,同时,萨克雷通过人物的真实性与平等性将历史引向了熟悉的路途,从而呈现了历史“质朴”而“可爱”的一面。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历史小说虽然仍然着力于展现“历史”的变迁,但个人已经完全地沉浸在历
史进程中,独立演绎自身的命运。个人的经历融入历史的浪潮中,成为展现历史的一扇独特的“窗口”。同时,个人以平易的个性真实地贴近生活,贴近历史,从而展现历史的常态。然而,由于这一时期历史小说的重心仍然在于展现风云诡谲的历史时代,因此不论是《双城记》、《亨利·艾斯芒德》,或是其他维多利亚早期的历史小说,都是“以社会群体作为主要行为承担者的历史小说”,它们对人物的刻画重心往往偏向外部行为,人物的性格有时难免归于大众化,拘泥于某一个性的模式化范畴。
三维多利亚时代中后期的“转身”:漫漫旅程中的心灵跋涉
从司各特一路徜徉而来的历史小说,在维多利亚时代中后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虽然小说仍然对公众事件与个人命运投以极大的关注,但此时的“个人”已经享有极大的自由意志,历史则渐渐成为人物行为苍白的框架或布景,它决定人物命运的“权力”在一点一点地被剥夺。
在维多利亚中晚期的历史小说中,主人公不再像“威弗利”式的英雄将自己的生活暴露在极端的历史行为中,也不像狄更斯或萨克雷笔下的人物以自己的方式逃避与历史之间的联结,这些“新时期”的人物一开始就不完全沉浸在历史语境中,历史只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渗入他们内心的探索历程,成为个人精神结构的组成部分。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重要的历史小说,如理德(Charles Reade,1814-1884)的《寺院与家庭》、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1819—1880)的《罗慕拉》、瓦尔特·佩特(WalterPater,1839~1894)的《享乐主义者马里厄斯》等等,这些小说里的人物在历史的过往中沿着生命的轨迹,探寻宗教难题,追求精神乐园,在历史中寻觅独立的灵魂世界、崇高的宗教信仰和命中注定的社会使命,开启了个人精神轨迹的成长之路。
不少评论家认为,维多利亚中期历史小说的转变与创新始于理德的《寺院与家庭》。虽然这部被誉为“19世纪最成功与最具新精神的历史小说”里充斥着零散的画面、幼稚的冒险情节以及极端的暴力场面,但却囊括了许多时代的符号,如意大利的探寻之旅、宗教冥想,关于责任与义务、历史与现实的诠释等等。值得关注的是,里德将笔墨着力用在未被历史称颂过的平凡人物的平凡生活和内心世界,在冷色调中缓缓地揭开中世纪的神秘面纱,从而展示了中世纪末文艺复兴早期“残酷”的日常生活。这部小说代表了历史小说转变期间的特质,即在世俗的存在状态中开拓人物精神世界,并在人物琐碎而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心灵的价值。同时,理德开始有意无意地展现平凡人物与历史之间的“疏离”。他将两者分置在不同的层面,使两者对立,甚至将历史背景设置为人物的强大“敌人”。小说中主人公的探求之路、使命与背叛并不仅仅在于表现中世纪向文艺复兴过渡时期所呈现的社会现象,此外,我们仿佛听到了一个自由人发出的“呐喊”。
而将个人的探求之路演绎得登峰造极的则是被视为“演绎人类心灵哲学历程”的《罗慕拉》,这部历史小说被不少人认为是作家乔治·艾略特一生的完美转折。艾略特曾经说过:“我不愿在严肃的历史中寻找阐释历史的抽象方式,我希望能从过去丰富而具体的历史事件中汲取素材,创作出简明朴素而流露真情的作品。”这部小说以15世纪意大利宗教改革为背景,展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由文化与基督教思想的冲突。它以黎明为开端,表现了一个妇女意识痛苦的觉醒历程,展示了女主人公通向精神启蒙的道路。小说中描写了人物的私人生活,大量地触及人物独立的思考、行为、希望,并推而广之,从而在个体的基础之上认知人类广阔的、永恒的整体,通过人物的精神特质,展现了佛罗伦萨在过往的历史图景中所呈现的多样性。从文章的标题,我们不难看出个人在这部小说里“至高无上”的地位。罗慕拉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她是一位代表人类精神与道德发展希望的女主人公,“她虽然不是一个完美的典型,她所获得的智慧也算不上出类拔萃或高深莫测,但她执著的探寻之路却真实地反映了人类心灵的发展历程。”庞大的历史语境在这部小说里被渐渐地分解为文化符号,人物沉浸在这些符号中,探寻与自己灵魂相关的精神命题,在历史中获得了心灵的超脱。艾略特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曾提到,自己之所以将小说设置在历史环境中,是为了“获得能自由呼吸而真实可信的个体生命”,同时使整部小说建立在人类情感经历的基础上。可见,艾略特已经进一步意识到历史小说的主体意识,并不遗余力地开拓了人物的心灵空间。此外,《罗慕拉》与《寺院与家庭》相似,也从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个人与历史之间的“疏离”。小说的最后,女主人公从婚姻、国家、宗教等一切历史关系的象征符号中解放出来,她的觉醒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决裂,不仅是与政治的复杂性与佛罗伦萨的黑暗面相背离,也是与外在秩序的一种疏离,是一种新的“洗礼”。与司各特、萨克雷笔下的主人公不同,罗慕拉高贵的人格与崇高的追求都建立在纯粹的精神世界之上,不被政治环境所玷污。可以说,《罗慕拉》是英国历史小说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它标志着历史小说迎来了一个巨变的时代。
维多利亚后期的小说沿着理德、艾略特所开辟的道路继续跋涉。《约翰·伊格利森》(《John Ingle-sant》,Joseph Henry Shorthouse,1834~1903)与《罗慕拉》的主题十分相似,都关注人物内心的成长历程,将外部世界作为人物情感的“催化剂”。这部小说在17世纪政治及宗教风波的背景下展现了人物心灵发展的曲折历程,是人物精神特质的完美提炼。它彻底地摆脱了“威弗利”小说的模式,人物不再是被动反映历史的一面“镜子”,而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纠结中保持着精神的探求,并从家庭、环境、教育等因素中获得了永恒的自由。这是一部演绎主人公灵魂的“戏剧”,它的最大特色是在淡化的历史背景下将人物设置为一个有思想的存在,他们以缄默的态度面对朦胧的世界。
个人的“成长史”在帕特《享乐主义者马里厄斯》的历史世界里演绎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小说主人公马里厄斯是一个宗教信徒,“他的成长就是一段历史的真实写照”,展现了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马里厄斯从罗马王国一路走来,到达巴黎、伦敦,他在不同的时代命题中探求个人心智发展历程中的哲学难题。他像一个长途跋涉的追寻者,在古典时期与维多利亚时代理性文明的语境中寻找精神上的“丰收”。此时,“历史”已经演化为一连串零散的符号,被分置在个人获取精神新生的漫长旅途中。
四结语
记录时代喧哗与骚动的英国历史小说从过去的风尘中一路走来,演绎了一段段属于历史的、个人的生命精华。历史小说中“个人”的角色经历了一个从渺小到重要,最终“膨胀”的过程,也经历了由外在行动为主导到内心精神世界支配的历程;他们在风云变幻的历史时代不断“成长”,不断诠释自己在历史中的角色与定位。如果说,在历史之中不断追寻人物的生存与心灵价值,是19世纪英国历史小说的独特道路,那么,“将历史视为构造人格的建筑材料”,则是20世纪现代主义历史小说发展的趋势。随着历史小说中“个人”地位的不断膨胀,“历史”已经渐渐失去了已往光鲜的地位,演绎为一段虚拟而零碎的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