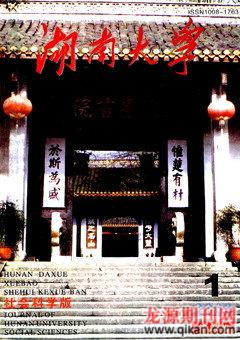中国散文文体的近现代嬗变
付建舟
[摘要]清末民初,中国散文文体发生巨大嬗变,这主要体现在传统的应用性散文文体严重衰退,文学性散文文体也今非昔比;而近现代散文文体如严复、章太炎和章士钊等人的“逻辑文体”,谭嗣同、梁启超的报章体,用作人等人的美文文体,林语堂等人的“小品文”文体等,异军突起,逐渐取代传统散文文体,并在文坛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传统散文文体;现代散文文体;嬗变
[中图分类号]1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09)01-0081-06
诗文在我国文学史上一向处于主导地位,然而清末民初,随着西方文学观念的涌入,情况大为改观,我国散文文体发生了急遽的变化。时至今日,虽然不乏一些零星的研究之作,但一般都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因此,研究中国散文文体的近现代嬗变就十分必要。
散文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文学”概念,也是一种十分棘手的“文学”文体。人们对它的认识也不像诗歌、小说、戏剧(戏曲)那样明晰。我国古代,将不押韵和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包括经传、史书,都称为散文,即除诗、词、曲、赋之外,不论是文学作品还是非文学作品,都一概称之为“散文”,以与韵文、骈文相区别。
一中国古代散文文体的基本形态
中国古代应用性散文文体比较发达,文学性散文文体也比较发达,而且种类多样。历时地看,先秦散文(包括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包含哲学、政论文和史传文章在内。诸子散文以论说为主,如《孟子》《庄子》;历史散文以记述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为主,如《左传》《国语》。两汉散文成就斐然,司马迁的《史记》把传记散文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唐宋以来,在古文运动的推动下,散文的写法日益繁复,出现了文学散文,产生了不少优秀的山水游记、寓言、传记、杂文等作品。明代散文,先有“以拟古为主”的“七子”之作,后有主张作品“皆自胸中流出”的唐宋文派。清代散文则不同,它把文学性散文与应用性散文融合在一起。以桐城派为代表的清代散文,注重“义理”的表现,其代表作家姚鼐对我国古代散文文体进行了总结,他把散文分为13类,包括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说、箴铭、颂赞、辞赋、哀奠。
古代散文文体的源头是《易》、《书》、《诗》、《礼》、《春秋》。一般认为,论、说、辞、序发端于《易》,诏、策、章、奏发端于《书》,赋、颂、歌、赞发端于《诗》,铭、诔、箴、祝发端于《礼》,记、传、盟、檄、发端于《春秋》。我们对这些文体以及其他文体进行分析后,认为中国古代文体可以分为应用性散文文体与文学性散文文体两大类。应用性散文文体主要由于实际应用的需要,产生于封建帝王的各种政教活动,不同的政教活动需要使用不同的“文书”,不同的“文书”有不同的要求,因而产生不同的文体。其中有的以叙事为主,有的叙事与抒情相结合,有的叙事与议论相结合,如铭、箴、诔、碑、封禅、颂等。文学性散文文体主要是文化传承的需要。诗文是中国传统公认的文学文体,其重要特点是叙事与抒情,而且抒情占上风。史传一般认为是历史文体,也是地位最重要流传最广泛的叙事文体,由于其文学性很强,也往往看作文学文体。作为正史之余的小说到晚清之后才逐渐成为文学的正宗。从诗发展而来的赋体和戏曲,不像诗那样以抒情为主,而逐渐以叙事为主。文学性文体,从魏晋以来就有一个鲜明的传统,即以是否有韵来对它分类,有韵的为“文”,无韵的为“笔”。刘勰《文心雕龙·总术》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两名,自近代耳。”这里对“文”与“笔”的区分,首先注重音韵,其次还与文体联系起来。梁昭明太子在《文选》序中说,文选所选之文以清英为贵,不选尊经之文,不选宗意之文,不选载言之文,不选记史之文,而独选沉思翰藻之文。他抓住了文学注重沉思与辞藻的重要特征,这对李兆洛产生极大的影响。李兆洛提倡骈体文,编辑《骈体文钞》。在《骈体文钞·自序》中,他说:“天地之道,阴阳而已。奇偶也,方圆也,皆是也。阴阳相并俱生,故奇偶不能相离,方圆必相为用。道奇而物偶,气奇而形偶,神奇而识偶。……吾甚惜夫歧奇偶而二之者之毗于阴阳也。毗阳则躁剽,毗阴则沉腿,理所必至也,于相杂迭用之旨,均无当也。”骈体文形式上的特点是重比偶,内容上的特点是重抒情。
二中国散文文体新体系的产生
中国传统散文文体是以《易》、《书》、《诗》、《礼》、《春秋》等五经为根本,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文体体系的,而现代散文文体是以现代知识为对象,以科学思想为根据,逐渐建立起新的文体体系。最明显的过渡性著作是龙志泽(字伯纯)1905年出版的《文字发凡》。在这部著作中,龙氏试图用中国传统的文体分类法与西方现代文体分类法对文体进行分类。
首先,他对传统的分类加以改造,在《文法图说》部分的“体制”篇中,他把“文章”分为四类:叙事体、议论体、辞令和诗赋类。同时,龙志泽还借鉴西方的文学理论,在《修辞学》部分的“构思”篇中,他以思想的性质为标准,把“文”分为四类:记事文、叙事文、解释文和议论文。“记事文者,记人记物者也。记事文之目的,是记者欲将其人之面目精神,仿佛现于读者之眼前也。”记事文分为科学的记事文和美术的记事文两种。“科学的记事文者,其记载诸物,在能将诸物分析,详其部分,显其全体,明白了然。”它能将事物之“形状精神全盘托出,以益人之智识”。美术的记事文与科学的记事文不同,“科学的贵于明晰,美术的在于含蓄;科学的贵于条举,美术的举其著明之特点而已”。科学的记事文是以精细之笔描摹事物的真相,使人有所知;美术的记事文则用艺术之笔描摹事物的神情,使人有所感。龙志泽企图用西方的叙事观念来界定叙事文,“叙事文者,历叙连续之事实,行动之变化也。”他还把叙事文与记事文严格区分开来。“叙事文与记事文不同,记事者说其事而已,叙事文者,是依言语之性质,次第表出之。如对人说话,说话要有整然不紊之次第,叙事文亦然。”他囫囵吞枣地运用西方的叙事概念,尚欠准确。一般来说,叙事文叙述存在因果关系的连贯事件,但不一定是时间关系上的连续事件。随着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引进和白话文的流行,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文学理论与批评著作大量涌现,许多书局都竞相编译、撰写,甚至请人翻译国外的理论著作或自撰著作。现代文法家基本采用西方的新文体分类法,如高语罕著的《国文作法》、陈望道的《作文法讲义》、踉工编的《记叙文作法讲义》、夏丐尊与刘薰宇合编的《文章作法》、章衣萍的《作文讲话》以及其他相关著作都是这样。他们首先对“文”进行分类,陈望道分为五类:记载文、记叙文、解释文、论辩文、诱导文;夏丐尊与刘薰宇也分为五类:记事文、叙事文、说明文、议论文和小品文;章
衣萍分为四类:记事文(Description)、叙事文(Narra-tion)、解说文、议论文。记载文就是记事文,一般记载人或物的形状与性质,它可以分为科学的记载文和文学的记载文两种。前者主传达知识,使人理解;后者主传达情意,使人感受。前者按照一定次序描述各部分的位置、形状、色彩;后者与其说是事物的报告,不如说是印象的表现。写出个性,使人感动。记叙文也称叙事文,它记叙人物与物体的动作变化,强调变化历程。叙事文包括四个要素,即人物、事迹、事件和地点。根据旨趣,叙事文可以分为三类:以给人知识为主的,如普通的历史、教科书之类;以动人观感为主的,如劝善惩恶的旧小说;以给人兴趣为主的,如滑稽小说之类。他们彼此之间大同小异。这里讨论的文体,不分应用性文体与文学性文体,但重点仍然在应用性文体。
从以上可以看出,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古代应用性散文文体的发展态势,由强而弱;文学性散文文体由弱而强。不过,各自的地位并不一致,传统诗文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其中还伴随着骈文与散文的长期争锋。小说与戏曲一直被排除在正统文学行列之外。到晚清,中国海禁打开,西方文化不断进入,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也不断发生变化,传统文学文体也逐渐蜕变,近现代散文文体观念逐渐产生。
三现代“逻辑文体”的产生及其反响
由于历史的发展,时代的需要,新的散文文体逐渐萌生。作为时代战斗檄文的“逻辑文体”随着报刊的不断发展而迅速发展,并逐渐成熟。逻辑文体的代表人物有严复、章太炎和章士钊。严复的“先秦文”风格、章太炎的“魏晋文”风格、章士钊的“先秦文”与“魏晋文”融合风格,均作为逻辑文体,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罗家伦在《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一文中指出,“这个时代普通出版品的倾向大大变了,鼓吹新政的空泛文章,进而为比较精密的法政议论,如《富国强兵策》一类的东西已经减少,出版最多的乃是《宪法古义》、《日本宪法解》、《日本法规大全》、《政治原理论》、《列国政要》一类的书。……所谓‘逻辑文学,原来不能算是十分确切的名词;不过当时文学的趋势,已确实的向着精密朴茂的方面,而渐渐合于逻辑的组织。如当时文学界最重要的两个人:一个章太炎,是对于印度的‘因明学很有研究的;一个严几道,是译西洋名学的,章太炎的文章一方面有印度思想的条例,一方面带政治潮流的刺激……”严几道翻译的西方的政法著作,每种都是风行当时整个时代的书。后来章士钊先生“一方面崇拜‘吾家章太炎先生,一方面对‘侯官严先生也是很恭敬的;又加上民国元二年议政的潮流、制宪的背景,所以《甲寅》杂志出来,可谓‘逻辑文学的大成了!”罗家伦认为,《甲寅》杂志“在民国三四年的时候,实在是一种代表时代精神的杂志,政论的文章,到那时候趋于最完备的境界,即以文体而论,则其论调既无‘华夷文学(引者按:叶德辉、王任秋等人的政论文学)的自大心,又无‘策士文学(引者按:魏源、龚自珍、康有为等人的政论文学)的泛泛气;而且文字的组织上又无形中受了西洋文法的影响,所以格外觉得精密。”严复具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素养,对先秦散文很有研究。他翻译西方的政论著作、社会学著作都具有古色古香的先秦文风。吴汝伦说,赫胥黎“欲侪其书于太史氏、扬氏之列,吾知其难也;即欲之唐宋作者,吾亦知其难也。”但是经过严复文体上的包装,其书乃“与晚周诸子相上下”。(P1318~1319)梁启超也说,严复“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模效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
他们的评价诚不污也。严复的文体观念在其“信、达、雅”的翻译理论中得到鲜明体现。“信”是指译文要忠实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达”是指译文要语言流畅,“雅”是指翻译要讲究辞藻,注意遣词造句。严复提倡翻译不仅要传信,而且还要文字通达,语言雅洁。他“在翻译西方学术著作中,采用意译的方式,把原文的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按照汉语句法,主要是先秦文言的句法,把原文的复合长句拆开变为平列句式,多用排比、对偶等修辞手法,语言古雅而不刻板,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语句系统。”不过,尽管在严密的逻辑上,他们具有共同点,但是他们讲究逻辑也各有自己的特点,即共性之中存在各自的个性。严复逻辑文体的传统资源是“先秦文”文体,章太炎的则是“魏晋文”文体,章士钊则兼而有之。
四现代“报章体”的产生及其反响
然而影响更大的还是报章体,或日新文体。作为晚清政治运动和文学革新运动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大胆进取,锐意改革,他们的散文无视传统古文的程式,直抒己见,畅所欲言,是政治斗争的有效工具。梁启超的新体散文更是对一切传统古文的猛烈冲击,为晚清的文体解放和“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开辟了道路。晚清文学改良运动,用浅显平易的新体散文代替僵化的桐城派古文、八股文和骈文等传统文体,并逐渐发展成一种新的文体,称为“新文体”,或“时务体”、“报章体”、“新民体”。
晚清知识分子大力提倡“报章体”。1897年,谭嗣同在《时务报》上发表《论报章文体》一文,认为“报章文体”在内容上无所不包,在形式上,打破传统的文章观念的束缚,以便于发表言论和宣传为标准。谭嗣同具有深厚的古文功底。在《三十自纪》中,他说:“嗣同少颇为桐城所震,刻意规之数年,久自以为似矣。出示人,亦以为似。诵书偶多,广识当世淹通传壹之士,传稍稍自惭,即又无以自达。或授以魏晋间文,乃大喜,时时籀绎,益笃耆之。由是上自秦汉,下循六朝,始悟心好沉博绝丽之文,……所谓骈文,非四六排偶之谓,体例气息之谓也。”谭嗣同认为,总揽一切知识与学术的史家与选家,都不足以根据时代的急剧变化,知识的快速更新,而描述记载并囊括之;惟有报章能够担当如此重任。报章文体与旧式文体相比有巨大的优越性。往昔文章体例,除词赋之外,其他的可以分为三类十种,“名”类包括“纪”、“志”、“论说”和“子注”四种。“形”类包括“图”、“表”和“谱”三种。“法”类包括“叙例”、“章程”和“计”三种。这十种文体不能适应现代知识更新和时代发展的需要,而报章文体不仅兼有传统十种文体的功利,而且还贴近社会现实,“其体裁之博硕,纲领之汇萃,断可识已。胪列古今中外之言与事,则纪体也;缕悉其名与器,则志体也;发挥引申其是非得失,则论说体也;事有未核,意有未曙,夹注于下,则子注体也;绘形式,明交限,若战守之界限,货物之标识,则图体也;纵之横之,方之斜之,事物之比较在焉,价值之低昂在焉,则表体也;究极一切品类,一切体性,则谱体也;宣撰述之致用,则叙例体也;径载章程,则章程体也;句稽繁琐,则计体也;编幅纡馀,又以及于诗赋、词曲、骈联、俪句、歌谣、戏剧、舆讼、农谚、里谈、儿语、告白、招帖之属,盖无不有焉。……斯事体大,未有如报章之备哉灿烂者
也。”谭氏试图从诸种不同的传统文体中吸收有益的成分,创造出更有活力、更能适应报章的新文体,这一理想在梁启超那里化为现实。1899年,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提出“文界革命”的口号,主张改造文体,他认为日本三大新闻主笔之一的德富苏峰“善以欧西文思人日本文”,其文“雄放隽快”,使文界别开生面。“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他要使诗文具有西方现代民主政治思想,从而获得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诗文的崭新特质。梁启超创造的报章文体风行一时,这种文体“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胡适指出其特点和影响,“梁启超最能运用各种字句语调,来做应用的文章,他不避排偶,不避长比,不避佛书的名词,不避诗词的典故,不避日本输入的新名词。因此,最不合古文义法。但他的应用的魔力也最大。”采用的措施,不是全部推倒传统诗文,而是借传统诗文以“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这种“新文体”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如果说谭嗣同侧重文体的融合,那么梁启超则侧重语言的融合。梁启超一反严复的渊雅文笔,使用浅近文言,提倡新式文体。他对严复的译笔提出严厉批评,“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文人结习,吾不能为贤者讳也。”梁启超的新文体受到康有为的重大影响,钱基博评论康有为的政论文说,“发为文章,则糅经语、子史语,旁及外国佛语、耶教语,以至声光化电诸科学语,而冶以一炉,利以排偶,桐城义法至有为乃残坏无余,恣纵不傥,厥为后来梁启超新民体之所由防。”报章体雅而不渊,畅而不俗,易于为读者所接受。
晚清“新文体”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极力赞成者有之,肆意攻击者有之。1902年,黄遵宪致函《新民丛报》,反映这种文体产生的巨大影响,“乃至新译名词,杜撰之语言,大吏之奏折,试官之题目,亦剿袭而用之。精神吾不知,形式既已大变矣;事实吾不知,议论既已大变矣。”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指出“新文体”魔力很大的原因:1)文体的解放,打破一切“义法”、“家法”,打破一切“古文”、“时文”、“散文”、“骈文”的界线;2)条理的分明,梁启超的长篇文章长于条理,最容易看下去;3)辞句的浅显,既容易懂得,又容易模仿;4)富于刺激性,“笔锋常带情感”。“新文体”不拘一格,一切为“我”所用。它打破文体界限,打破文白疆界,充满激情,富有活力。它犹如一股飓风席卷晚清各界,官场上,大吏的奏折借鉴它;科场上,试官的题目采用它;报刊界,大小报人竞相模仿它。这种巨大的威力,这种深刻的影响激起复古派与顽固派的强烈反对。“新文体”是对桐城派古文“雅洁”的反拨,古文家严复一向讲求语言“雅训”。他翻译的“信、达、雅”标准以及他的翻译实践都体现这个特点。语言驳杂不纯的“新文体”强烈地刺激着他敏感的神经,他痛斥“新文体”,谓“报馆之文章,亦大雅之所讳也”。不仅如此,他还对梁启超进行人身攻击,“大抵公操笔为文时,其实心救国之意浅,而俗谚所谓出风头之意多”,企图消解“新文体”的启蒙意义。另一方面,严复也不得不承认“任公文笔原自畅达,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他也认识到这种文体的巨大效应,“梁任公笔下大有魔力,而实有左右社会之能。故言破坏,则人人以破坏为天经。倡暗杀,则党党以暗杀为地义。”顽固派叶德辉面对急速发展的新文体所运用的新词语,激切地说:“观《湘报》所刻诸作,如热力、涨力、爱力、吸力、摄力、压力、支那、震旦、起点、成线、血轮、脑筋、灵魂、以太、黄种、白种、四万万人等字眼,摇笔即来,或者好为一切幽渺怪僻之言,阅不终篇,令人气逆。若不共惩此蔽,吾恐朱子欲废三十年科举之说,将行于今日。”还感慨地说:“而后有新学之猖狂,有桐城湘乡文派之格律谨严,而后有今之《时务报》文之藩籍溃裂!”批评也罢,赞成也罢,谭嗣同、梁启超等人毕竟怀着强烈的使命感,极力主张新文体,他们采用浅近的文言、新的语汇入文。这种语言形式与报章特有的传播载体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感染力极强的文体。报章体不仅在散文文体方面影响甚大,而且在思想文化方面更是如此。
五现代“美文”“小品文”文体的产生及其反响
梁启超的“新文体”主要是借鉴日本的报章体,注重语言的感染力;到五四时期,散文文体又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代意义上的散文文体正式确立。从五四时期开始的现代散文指除诗歌、戏剧、小说以外的文学作品,包括杂文、小品文、随笔、游记、传记、见闻录、回忆录、报告文学等。散文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杂文、短评、小品、随笔、速写、特写、游记、通讯、书信、日记、回忆录等都属于散文。总之,散文篇幅短小、形式自由、取材广泛、写法灵活、语言优美,能比较迅速地反映生活。
新文学家对散文的界定是相对于韵文的,他们所指的散文一般指无韵的文章。而“所谓韵者,系文字音韵上的性质与规约,在中国极普通的说法,有平上去入或平仄之分,在国外极普通的有长音短音或高低抑扬之别。照这些平仄与抑扬排列起来,对偶起来,自然又有许多韵文的繁琐方式与体裁,但在散文里,这些就都可以不管了……”。当时,文坛一般把长一点的文字称作散文,把短一点的叫做小品。郁达夫声称:“我们的散文,只能约略的说,是Prose的译名,和Essays有些像,系除小说、戏剧之外的一种文体;至于要想以一语来道破内容,或以一个名字来说尽特点,却是万万办不到的事情。”从内容上看,中国古代散文包括序跋、奏议、辞赋、哀祭等,而现代散文则一般分为描写文、叙事文、说明文、论理文等。传统散文,崇尚古雅,模范六经;现代散文则注重表现个性,自由挥洒。“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任何散文都来得强。”
一些文人学者大力提倡美文,周作人的《美文》(《晨报副刊》,1921年6月8日)、王统照的《纯散文》(《晨报·文学旬刊》第三号,1923年6月21日)、胡梦华的《絮语散文》(《小说月报》第17卷第3期,1926年3月)等是其中的代表作。所谓美文是指抒情性散文或特别讲究文字技巧的散文。周作人在文章里指出:“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为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中国古文里的序,记与说等,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针对当时封建复古派把白话散文作为俚俗粗鄙的街谈巷语,只有古典作品才能称为“美文”的谬论,周作人理直气壮地称具有文学性的白话散文为“美文”,他指
出:“文章的外形与内容,的确有点关系,有许多思想,既不能作为小说,又不适于做诗,……便可以用论文式去表他。他的条件,同一切文学作品一样,只是真实简明便好。”这种“美文”不是“长篇阔论的逻辑的或理解的文章”,它是近世自我的解放和扩大力的一种“不同凡响的美的文学”,它的特点除了“真实简明”而外,还在于突出作者的个性和真情。在一篇“絮语散文”(美文)里,“可以洞见作者是怎样一个人:他的人格的动静描画在这里面,他的人格的声音歌奏在这里面,他的人格的色彩渲染在这里面,并且还是深刻的刻画着,锐利的歌奏着,浓厚的渲染着。……”这种“美文”可以使人产生美感。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也指出:“白话散文很进步了。……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保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周作人提倡美文,意在审美情趣;胡适盛赞美文,意在为白话文张目,尽管他们的意图有别,对美文的赞同是一致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小品文”盛极一时。“小品文”又称作“小品散文”或“散文小品”,泛指文学体裁中与诗歌、戏剧、小说并举的散文。小品文是一种寓有抒情意味和讽刺性的短小散文。其特点,主要是通过事实和艺术形象来表现思想内容,议论较少,叙述、描写或抒情成分较多,以幽默的方式和喜剧性的情节,活泼、轻松的语言,使人发笑,并使人在笑过之后,看到问题的实质,发人深思。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小品文遍布报纸副刊的大大小小专栏。《论语》半月刊、《人间世》半月刊、《太白》半月刊、《新语林》半月刊以及《文饭小品》月刊、《芒种》半月刊、《西北风》月刊等以刊登小品文为主的刊物竞相出现,同时出现了“科学小品”、“历史小品”和“幽默小品”、“讽刺小品”等名目。正如朱自清1928年在《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一文里总结时指出的那样:“三四年来风起云涌的种种刊物,都有意地发表了许多散文,近一年这种刊物更多。各书店出的散文集也不少。《东方杂志》从二十二卷(1925)起,增辟新语林一栏,也载有许多小品散文。……去年《小说月报》的‘创造号(七号),也特辟小品一栏。小品散文,于是乎极一时之盛。”林语堂提倡小品文“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人间世·发刊词》),小品散文的写作要“各依性灵天赋”《论小品文笔调》),“无关社会学意识形态鸟事,亦不关兴国亡国鸟事”(《小品文遗绪》),这种以资产阶级个人为中心的文学主张完全否定了小品散文的社会功能,把小品散文看作是一种闲适的“小摆设”。许多作家纷纷撰文探讨小品散文的内涵、特质和社会功能。代表作有钟敬文的《试谈小品文》、阿英的《(现代十六家小品>序》、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郁达夫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鲁迅的《小品文的危机》等。研究小品文的专著有李素伯的《小品文研究》、冯三昧的《小品文作法》、石苇的《小品文十讲》、钱谦吾的《语体小品文作法》等。郁达夫在《关于小品文》一文中,对小品文的偏颇提出批评,他指出,“我们以为应该提倡小品文,积极批评小品文,使得小品文发展到光明灿烂的大路。我们应该创造新的小品文,使得小品文摆脱名士气味,成为新时代的工具。”鲁迅也反对把小品文当作“小摆设”,他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指导下,写下了《小品文的危机》一文,强调它对社会现实的迅速反应和作为“匕首”、“投枪”的社会功能。他有力地批评了林语堂等人的主张,指出“小摆设”之类的“麻醉性的作品,是将与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归于尽的”。他探讨了小品散文的特性和社会功能,认为“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
延续二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散文文体,到清末民初,逐渐被现代散文文体所取代。这不仅仅是个文体问题,更是个文化问题,从内容与形式的一致性来看,传统散文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传统散文文体与古代的社会生活相适应;现代散文是现代文化的载体,现代散文文体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现代文化和现代社会生活与传统文化和古代社会生活全然两样,散文文体发生近现代嬗变就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