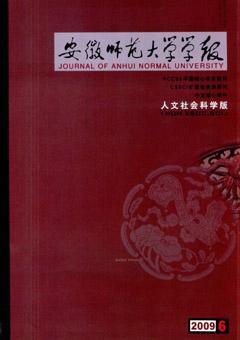新时期初“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生成肌理
关键词: 文学与政治;形象的表现;文学的独特性;审美意识形态
摘 要: 围绕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争,通过对新时期初期的“形象的表现”、“美学的反映”、“形式分析”与“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的主体性”的复杂关联,探讨新时期初文论界是如何摆脱文学的从属论、逐步确认文学的独特性的。
中图分类号: I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09)06063706
Generation of “Aesthetic Ideology” in Early Post-Cultural Revolution Era
LIU Fengjie(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123, China)
Key words: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mage expression; uniqueness of literature; esthetic ideology
Abstract:
Centered on the disputes over the literature-politics nexus, explore the shift of literary theories and criticism from the “subordination of literature to politics” to the recognition of the uniqueness of literature, through the interconnectedness of “imagistic expressions”, “aesthetic reflections”, “form analysis”, “aesthetic ideology” and “subjectivity of literature” in the early Post-Cultural Revolution era in China.
近来文论界对于“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生成颇为关注,主要是将新时期以来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争作为其产生的思想背景,从个人的理论创造经历探讨了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生成情况,认为“审美意识形态”一词曾出现在1982年孔智光的文章中,“在我们看来,艺术的本质是审美的意识形态。”[1]1983年周波在回答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之所以是文学批评的客观标准时,也出现了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和形象性的艺术特点”的字样。[2]同时,钱中文在1982年提出“文艺是一种具有审美特征的意识形态”,[3]随后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又于1984年提出“审美反映”的概念。童庆炳也于同年强调“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大体说来,到了1980年代中期,“审美意识形态”的理论已经基本成形。[4]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直接源起上,对于它与新时期文论史的更为细密的关联性却重视不够,因而,揭示其他的间接源起原因,才能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时代产物的整体性生成特征,同时丰富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历史内涵与美学内涵。本文拟以新时期初的文学与政治关系论争为背景,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论者加以讨论,再现审美意识形态论生成的丰富肌理与复杂景观。丰富指其包含更多的理论可行性,复杂指其包含更为多样的理论目的。
一
徐中玉像众多学者一样,参与了新时期初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争。1979年第4期《上海文学》发表《为文艺正名》,很快引发了论争,他于1979年第11期《上海文学》上发表《文艺的本质特征是生活的形象表现——学习鲁迅对文艺性质、特征、任务、作用的看法》,虽然避免了直接的争论,但如其文章所标示的那样,“文艺的定义和全部本质是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个问题提得好,需要充分展开讨论。”可以看作是“正名”的一种理论努力。但从论述策略看,选择鲁迅作为切入点意在重读鲁迅,纠正将鲁迅纳入“工具论”的惯用做法。如王得后认为工具论是没有驳倒的,论据之一就是鲁迅说过文艺是宣传,文学与阶级性不可分,所以文艺应当是工具。[5]张居华在坚持工具说时,除引证毛泽东、周恩来、列宁、马克思、高尔基之外,鲁迅的言论也成为主要引证对象,突出鲁迅的“一切文艺,是宣传”的观点,认为鲁迅强调革命之所以“要用文艺者”,就因为文艺通过自己的形象化能够更好地服务于革命斗争,成为武器。[6]因此,在这样的论证里,鲁迅对于文艺特征的强调,只在表明文艺是一种特殊的工具,而非对于忽略文艺自身特征的提醒。如此一来,鲁迅也就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工具论者。所以,弄清鲁迅的思想实质,不仅是对鲁迅的真实还原,将被极左思想搞浑了的鲁迅研究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去,也能借此生发开来,透过鲁迅的论述研究文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将“正名”引发的对与错的一般性辩论,转换成为关于文艺本质的真正探索,弄清了后者,这既是“正名”理论延伸的需要,也是为从此不要再“正名”提供理论基础,由此才能开辟新的文论前景。
徐中玉在论述鲁迅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观点时,否认鲁迅是工具论的拥护者。首先,他承认鲁迅运用过“武器”、“工具”、“兵器”、“器械”等概念来说明文艺活动,但他认为鲁迅此时论及的是“革命文艺”的功能而非“文艺”的一般性质,“他这样说乃是在论述文艺与革命的关系,不是在为整个文艺下定义。”因而,我们不能用鲁迅关于“革命文艺”的功能的论述来界定“文艺”的一般性质,若这样做,那是犯了用个别性取代普遍性的错误。其次,徐中玉还证明鲁迅不仅是坚持“文艺”艺术规律的,即使在面对“革命文艺”时,他承认“革命文艺”有着工具的作用,却也同时认为不应忽略自身的艺术特征。鲁迅曾说:一切文艺都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都是文艺。在徐中玉看来,落实在后一句上,就反映了鲁迅反对“革命文艺”的先有“宣传”而缺乏艺术性,鲁迅说他对于只会发出议论的文艺作品,却总有些格格不入,就是明证。在徐中玉这里,鲁迅不仅与工具说者毫无相同之处,而且还是工具论的批判者,工具论者一直用来支撑自己的理论观点的一根重要理论支柱就这样被徐中玉抽空了。徐中玉明确反对工具说,他指出:
世界上时时有革命,却不会每时每刻都有革命。文学史上有革命文学,却不都是革命文学。对没有发生革命时候所产生的文学,以及即使产生在革命时代而缺乏革命内容但也不是反动的文学,就不能说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样的时代和这样的文学应该承认在历史上并不是非常短促和少量的。
最后一句,虽然语气上留有余地,但其策略明确,就是将工具说限制在革命文学之中加以讨论,且在这个范围之内,又加以艺术性的限制,从而使得工具论的论述只有极其有限的有效性。这不无道理。但除此而外,就一般的文艺而言,工具论就更加不起作用了。这是相当彻底的否定态度。
徐中玉将鲁迅所强调的文艺是时代人生的多方面的记录与不应忽略艺术技巧的观点相结合,形成了“文艺的本质是生活的形象的表现”这一重要观点:“人生无比丰富、复杂,形象地把它表现出来的方式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文艺的本质、特征都要求作者能够在作品里描写一切的人、阶级和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也就是说,只要生活里真实存在的,作者熟悉的,不管什么事情,什么材料,都可以写,应该写。而且还应该允许作者觉得怎样写有益就怎样写。”[7]尽管徐文还使用了“形象的反映”一词,但就其主导倾向而言,是强调“形象的表现”的,因此,可以将这篇文章看作是1970年代末,从反映论开始转向表现论的一个重要信号,这个信号因为文本中的反映与表现混合而有些模糊,但文本中对于表现的重视明显超过反映,模糊中也体现了一种新观点的诞生,突破正在积聚中。因此,当徐中玉在文本中将生活、形象、表现、真实、自由书写等结合在一起形成自己的论述空间时,这样的构成要素及表述方式,具有超乎寻常的理论力量,不仅是对工具论的否定,也是对反映论的游离,意味着在讨论文艺的性质时强调的重点已经从外在的(如革命、政治、阶级、社会等)转向内在的(表现、我想怎么写就写、形象等),从尊重文艺的客体属性转向了尊重文艺的主体创造,从强调文艺的被动性转向了强调文艺创造的主动性。这才是对工具论的彻底扬弃的开始。几年后,文论界出现了性格研究、主体研究、审美反映研究等,应该说,是接着往下、往深处说的。徐文是反对工具论中所达到了第一个清晰的表述状态,虽然是借用鲁迅的观点开拓自己的论述空间的,可其理论上的意义是应当高估的。
二
由“为文艺正名”引发的关于文艺是不是工具的论争很快演变成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争,这是深入。王若望介入了这场论争,而且成为论争的焦点之一。但王若望如果只是强调文学不能从属于政治而一般性地主张文学的独特性,那么他就缺乏深刻性。我认为王若望的贡献就是提出了“美学的反映”这样一个新命题:“文学艺术是社会现实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遵循美学的特殊规律进行反映的,而不能解释为只是政治的反映。”[8]王若望的理论根据是什么?是重新解读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观点,在确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前提后,认为构成意识形态的政治学说、哲学、宗教、文艺、艺术、法律、道德等等,都拥有自己的特殊规律、特殊功能和独特的表现形式,从而或比较直接,或比较曲折地反映经济基础的形态和变化。这样一来,王若望也就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角度强调了政治与文学的区别与平等,松开了文学对政治的依附。
王若望从两个方面论证了文学的独立性,一个是文学可以离开对于政治的依附而创造出杰出作品,如《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等就是例证。相反,依附于政治,却往往失败,如《死魂灵》的第二部、曹禺后期的创作等。一个是王若望在提出“美学的反映”的同时,首次大胆触及“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评价原则。这一原则是在从属论的思想背景下产生的,若是反对从属论而不反对这个第一、第二的划分,那是不彻底的。能够思考这个第一、第二的划分问题,意味着王若望的“美学的反映”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要落到实处,这个实处就是文学本身是自主的。为此,王若望认为喋喋不休地分析作品的政治意义的做法,常常忽略了作品中的艺术表现、美学成就等内涵,并且从文学接受的角度证明人民的喜爱艺术品,并非出于政治标准第一,而首先是从“艺术上是不是吸引人”出发的。这样一来,王若望就将文学的审美性提到了重要的位置上加以肯定,解构了第一与第二的位置划分,试图将二者统一与融合起来。这对于论证文学的创作与欣赏都是与文学的美学特征密切相关的,无疑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当然,王若望在提出了“美学的反映”后,并没有对何为“美学的规律”进行充分的证论,而是将其作为一个新的合理的预设加以运用,从而实行他对从属论的批判与否定。王若望部分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原因在于从属论本来就缺乏严密的逻辑支撑,尤其是与大量的文学史实相冲突,因此,只要从逻辑的与史实的层面稍加申论,从属论攻而即破是一种必然。王若望的“美学的反映”之“美学”力量的获得,从逻辑上说,是来自于意识形态各部门间的区别,这个区别是难以否认的,所以文学具有独特性;从实践上说,不从属于政治的创作比比皆是,且成功,何以文学非要从属于政治呢?事实支持了文学的独立性。除此而外,在王若望这里,“审美”如何靠着自身的内涵而确认自己,同时是如何否定从属论,并与其他的社会活动保持联系等至关重要的问题,根本没有获得重视。我认为王若望对于这个命题的论证是粗糙的,即没有对于这个命题的合理性、历史源起、逻辑内涵进行深入探索,还只停留在一种理论假想之上。但是,王若望提出这个命题,仍然是其理论想象能力的一种表征,能够引发随后二十余年间人们不断议论的一个中心话题即“审美反映论”,这本身就是一种贡献。
当钱中文、童庆炳等人将“美学的反映”转换成为“审美反映”时,他们更加自觉了,有关“审美反映”基本特征的分析才正式出现。钱中文于1982年提出了“文学审美反映生活的完整和丰富”问题,并同时提出“文艺是一种具有审美特征的意识形态”。[9]出发点也是在文学与政治、道德之间或者说在文学的美学分析与历史、社会分析之间寻找平衡点。其后,钱中文于1986年充分证论了审美反映的内涵,如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与语言、符号、形式相关,通过想象和幻想保持主体的主观性等。[10]童庆炳基于过去“把文学看成是政治的附庸和传声筒,忽视文学本身的独特的规律和审美特征”,又担心有人提出文学是“自我表现”,否定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提倡抽象的人性论,所以是两面作战,既反左也防右,既强调文学作为一般意识形态的特点,也强调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11]3他于1984年明确提出并界定了“审美反映”:“以人们的整体的、具有审美属性的社会生活作为反映的独特对象和内容,以艺术形象、特别是典型形象作为反映的独特的形式,而无论是文学独特对象、内容,还是由这种独特对象、内容所决定的反映的形式,都具有审美的特性,因此,对生活的审美反映是文学的基本特征。”[11]65概括地讲,童庆炳的“审美反映”论的基本意涵包括两个要点:其一,所反映的对象具有独特性,其二,所反映的形式是形象的。比较而言,钱中文与童庆炳关于审美反映的论述,更加系统更加成熟,但其基本内涵与王若望所寄望的是一致的,而且倡导审美反映的目的也是相近的,即反对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但追求的决不是文学的全然独立,而是努力重建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平等关系。从王若望的“美学的反映”到钱中文、童庆炳的“审美意识形态”、“审美反映”,其间一脉相承处是明显的。
三
刘纲纪在参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争时明确表态,“决不是要否认文艺同政治的密切关系,宣扬文艺脱离政治,不问政治,而是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和克服我们过去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所存在的片面性,以利于我们的文艺的发展。”刘纲纪的切入点主要不是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入手,而是转向从生活本身的多方面性入手,因此,他在申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命题时,鉴于生活的多方面性,认为文学的内容也应当是多方面的。这样的论述,结合事实立论,仍然具有说服力。“确认文艺所反映的生活内容,包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只限于阶级斗争。”所以,“文艺作为一种和其它社会意识形态不同的意识形态”,自有其内容上的独特性,不能与政治划等号。
刘纲纪在回归文学特征问题时,与王若望相似,谈的也是政治标准第一与艺术标准第二的合法性问题。刘纲纪认为从政治标准第一出发,形成了固定的认知模式,对那些政治正确的作品,哪怕艺术水平不高,也持肯定的态度;相反,一个作品一旦被判定政治错误,不管它的艺术水平有多高,也对它持否定态度。他提出了相反的看法,政治正确而艺术水平不高的作品,从艺术的角度看要加以否定;政治上错误而艺术水平很高的作品,从艺术的角度看应加以肯定。他的结论是:“我们对一定的文艺作品在政治上应取何种态度和在文艺批评上应如何评价它,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其实,刘纲纪主张的是政治的归政治,从政治的角度加以评判;艺术的归艺术,从艺术的角度加以评判。他从政治标准第一回归艺术批评就是进行艺术水平评价,在艺术水平的评价中,政治上的对或错没有什么重要性,所以,他已经将“文艺批评”与政治评判相当彻底地区分开来了,“文艺批评”执行的不是政治路线而是艺术路线,这条艺术路线就是遵照艺术的特有规律进行。这样斩钉截铁的态度,在刘纲纪之前还是不多见的,比起王若望来,更加细致与明确。
为此,刘纲纪提出了一部作品的评价包括三个步骤,从而导向了形式论的提出。第一步,判断作品在政治上的对与错,即使判断这个作品在政治上对了,这也不够,这既不能由此判定这作品在内容上就是科学的,也根本不能判定这个作品的艺术水平的高与低。第二步,接着还得判断这政治上对了的作品在思想上有无深刻性,是否揭示了生活的本质的新的方面,政治上对了的作品若没有思想上的深刻性,这政治上的对了也是空洞的。但即使这个作品具有了思想上的深刻性,这还不够,因为还不能由此确定作品的全部价值,思想的深刻性可以属于文学,也可以属于其他的人类认知活动。第三步,“还必须分析作品的形式”,将对作品的内容分析与形式分析统一起来,“这才能最终确定作品的价值”。“形式更是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艺术家不同于思想家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能够把某种思想表现在美的、动人的形式之中。”艺术作品的“价值的高低,密切地联系于它的形式的好坏。一部艺术作品,不论它的思想如何正确,如果形式拙劣不堪的话,作为艺术作品来看就没有什么价值可言。”[12]刘纲纪的全部证论引向没有形式“就没有什么价值可言”这一层,可见对于形式的重视已经超过对于内容的重视,这意在表明,文学的价值可以说是决定于政治的正确、思想的深刻,但最终还是决定于形式的好坏。形式不存,文学的价值不存。这样的结论,在今天看起来,没有什么惊人之处,可在当时,这就否定了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批评标准,将文学的价值与形式直接相关,并受其左右,也就不仅是重提文学的相对独立性,而是将这种相对独立性提到了不容否定的高度,此时的“相对”颇接近于“绝对”,“形式论”呼之若出。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形成真正的“形式论”还不具备条件,一者,西方形式论的美学观还受到普遍的抑制;二者,国内文论界还无法立即从批判形式论的思想习惯中走出来;三者,中国学者由于长期处于反形式论的语境与氛围中,还缺乏形式论的相关知识谱系来支撑他们创立一种全新的思考模式。刘纲纪的这种形式论只能是针对政治论的一种应对选择,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全新论证,不可能形成形式主义文论引进后全面探讨形式的重要性、否定内容决定论的认知局面。鉴于与后起的形式主义文论之间还存在着重要差异,我将刘纲纪的形式分析称作是新时期初中国文论中的形式论的初现。从偏向形式重要性的分析上来看,刘纲纪的形式分析与钱中文、童庆炳的审美分析是一致的,只是后来的两位学者比起刘纲纪来,更加注意将审美分析与历史、社会分析相结合,强调兼容性,但也抹平了刘纲纪形式分析中更加突出形式要素的认知棱角。从刘纲纪的关于形式论的不自觉的遐想到钱中文、童庆炳的主张审美意识形态论,形式论在新时期经历了第一场转折,忽现却又忽隐,要等到1980年代中期以后,借助西方形式主义文论的全面引进,才算卷土重来,开辟了新的理论空间。
四
我在上文的分析,是将徐中玉的“形象的表现”、王若望的“美学的反映”、刘纲纪的“形式分析”引向钱中文、童庆炳的“审美意识形态”,这当然是一条发展的路向,因为无论从思想背景还是理论思考的一致性言,上述观点都是相近的,所以,我说审美意识形态论是一个时代里多数学者相近思考下的共同思想产物,不能否定直接提出者的创造功绩,但正是因为有了前赴后继的创新追求,才有了这一理论成果。
但有没有另一种可能性呢?只将徐中玉、王若望、刘纲纪的上述思考整体地归入“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发展路径,我认为是对新时期文论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的一种削足适履式的剪切,而未看它的自由流溢与新变。因此,如果说在徐中玉、王若望、刘纲纪阶段上的有关文学独特性的思考还是比较一致的话,那么,1980年代后则出现了两种发展路向,一种是藕断丝连,一种是快刀斩乱麻。前者是钱中文式的,后者是刘再复式的,二者都保持了对于历史的关注,但关注点有所不同。钱中文式的关注相对抽象些,立论多从超越特定历史的角度出发,而特定时代的历史内涵只是作为历史片断出现在自己的论述中,所得结论未能引起更大的共鸣。而刘再复式的关注相对具体些,主要是从特定时代的历史内涵出发,其反思与立论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所得结论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刘再复在文论界普遍关注文学是什么的基础上,将其上升到了人是什么的高度加以认识,在他这里,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转变成人与政治的关系进行论述,结果,文学要不要依附于政治,变成了人要不要依附于政治。这是刨根究底。一旦人不再依附于政治了,文学当然也就不再依附于政治了,文学的独立性是由人的独立性来加以解释的。刘再复的这一思想集中在他的主体论上,“应当把人当作人,不应把人降低为物,降低为工具和傀儡,这种物本主义只会造成人物的枯死。也不应把人变成神,这实际上又把人变成理念的化身,这种神本主义必然剥夺人的丰富性。我相信,物本主义和神本主义只能把文学艺术引向末路。”[13]
就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而言,刘再复的解构是彻底的,他通过还人以主体地位,同时也就还文学、政治各自都有主体地位,人应当是自由独立的,政治与文学也应当是自由独立的。刘再复的主体论建构与文学的独特规律分析并非一回事,但既然已经证明文学是独立的,那么文学就应当具有自己的独特规律,所以,刘再复的主体论还是导向了文学的独立论,为讨论文学的独立问题提供了逻辑支撑。在文学的独立方面,刘再复更多地是从徐中玉、王若望、刘纲纪的一路直承下来的,比如他强调文学研究应当“由着重考察文学的外部规律向深入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转移”,过去的文学研究主要侧重于文学与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中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外部关系,现在应当转移到研究文学本身的审美特点、文学内部各要素的相互联系、文学各门类自身的结构方式和运动规律等内部规律上来。刘再复指出:
我们对文艺本质的看法,过去就单纯地从认识论和政治的角度来看,把文学看成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当然没有错,但是,过去仅仅允许用这个角度来规定文学的本质,这就不够全面。事实上,对文学本质的规定,还可从其他角度,例如,从哲学角度来看,可以说,文学是克服异化,使人暂时获得复归的一种手段;从价值学来看,可以说,文学是人的人格和思想情感的表现;从心理学来看,可以说,文学是苦闷和欢乐的象征,是人的内心情感活动的升华;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中,也可以说,它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只是暂时的);从审美的角度看,它是有缺陷的世界中的一种理想之光。[14]
结合刘再复引述及提出的概念有:情感性、非自觉性、变态、自身、内宇宙、内部规律、形式、人类精神本体学等概念,试图消解或颠覆阶级、政治、认识论、反映论、外部规律、工具、服务、线性的因果关系的单一作用,刘再复实际上运用了他当时所能掌握的各种知识,将它们糅合在一起,也许是生硬的,却用这样的丰富的但却有些异端的思想观念,向反映论、认识论发起了思想挑战。
当然,钱中文式的审美意识形态论做的是调和的工作,没有完成对于文学与政治的本质区别。[15]倒是刘再复借助主体论、又借用韦勒克的形式批评,具有了更大的可能性。但刘再复的观点胶着于主体论,哲学的意味更重一些,而文学的独特性在他的理论构架中却似一种副产品,这使他一直未能集中精力提出类似钱中文的“审美意识形态”与“审美反映”那类属于美学与文学领域的核心概念,他对文学独立性的认识更多地停留在呼吁的层面上,而非落实在理论建设的层面上。这要等到形式批评的千呼万唤始出来,才能将文学的审美性研究带向一个更高的层面。
参考文献:
[1] 孔智光. 试论艺术时空[J]. 文史哲,1982,(6).
[2] 周波. 试谈文学批评标准的客观性[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3,(6).
[3] 钱中文. 论人性共同形态描写及其评价问题[J]. 文学评论,1982,(6).
[4] 张亚骥. 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发生、发展及相关论争述评[J]. 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09,(1).
[5] 王得后. 给《上海文学》评论员的一封信[J]. 上海文学,1979,(6).
[6] 张居华. 坚持无产阶级的党的文学原则——“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不容否定[J]. 上海文学,1979,(7).
[7] 徐中玉. 文艺的本质特征是生活的形象表现——学习鲁迅对文艺性质、特征、任务、作用的看法[J].上海文学,1979,(11).
[8] 王若望.文艺与政治不是从属关系[J]. 文艺研究,1980,(1).
[9] 钱中文.人性的共同形态描写及其评价[J].文学评论,1982,(6).
[10] 钱中文.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也是最丰富的——论审美反映的创造性本质[J]. 文艺理论研究,1986,(4).
[11] 童庆炳.文学概论(上)[M].北京:红旗出版社,1984:3.
[12] 刘纲纪.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J].文学评论,1980,(2).
[13] 刘再复.性格组合论[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3.
[14] 刘再复.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近年来我国文学研究的若干发展动态[J].读书,1985,(2)(3).
[15] 刘锋杰.“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观点之质疑[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2).
责任编辑:凤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