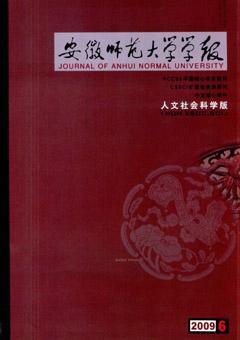新时期初文学的“去政治化”及其叙述策略
薛 雯
关键词: 新时期;去政治化;艺术特征;叙述策略
摘 要: 新时期初的文论界通过争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通过对“工具论”、“从属论”的反拨,形成了“去政治化”的思想认识倾向,围绕着对艺术特征、美学的规律的肯定,强调以生活至高论代替政治至上论,以广义政治论取代狭义政治论,从坚持他律论到坚持自律论,试图完成文学“去政治化”的理论建构。
中图分类号: I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09)06064306
De-politicization of Literature and Its Narrative Devices in Early Post-Cultural Revolution Era
XUE Wen (College of Printing and Art,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Key words: the Post-Cultural Revolution Era; de-politicization; artistic features; narrative device
Abstract: In the early Post-Cultural Revolution Era the circle of literary theories, through the disputes o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and the nullification of “instrumentalism of literature” and “subordination of literature”, developed a tendency of “de-politicization”. Centered on the recognition of artistic features and the rules of aesthetics, the circle emphasizes the substitution of “life paramount” for “politics paramount”, the replacement of politics in the narrow sense with politics in the broad sense, as well as the shift of other-discipline to self-discipline, in an attempt to realize the de-politicize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文论界将60年来的文学与政治论争概括为三个阶段:政治化阶段(1940年代到1970年代末)、去政治化阶段(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再政治化阶段(1990年代以来),尽管相关研究成果斐然,但如何深入到各个阶段中去寻找内在的发展脉络与肌理,却不够充分。本文以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即通常所说的“新时期初”有关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争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去政治化”的过程及叙述策略,为建构新的文学政治学提供一定的思想启示。
从“拨乱”到“反正”:肯定艺术特征
新时期初在认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时,首先经历了批判“四人帮”的“拨乱”而未“反正”的过程,紧接着出现的“为文艺正名”才是真正的“反正”,初步确认了文学的艺术特征,奠定了“去政治化”的第一块基石,为摆脱文学对于政治的依附提供了最初的理论说明。
有关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述,“文革”前形成了这样的观点:文艺必须服从政治,这是不可怀疑的历史规律与正确结论。许怀中在1962年以“最辩证、最彻底地解决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为标题论述毛泽东的《讲话》,指出:“‘五四运动到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前的二十三年间,由于进步的、革命的文艺理论家和作家的努力,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问题的探索,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做出了一定的历史贡献。到了毛主席《讲话》发表,这个问题就得到了真正的彻底的解决。”[1]许怀中虽然也主张“不能以艺术挤掉政治,也不能以政治代替艺术”,要反对“艺术即政治”、“政治即艺术”,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附属地位决定了它的基本特性与功能是为政治服务的,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里所使用的 “最辩证、最彻底” 词语,宣示这个问题的争论已经结束,只要按照这样的理论去办就万事大吉了。
随着“四人帮”的倒台,批判“四人帮”的文学控制成为一件大事。但客观地讲,人们维护的仍然是原有的文学政治观。如林思草既驳斥“四人帮”的论调,又维护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全盘肯定《讲话》的结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第一,文艺从属于政治,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与螺丝钉,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第二,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都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他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真正懂得怎样利用文艺武器为本阶级的政治服务”。[2]这篇文章,仍然沿用齿轮、螺丝钉、工具、武器、战线、服务等概念来定性文艺,与“文革”前的理论观点没有丝毫差别。这是“拨乱”而未“反正”,拨“四人帮”借“文学为政治服务”所造成的“乱”象,可又回到“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原命题,维护它的正当性。
“为文艺正名”的提出,才是正本清源的开始。1979年《上海文学》发表编辑部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3]将长期以来文学创作中的公式化与概念化的主因归结为“作者忽略了文学艺术自身的特征”,才信奉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是新时期文论中第一次明确强调文学艺术要有“自身特征”,反映了潜在的要自律的意识。这是真正的“拨乱反正”,“拨乱”不仅仅是拨“四人帮”将文艺作为阶级斗争工具之乱,而且也是拨一切将文艺作为阶级斗争工具之乱。“反正”要“反”到“文学艺术的基本特点,就在于它用具有审美意义的艺术形象去反映社会生活”。
《正名》对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说的否定是坚定的,公开声称它是一个“不科学的口号”:
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个提法,如果仅仅限制在指某一部分文艺作品(对象)所具有的某一种社会功能这个范围内,那么,它是合理的。如果把对象扩大,说全部文艺作品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文艺作品的全部功能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那么,原来合理就变成了歪理。“四人帮”的鬼把戏正在于:他们把一部分文艺作品所具有的某一种社会功能——“阶级斗争工具”,作为全部文艺的唯一功能来加以宣扬,从而把“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歪曲成了文艺的定义和全部本质,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文学艺术的特征。
《正名》一文关于文艺与真善美的分析,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是对过去扩大文学与政治关系论述领域思维习惯的限制与收缩。《正名》认为文艺要追求三种价值:“解决为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主要是为了求得真的价值;解决政治的关系,主要是求得善的价值。在真和善的基础上,还要解决内容和形式关系,这是为了求得美的价值。”既然认为真、善、美各司其职,那么,文学与政治的关联只是文学的一种价值,当然也就没有必要将其放大作为文艺的基本属性加以确认了。文艺是阶级的工具说,本来是以偏概全的,当然就不科学了。《正名》提出“用具有审美意义的艺术形象去反映社会生活”,在“艺术形象”之前再突出“审美”的制约作用,已经在不自觉中将文学的性质与审美直接相关联,这对于过去只从政治的角度来观察文学,是一次开拓。文学是政治的与文学是审美的,尽管不是两个无法关联的话题,但是以谁为主,仍然体现了对于文学本质的不同认识。当然,《正名》一文还没有对“审美”的内涵进行清晰界定,这还带有新时期初人们在认识文学审美本质时的过渡色彩,还比较粗糙。这要等到后起的主体论、心理批评与形式主义文论的引进与实践,才能获得更好的解决。
围绕《正名》一文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反对《正名》的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观点进行了辩护,主要有王得后的《给〈上海文学〉评论员的一封信》、吴世常的《“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个科学的口号》、张居华《坚持无产阶级的党的文学原则——“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不容否定》、曾繁仁《应该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理论》、李方平《真实性、公式化与文艺为阶级斗争服务——与〈为文艺正名〉商榷》等。坚持工具说的主要理由是:这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中推导出来的;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创作就带有阶级性,其完整的称谓应当说“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形象化的工具”;工具说与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样的创作弊端是脱离生活而引发的;不能因为“四人帮”利用过工具说就否定工具说等。其中“形象化的工具”一说,尽管突出了文学创作的“形象化”特征,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将文学视作“工具”的功利主义倾向。“形象化的工具”仍然只是“工具”,而只要身为“工具”,也就无法避免依附性。“形象化的工具”与“审美的艺术形象的反映”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是:前者保留了工具说的巨大影响,是对工具说的修补,文学本质上还是工具性的;后者突破工具说,试图重建文学的本质认识,文学本质上不是工具。
反对工具说的占有上风,主要的有顾经谭的《文学的发展与“为文艺正名”》、周宗岱的《“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个科学的口号吗?——驳吴世常同志》、邱明正的《一个不精确的口号——评“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罗竹风《文艺必须正名》、徐中玉《文艺的本质特征是生活的形象表现》等。这些文章主要思考了两个问题:工具说应当被否定,否定工具说后文艺的本质特征是什么。顾经谭认为:文艺产生在阶级社会以前,并在阶级社会消亡以后还得存在,怎么能够说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呢?“甚至在阶级社会中也不是以推动阶级斗争作为自己唯一的直接的功能。因此,不能以‘阶级斗争的工具之名来作为它的质的规定性。如果硬是用‘工具说来概括文艺的实质,那就未免名实两乖,以偏概全了!”[4]这与主张工具说的只在阶级社会的范围内讨论文艺的性质是不同的,它从文艺的起源与文艺的永存发展来看,视野开阔,结论的有效性也就大些。特别是顾经谭强调即使在阶级社会中,文艺与法律、政治也是不同的,它未必都是作为工具发生作用的。这与工具说针锋相对,涉及到了坚持工具说与否定工具说的根本分歧,主张工具说的基本上不谈文艺与政治、法律的根本区别,将它们混合在一起加以定性;而反对工具说的则抓住文艺与政治、法律等必然有区别立论,当然着重于它们的相异了。
由反对工具说形成的“艺术特征论”尽管突出与肯定了文学的自身规律,但总的看来,还缺乏对艺术特征的具体说明。虽然如上文所论述的那样,已经提到了“审美”,但还缺乏对“审美”的具体说明。因此,反对工具说的用文学应当具有“艺术特征”反对文学应当成为工具,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说明往往是有力的。但到底什么才是艺术的特征,却论述得极为模糊,这于认识文学本质特征没有什么大的帮助。
摆脱“从属论”:“美学的规律”的出现
到了1980年代初,文论界争论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评价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从属论”。否定“从属论”的,提出了“美的规律”问题,为文学的“去政治化”提供了文学之所以能够独立的理由。与此相关,文论界所使用的关键词汇,已经从反对工具说时的“形象”、“艺术的特征”、“特殊的意识形态”等转向“审美”、“情感”、“审美反映”等。文学的审美本质开始以一种近乎清晰的面貌呈现。
这一过程与邓小平有关。邓小平先是提出“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5]他指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发展利少害多。”同时强调:“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邓小平的观点中止了工具说,取代“从属论”,形成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口号,打开了文学本质论述的新空间,使得由“正名”阶段所提出的“艺术特征”的命题,可以向着更深刻的方面发展。
文论界在反思文学与政治关系时,王若望发表了《文艺与政治不是从属关系》一文[6],否定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基本观点。王若望并非认为文艺中没有政治,但文艺的反映政治,其实是通过反映生活而自然具有的。他以《红楼梦》为例,曹雪芹的现实主义创作,由于忠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形形色色之面,所以也反映了政治。因此,在这部称得上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的作品里,谈不到为政治服务,更谈不到从属于政治,但这部作品却处处表现了中国封建社会这个大的政治。他认为这样来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才是正确的。此外,他还结合《水浒传》、《西游记》、鲁迅的“遵命文学”、曹禺前后期创作变化、果戈理的《死魂灵》、巴尔扎克的世界观与现实主义的冲突等问题具体阐释了文学是不为政治服务的,结论是:文艺不是因为为政治服务才去写政治的,而是为了反映生活的真实性与全面性才去反映政治的。尤其是提出了文学对生活是从“美学的特殊规律进行反映的”,则表明了文学的活动是以自己的特有方式进行的,既建立在超越政治的生活基础之上,也建立在超越政治的“美学的规律”基础之上,文学之所以能够摆脱政治的束缚,就是因为它不需要政治的指导与制约,可以自由地活动。比较而言,王若望的这个“美学的特殊规律”,比起“正名”时的“审美的艺术形象”来,又有突破,这就是“特殊”一词终于出现。既然“特殊”,文艺当然就不必简单地服从政治、反映政治了,它有自己的活动规律,只有遵循这个自己的特殊的活动规律行事,文学创作才是正确的。王若望使用“美学的规律”这个词语,是马克思的“按照美的规律造型”的具体运用,这一点强化了他的论述。
朱捷反驳王若望的观点,主要论证了文艺与政治的相关性,“任何时代、任何作家的文艺活动,都或近或远,或明或暗地离不开当时的政治”。其论证的思路是:文艺不可能脱离政治,因为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政治,必然地会反映在文艺创作中。他在谈到文艺的特征时,强调的只是文艺的形象性。[7]朱捷的论证较为简单,比如所强调的“不脱离”,其实与“从属”概念不对等,不能说“不脱离”就是“从属”。“从属”是服从,是按照“主人”的意见做。不脱离是指二者有关联,但这种关联并不表明一者要服从于另一者。朱捷既认识到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某种弊病,又不想彻底放弃这个观点;看到了生活对于创作的重要性,却时时想用政治来加以限制;模糊地意识到文艺有自己的特殊性,但只能用形象性加以表述,找不到更为清晰、更为准确的界定方式。
与朱捷观点相近的还有吴世常、罗启业等。吴世常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在今天,主要就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就是在作品中要用马列主义思想去教育群众,以无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目的是要使无产阶级的思想真正成为‘统治地位的思想,使党的工作着重点顺利地转移到四化建设方面来,以日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试问象这样的为政治服务的文艺,它的路子会‘越走越窄”吗?”[8]罗启业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是应该继续坚持的基本原则。我们所讲的政治,绝不仅仅是指的阶级斗争;经济建设也是政治,‘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当前的最大政治”;‘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9]他们有时是在推演邓小平的相关说法,但由于未能接受邓小平对于“服务论”、“从属论”的明确否定,难以跳出僵化的认识框架,缺乏新意,难免是将对“服务论”、“从属论”的否定置换成对于“服务论”、“从属论”的肯定。
值得关注的是,从1982年起出现了“审美反映”与“审美意识形态”概念。尽管在“正名”阶段及否定从属论之际,出现了“审美”与“反映”的连用,但这样的连用是不自觉的,主要用意是强调反映具有审美特色,至于这种反映具有何种审美特色,这一审美特色具有何种内涵,都没有论及。可“审美反映”的提出则不同,它已经明确了“审美反映”不是一般的“反映”,而且指出了这一反映的审美特色到底是什么,因此,可以说,“审美反映”是“美学的规律”的具体化与深化,也是新时期以来有关文学与审美关系思考的新的理论结晶。“审美反映”论的突破有两个:其一,文学的审美特性不是仅指文学的形象特性,前者远比后者深刻与全面。用形象来规定文学,只是从一种较为外在的层面来规定文学,而从审美的角度规定文学,则是从本质的角度规定文学。其二,“审美反映”作为一种独特的反映形式,不同于逻辑的反映,前者是非认识的,是情感的,但可包含认识;后者是认识的,可以包含情感,但是理性的。正如童庆炳所指出的:
随着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我们批判了‘文革时期的文艺极端政治化和工具化的做法,并冲破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思想束缚,也从长期以来就规定的文学的特性是‘形象的单一理解中解放出来,特别是80年代初掀起的‘美学热的滚滚浪潮,使大家在讨论中逐渐形成了文学的特性是审美的共识。这就是说,审美是区别文学与非文学的根本特征。那么什么是审美呢?审美,最简明的概括,就是情感的评价。[10]
“审美反映”与“审美意识形态”的提出“确认了文学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应有的独立品格与自身规律”,称它是“新时期以来文论发展的最大成果之一”,是名实相副的。[11]这彻底结束了由工具说、从属论、反映论、认识论所构成的文学本质观,代之以由审美、情感、价值构成的新的文学本质观。
“去政治化”的三种叙述策略
经过论争,文论界中“去政治化”的倾向越来越鲜明,其中深入者大体通过以下三种叙述策略,提供了“去政治化”的可能性。
其一,强调以生活至高论代替政治至上论。政治至上论强调文艺创作必须服从与反映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即使描写其他的生活题材,也应突出政治的关键与核心地位,因此,创作总是应当流露出强烈而自觉的政治倾向,为一定的政治斗争服务。而生活至高论强调文艺创作首先要服从的是生活而非政治,认为强调文艺创作首先要服从政治需要的做法,不符合创作的实际与规律。张文勋指出:真实是艺术的生命。“文艺作品缺乏真实性,也就谈不上政治思想性和艺术性。”因此,“写真实,就是要从生活实际出发,要按照生活本来的面貌去反映生活。”在张文勋这里,创作从生活的真实出发,也要受到生活真实的检验,可谓起点是生活的真实,终点还是生活的真实,离开了生活的真实,就没有了艺术,那里还有艺术中的政治呢。[12]所以,写真实是文艺创作的第一原则,而文艺要反映政治则没有这么重要。李沛、王佐夫指出:文艺的内容是通过反映生活的多方面来实现的,比起政治来,这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文艺是以社会生活的整体作为自己的对象,它不光表现人们的政治生活,而且也表现经济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友谊、爱情、家庭生活等。它不只反映人们的阶级关系,也反映人的一切社会关系,包括人和自然的关系,表现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以及人类‘共同美的一些内容。”[13]虽然主张生活第一的论者大都强调政治是生活的中心或核心,起着主导作用,但主导作用毕竟不是唯一作用,所以,他们的论述就从突出政治转移到了突出生活上了。生活的重要性取代了政治的重要性,这对赋予文学创作以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
其二,强调以广义政治论取代狭义政治论。狭义政治指的是一个政党在一个特定阶段内的具体任务与政策方针。1950年代中,文论界提出了“写政策”、“赶任务”等口号,就是文艺服务于狭义政治的典型表现。过去强调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实际上强调的是为狭义的政治服务。这样一来,今天有什么样的任务与政策,文艺就得表现什么样的任务与政策。这使文艺创作疲于奔命。而广义政治指的是一个党、一个阶级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总任务与总追求,代表的是党与阶级的最大利益、最终利益。当时不少的论文都认为反映这样的政治,才是真正地反映了政治,才与人民群众的愿望与利益相一致。周扬在这一方面颇具代表性,他曾经是“写政策”的倡导者,虽然继续主张文艺不能与政治无关,但转而认为要扩大政治内涵:
文艺反映生活的真实就应当适合一个历史阶段的政治需要。在今天来说,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凡是有利于实现现代化的,又是能直接间接鼓舞人们献身于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都是为无产阶级所需要的,都是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的,而不应该把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狭隘地理解为仅仅是要求文艺作品配合当时当地的某项具体政策和某项具体政治任务。政治不能代替艺术。政治不等于艺术。[14]
周扬的观点破除了“狭义政治”观,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纳入服务政治的范围,显示了除阶级斗争之外,“只要真实地反映人民的需要和利益”,就是服务政治,影响政治,这是将政治概念人民化,将人民的利益崇高化,文学的政治化转变成文学的人民化。罗启业也有相关看法:“文艺为政治服务,不是要求文艺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为一定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服务,要求作家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鼓舞人们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前进。”[15]当“文学为政治服务”被“文学为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而取代时,狭义的政治也就失去了它的原有权威性,从而解放了文学创作的生产力。
其三,从坚持他律论到出现自律论。他律论即不从文艺自身来界定文艺的本质,而是通过对文艺与经济、政治等相关性来界定文艺本质与特性。这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理论基础,但在此时显然受到了挑战。张文勋指出:“我认为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的‘左的错误,根本危害在于它抹煞了文学艺术的特征,取消了文艺对于政治的相对独立性,违反了文艺的规律。”[12]尽管在确认文艺的独立性时用了“相对”二字加以限制,可能会造成歧义,但“独立性”这一概念的浮出中国文论界,已经是不小的进步。王若望在质疑“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时,从人民需要的角度强调群众接受艺术品,不是从政治标准出发而是从艺术标准出发的,“工艺美术品上的装饰画,一度都是画的学大寨,红旗飘飘或写的语录书法,对这样的政治标准,人民眼中并不把它列为‘第一,因为人民是从美学的角度选择美术工艺品的。”[6]王若望没有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主张二者水乳交融,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对于文艺的自身特性的忽略。这一时期,有学者引述别林斯基关于“艺术首先必须是艺术”的观点,将其视为马克思主义关于艺术不能等同于政治的思想来源,虽然有些对接不上,但这样的引用体现了回归文艺自身的企图。“别林斯基在《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中指出:‘毫无疑问,艺术首先必须是艺术,然后才能够是社会精神和倾向在特定时期中的表现。不管一首诗充满着怎样美好的思想,不管它多么强烈地反映着现代问题,可是如果里面没有诗歌,那么,它就不能够包含美好的思想和任何问题。我们所能看到的,充其量不过是执行得很坏的美好的企图而已。……破坏了艺术法则,是不可能不受到惩罚的。”[16]借用别林斯基间接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论证策略,想实现对于原有理论构架的突破与否定。此时出现的“审美反映”与“审美意识形态”等提法,已经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强调了文学的自身特性,是自律论的一个重要成果。
但我们认为,反对工具论、从属论的,大都着眼于文艺与政治间的不一致,并进而强调文艺对于政治的矛盾与冲突,证明文艺应当具有特殊性,但一般地讲,这样的看法还没有发展成为超越论,即认为文艺可以超越政治而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这只有等到主体论的出现,才能展示另一种理论生机。
参考文献:
[1] 许怀中.最辩证、最彻底地解决了政治的关系——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J].厦门大学学报,1962,(2).
[2] 林思草.文艺在革命中的地位是摆好了的——兼驳”“四人帮””歪曲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谬论[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79,(2).
[3] 本刊编辑部.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J].上海文学,1979,(4).
[4] 顾经谭.文学的发展与“文艺的正名”[J].上海文学,1979,(7).
[5]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J].文艺研究,1979,(4).
[6] 王若望.文艺与政治不是从属关系[J].文艺研究,1980,(1).
[7] 朱捷.文艺•政治•规律性——兼与王若望同志商榷[J].山西师大学报,1980,(2).
[8] 吴世常.试谈文艺与政治关系中的三个问题[J].上海师大学报,1980,(4).
[9] 罗启业.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的探讨[J].广西大学学报,1980,(2).
[10] 童庆炳.谈谈文学性[J].语文建设,2009,(3).
[11] 童庆炳.审美论—语言论—文化论:新时期30年文论发展轨迹[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8(4).
[12] 张文勋.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J].思想战线,1980,(1).
[13] 李沛,王佑夫.正确认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学习邓小平同志《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体会[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0,(00).
[14] 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周扬近作.北京:作家出版社,1985:8182.
[15] 罗启业.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的探讨[J].广西大学学报,1980,(2).
[16] 傅腾霄,刘秉书.试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J].阜阳师院学报,1982,(2).
责任编辑:凤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