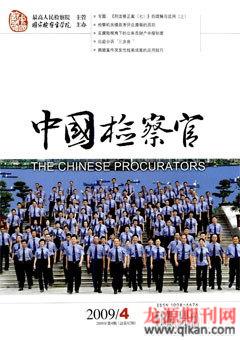斡旋受贿犯罪主体的扩张与界定
吴华清
我国《刑法》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这是对斡旋受贿犯罪的基本界定,在此基础上,新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又增加了两种斡旋受贿的类型:一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行为:二是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行为。这两种新类型的斡旋受贿行为与《刑法》原来规定的斡旋受贿相比,在“斡旋”与“受贿”这两个本来意义的行为表现形式和逻辑关系上没有区别,即都是“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然后“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但是在行为主体上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此次不仅仅限于国家工作人员,还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与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等五种。这样以来,构成斡旋受贿犯罪的主体就扩展为六种,很明显。从法律层面上,斡旋受贿主体呈扩张之势。对于这种扩张,其必要性问题以及如何操作目前在刑事法学界与实践部门已经引起广泛关注。其中的近亲属、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比较容易把握。而“关系密切的人”的界定却很困难。为此。本文拟从斡旋受贿犯罪主体扩张的背景、扩张的必要性、“关系密切的人”界定三个方面谈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斡旋受贿罪主体扩张的背景
毫无疑问,每个国家工作人员都生活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任何国家工作人员在这个社会中。除了因为职务行为存在大量的职权关系之外,尚存在大量的一般社会关系。比如血缘、亲属、朋友,乃至存在一些基于不正当欲求而产生的情感关系,从而就会形成职权关系之外的“关系圈”(身边人、身边人的身边人……),这是客观存在的、任何国家工作人员都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一旦这个“关系圈”的某些人。为了满足一些不正当需要或者实现某些不正当需求,必然要借助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及其地位。获取各种利益,从而最终导致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权钱交易。
从近年来我国纪检和检察机关查处的许多贿赂犯罪的实际案件来看。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的“身边人”,如配偶、子女、情人、有某些特殊关系的人参与作案的现象十分普遍。有些地方甚至发展到这些“身边人”可以左右国家工作人员的公务活动的程度,从而借此大肆索贿收贿。但是根据1997年《刑法》有关受贿罪的规定,包括斡旋受贿行为在内。受贿罪的主体仅限于国家工作人员本人,强调受贿只能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非国家工作人员不能单独构成本罪。因此,司法实践操作时,即使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这些“身边人”参与了贿赂犯罪,但司法机关充其量也只能将领导干部“身边人”作为受贿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2007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次用“特定关系人”这个术语来界定这些“关系圈”或者“身边人”,认为“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但该《意见》仍然是把“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的情况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为了适应新时期反腐败斗争的需要,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扩大了受贿的主体范围。该规定不仅设立了新的罪状,把非国家工作人员作为独立的斡旋受贿犯罪。而且也特别增设了“其他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这一全新概念。并明确了“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也构成受贿犯罪。很显然,这一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和与之关系密切的人的法律责任,扩大了反腐败的范围,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有利于国家工作人员廉洁奉公,正确地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同时。这一规定也是适应我国已经加入和批准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需要。
二、斡旋受贿罪主体扩张的必要性评析
《刑法修正案(七)》出台之前,刑法学界关于斡旋受贿犯罪的主体应否扩张,就已经存在否定与肯定的争论。否定的观点认为,斡旋受贿犯罪的主体只能限于国家工作人员。主要理由是:第一,斡旋受贿属于受贿犯罪,在刑法典中往往被置于渎职犯罪的范围,犯罪主体当然是国家工作人员或公务员。如果将犯罪主体扩大到非国家工作人员,犯罪性质就发生变化。因为非国家工作人员通过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而收受其财物,很难说是斡旋受贿。如果认为对这种行为需要定罪,那只能另行规定,另外确定罪名;第二,日、韩刑法规定的斡旋受贿罪。其犯罪主体均规定为公务员,可见,外国的立法例也说明《刑法》第388条关于犯罪主体的规定并无不妥;第三,《美国模范刑法典》规定的影响力之其它交易罪显然不是受贿犯罪,难以与斡旋受贿相提并论;如果认为这一规定值得借鉴,那就应当另外单独加以规定。而不必扩大斡旋受贿犯罪的主体,因为这无异取消斡旋受贿犯罪。
但是实践中,斡旋受贿的形式随着经济社会变革越来越复杂化,斡旋受贿犯罪主体扩张的呼声越来越大,为此,也出现很多肯定的观点。他们认为。首先,现行《刑法》将斡旋受贿犯罪的主体仅仅界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对于打击斡旋受贿行为是很有限的,在打击犯罪方面有很大的疏漏。而且纵观世界各国关于斡旋受贿的刑事立法,对斡旋受贿的主体规定也并不是仅仅局限于公务员。因此认为应将斡旋受贿行为的主体扩大,而不仅仅局限于国家工作人员。其次,无论是国家工作人员还是非国家工作人员斡旋受贿,都必然会侵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所不同的是,国家工作人员斡旋受贿既侵犯了本人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也侵犯了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而非国家工作人员斡旋受贿只是侵犯了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因此,如果一味地要求斡旋受贿犯罪的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则未免有放纵犯罪之嫌。
围绕斡旋受贿犯罪主体是否有扩张的必要,肯定的观点与否定的观点出于不同的论证角度,虽然也都引用了不同的外国立法例,但两者因追求的目的不同所以结论也完全相反。我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矛盾,其中一个基本逻辑就是扩张斡旋受贿犯罪主体的利弊权衡与选择的价值取向的不同。为方便评论,这里
先简要列举一下扩张斡旋受贿主体的利弊:从利的角度来看,扩张该犯罪主体无非是出于三个需要:一是,适应当前深入持续加强反腐倡廉工作的需要。特别是要加大对国家工作人员“身边人”的教育力度。充分发挥刑法规制的教育机能应该是扩张斡旋受贿犯罪主体的首要目的;二是,编织有效应对贿赂犯罪的严密法网,加大对贿赂犯罪的惩处力度,即充分发挥刑法的惩罚功能。这是扩张斡旋受贿主体的重要目的;三是。适应反腐败斗争的国际形势的需要。这是基于我国已经加入和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之后,如何使国内立法适应该《公约》的需要,但是这种需要并不是扩张斡旋受贿犯罪主体的必然结果。而只能是随附性的、形式性的要求。从弊的角度分析,当前扩张斡旋受贿主体至少面f临着三个现实的挑战:首先,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把握并量定“关系密切的人”的范围?由于这里的“关系密切的人”是非国家工作人员,他们存在的边界很宽泛。因此,要准备界定其范围,既涉及到司法资源的成本把握,又涉及到很重要的隐私权、名誉权等权利保护问题:其次,斡旋受贿犯罪主体扩张,打破了职务犯罪只能是身份犯(特殊主体)这一刑法传统理论界说,这是否意味着其他相关的职务犯罪也可以突破?最后,由于《刑法修正案(七)》把“关系密切的人”斡旋受贿行为作为独立的受贿犯罪类型处理,这样以来,该犯罪主体就转化为“关系密切的人”,那么,“关系密切的人”所依附的国家工作人员应该如何处理就成为又一个疑难问题,不处理显然不合目的,而处理了法律根据是什么?
对上述分析的利弊进行比对,我们可以看出,从严厉惩治腐败犯罪这个宏观角度看待,扩张斡旋受贿犯罪主体无可厚非,但从刑法理论体系与刑事司法操作角度来说,这种主体扩张确也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深入权衡利弊,我认为,要真正贯彻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我们必须慎重把握“关系密切的人”的范围,尽量做到收缩该罪的“犯罪圈”,能不扩大范围的尽量不要扩大范围。以彰显刑法的谦抑性基本思想。
三、如何界定“关系密切的人”
由于《刑法修正案(七)》第一次提出这个概念,在此之前刑法理论也没有进行研究,因此,如何把握“关系密切的人”的范围成为当前的疑难问题。全国人大办公厅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法工委负责人郎胜解释说,“关系密切的人”,有的是国家工作人员身边的工作人员,或者是与他有特殊的关系。这些关系非常密切的人。有些源自于曾经是同学、曾经是老乡、曾经过从甚密等等。这些人在社会上利用与国家公务人员的某些特定关系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索取贿赂,这也是一种腐败现象,也是对公共权利的侵蚀……在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举行的“《刑法修正案(七)》座谈会”上,著名刑法学家王作富教授对此概念进行了详细解析,先生认为这里的“关系密切的人”很难从条文上具体化规定,从近年来发生的实际案件来看,这个条文主要针对的是一些国家工作人员所谓的“情人”、“情妇(夫)”等而言。为更明确说明这个概念的外延,先生把“关系密切的人”概括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男女双方存在着不正常或者正常的情感关系,表现亲密,超出一般同志关系的人;第二种是近亲属之外的亲戚朋友,因为双方存在共同利益关系从而形成了密切关系的人:第三种是因为情趣相投而形成密切关系的人。如酒友、棋友、牌友、票友、旅友等等。这个概括立足于我国斡旋受贿犯罪发展的基本历程,比较全面系统地描述了当前能够影响国家工作人员权钱交易的各种社会关系情况。应该是相当权威的论证。
笔者认为。如果仅仅从国家工作人员和非国家工作人员两者之间的“形式关系”去认定是否属于关系密切,既无法识别。更无从测量。要准确界定“关系密切的人”,必须引入或者求证一个客观的事实,以此作为认定的依据,这个客观事实就是“关系密切的事实”。所谓“关系密切的事实”,是指能够证明国家工作人员和非国家工作人员两者之间存在着从事公务活动之外的交往活动的事实,而且这些交往活动足以能够表明两者之间超出普通社会群体之间关系。概括而言,我认为,应该把王作富先生的概括进一步转化为下列具体事实,这些事实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能够证明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存在特别情感关系的事实。这些事实一般表现为长期同居、多次幽会、曾经相恋等等;二是。能够证明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存在共同利益关系的事实,比如共同投资企业、共同参与融资、理财、股票、期货投资等等活动;三是,能够证明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存在共同情趣,且已经形成亲密关系的事实。比如两者之间经常性的一起从事酗酒、打牌、品戏、钓鱼等等休闲活动,从而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共同情趣。
至于实践中到底应该如何适用。毫无疑问,还要依靠“两高”尽快予以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在司法解释没有出台之前,只能要求司法机关根据案件的事实特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