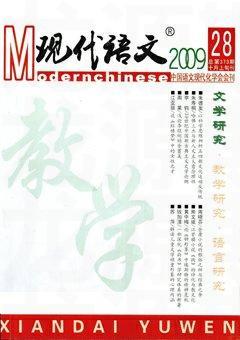模糊的男主角
摘 要:曹禺的《雷雨》是中国现代话剧中演出及研究最多的作品,充分显示出作者的创作个性。周萍是《雷雨》中在评价上分歧较大、认识上较为模糊的一个人物,本文试图从周萍的角色定位、形象塑造、命运发展等方面来探索这一人物的塑造。
关键词:曹禺 《雷雨》 周萍 人物
曹禺是一个感受型、直觉型的艺术家,他的一切形而上的思考都体现在鲜活的人物形象上。通过他笔下的人物,我们可发现他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就人物塑造而言,《雷雨》中八个角色,个个是复杂丰满的立体形象,但我们仍可大略地用一句话概括其中七个角色的主要欲望和倾向——周朴园是秩序,繁漪是爱情,侍萍是安全,四凤是归宿,大海是正义,鲁贵是金钱,周冲是理想,只有面对周萍,我们一时语塞。笔者试从周萍的角色定位、形象塑造、命运发展等方面来初步探索这一人物的塑造。
一、角色定位的焦点性
关于周萍角色定位的焦点性问题,可以先从线索谈起。对于《雷雨》一剧戏剧冲突的主线索,大致有三种看法,一是繁漪与周朴园的冲突;二是侍萍与周朴园的冲突;三是繁漪与周萍的冲突。[1]笔者认为第三种看法最合适。以介绍人物,引出主要矛盾为目的第一幕是这样安排的:一开场鲁贵和四凤的谈话,就点出她和大少爷的交往,来找矿主的鲁大海也诅咒那躺在花园像是“要死的大少爷”。鲁贵叙述了“闹鬼”的故事之后,繁漪登场,没说几句话,即向四凤打听“他”的情况。天真的周冲向母亲讲完自己的“梦”后,突然也提到哥哥近来讲的“许多我不大明白的话”。层层铺垫之后,周萍上场,紧接的三段戏,一场比一场紧张:首先当着周冲,繁漪话中有话,句句紧逼,周萍躲躲闪闪,步步退让;然后周朴园登场,逼繁漪喝药的全部压力,最终落在周萍那一跪之上;最后是周朴园对周萍的盘问,观众和周萍都在他与繁漪关系泄露的错觉中,惶恐地虚惊一场。整个第一幕,围绕周萍与繁漪过去的关系及和四凤现在的交往,完成全剧最主要悬念的构设。再来看剧情的进展:对这个时间跨度长、人物关系复杂的剧作,作者采取的是以“现在的戏剧”带动“过去的戏剧”的手法。“现在的戏剧”是周萍与四凤交往并准备离家,“过去的戏剧”有两个,一是3年前周萍与繁漪的私情;二是30年前周朴园与侍萍的旧事。不甘被弃的繁漪为挽留周萍,无意中引爆了30年前的往事,揭穿周萍是周朴园与侍萍之子这一秘密,是全剧高潮所在,将剧中三组主要冲突(周朴园与侍萍、周朴园与繁漪、繁漪与周萍)纠结重合在周萍身上,并导致悲剧结局的迅速出现。可见,从开端看悬念,从进程看发展,从高潮看统一,我们都可确认,周萍始终处于剧情冲突主线的焦点上。
作者自述他写《雷雨》是受到了“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的“诱惑”[2],他最先写出的片段,恰好是扣题的“雷”与“雨”两场。四凤在轰轰雷声中跪地发誓不见周家人的面;繁漪在窗外暴雨中凝视四凤、周萍的死尸般的身影。再写周朴园逼着繁漪吃药的那一场,再跟着写的是鲁妈和周萍相认的场面。在以上“戏眼”中,周萍均处于冲突焦点,构成《雷雨》情节支架的五重三角性爱关系(周冲——四凤——周萍;四凤——周萍——繁漪;周萍——繁漪——周朴园;繁漪——周朴园——侍萍;周朴园——侍萍——鲁贵)和一个秘密(周萍身世)都已见端倪。显然,在作者创作构思和写作冲动中,周萍也处于核心位置,他应该属于逗起作者兴趣的“几个人物”之一。
二、形象塑造的矛盾性
在《雷雨》的观赏评价中,周萍一直被冷落。他不像繁漪、侍萍、四凤、周冲那样广博人们同情,也不像周朴园、鲁贵那样遭到人们普遍憎恶,他给人的感觉是暖昧的、模糊的,许多人甚至不承认他属于悲剧人物。朱栋霖等研究者在正确指出周萍与繁漪的冲突是《雷雨》主线索的同时,更多强调的是“周萍在戏剧结构中的重要性”。着眼于性格分析的长篇论文《繁漪与周萍》中,论及周萍的文字仅占四分之一,往往是为了给繁漪提供参照。最耐人寻味的是作者的态度。初版序言中作者强调“演他的人要设法替他找同情”。1978年接受采访时却说“周萍这个人物太混帐,太卑鄙了。活该这个人,对他的‘坏要让观众慢慢觉得才好”。[3]周萍是新旧版本中改动最大的人物,仅从人物介绍来看,初版长达3页、1500多字,为全剧人物介绍之冠。以后各版大量删削,1951年开明版仅有区区一行半,成为人物介绍中最少的。如果说以上变动不无时代、社会政治等因素的外在影响,初版对周萍这一形象说明上的潜在分歧,也许更能显示作者的内在矛盾。
作者在初版序言中曾说“‘极端和‘矛盾是《雷雨》蒸热的氛围里两种自然的基调,剧情的调整多半以它们为转移”。[4]他明确指出,繁漪是“极端”的代表,而周萍是“情感和矛盾的奴隶”。这种以二人性格基调调整剧情的说法,和前面从结构角度将二人冲突作为戏剧主线的分析相符。正如作者所介绍的,他身上有“慧”、有“蛮”,但现在已成为“美丽的空形”。他有冲动的激情和决绝的勇气,但紧接着是无旁无尽的“悔”;他一再触犯禁忌,而他是有道德观念的;他似乎绝情绝意,但他又是“有情爱的”;他赌钱酗酒,“精神颓丧,永远成了不安定的神情”,“同时又是渴望着生活”。痛苦焦灼、不得其所使他不仅佩服、景仰“模范市民”、“模范家长”的父亲,甚至羡慕没有顾虑、敢于做坏事而心安理得的鲁贵。对这个人物,我们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似乎只能是“矛盾”。
三、命运发展的悲剧性
首先,我们谈谈周萍的命运成因。自《雷雨》始,对周萍类男性主角悲剧性命运的探索,贯穿曹禺整个创作。从周萍、方达生、仇虎(包括焦大星)到曾文清,都有着萎缩、怯弱、无聊、空虚的精神特征。他们都陷于一种“周萍式困境”——挣扎于两个女性之间,感情倾向于幼者、弱者,又时时摆脱不了母性强悍女子的控制,这是些长不大的,永远不能自立的孩子,是由于未能正常享受母爱因而永远不能从潜在恋母情结阴影中走出的儿子。周萍本来并不缺乏年轻人的激情,也不满父亲的专横,正是这一点使他赢得了繁漪的爱情、周冲的敬重。然而他“性格上那些粗涩的渣渣经过了教育、提炼,成为精细而优美了”,因此,“在他灰暗的眼神里,你看见了不定、犹疑、怯弱同矛盾”[5]。对繁漪的疏离是他“蛮力”销蚀的表现。半是慑于父亲的威严和所谓道德谴责,半是为着厌倦,他转向单纯善良的四凤;而对一心一意指望他的四凤,他也怯于门第观念不敢负起责任。在无法解决的重重矛盾中,最终只能发出“我够了,我是活厌了的人”的哀叹,饮弹而亡。
周萍被攻击最多的是他对周朴园的唯命是从、甘当孝子,以及对繁漪颇承父范的始乱终弃。前者从意识形态角度,后者从社会伦理层面,决定了周萍形象的否定性因素。周萍在由乱伦带来的巨大恐慌和无从建立生活准则的焦灼之下,确实表现出对传统秩序的复归。然而他对周朴园的谦恭,更多是罪犯在审判者面前的畏缩,是失足子辈对“倔强”“冷酷”“无暇”父辈的顺从,并不能完全看成对其价值观的认同,正如他死死抓住由“下等人女儿”四凤带来的生机,并不说明他对劳动者身份的尊重。与周朴园为门第抛弃侍萍不同,周萍和繁漪关系中的不自然因素,使我们即使责备他“始乱”,也很难要求他“终继”。周萍一次次拼命挣扎,一次比一次掉进更探的泥淖,当发现最后只是饮鸩止渴时,他只留下一句话“爸,您不该生我!”,周萍的悲剧性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他的遭际集中体现了作者痛感的“宇宙是一口残酷的井,人类在无望的挣扎”[6]的命题,作者在“序”中还明确指出:“天地间的‘残忍,这种自然的‘冷酷,可以用四凤与周萍的遭遇和他们的死亡来解释,因为他们自己并无过错。”[7]作者显然无意指责周萍,但对这个角色却有一种特殊嫌恶。作为一个贯穿全剧的重要角色,作者始终没有给过周萍展示内心的抒情、独白机会。(可对比《雷雨》中深夜独处的周朴园和《日出》中破产后的潘月亭的处理)放弃这个最易使观众体察人物内心并获取同情的手段,无疑使观众很难认同角色。
面对繁漪的一次次冲击,周萍反复重申的则是:“你是冲弟弟的母亲”,“我是我父亲的儿子”。这里,作者揭示出作为社会人的一种永恒的窘况。男子首先视自己为一个社会人,他需要被社会定义,否则就无以确认和自立。他们反抗秩序往往只是为了进入秩序,他们不能无所羁绊,他们总要有所依凭。这是周萍们的真实处境,也是软弱、妥协性格形成的根本原因。众所周知,曹禺笔下人物多有原型,作者自己对许多重要角色的来源都作过解释,对周萍一角却始终保持沉默。这个人物,总令人联想到作家自我。作者偏爱火光电闪一样热烈极端的性格,对自己怯懦矛盾的性格又苦恼终身难以摆脱。曹禺笔下的男性主角们,承担着他真实的生命体验和现实思考,他在现实中无法超越的东西,他的男主人公们也止步于斯。他们身上不仅带着作者自己的性格痕迹,还体现着作者对人类有关权利、义务,欲望、责任,自由、规范等两难命题的悲剧性思考。
其次,谈谈周萍的命运发展轨迹。关于周萍性格的解说,将近1500字之多,就可见作者对它所知道的部分,是到了“细微之极的程度”[8]了。其中,他不仅展示了周萍命运发展的“现在时”,还给出了周萍的“过去时”并揭示了将来可能的发展。他此后的创作几乎不自觉地苦苦追索着周萍的命运,构塑了青年男性的“周萍系列”,探索了他可能的各种命运和发展,在《日出》中,我们可以看到周萍的“过去时”——方达生,那个“有亮而黑的眉毛,有厚的耳垂,粗大的手掌,乍一看有些慧气的”刚进城的“乡下人”[9]。他比陷人罗网的周萍更执着地“永远在心头活着”,他碰到的是已冲出家门不肯诱惑他的陈白露,他还有勇气去救助孤女小东西而不是向一个少女寻求救赎。虽然作者解嘲了这个书呆子理想的空泛性,但只是在这个有着似是而非光明结局的追逐者身上,作者认可有自己的影子。在《原野》中,我们可以看到周萍的“现在时”——仇虎,是生存于旷野还未进入城市的周萍。他集中代表了作者所理想的、灌注全部原始生命力强悍的男子形象。在这里,那“炼钢熔铁”的“原始蛮力”实体化了,仇虎的冷酷嗜血,他的快意复仇,对情欲的沉溺与豪放,处于一种生命的本真状态。然而,当完成复仇赢得爱情进人黑森林之后,他也被吞噬周萍野性的魔鬼——道德评判、良心审视追上。他不甘地听命着心底酣畅淋漓满足欲望的呼唤“渴、渴”,“哪儿有水!——哦,我拿一桶金子换一桶水!”[10]同时脑中眼前又浮现出摄人心魄的幻象,面对面前的水,他喝不到口,也像周萍那样,“如老鼠僵立不动”。强悍如仇虎,虽然是不无英武地倒下了,毕竟选择了和周萍同样自绝的路。到了“将来时”曾文清那儿,周萍已完全蜕化为“生命的空壳”,他连爱的心力都没有了,只想有个人不远不近,不即不离,在相对无言的沉默中,品味一丝爱意和慰藉。他早已失去“生命的渴”,只剩下把盏浅尝的慵怠懒散,靠一种精致的外壳维系着中空的生活表象。周萍出走未遂,还留下一个欲行未果、被命运阻断的背影;文清却是走成了的周萍,结果“飞不动”又回来,再也无法自欺欺人,像耗子那样寄生地活着,只好如耗子一样卑微无息地死去。周萍的命运发展轨迹基本代表了曹禺的青年男性形象,性格特点从强悍走向懦弱、行为方式从极端走向矛盾、人生态度从生命的渴(充满原始活力朝气)到生命的空壳(如卑琐寄生的老鼠)的发展轨迹。
对周萍,作者似乎写得不够放达,其实他来自曹禺心灵最深处。正如作者赋予周萍的最主要特征是矛盾,这个形象的塑造也体现了作者的矛盾心理,他显然在隐藏自己和表现自己之间,暴露出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憎恶与挚爱,造成观众审美鉴赏和道德评判中较多分歧。以上一些肤浅的探索,期望能还原一个较为清晰的周萍。
注释:
[1]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第275页。
[2]曹禺:《曹禺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15页。
[3][4][5][6][7]曹禺:《雷雨·序》,《曹禺文集》(一),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第17页,第53页,第212页,第212页。
[8]曹禺:《雷雨的写作》,《曹禺全集》(五),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
[9][10]曹禺:《曹禺文集》(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125,第212页。
(宋建军 江苏省无锡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214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