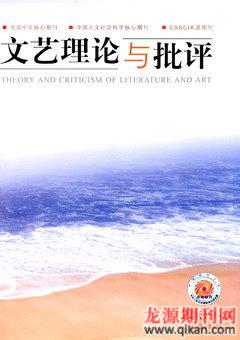兵戈沸处同国忧
付艳霞
作为宗璞先生鸿篇巨制《野葫芦引》的第3卷,《西征记》的出版让所有满怀期待的读者松了一口气。病痛和写作又斗争了近十年,最终又一次在精神的傲岸面前黯然。从1987年的《南渡记》,到2000年的《东藏记》,再到2009年的《西征记》,20多年间,宗璞先生要在葫芦里装宇宙的“痴心肠”虽百折而未悔。她“同国忧”的“秃笔”在“西征”的时候,变得更为雄健和刚毅,她笔下的知识分子担当国家和民族大义的情怀更为深沉和热烈。从风格、内容上而言,如果说《南渡记》饱含初尝抛别北平的忧伤,《东藏记》侧重偏安昆明的世情与浪漫的话,《西征记》则直接描写了抗日正面战场的悲壮与豪情。
宗璞说:“个人的记忆是会模糊的,但一个民族的记忆我们有责任让它鲜明。用小说的形式来留住历史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作为“以小说写历史”的重要一环,《西征记》要写抗战最为艰难的时刻,也要写到内战爆发前夜的矛盾纠葛,因而必然要正面涉及战争。这对擅长以优雅笔触描摹知识分子世情命运的宗璞而言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又未尝不是了却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童年因为日军侵略而颠沛流离的记忆,几乎覆盖了她的一生,甚至决心创作《野葫芦引》也是因为这样的记忆缠绕。战场必须要写,怎么写?这应该可以算作阅读和评价《西征记》的一个重要的“眼”。
以人物统领材料的叙事策略
宗璞的同胞兄长曾是远征军,多次向宗璞讲战地经历和见闻,宗璞也曾亲身到云南腾冲去寻找战地遗迹,查访战斗故事。而有关盟军对中国抗战的援助,滇缅公路作为抗日输血管的修建和运输情况,云南当地的土司对抗战的支援,发生在西南大后方的著名战役,如同古保卫战等史料都化身在小说中。《西征记》在宽阔的历史背景上,始终活跃着让人心荡神驰的人物。尽管她不熟悉战地,不熟悉知识分子以外的人群,不擅长写大场面、大冲突,但这些资料和史料的准备多少弥补了她的不足。她所擅长的依然是塑造人物,勾勒人物性格的新变化,描摹大背景中的世情。因而,她采取的叙述策略是以人物带材料,正如她在书的后记里写的:“材料是死的,而人是活的。用人物统领材料,将材料化解,再抟再炼再调和,就会产生新东西。掌握炼丹真火的是人物,而不是事件。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烛照全书,一切就会活起来了。”
小说以触目惊心的征调标语开篇,“这是你的战争!”以责无旁贷的敦促和提醒,使小说中的人物和读者同时进入了“战不我待”的全民抗战状态。历史的重任落在了澹台玮和孟灵己这一代青年学生肩上。上不上前线,是西南联大的学生需要做出的选择。有人选择了民族大义,如澹台玮、孟灵己;有人选择了继续求学,为未来民族的发展积蓄力量,如庄无因;也有人选择个人安危和个人前途,如蒋文长。
而带动材料的主要力量,还是澹台玮和孟灵己。澹台玮做了盟军的翻译,并最终牺牲在战场上。孟灵己做了战地医疗志愿者,还在关键的时刻充当了当地农民的心理医生,说服土司支持抗日的说客。最终她经受了战火的考验,也直接分享了抗战胜利的狂喜。两个主要人物都已经由不谙世事的少年变成了有主见、担当民族大义的青年。小说通过两个人在战场上的见闻,描写了滇西远征军的战斗,描写了盟军对抗战的支持,描写了战略物资腐败案,也写到了农民、土司对抗战的支持。虽然,个别地方阅读起来像史料报道,但因为两个主要人物统领了滇西战场的故事发展,并没有特别影响阅读。更何况,在描写每一个战地故事的时候,作者也注意塑造人物,修筑滇缅公路的老战一家,不知名的孤儿女兵等等。这些人物在材料里熠熠发光,让人印象深刻。
英雄慷慨与侠义传奇的美学风格
尽管上述的叙述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弥合了宗璞在题材内容上的优势和劣势之间的鸿沟,但从阅读的角度看,两方面的差异依然明显。凡是涉及到知识分子内心世界、普通人物人伦世情的情节,都显得圆熟而有吸引力。与《南渡记》和《东藏记》相比,《西征记》的英雄慷慨是题中应有之意。而似乎是为了与战场的豪迈慷慨相辉映,《西征记》里亦颇多了一些侠义传奇的情节描写。
在《东藏记》中因打了败仗而赋闲在家的严亮祖,在《西征记》中重上战场。抗战胜利,内战却爆发在即。面对前来劝其和平起义的共产党,何去何从,严亮祖的选择了然于胸。与《南渡记》中从容自杀的吕非清相比,严亮祖用传统武功自杀显然更悲壮、更惨烈。吕非清对抗的毕竟是异族入侵的奇耻大辱,而严亮祖是为了避免“相煎何太急”的内战。生灵涂炭的战争在外辱消失之后依然要继续,这显然对所有的人都是难以接受的事实,因而所有的人都表现出了慷慨激昂的一面,教授江防自不必说,连孟弗之也在国民政府的暗杀面前慷慨陈词。
荷珠这个人物的死也颇有侠骨柔情。这个放蛊的姨太太,颇有山野女子的古灵精怪和心机门道,在《东藏记》中,每次出场都带着压抑素初母女的娇蛮和霸气,显得不那么可爱。然而,在严亮祖棺前自尽的选择,仿佛一道横空出世的闪电,一下子提升了她的人格光亮。“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她的死固然可以理解为蒙昧女人对丈夫无条件的追随,但同时,这未必不是一个普通女子对不可预测的未来之路的恐惧和抗争。严亮祖和荷珠的侠义赴死之中,体现了另外一种对民族大义的坚持和担当。
传统文化视野下的现实情怀
研究者对宗璞小说中的传统底蕴,对宗璞的创作追求多有论述。“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无为”而“有为”的辩证,悲悯和宽恕一切等等,都在小说的不同人物身上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而作者塑造这些人物的内在底里,显然在于她积极的文学观和人生观,在于她对现实的体恤和打量,在于她温热的内心和宽厚深沉的人生体察。
两代知识分子这些主要人物自不必说,让人印象最为深刻也最值得一提的是吕香阁。这个人物自从在《南渡记》中一出场,就是一个颇有心计的人,作者说,连她的眼神都是两层。在《东藏记》中,她在昆明的聪明、市侩、周旋和算计就体现得更为明显。在《西征记》中,她甚至可以用冷血来形容。严亮祖和荷珠自杀辞世,素初出家,剩下颖书、慧书两个孩子,境况可谓凄惨,然而吕香阁此时的第一反应,却是代卖严家留下的东西能赚多少钱。这样一个甚至令人生厌的人,作者给予的是冷静的描摹和骨子里的宽容。在宗璞笔下,凌雪妍、仉欣雷、澹台玮等这些美丽单纯的生命都猝然逝去,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叹惋和遗憾,然而对香阁的命运如此处理,真是引人深思。
无论宗璞在写什么,怎么写,都始终有一个关注世态人心的现实情怀。而且是一种积极的情怀。这种情怀是建立在传统文化底蕴支撑下的现实关怀,是一种“云在青天水在瓶”的境界,是参透了人生局限和苦难,尝遍了生离和死别,见证了毁灭和新生的胸怀。宗璞一贯“诚、雅”兼修,而评论界将其定位为“兰气息,玉精神”。
正如作家张抗抗在《宗璞先生的韧性写作》一文中写到的那样:“在她的作品中,始终可见其对社会的批判意识、对人性的剖析、对人格力量的褒扬。她从不回避社会矛盾,从未停止过思考,她内心深处鲜明的爱憎,以文学的方式,曲折含蓄地得以传达,其中潜藏着她的人文关怀和思想追求,并至今默默持守。宗璞先生内心的道义担当,使她的写作之路,成为文学的韧性之旅。”
宗璞的意义与价值
宗璞在当下文坛中的意义与价值,固然与其家学渊源、传统滋养、人生经历和所处环境等因素密不可分。然而,单纯这些因素显然不能成就一个作家,更不能让一个作家保持持久的、与鲜活的现实紧密相关的创作生命力。宗璞在《西征记》里写远征军的抗战,题材是早就定好的,但发表的年份正值《我的团长我的团》热播。宗璞写到的人性善与恶、美与丑都可以让人在阅读的过程中忽略历史背景和特殊境遇,而仿佛能够和当下的各色人等对号入座。而且,2008年,在创造鸿篇巨制的同时,她还发表了四篇“新笔记小说”:《恍惚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有商界成功人士、普通打工者、失业的白领。书斋里的作家始终不忘新鲜的现实,又常常能够在司空见惯的现实中发现生活和人性的永恒。老作家遇到的新现实,没有“倚老卖老”,没有“不懂装懂”。这或许是宗璞在当下的文学环境中最值得称道的意义和价值。这一点,只需看一些有一定的历史经历的作家的近作和表现,境界高下可不辨自明。
读《西征记》,重读《南渡记》、《东藏记》,感受到了久违的文学美感和文学精神的滋养。阅读当下的很多小说,已经很难找到这种“美学的和历史的”文学精神了。如今,下一个期待已然开始,“北归”,显然依旧会是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舞台,他们的道路选择,他们的未来,将在内战中的北平城徐徐展开。而此时,重读宗璞先生的《自度曲》,或许可以更深地理解前三记,可以更期待《北归记》。
“人道是锦心绣口,怎知我从来病骨难承受。兵戈沸处同国忧。覆雨翻云,不甘低首,托破钵随缘走。悠悠!造几座海市蜃楼,饮几杯糊涂酒。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只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