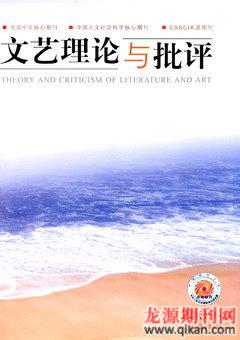《潜伏》的结局到底想说什么
秦喜清
一、令人崩溃的结局
看过《潜伏》的人,对之无不交口称赞,受“内伤”者有之,“中毒”者不在少数,挑灯夜观、欲罢不能的,更是占《潜伏》观众的大多数。这部电视剧,情节构思细密、严谨,情感表达浪漫、深邃,它调动着观者的智力参与和情感投入,同时,它以隐而不露的手法触及信仰话题,从而引发热议,在几十年的中国电视剧创作中,这样优秀的作品尚不多见。
在众多的评议声中,对《潜伏》结局的读解最引人注目,因为这个结局着实令人痛彻心扉。由于身份暴露,翠平不得不提前撤离,她在机场与余则成咫尺天涯,不得相认,后在小镇隐居,生下他们的女儿;被胁迫飞往台湾的余则成,继续潜伏的使命,他挂念自己的妻子,一再打听她的下落,但为了工作,不得不在组织的安排下与他人再结连理。在这样的铺垫之后,《潜伏》剧情被推向最后的高潮:翠平怀抱出生不久的女儿,独自站在山坡之上,眺望着远方的山路,守望着丈夫的归来,在青山环绕之下,一个凄凉的背影,一份孤单的守候。此时,身在台北的余则成把他和晚秋的结婚照挂在墙上,他们退回一步,神情庄重地望着照片,特写镜头中的余则成若有所思,他的眼前晃动着翠平的身影,当镜头再次回到余则成时,两行泪水夺眶而出。一边是望穿秋水,一边是黯然神伤,夫妻在空间上的分离,衍化为观者情感上一道难以弥合的伤口,致使许多人在观看此剧之后惊呼心理“崩溃”。
伤心之余,更多的观者对《潜伏》的结局表示疑惑甚至愤怒,不单因为有情人不能成为眷属,相爱的人不能长相守,更因为“组织”莫名其妙的冷漠态度。在全剧结束前,前来与翠平谈话的上级领导表情漠然,他对待产的翠平没有表示丝毫的关切,只是生硬地要求她在接到命令之前,不能离开镇子一步,以确保余则成的安全;余则成在香港与“组织”接头时,每次都询问自己太太翠平的下落,却都被告知找不到,最后甚至说“找到了又能怎么样,你们已经不可能在一起了”。迫于观众对原有结局的强烈不满,北京电视台在播放《潜伏》时调整了余则成与组织的那段对话,把原台词改成“这样优秀的同志,我们必须找到”,以多少减弱一下原版台词的冷漠之感。
不管编导主观意图为何,《潜伏》结局的安排明显突兀、生硬,它与全剧情感和叙事逻辑之间存在裂隙。从文本分析的角度说,这种裂隙正是蕴含作品深意的所在,它包裹的是创作者的思想和情感立场。那么,这样一个结局是如何形成的,它包裹的到底是什么?
二、理想与现实的双层结构
为了剖析《潜伏》结局的深义,必须从《潜伏》的双层人物关系结构谈起。
作为中共内情员,余则成身上交织着两条人际关系线索。一面是以吕宗方、左蓝、翠平、秋掌柜、罗掌柜、廖三民为代表的正面人物,另一面是以吴站长、马奎、李涯、陆桥山、谢若林等为核心的反面人物。显然,第一种人际关系建立在共同的理想和信仰基础之上,它以牺牲小我、保全事业的利他主义为原则。在剧中,为避免余则成暴露身份,吕宗方、左蓝、廖三民先后献出宝贵的生命;秋掌柜被捕后不惜咬断舌头,以给余则成传递信息,这个壮烈的场面甚至使审讯他的敌人也感到十分震惊,吴站长下意识地扣好领扣,这个反应镜头暗示出秋掌柜坚定的信仰所蕴含的巨大力量。在这种人际关系中,人们互相尊重、互相关怀,没有等级之分,没有上下之别。余则成对翠平的接受、对晚秋的帮助、对参与行动(刺杀陆桥山、给钱斌送药酒、李涯谈话录音)的有关人员的安全撤离的关心,都体现了同志之间的大爱精神。上级组织通过电台的指导、鼓励,同样给予身陷敌营的余则成以最有力的心理支撑。影片最后,上级组织多次催促余则成归队未果,无奈之下最后明码呼叫,通过一首普通母亲写给儿子的诗,向“深海”(余则成的代号)发出深情而挚诚的呼唤:“家院的柴门为你打开,炕头的油灯为你点亮,全家的牵挂啊,是这鲜红美丽的窗花,妈妈为你守岁,为你祈祷。”这里,“家”这个比喻最贴切地体现出这种新型人际关系的特征,共同的信仰将人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在家庭式的关系中享受温暖的关怀和抚慰。
相反,以吴站长为首的反面人物,大多奉行“人不为我,天诛地灭”的行为准则,他们惟妙惟肖地展示出后理想、后信仰时代个人利益至上、他人是地狱的残酷现实。这里,私利最大化是所有行为的核心,它侵蚀了信任、友情和是非观念:吴站长为保护天津站的名声及个人地位的稳固,不惜一再掩饰错误;马奎、陆桥山、李涯为争夺副站长的位置,勾心斗角,下绊儿拆台,无所不用其极。不少人从现代办公室政治的角度把玩《潜伏》人物之间的明争暗斗,实在是对这种人际关系本质的最好注解。正是在后者的衬托下,《潜伏》中所表达的理想和信仰才那么朴素、纯真,它宛如春天的雨露,滋润着焦渴的心田,使人们暂时脱离现世私利的泥潭,享受片刻精神世界的美好。
从情感逻辑看,全剧接近尾声时“母亲”对“深海”的明码呼唤,是第一种人际关系的高潮体现;从人物关系看,分别与翠平、余则成谈话或接头的上级“组织”原本属于前一种人际关系范畴,因此,它在情感表现上理应延续全剧的一贯风格,应该充满关爱之心,温暖且鼓舞人心。这样,全剧的情感逻辑才能保持前后的连贯性,才不至于使观众产生突兀、生硬、不合情理的感觉。而《潜伏》结局的处理,显然与全剧的情感逻辑不一致,由此也使叙事显得不那么合理、可信。
三、彷徨与迟疑的立场
关于结局,此剧的编导姜伟曾表示,他没有想过别的结局,他不认为所谓的大团圆结局才算完美,反而遗憾和凄美才使这个结尾更加完整。残酷是革命者生活的大部分,他在剧中所做的正是保留残酷的部分。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不是大团圆结局,因为事实上,一般观众也都知道悲剧的结尾更意味悠长,更令人遐思不断;问题的关键也不在于是否保留生活的残酷,因为正是革命者忍受痛苦的生死离别,才彰显他们精神境界的崇高和理想的伟大。真正导致观众疑惑的是编导在结局中所要表达的“荒诞感”。
正如编导自己所说,他一直试图在剧中保持某种荒诞感,比如翠平和余则成之间的强烈反差,再比如余则成悬而未决的入党问题。后者的荒诞感尤为明显。在剧中,余则成只是在翠平的带领下宣了誓,但一直没有得到组织的正式承认,直到全剧结尾处,上级告诉余则成找不到翠平,并且让他与另外一个女人恋爱、结婚,此后才通知他“经组织研究,正式接受你为中共党员”。按姜伟的说法,他在此“想强化后面的那个荒诞性”。演员孙红雷也把荒诞演出来了:他听到之后,沉了一下,说“我会奋斗终生的”,然后看着窗外,眼睛里还有一种愤怒、费解的感觉。但考虑到这样的处理怕有敏感的东西在里面,最终还是拿掉了。(参见《(潜伏)创世纪》第443页)即使如此,在现在的完成片中,我们依然可以在孙红雷的表情中察觉到一种被压抑的愤懑情绪。这个段落与翠平带领余则成宣誓时那种执着的眼神和语气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同时,它也多少让人联想到此剧第二集中的一个重要情节。当时,余则成暗杀李海丰成功,后被命令继续潜伏南京,协助有关人员索回被日军扣留的军用物资,在此期间,余则成得知所谓的军用物资实际上是戴笠和胡蝶的私人物品,上层人物不惜向日方提供中共抗战的信息以换取日方合作,这样龌龊的勾当动摇了余则成对党国的信任,深陷迷惘之中,他感到“恍惚”,不知道自己是在为谁而战斗。最后的结局虽然与此段落性质不同,但同样传达出某种荒诞情绪,余则成的不解、困惑多少暗示出理想和信仰的动摇以及由此产生的失重感。
这样,尽管全剧通过入党宣誓、左蓝的牺牲、朗诵《为人民服务》以及余则成对解放区诗意的描绘,正面地表现了信仰的巨大感召力和正义事业的伟大,但在结尾处,“组织”的严酷与冷漠、余则成的疑惑与愤懑,却以难以言表的荒诞感表达了一种明显相反的思想立场,即在信仰面前的彷徨与迟疑。
因此,很难说遗憾和凄美使这个结尾更加完整,相反,它给一个趋于完整的叙事带来了无法弥合的断裂。而这种断裂的根源在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使我们原本完整的价值观和历史观受到质疑和挑战。目前摆在人们面前的是彼此矛盾、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完整的价值观和历史观的缺失,直接或间接地造成影视作品中情感和叙事的矛盾和断裂。从这个角度看,《潜伏》的结局实在是一个时代深层问题的症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