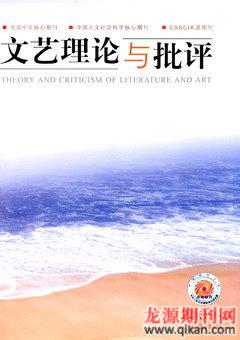农民工小说的流变与发展
周水涛
农民工小说创作主体由两支队伍构成,一支是内地“体制内”精英作家队伍,一支是东南沿海的“打工作家”队伍。“打工作家”来自农民工阶层,其创作是一种典型的“草根创作”。与内地农民工小说的精英创作相较,南方的草根创作有着特定的创作主体与接受群体、读者群庞大、创作发展过程漫长、创作立足于真实打工生活等特点,因此,考察农民工小说草根创作的流变与发展既具有学术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
我们可以将南方农民工小说的草根创作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1980年代:萌发阶段
尽管林坚早在1984年就在《特区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深夜,海边有一个人》,但打工小说创作的普遍出现是90年代的事。1980年代是农民工小说草根创作的萌动时期。这一阶段的创作有两个特点:
(一)创作稀少
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当时部分刊物登载打工小说的状况来说明问题。《大鹏湾》、《佛山文艺》、《江门文艺》是以刊登打工文学而闻名的刊物,这三家杂志社一向以最早刊登打工文学而自豪,因此,对这三家刊物的考察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大鹏湾》:1989年第1期(总第2期)共刊载16篇文字作品,其中没有一篇打工小说;《19881997作品精选·小说篇》号(1997年6月出版)共刊登11篇“精选”打工小说,这11篇小说都发表于1990年代,其中没有一篇创作于1980年代,这一“精选”时限至少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条信息:1980年代打工小说可供“精选”的基数甚少。以上考察说明:打工文学不是当时《大鹏湾》的主打产品。
《佛山文艺》:原先是小报,1980年代中期改为16开的文艺刊物之后,“武林传奇”仍是它的主打卖点——新版第1期没有刊登“武侠小说”导致全部刊物积压,这一“历史事实”表明1980年代的《佛山文艺》的运作重心不在打工文学。
《江门文艺》:该刊的总102期(1988年)的目录能从侧面反映当时打工小说创作的概况——没有辟出后来才有的“人世间”、“打工岁月”等专门刊登打工小说的栏目,而是仅辟有“小说”与“卡片小说”等栏目,但从《故乡,蹒跚的岁月》、《权力,在10岁的头顶闪光》、《夫妻之间》、《没有新娘的婚礼》等小说标题中很难看出这些作品直接关联打工。因此,我们可以大胆断定:打工小说在此时的《江门文艺》发文总数中所占比例极小。
三个刊物早期刊登打工文学或打工小说的概况表明,打工小说在1980年代还处于萌发阶段。
(二)思想稚嫩
从创作的思想内涵角度切入能更直接地认识当时的创作概况。当时草根创作的主题相对单一,并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与后来同类作品的主题的多样性比较,其主题的单一及主题覆盖面的狭窄显而易见。例如,进入21世纪90年代之后,农民工社会地位的边缘化、外来工与土著的矛盾、打工女性生存安全、资本资源与劳动力资源的价值悬殊、资本的权力等问题一般的草根创作都会涉及,但在1980年代,很少有作品涉及这些问题。因此创作主题的单一是农民工小说的草根创作萌发的重要表现。
与创作主题的相对单一相伴的是生活透视深度问题。陈荣光的《老板,女工们》(《特区文学》1987年第3期)能比较全面地说明这一问题。作品的描写内容是劳资对立问题。港商江老板出于“赶货”和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的原因而强迫工人加班,引发劳资尖锐对立,但最后“老板”和“女工们”握手言和:江老板母亲的恋乡情与爱国主义情怀感染了江老板,加之工人们在暴风雨到来前夕盖上了露天存放的成品货物,江老板幡然醒悟,不仅收回解雇成命,而且将领头“闹事”的王肖娟提升为主管。显然,是作者的“浪漫情怀”与稚嫩的眼光促使矛盾迅速消解,从而放弃了对农民工生存困境的揭示及对农民工生存困境与企业主的利益追求的必然关联的思考,“大团圆”的结局掩盖了劳资冲突的深层次原因,影响了作品对资本本质属性及国际“资本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作的审视,屏蔽了尖锐的社会矛盾。生活透视深度有限还表现为创作附和主流意识的某些思想观念,演绎具体的政策。例如在某些作品中,外来资本家或内地企业主在个别作家的笔下竟然变成了能体恤民情和关心经济建设的“厂领导”,有些劳资冲突因为有红顶官帽的“厂领导”明智处理而致使冲突迅速消失,罗建琳的纪实小说《蛇口,一次短暂的“罢工”》(《特区文学》1986年)可作为具有这一表征的代表作。
二、1990年代: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是草根创作迅速发展的阶段。根据实际发展状况,这一阶段应该分为两个时段。
(一)90年代前半期为发展阶段
在规范发展阶段,打工小说创作队伍不断壮大,在新人不断加入创作队伍之际,部分作家脱颖而出,其姓名逐渐为人们熟悉:林坚、张伟明、周崇贤等早在萌发期取得创作成就的作家的名字在这一阶段更加响亮,黄秀萍、斯土、鄢文江、黎志杨、缪永、阎永群等作家因自己的创作被人们认可而先后为人们熟识。与此同时,《作品》、《花城》、《广州文艺》、《特区文学》、《大鹏湾》、《佛山文艺》、《打工族》、《江门文艺》、《嘉应文学》、《侨乡文学》等刊物成为打工小说的主要载体,还有一些以刊登打工文学作品为主的刊物应运而生。广州一带,几乎每个市县都有自己的打工族文学杂志,许多杂志已经成为打工族的精神寄托及打工群体相互联系的纽带。部分刊物虽然看重经济效益及在一定程度上迎合大众化的审美需求,但反映现实、干预生活、培养新人还是它们的主要宗旨。
一些刊物的惊人的发行量从另一角度证明了打工小说创作在这一阶段的兴盛。例如,《江门文艺》于1993年1月起将双月刊改为月刊,后来又改为半月刊,其月发行量一度高达几十万份。
有影响的打工作家作品不断涌现也说明了农民工小说草根创作在此阶段的快速发展。张伟明的《对了,我是打工仔》(《广州文艺1990年第2期》),海珠的《703》(《花城》1990年第2期),黄秀萍的《绿叶,在风中颤抖》(《特区文学》1992年第1期)、《这里没有港湾》(《作品》1992年第1期),黎志杨的《禁止浪漫》(《佛山文艺》1992年)、《驶出欲望街》(《广州文艺》1995年第2期),周崇贤的《那窗那雪那女孩》(《作品》1993年第6期),鄢文江的《彷徨在三叉路口》(原载《佛山文艺》1993年5月号“打工文学专号”),黄岸贤的《白领丽人》(《外来工》1994年第6期)等代表着打工文学成就的中短篇小说就是在这一阶段出现的,而谭伟文的《广州梦》(花城出版社,1993年)、林坚的《有个地方在城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周崇贤的《隐形沼泽》(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等
长篇小说开始显现出打工小说创作的厚重。在整个严肃文学边缘化之际,打工小说在南方文坛上激起朵朵浪花。在规范发展阶段,打工文学创作品味较为纯正、指向相对集中,价值分化程度相对有限。——这些特点只有以后期创作为参照才能显现出来。
(二)90年代后期为分化发展阶段
在这一阶段,农民工小说草根创作出现了价值指向分化或创作分流现象。在分化发展阶段,草根创作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局面。在这一阶段,存在着对比鲜明的三种创作倾向:
具有纯文学倾向的创作:这一创作处于弱势地位,但这部分作品承接了前期创作的基本风格,延续了打工小说的“纯文学”流脉,如鄢文江的《厂花之死》(《江门文艺》1995年第5期)、吕啸天的《摇摇滚滚青春路》(《大鹏湾》1997年第6期)、周崇贤的《我要——活——下——去》(《作品》1997年第12期)、任重的《伊人之旅——段作家与打工妹刻骨铭心的故事》(《佛山文艺》1998年第8期下半期)、依燕的《飘零燕》(《佛山文艺》1998年第12期下半期)等。反映现实,揭示矛盾,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风格庄重,是这些作品的共同之处。
具有通俗文学色彩的创作:这类创作在该阶段打工小说创作总体中占有较大比重,周崇贤的《南部沧桑》(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5年)与《南国迷情》(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秦和涛的《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大鹏湾》1995年第12期)、寇崇善的《我要嫁给深圳》(《大鹏湾》1996年第1期)等可以看作这一时段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通俗文学色彩”主要是通过“言情”和“故事叙事”表现出来。从整体上看,这一板块的创作又可分为两类:既言情又反映现实的创作和以打工生活为平台而言情的创作。
具有庸俗文学色彩的创作:这类创作是打工小说或打工文学蜕变的产物。蜕变首先通过刊物封面的“美女化”等外在“形式”表现出来。以年轻女性为主要叙事对象是打工小说蜕变的内在表现。实际上,有些刊物已经到了堕落的边缘——在打工文学迅速发展之际,本地商人纷纷“转产”,内地商人纷纷南下,先后介入打工文学生产,或创办杂志、报纸,或购买文稿、版权,或与已经占领打工文学市场的刊物“联营”,或包销产品,书商们削尖脑袋钻进打工文学运作市场。一时间情杀、情仇、苦情、包二奶三奶等内容充斥这些以牟利为目的的刊物,一见生情、邂逅逢场作戏或“一夜情”、未婚同居、怀孕、堕胎、三角或多角性爱纷争、移情别恋等是作品的核心事件。
以上三种不同的创作显现出不同的价值定位,体现的是不同创作主体(包括传播媒体主体)的创作追求。
三、21世纪初:调整阶段
进入21世纪之后农民工小说草根创作整体上进入了调整阶段。这种调整有两种最明显的表现。
(一)打工小说刊物的自我定位
打工小说刊物的自我定位直接关联着打工小说的发展方向。
在“打工文学”领域的去留是以打工小说为主要卖点的刊物自我定位的第一步。进入21世纪后,在市场规律、社会干预、受众选择等因素的作用下,或知难而退,或被淘汰出局,部分刊物在“打工文学”领域内消失,“打工文学”刊物领域出现了重新洗牌的现象。那些纯粹以盈利为目的的刊物率先消失,随后《打工报》等销量及影响都存在一定局限的刊物消失,而《佛山文艺》、《江门文艺》、《大鹏湾》、《打工族》等刊物因其有可观的读者群支撑而继续存在,部分刊物一直坚持到今天,显现出“长盛不衰”的发展态势。
价值选择是打工小说刊物自我定位的第二步。对于南方打工小说刊物而言,价值选择主要是指刊物的服务对象选择及服务方式选择。这是两个合二为一的问题。应该说,在2001年,那些品味较为纯正的刊物的相互价值定位区分并不十分明显,但后来其相互之间的区分度逐渐增大。《江门文艺》将打工族作为自己的主要受众,在栏目设置、小说题材及主题选择、作品情节类型确定等方面充分考虑年轻的打工群体的审美情趣,在审美接受方面充分考虑这一群体的接受水平。经过几年的努力,描写打工群体现实生活的作品已经占据较大比例,注重作品的大众性、可读性、寓教于乐已经成为《江门文艺》的基本特色。《佛山文艺》的整体风格不同于《江门文艺》。进入21世纪之后,《佛山文艺》不断调整自己的价值定位。现在,这一刊物的价值选择显现出一种综合性:既照顾打工群体的审美需求,又考虑其他受众的阅读兴趣,刊物既显现出明显的大众化倾向,又带有一定的“精英性”。例如,“新乡土小说”、“本期特别推荐”等栏目主要刊载具有纯文学禀赋的小说,韩少功、迟子建、谈歌、阿成、冯积岐、何立伟等知名作家的小说曾经出现在这些栏目中。通俗性与精英性并存是《佛山文艺》的最显著特征,兼顾打工群体与一般读者是《佛山文艺》的“双重选择”。
在打工群体庞大、人口密集、刊物(包括电子“刊物”)集中的南方,打工文学刊物是相互影响、其价值定位互为参照的。例如,《佛山文艺》与《江门文艺》一直相互关注对方的价值定位与功能设置,避免自己与对方重复,将自己的定位与对方形成互补。
总而言之,进入21世纪之后,留守打工文学领域的刊物开始寻找最适合自己生存的空间。
(二)创作主体的自我定位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嘈杂纷扰的局面在南方文坛的慢慢消失,农民工小说草根创作开始了自我调整。
这种调整首先表现为整体创作“教”、“乐”配置的变化。进入21世纪后,农民工小说的草根创作开始寻找一种最佳的“教”、“乐”配置,笔者认为,经过几年的摸索与探寻,南方打工小说已经找到了“教”、“乐”的最佳契合点,即寓教于乐,“教”、“乐”并重。例如,姚汝泾的《女鬼》让古老的“冤鬼找替身”的故事框架负载现实内容,用荒诞夸张的手法展示了“三陪女”生命的轮回,进而展示了乡村打工妹的都市生活困境及女性生存的道德问题。
农民工小说草根创作的自我调整还表现为作家个体的不同价值选择。出于自己的生活经历、学识素养、审美情趣、价值立场,作家在创作上或侧重于“教”,或偏重于“乐”,这种不同的“教”、“乐”侧重形成了作家群体内部创作个体不同的价值选择。在经过了“发展期”的激动与浮嚣之后,作家们开始调整自己的价值选择,各自的价值定位渐趋形成。笔者认为,周崇贤与王十月的价值定位具有一定的倾向性与典型性。周崇贤与王十月在“教”、“乐”的增益取舍上呈现不同的发展趋势:周崇贤由重“教”向“教”、“乐”并重发展,王十月由重“教”、“乐”并重向精英倾向发展。
周崇贤80年代创作的《困惑》(《凉山文学》1988年第5期)等作品应该纳入典型的严肃文学范畴。《打工妹咏叹调》、《古河上的挑夫》等创作于90年代初期的作品在格
调上仍然趋近精英文学,但随后问世的《青春无注释》(《佛山文艺》1993年第6期)、《那窗那雪那女孩》(《作品》1993年第6期)、《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佛山文艺》1994年第4期)等作品的风格开始发生变化:性爱描写在整体情节设计中处于重要位置,打工者的流浪漂泊、身心疲惫、孤苦无依、是这些作品的主要叙述内容,而这些内容有相当一部分是依靠与性爱相关的事件来演绎的。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周崇贤的小说创作就显现出比较明显的通俗文学色彩,如《南部沧桑》(1995年)、《南国迷情》(1999年)等长篇小说及《“锁王”刘一手的卧底岁月》(《打工族》2001年3月下)等短篇都具有以通俗的“形式”负载深沉的“内容”的特点。进入21世纪后,周崇贤打工小说创作的“教”、“乐”配置趋于稳定:一直关联着严肃而急迫的话题,申说着弱势群体的冤屈与痛苦,同时也用犀利的目光审视着打工群体的人陛与人格,在题材确定、情节设计、人物类型等方面显现出明显的“大众化”倾向,如人物的塑造吸收了中国传统的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的某些因素。
至此,周崇贤将自己创作的“教”、“乐”比值调整到了一个最佳的契合点。周崇贤小说的“教”、“乐”配置具有典型性。进入21世纪后,鄢文江、刘万能、肖建国、洪永争等一大批作家创作的“教”、“乐”配置状况与周崇贤小说相近。
王十月的创作体现着农民工小说草根创作发展的另外一种趋势:由“教”、“乐”并重向精英化方向发展。王十月的创作在2000年左右引起打工文学界的注意。王十月早期的创作被鲜明地打上了市场改写打工文学的印记。当时曾有学者以其小说《化个蝶儿去》为例犀利地指出其创作的庸俗因素。但随后,他的创作朝向另一方向发展。从《出租屋里的磨刀声》(2001年)、《战栗》(2004年)、《烦躁不安》(2004年)、《烂尾楼》(2005年)、《刺个纹身才安全》(2006年)到《示众》(2007年)、《国家订单》(2008年),王十月的创作显现出由“教”、“乐”并重到重“教”轻“乐”、再到与精英创作“合流”的发展趋势。发表于2000年的《化个蝶儿去》表明作者顺应了当时的打工小说“创作潮流”,为了迎合部分读者的“特殊审美需求”而“找乐”。发表于2001年的《出租屋里的磨刀声》表明王十月的创作开始发生变化:性爱情节及性描写在这一作品中仍然存在,但性爱情节及性描写承载的是沉重的主题——磨刀,是一种象征性或意向性的反抗行为,这一行为的核心隐喻是一个弱势群体的底层位置与失语状态。2004年发表的《战栗》表明性爱情节及性描写在王十月小说创作中不再占有重要位置,这一作品通过一对乡村夫妇短暂的城市经历演绎了打工者是“城市丛林中的食草动物”这一文化思考。在随后发表的《烂尾楼》、《厂牌》等作品中,“教”处于更重要的位置。在这些作品中,作品主旨主要通过一般生活事件来演绎或表达,性爱不再是作品主题的主要载体。对于王十月自2004年至今这一阶段的整体创作而言,精英化倾向主要表现为整体风格趋于端庄和艺术表达趋于精粹。《示众》、《国家订单》的发表标志着王十月的创作开始与内地农民工小说的精英创作“合流”。例如,为王十月赢得普遍赞誉的《国家订单》(《人民文学》2008年第4期)打破一般打工小说习惯的人物塑造模式,一分为二地看待“小老板”等企业主的禀赋及生存状况,通过对“来料加工”型企业的描写而展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国际产业转移及“世界工厂”与中国劳工可悲命运的关联,展示南方打工世界“利益链”上群体之间的复杂关系,表明王十月已经置身于打工阶层之外观照打工生活,其文化视野更加开阔,思想更加深沉,思维更加敏锐。
王十月打工小说创作进入21世纪后的发展趋势代表着农民工小说草根创作的另一种发展趋势,张伟明、于怀岸、曾楚桥、斯土等打工作家的创作发展与王十月相同。例如,张伟明具有纪实性的长篇小说《深眸·女——对珠三角回流打工女的深度追踪与记述》(作家出版社,2007年)呈现出一种“正宗”的“主流文学”格调,于怀岸的《台风之夜》(《芙蓉》2004年第4期)显露出浓郁的精英意识。
以周崇贤为代表的打工作家“教”、“乐”并重,以王十月为代表的打工作家的创作具有精英化倾向,这两种发展趋势表明,经过20多年的演变与发展,在渡过了1980年代的萌发阶段、90年代的发展阶段,在经历了曲折与迷失之后,农民工小说的草根创作在进入21世纪后步入了健康发展的正轨。在此我们要特别指出:步人正轨的是草根创作的“正宗之作”,因为“打工小说”的整体构成较为复杂,其中的庸俗之作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不能归入“打工文学”的,因为它是当下“庸俗审美文化”的衍生物,是酒肆茶楼在文坛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