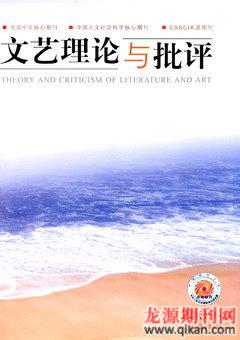略论农民工题材小说中的乡村妻子形象及文化寓意
方华蓉
乡村妻子是当代农民工题材小说中_二类有着独特魅力的艺术形象,当农村青壮年丈夫纷纷涌向都市时,是她们,或以其柔弱的肩膀支撑着凋敝的乡村与破败的家庭,或漂泊都市,最后差不多沦为都市的猎物或苦役。她们见证了作为中国底层农民与乡村女性的双重痛苦,她们的身体,成为演绎乡野贫困与性别歧视的意义场所。正因为如此,“乡村妻子”成为了农民工题材小说中一种负载着多重寓意的文化能指。
一
打工,一个辛酸的字眼。迄今为止,中国当代文坛还没有一种写作像农民工题材小说那样如此让人揪心不已,它是很难引起读者审美愉悦和阅读快感的创作。近30年来,持续不断的打工浪潮直接冲击着几千年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农业社会,无数本应该以忠贞为婚姻准则、以亲情为纽带的乡村家庭早已名不副实。夫妻分离,天各一方,对那些留守在乡野的农民工妻子,她们的任劳任怨,默默守候就不再是一种诗意浪漫的乡村情韵,相反,却成为了实实在在的肉体折磨与不可言说的精神创痛。她们的丈夫,作为“都市外乡人”受够了城市的各种欺凌、侮辱与折磨,是这些乡村妻子,一方面,以仁厚、无私与宽容慰藉和支撑着颗颗受伤累累的心,她们的美好品行不再是单纯的个体行为,而上升为一种抗拒都市冷漠与堕落的道德力量;另一方面,面对乡村颓败与都市奢靡的双重夹击,这种道德力量无疑显得苍白乏力而让人更加感伤与忧虑。农民工丈夫的长年不归确实造成了乡村家庭的破碎与残缺,随之带来了各种深刻的道德伦理危机。
罗伟章的《我们的路》是近几年农民工题材小说的精品之一。文章以五年未回家的打工仔“我”为叙述视角,一方面痛陈了农民工丈夫在都市的各种辛酸与不幸,而正因为有了一位守候在乡野的妻子,有了她的等待与抚慰,“我”才能一次次抗拒都市的诱惑,抵御孤独的侵袭,并承受住了各种各样的歧视与欺凌。另一方面,作者将叙述视角移向乡村和乡村女人的身上,在赞扬她们坚韧顽强、任劳任怨、独立支撑家庭的美好品行的同时,又十分难过地揭示了一种弥漫在乡村的深刻的精神危机。“我”的妻子金花,身患严重风湿病,五年里,像许多留守在乡村的农民工妻子一样,“家里没有男人,女人就只能把骨髓里的气力抠出来,起早贪黑地忙,也不一定能盘活几多日子……”家里没有了男劳力,农村的凋敝破落是可以想象的,所以“我”迫不及待的返乡之旅却以沉重痛苦的心灵折磨和最后还是毅然决然的离开而黯然收场。乡村土地的荒芜真正是人走向荒芜的逼真写照,对乡村妻子而言,受穷受累还不是最难熬的,肉体的创伤在精神的世界中或许可以得到抚慰,可痛苦的是她们连这样的精神慰藉也不存在了,丈夫的长年不归给她们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孤独,由此造成了乡村伦理道德的严重失范。“我”五年未归,妻子金花忠贞不渝,严谨保守,即使这样的女人也直言不讳:“家里的人日子也不好过”,又遑论那些一直贫困不堪、音信全无、多年未归的其他农民工的妻子呢?偷情、私通、背叛等不光彩的行为已经成为了乡野妻子们司空见惯的事情,在“我”那小小的山村里,人们对于女人们偷人养汉的事早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而正因为如此,才更加催人深省。
许春樵的《不许抢劫》中的梅花,清纯高雅,是一个迷恋琼瑶小说、幻想浪漫爱情的农村女孩,仅凭对真爱的向往,她冲破一切阻力与乡村穷小子杨树根结合在一起,然而,爱情,失去了经济基础作为依托,也只是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种下的一株罂粟花。梅花最终毅然决然地抛弃丈夫和孩子,与猥琐不堪的城里人私奔。杨树根只能孑然一身,远赴城市,成为了众多辛酸农民工中的一员,饱尝人世冷暖。漠月的《找不到话说》呈现给读者的是另一幅让人可以为之窒息的乡村图景。“村里的青壮年都外出打工去了,家里只剩下妇孺老幼,地没人种,到了农忙季节李红旗便成了宝贝”。土地的荒芜终究可以重新耕种,而“人无法忍受人的荒芜”(刘亮程语),于是,那些丈夫在外的乡村妻子们故意把李红旗推到了整个村子“孩子他爹”的位置上,而李红旗这样的当代乡村西门庆人数不少,且当得合情合理,他甚至被作为医治乡村妻子们“疾病”的能手而广受欢迎。
打工,以至家庭破碎、贫困,却又无法阻止堕落,农民工家庭确实面临着一种进退维谷的两难处境,而许多小家庭的困境投射的却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所面临的某种深刻的危机和尴尬。从上世纪80年代到今天,一波一波的打工浪潮席卷大江南北,很少有一种社会变革像打工这样如此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城市与乡村,如此深刻地改变着城乡两种文化与生活的面貌。“整个古代中国都是乡村性的,因此它没有必要独立出一个‘农村来。它的城市是乡土的、田园的自然经济的一个合理的延伸,它的市井社会是整个乡土社会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可如今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在包括众多农民工的努力下全力塑造自己新面貌的同时,反过来对中国传统社会和乡村的秩序、内容和生存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其中最为严重的是:传统稳定的乡村家庭链条被剪断了,许多传统的伦理道德被抛弃了,农民工家庭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与道德危机。这是多么让人黯然神伤的事情,农民工丈夫们漂泊都市,以繁重的体力劳动换取微薄的收入,饱受各种侮辱与歧视,他们的乡村妻子,或以坚韧不屈的生命意志抗拒着种种贫困与孤独,或最终无法抵御孤独的侵袭而身陷畸形的爱欲游戏之中。农民工丈夫及其乡村妻子的种种际遇,深刻地昭示了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城市,不仅剥夺着乡村丈夫的体力劳动,同时也整理着乡村家庭的伦理道德秩序。这种剥夺与整理给乡村带来的严重后果是不堪想象的,丈夫们背井离乡,渴望富裕生活的打工生涯事实上却导致乡村越来越贫困,越来越荒芜,并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乡村,已经被整合成了贫困颓败、破落凋敝的场所,几乎所有的农民工文学都以赤裸裸的真实和辛酸的笔调痛陈着这种让人焦虑的悲哀,却又显得无能为力。“凡是男人在外打工的,家里媳妇都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太好解决,也没有人敢去解决”。(《找不到话说》)那么就只有顺其自然,任由发展了。从这个意义而言,留守的乡村妻子们成为了乡土文化与乡土生活日益沉落的有力见证。她们的悲哀,它们的无奈,同样见证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在走向未来中的得与失、选择的艰难与矛盾。
二
如果说留守在乡野的农民工妻子,更多地见证了乡村的颓败与困境,更多地倾诉着乡野的贫穷与无奈的话,那么对那些随其农民工丈夫漂泊都市、“向城求生”的乡村妻子们来说,情况则要复杂得多,作家对她们的形象塑造以及负载于她们身上的文化寓意也要深刻得多。
一位位单纯朴素、谨小慎微的乡村妻子们,面临如庞然大物般的都市和无处不在的欺凌与诱惑,她们到底依靠什么才能求得在
都市的生存机会与空间呢?对问题的追问会使人万分痛苦。这类乡村妻子中的一部分人,与她们的农民工丈夫一样沦为了都市的苦役,她们以柔弱的身体,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挣取微薄的收入,在冷漠的都市承受着灵与肉的双重折磨。宋剑挺的中篇小说《麻钱》中的农民矿工刘干家的妻子,随其丈夫在矿井打工,在刘干家塌方死去之后,她以柔弱的身躯继续在窑上卖命苦干,默默忍受着所有的痛苦,最后换来的报酬却并非活人可以用的现钱,而是一种据说只有在阴间通行的麻钱。罗伟章的《大嫂谣》以辛酸动情的笔调,讲述了一个为生活所迫、已50多岁、拖着病弱的身躯、远赴南方打工的农村妇女的故事。这类走向都市以出卖苦力求生的乡村妻子,其辛酸、无奈凸显的正是整个农民工生存状况的艰难与尴尬,展现的是农民工“向城求生”中最惨不忍睹的一面。还有一部分乡村妻子,她们在走向城市的旅途中,不是以出卖苦力,而是以出卖色相求生,她们最后都差不多沦为了都市的玩物,她们以其生殖功能为农民工丈夫传宗接代,以其容貌与姿色取悦那些无聊的城市男人,她们游走于乡土与都市,她们既有着乡村的淳朴与狡猾,又有着都市的现代与堕落,是农民工题材小说中最有深刻寓意的矛盾集合体,也是笔者想要重点讨论的一类乡村妻子的形象。李肇正的《女佣》与王十月的《出租屋里的磨刀声》是近几年塑造这类乡村妻子最为出色的农民工题材小说,也是作家质疑城市文明的一个视角,表达个人沉痛的文化反思中最为深刻精彩的作品之一。《女佣》中的乡村妻子杜秀兰:勤劳善良,美丽淳朴,随其丈夫来到都市,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女佣的工作。在上班的过程中,杜秀兰小心谨慎,勤勤恳恳,得到的却是境况一样黯淡的城市人的轻蔑与猜忌,甚至包括那位半死不活的雇主老太婆的刻薄谩骂与冷嘲热讽。杜秀兰忍无可忍,主动出击,她以加倍的狡猾与狠毒报复那些都市人。最后,为了拿到城市人的名片,她半推半就,却也心甘情愿地成为了老太婆的两位儿子、甚至他们众多朋友们的情人,杜秀兰付出了肉体与尊严,牺牲了作为乡村妻子的清白与淳朴,成为了都市人的猎物。《出租屋里的磨刀声》是近年来反映农民工扭曲心理最为出色的打工小说之一,那对从四川贫困山区逃出来、辗转漂泊到深圳的小学教师——宏夫妇,原本以为自由随性的大都市能成全他们在穷乡僻壤不能实现的爱情,没想到深圳却张开了血盆大口,以无处不在的诱惑吞噬了单纯美丽的女教师,她沦为风尘妓女,也彻底粉碎了已沦落为农民工的男教师那仅存的人格与尊严。他们的爱情,既不能抗拒来自家族的阻力,更不能抵御都市的蹂躏。一场美丽诗意的爱情却开出了惨不忍睹的“恶之花”,而那位已沦落为妓女的乡村妻子,她的无奈之举却深深地伤害了深爱着她的丈夫,使他陷入了不可抑制的悲愤与扭曲之中,最终只能靠磨刀,在虚拟的空间报复那些诱惑宏的城市男人们。
这些游走于都市,向城市男人们主动出击的乡村妻子,无一例外都沦为了都市人的猎物,她们的身体,满足了一些无聊空虚的城市男人们对美丽与淳朴的想象,同时也见证了乡村妻子们“向城市求生”中最血泪斑斑、最扭曲变异的屈辱史。她们在都市的左冲右突,除了与她们的农民工丈夫一样遭受着屈辱,又不得不承受着另一层更为沉重的性别罹难。比如杜秀兰,因为是农民,她受到了城里人的一致猜忌与仇恨;因为是女性,她更难以找到工作;又因为是漂亮的女性,她天生被敏感多疑的城里人当作“红颜祸水”,几乎是顺理成章地沦为妓女,连混得最灰头土脸的城市工人都可以堂而皇之地玩弄她,戏耍她。但非常耐人寻味的是,作家们都无一例外地以乡村生活的贫困艰难谅宥了乡村妻子们的堕落。虽然她们已经沦为了风尘女子,已经沾染了不少的歪风邪气,早已褪尽了身上朴实单纯的乡村民风,甚至多了几分狡猾、狠毒、淫荡与无耻。作家一方面同情她们的遭遇,原谅了她们的堕落,另一方面却强化了对都市文明的痛彻反思。
以宏和杜秀兰为代表的乡村妻子,怀着良好的愿望,以清白之身来到都市,遇到的却是无处不在的身份歧视与性别歧视,即使濒临下岗,境况一样糟糕的城里人,也以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无端猜忌、谩骂、仇恨她们。城市一方面千方百计地排斥她们,另一方面又对她们展现出了无处不在的诱惑。这些乡村妻子们梦寐以求的城市生活与都市文化,原不过是混合着虚伪、豪华、享乐与自私、刻薄冷漠的人情关系的杂交体,而最为作家们深感忧虑的是,堕落的城市文化却以其无孔不入的强势正一层层地剥离着乡村妻子们身上那仅存的一点点美好的乡村气息,她们已经落入了城市文化的大染缸中,已经身不由己地沾染上了它的堕落与颓废气息。所以,杜秀兰与宏明知愧对丈夫,明知城市生活的虚伪,却仍然周旋于风月场中,并想方设法挤进城市缝隙。然而,令人欣慰的是,杜秀兰虽然成为了众多城市男人的情人,却能始终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一度拒绝他们的耍弄,宏最终与丈夫出走,不知所终。这是否意味着作家们在全面的反思与质疑都市文化的同时,仍然希望重拾美好朴实的乡村民风,重建厚道清白的乡村道德的良好愿望呢?
三
在整个农民工题材小说中,作家们对乡村妻子在特定境遇下的人生形式和生存方式,以及她们沉重痛苦的精神历程作了淋漓尽致的展示,她们,作为一类具有独特隐喻意义的形象得以凸现,作为一种文化能指获得了多重意味。
第一,乡村妻子们的悲哀、无奈正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乡村仍处弱势地位的沉痛隐喻。这真是一个让人想来心酸无比的对照,农民工与他们的乡村妻子,他们用体力、血汗,甚至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为中国实现城市化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可是,面对城市的欣欣向荣,面对城市人的颐指气使,他们的故土却处于破落凋敝的荒芜中,他们自己总是处于欺凌与极大的自卑中。罗伟章的《我们的路》中,城市里摩天大楼鳞次栉比,充斥着内衣秀,裸体宣传画等种种新潮时尚的东西,而乡村,正如妻子苍老得几乎认不出来的容颜,破落得恍如隔世。城市人也因此以极大的优越感,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审视着乡下人。《女佣》中的杜秀兰刚一进城,就陷入流言蜚语和冷若冰霜的提防与敌视之中,她们被认为是“只配在乡下种田,到城市来凑什么热闹?”“乡下来的,以后就要不太平了。”作家们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深厚的人道同情,以赤裸裸的真实展现了城乡两个世界之间的巨大落差。乡村的苦难,农民的贫穷,未能得到更多及更为必要的同情与关怀,相反,城市一方面在享用着他们的劳动,另一方面又以傲慢与冷漠对待他们的苦难和不幸,从而有意拉大了城乡之间的现实距离。
第二,乡村妻子们悲哀无奈的现实人生和她们所面临的巨大精神压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方式,甚至是自身形象的改变,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乡村文化处于弱势地位而被城市文化渗透和改写的沉痛隐喻。
“身处一个纸醉金迷的都市文化雾围之中的乡村人,他们在物质与精神两个世界里都被眼前这个都市剥夺得一无所有,物质的家园没有了,精神的家园也丧失了。”物质层面上的巨大落差,势必使农村乡土文化在面临城市文化的进攻中,总是处于被颠覆,被改写的巨大浪潮中,乡土文化早已今非昔比,面目全非,在城市文化的渗透和改型下,它已经无可挽回地“堕落”了,蜕变了,而作为农村乡土文化的载体之一——乡村妻子,她们的一系列遭遇,恰恰不幸言中了这一现实尴尬。《不许抢劫》中的梅花毅然决然地抛夫弃女,与富裕的城市男人私奔;许多留守的乡村妻子,身陷狂热与畸形的爱欲游戏中;杜秀兰与宏,虽不情愿,却也半推半就,甚至是自觉地周旋于风月场中。传统、温柔、忠贞的乡村妻子形象完全被颠覆了,乡村女性是乡土文化的重要载体,她们的生存方式以及生活形象的改变,无疑是农村乡土文化被颠覆与被改写的隐喻,而最让人忧虑的还在于——城乡之间的文化隔离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形势下进一步恶化,在这种迅速恶化的城乡文化隔离状态下,有些乡村妻子人性中“恶”的因子得以滋生与蔓延。《女佣》中的杜秀兰,一个淳朴善良的乡村妻子,面对城市人的挑剔与提防,她加倍地予以报复还击,她对老太婆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杜秀兰,始终心安理得,没有丝毫愧疚。当她为拿到城市派司,决定再与大宝二宝兄弟联系的时候,快要消失的岂止是一个淳朴善良的乡村女性,而与之共同沦落的,大概还有一种业已进退维谷的乡土文化吧。这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悲壮的农村文明演进史,在中国走向现代化,在城乡互动之际,乡村,作为弱势一方,并没有将他们的文化带入都市,更没有为城市提供一种新鲜材料与范式,等待着他们的,也只能是被城市文化的巨大浪潮所吞没。
“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这对于乡村妻子们,甚至是整个农民工题材小说而言,无疑都是相当精到的洞见,那些苦苦守候在乡野的农民工妻子,那些游走于都市缝隙的乡村妻子,她们悲怆的人生际遇,折射的正是一个民族,在无情的时代摩擦与更迭中留下的悲剧性生命体验与沉痛的社会文化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