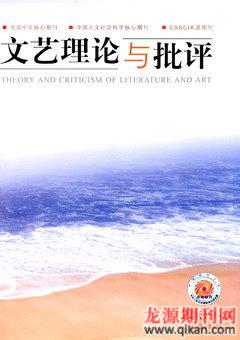三十年文学审美价值创新的多重呈现
方 伟
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已经30年了。在时间的先后上,它的发端要先于“改革开放”的正式起始。30年来,随着社会文化各方面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文学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其中文学审美价值的生成与凝结,在持续不断的创新之中获得了累累硕果。30年来的文学审美价值创新实践,它在文学、文化乃至社会中的多重呈现,直接或间接地证明着新时期文学所获得的成就。不可否认的是,其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也促使人们在不断地思考。
审美价值创新“路线图”
新时期文学是在“回归自身”中开始前行的,这是文学界的一般认识,但这种认识是将文学置放在了“艺术审美”光环的笼罩之中,仿佛新时期文学从一开始就与艺术审美画上了等号。实际上,这一回归不应该被过多地看作是艺术审美自身的回归,而把对社会政治的认识和表现搁置一旁。那种以为文学就是单一的、单纯的“艺术”的观点,多少存在着对文学历史与文学现实认识的偏误。问题的关键不是文学能不能脱离社会政治,文学是不能脱离政治的,而是应如何去认识社会政治、把握处理好它与文学的关系。辨识这一点十分重要,新时期文学审美价值就是从“思想审美”开始的。在跨越了“文化审美”、“先锋审美”、“大众审美”、“欲望审美”、“后现代审美”之后,“思想审美”仍然在当下的文学创作实践中发挥着作用。在新时期文学是在艺术审美回归的话语遮蔽下,看似把文学推向了自身差异性表现的极致,实际上是把它的生存环境主观地简单化了,从而缺乏一个持续发展、整体性的“生态系统”,文学的发展很可能会愈来愈变得孱弱不堪。
在从“思想审美”、“文化审美”、“先锋审美”、“大众审美”、“欲望审美”到“后现代审美”的发展路径中,各种“审美”之间既是一个基本的纵向连接关系,又是一个复合而多重呈现的关系,它们作为发展阶段上的“节点”,曾发挥过比较明显的作用。“思想审美”为新时期文学奠定了广泛、深入的大众阅读基础,并在新时期社会文化发展中获得了突出而坚实的地位。可以说,没有“反思”文学、“开拓”文学和“改革”文学的出现,新时期文学很难会有已经历史化的辉煌始端,后面的接续与发展也将变得难以想象。在新时期文学审美价值的生成中,“思想审美”的影响和作用是明显的。在对社会思想的深入思考和审美拓展中,实现了从“思想审美”到“文化审美”的跨越,“寻根”文学、“新现实”文学和“新文人”文学一方面试图清理历史与现实的文化关系,一方面在社会现实生活中侧重于探究多种文化存在与文化情味。这些都为后来的“文学研究”、“文化批评”的兴起提供了具体的审读对象和人文环境条件,也潜在地为“文学创作作为文化产品”的“转身”埋设下了“伏笔”。这是“文化审美”价值创新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它价值创新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结果。
“先锋审美”与“大众审美”,其实质就是试图超俗与尽趋通俗的两种不同的文学表现。这里的“试图”与“尽趋”,在新时期文学30年中几乎贯穿始终,“先锋审美”从“现代派诗歌”、“实验小说”、“先锋戏剧”到信息文化中部分玄幻、怪诞的文学作品,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和当下流行文化、新新文化的影响下,以变化、变异、荒诞、颠覆、拼接与实验的形式、形态,表现个体自我对思想、文化和生活的看法与认识,甚至是有意识地、自主地进一步表现出了边缘化、另类化的看法与认识。客观地评价“先锋审美”,虽不能说它在价值创新上没有一定成果的存留,但有一个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重视并获得解决:这就是在“先锋审美”打破、打乱了传统文学、现有文学的审美形态与内在结构以及文学秩序后,是否足以支撑新时期文学发展新的局面?“大众审美”很容易被引入到一个受文学的“纯粹主义”指斥的窘境之中。在极端化的审美视阈里,“大众审美”并不被看作是审美的过程和结果。本来,“大众审美”作为文学表现的努力路径之一是不应存在疑义的,文学作品在接受层面的最大化,既是文学表现审美魅力的一种衡量,也是文学实现自身精神目的的一种要求。虽然新时期文学的“大众审美”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已逐渐变得复杂化、多样性,甚至是刻意地去迎合一些低级趣味,但是从通俗文学到“大众文学”,还是实现了某种在阅读空间上的拓展、延伸。应该清楚认识到的是,“大众审美”作为文学发展特别是文学阅读本来就是不可或缺的,这在文学本身也是与生俱来的。
其实,曾经喧嚷一片的“下半身写作”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就对“情色文化”与“情色文学”有过思考。可能在有些人看来,“下半身写作”提供了现实生活中关乎“情色”部分的新鲜经验,或许这是一种叛逆、挑战的价值空间营造。实际的情况却是,在1990年代中后期,不少女性作家竞相搭上“欲望列车”驶向自我欢娱的目的地,并紧紧拉扯住接受主体的神经末梢,让文学在感性的满足和奢乱的浮现之中获得了冲动释放。倘若认定“欲望审美”在良性价值上有所凝结,也只是在写作与阅读的多个层面、多维指向上有着不同的呈现而已。真正“现代派”文学的生成,一直受到人们的质疑。作为一种文学创作思潮的舶来品,它所对应的现实社会能够提供生活的“土壤”来与之呼应吗?在这一问题还没有完全历史化的时候,“后现代审美”却借着信息文化的迅速崛起进入到了当下文学的各个环节。如果说“现代派审美”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固化,能够提供变异、荒诞、超俗、边缘化的审美情感经验,那么,“后现代审美”已经很难有什么介入社会生活实质的沁人心脾的感受。换言之,“后现代审美”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主观性的自我审美认知,因为“后现代文化”在当下还是一种外源性的流行思潮,不是基于本土社会发展进程而在社会生活内源性上的价值生成。
“后现代审美”直接的结果是颠覆与“异军突起”的审美感知。在思想、文化、“先锋”、“大众”、“欲望”审美的发展链条中,“后现代审美”的存在是既作为一种结果也作为一种态度。而正是后者,对新时期文学现代性与大众性在今天的双重显现起着一定的作用。
创新的现代性与大众性
当下,尽管在“新时期文学30年超越现代文学30年”这一话题上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意见,其实,这一话题延续的还是“学院式”的教学思维,人们应该对新时期文学本身进行价值结果的多方研判,以此来作为“超越”显现的标尺。
现代性与大众性,是新时期文学本身发展的一个主轴。这里,可以在思想、文化、“先锋”、“大众”、“欲望”、“后现代”审美这样一个线路上来展开它们的价值结果,进而探析、认识新时期文学现代性与大众性的成败得失。
现代性是一个哲学范畴,不同时期的哲人有着不同的认识与阐释。当“后现代”的“现代性”(后现代性也是一种现代性)在社
会文化活动中四处弥散的时候,之于现代性本身的释义也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其含义在信息的呈现或传达上表现出了一种前倾的取向与态势,它的根本是趋真的、向善的和积极的认知蕴含。新时期文学“思想审美”的现代性,是在拨乱反正、追索真理的文学审美探知中,显现了人们对待社会与人的价值态度,成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人文基础之一。“文化审美”是在对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观照下,积极追索现代文化要义的一种文学活动,由思想的探求过渡到文化的反思,传达了在现实生活中对历史文化的拷问和对庸常人生的反讽与冷幽默。自1970年代末开始至今的“先锋审美”,一直是在倡导着个我突破和与众不同,现代性的“价值”显露最直接。“先锋审美”现代性的社会文化意义还远不只是文学上的,它对人们心理行为有着多方面得影响与触动,营造着一种社会文化舆情。只是这种社会文化舆情,有时候会带来一些精神价值认知的混乱和不明情感与情绪的无序蔓延。“欲望审美”被看作是一种从人化审美到物化审美的过程性结果,这一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旁逸斜出,也可以说是一种并不值得刻意去关注的“另类写作”。不过,“欲望审美”的现代性勾画出了现实社会语境中“欲望生存”的芜杂景象,并传达着躁动、慌乱、压抑而又与渴望、生活、改变相互混合的情感与心理信息。在“后现代审美”多多少少成为某些阶层、某些人“文化想象”,而社会生活还没有被上升到工业文明发展的高度的时候,就被信息文明的强势进入给拆分、解构而渐渐趋于平面化了。“后现代文化”作为一种中心分化、话语离散的文化,其价值中心的建立与废弃决定于信息位势形成的高低,而不是过往的价值地缘关系。“后现代审美”现代性的得失,也正表现在它对文化与文学传统的解构、颠覆和主观拼合。对文化的正确审视和对文学的有益继承,是一个不容回避也不能漠视的基本话题。
现代性与大众性在各自极端的意义上,形成相互对等、充满张力的审美发展诉求;在互为转换的意义上,可以是相互涵盖、交汇融合的审美多重呈现。这是30年来新时期文学审美价值创新的一个重要征候,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在回归自身中的价值主导和这一价值主导的不断泛化”。“大众审美”作为现代性与大众性连接和转换的一个重要端口,它的现代性强烈地显现着这一重要征候:一方面是形成的一种价值中心中试图获取“大众”的认同,另一方面是在迎合“大众”中建立一种价值中心。这也是现代性与大众性之间的互为过渡。
大众性的“大众”含义在30年中发生了很大变化,它的实际构成也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在思想、文化审美的阶段,“大众”与“广大群众”能够形成基本的对接,它们大众性的呈现是在反映社会人们大体一致的人文审美需求,文学传达出的思想关怀和文化关怀,与当时广泛且较为深入的阅读空间形成了一种遥相呼应的美好关系。这里的大众性没有衍生、虚拟的成分,它是一个具体、实际的存在。而对于“先锋审美”、“欲望审美”、“后现代审美”而言,大众性就表现得复杂多变。大众性在“先锋审美”那里,不是一个在创作实践过程中被自觉思考的问题,它主要企及的是个体自我精神吮吸的沉迷状态,如果能够产生一定范围的审美影响当然也乐见其成。“欲望审美”却是首先要获得实实在在的大众性。“个人化”、“下半身”和“物化”的写作,个我性、私密性、自我欲求等,都成为了博得大众阅知结果的“幌子”。那种在文本中彻头彻尾包蕴着的盼望相知相通的欲念,成为“欲望审美”大众性的突出特点。“后现代审美”的大众性与当下的大众文化情境息息相关。这一情境的基本轮廓是:一方面是物质欲求依然旺盛,一方面是精神渴望日益凸显;一方面是从众心理不可自控,一方面是个体意识持续增强;一方面是文化素养参差不齐,一方面是情趣爱好大致趋同;一方面是乐得直观易解、痛快淋漓,一方面是想着千奇百怪、花样百出。这样,“后现代审美”的大众性,是一种既欲以个体自我为中心同时又趋众趋同的表现状态。“大众审美”发展到当下,“大众”的含义已成为一种有着空间、层面和群落多方集合的文化接受与消费人群。它表现出这样三个特点:这个群体在范围与数量上的含义是流动变化的,很可能会随着流行文化一时的强与弱而发生大的波动;这个群体的空间支撑和群落主导,目前基本上是由对信息文化乐此不疲的人们所组成的;这个群体在审美需求上不会刻意地去追求一成不变,缺乏忠诚度,总是在动态地调整着自身的欣赏、喜好和娱乐,因而在范围与数量上极大地表现出松散和多向度的一面。如此,“大众审美”的大众性也便在其中昭然若揭。
时至今日,新时期文学当下的现代性与大众性,在它的两边意义上,一个是精神价值的持续探路、一个是话语信息高位势的形成;在它互为转换的中间意义上,是要获得审美价值的创新在信息文化形成、发展中的引领与普及。这也成为新时期文学在以后发展的一种价值预期。
30年来文学发展的成果是巨大的,它对整个社会文化的繁荣进步起到了驱动、支撑乃至某种程度上的主导作用。文学审美价值创新的多重呈现和获得结果,向人们提供着这样的事实依据和说服力。尽管文学发展到今天面临着诸多挑战,它的生存很可能正处于“作品多、读者少”的窘境之中,它在社会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或可逐渐平平,但文学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它审美特质价值空间的不断拓展与延伸,应该是人们精神生活中一个长久的想象依赖和享乐源泉。30年文学审美价值的创新在证明着过去和现在,那也当然能够昭示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