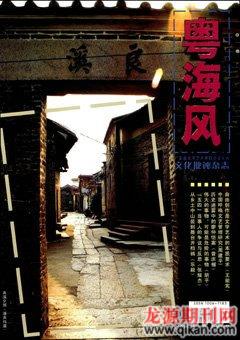伟大的事物,可能是危险的事物
胡 平
一、从农家乐到统购统销
20世纪50年代初,在一般农民心目中,毛主席是具象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可感可触的生活化的政治。
毛泽东在将土地给了农民的同时,也将一种从未有过的生产方式、精神方式,给了中国的农村——
北京市郊的六郎庄,是优质的京西大米的出产地。从海淀西至颐和园外,都有这个庄的土地。一眼望去,处处可见谷穗甸甸的稻浪,旋着微波,恍如一个愉快的小伙子在打着呼哨,间杂着一块块碧绿的藕塘和荸荠田,早熟的小稻正在收割,大片的红芒稻就要登场。场上地里,人们忙着割、晒、打稻子、捆草把,落稻机的击打声应和着人们发自肺腑的笑语。供销社紧急调运来十几架落稻机,一架得650斤小米,当然不便宜,但是为了不耽误这少有的好年成,供销社院子里挤满了来贷款购买的农民……
黄河两岸的农民,也在为眼前的好年成而欢欣鼓舞。从冀中平川到晋东南山地,在广阔的田野或层层的梯田里,高粱深红,玉茭金黄,在蓝得几乎透明的天穹下,像是一束束竞相追逐的火苗,在放肆地生长……
几乎能与农民的欢乐一起婆娑起舞的土地,其苏醒的性灵,源自于农民的精耕细作,加工加肥。六郎庄里,谁家地里的大粪、豆饼都比往年上得足。尚不到清明,老早就有人下地抹稻埂了。捉地(即稻田插秧前,将去年的禾兜用手翻过,使其烂在地里)、插秧、蓐草也干得特别起劲。在晋东南石厚土薄的山地,农民们犁、锄、耙各三遍,施肥由过去的每亩三十担,猛增到八十担,才把荒地变成了熟地。
被无数的大小河流交织的苏南,河底里不断淤积起来的河泥,成了农田里最好的乌金。在土改结束后的1951年春天,触目皆是罱河泥的小船。常常是一对夫妇,女的站在后梢把橹,男的站在船头罱泥,手下立着两根交叉的长竹竿,仿佛一把长柄的剪刀,剪刀头上装着两只相对的麻线织的网,或篾编的箩,向河底使力一夹,就把河泥罱起来了。夕阳西沉的时候,每个村子的周围都是三三两两满装河泥的归船……没有船或一时借不到船的农户,便多多收垃圾或粪便。人们都在感叹:今年早起拣狗屎的人比狗屎还多!
在各地蓬蓬勃勃的生产热潮中,二流子、懒汉、和尚,大部分也像离开厕所一样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昔日的生活。京郊的槐房村里有16个二流子,过去因为没有土地,没有职业,过着坑蒙拐骗、吃喝赌嫖的日子。土改后,除一人外,都参加了劳动。改邪归正的二流子高玉禄说:以前我连个地渣儿也没有,不偷没有办法,现在有了土地可得好好种了。
满怀新生活憧憬的农民,必然会对文化有热烈的要求与渴望。
常熟县,1950年冬有6万多农民参加冬学,该县的县委书记说:现在农村的小学教室都快被挤破了。师资缺乏是急需克服及解决的严重问题。在东北农村,农民们在冬学中如此地用心,以至于你到处可以看见歪歪扭扭的粉笔字迹,他们把所有可以写字的东西:雪地、门板、柜门、灶台、墙壁等等都当成了黑板。平时过日子是很节俭的,甚至舍不得点豆油灯,只用自家种的麻籽榨点油,放在灯碗里,让它发出一些些昏昏的光亮就可以了。在冬学中农民们却点起了煤油灯,两盏、三盏,把灯心捻得大大的,让满屋子亮堂堂的。就在这温暖了一个冬天的橘黄色光芒里,从前一个大字不识的人,已经学到能够记简单的账和写简单的字了……
老家湖北省浠水、土改时正值少年、日后做了新华社记者的杨继绳先生回忆道:
从我亲身经历的情况来看,中国农民真正舒心的日子是1950年到1953年。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我目睹并亲身享受到了“农家乐”:交完了公粮都是自己的,多余的粮食可以自由上市。吃饱了饭的农民,唱着歌把最好的粮食送给国家。我们这些系着红领巾的孩子,在长长的送公粮的队伍旁边奔跑、雀跃,分享着大人们的快乐。(杨继绳《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
毛泽东成了一个庇佑天下农人发家致富的神。
神龛,则是40年代起他就在文章、讲话里屡屡提及的新民主主义阶段。
普列汉诺夫说过一句名言:可以在俄国烤出社会主义大饼的面粉,俄国的历史还没有磨出来。进城之前,开国之初,毛泽东也认为,能够在中国煮出喷香的社会主义大米饭的稻谷,中国的历史还没有收割。社会主义要在中国开始全线进攻,也许要到共产党人坐了天下的十五年之后,在这十五年里,得有一个被称之为新民主主义、既有社会主义因素又有资本主义因素存在的过渡阶段。
刘少奇似乎特别热衷诠释这一阶段,有勇气不避这一阶段在意识形态上的重大风险。他去天津,对资本家们发表了要将他们从冰封的疑虑中拖出来的著名讲话,内有“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的言辞,他保证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至少“可搭伙10年至15年”,如果过早消灭了资本家,“消灭了以后,你还是要把他请来的”。他反对过早地“动摇、削弱、直到否定私有制”和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步骤,在城市里如此,在乡村里亦如此。
1948年9月,他在西柏坡便说过:“单是给生产者以土地,只是建立了领导权,还须进一步使他们成为小康之家。”(《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问题》)1951年7月,他又在中南海春耦斋里讲:“私有权在今天中国的条件下,一般地还不能废除,并对提高社会生产力还有其一定的积极性。”在农村对私有制“又动又不动是不对的。太岁头上动土,你去动摇一下,削弱一下,结果猪牛羊杀掉”,是对生产力的破坏……(《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
农民们在这来自北京、带有浓重湘音的承诺里,酥酥地荡漾着自己的发家致富之梦。又伴着滚落的串串汗水,将它们撒播进脚下的黄土地、黑土地、红土地。
刘少奇当然是个成熟的政治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共产党又将“资产阶级”给请了回来,决心和他们“搭伙”走很长一段被称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时期,农村里包产到户,责任到田,农民们发家致富的欲望以及各级干部勃发这欲望的欲望,恰如板结的土壤里蚯蚓在执著地蠕动,缺水的田垅中泥鳅在叭叭地蹦达……已经证明他对新民主主义阶段情有独钟,的确是有着某种历史预见性的。
刘少奇又显得不够成熟。
为着对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垂青,以及在那几年里他讲的诸如“剥削有功”、“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一类让毛泽东听起来颇为可疑的话,渐渐地在他与毛的关系上打下了个冰冷的榫子,直至“文革”,被视为毛身边的赫鲁晓夫而遭到全面清算。
同样出身农家的刘少奇,当然不会忽略乡下的情况:
1952年里,五亿多从未吃过饱饭的乡下人,敞开胃袋,在这一年里,足足多吃掉175亿公斤粮食,一些地方开始有了存粮,孩子不再啼饿,老人不再叹饥。男人的脸上血色在渐渐地驱赶菜色,下体也趁机在女人的肚皮上作乱起来,1951、1952两年里,全国农村共生下四千二百五十四万九千七百四十个孩子……(参见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与失败》 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第一版)
但刘少奇,显然不像毛泽东一样抡圆了双眼,充分注意起土地改革后农村新一轮分化的现象——
在北方,河北省中共沧县地委在一份报告中称:
经过几年来生产运动的开展,农业生产已有相当的恢复,有的农民已开始添置调整土地,生产逐渐上升。但也有因贫困出卖土地,生产也就随着下降,农村的阶级关系亦随着开始了新的分化,主要表现在买卖土地上。肃宁、河间、任邱、建国等县,1949年、1950年出卖土地的有138户,占总户数的10.7%,共卖出土地383.95亩,占总亩数的2.19%。从出卖土地的原因上看,河间、任邱二个典型县调查,计出卖地户62户,用于盖房子的5户,远地换近地的12户,买牲口的6户,共23户(这些因调整生产卖地是正常现象);因生产生活困难及丧失劳动力而卖土地者39户,占总户数54%。(见《中国农报》第二卷第四期,1951年2月)
在南方,1953年,浙江省海宁县政府对仲乐乡东王村106户农民的情况作了一次调查——
在土改以后,由于劳动互助运动的发展,74.1%的贫农上升为中农,但因遭受天灾人祸而出卖土地的贫农也有几户,借债的16户(其中,中农4户,贫农12户),卖工的30户(中农3户,贫农27户)。少数中农却上升为富裕中农,其中有5户放债,10户开始雇工,买进土地的有8户。个别中农如该乡九龙村的中农朱荣堂,随着经济的上升,打起六条木船,放租经商,趋向新富农。”(见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
这次调查有多大的典型性虽不得而知,但在海宁县作了多年实证调查的张先生可以肯定,此次调查中发现的土地买卖、高利贷、雇工等现象,当时在海宁县其他乡也有发生,只不过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当然,在部分农民眼里,正因为现在土地可以买卖,这日子才会有奔头。河南作家周同宾先生,他父亲在土改之前用十石粮食买了别人一些地而成了中农,比起那些在土改中家徒四壁的贫农无偿地得到了土地,他并不后悔:“拿粮食买来的地,种着心里踏实;一个钱不花,人家的地就成了自己的,天下哪有这事!”土改后——
……父亲最满意的是,新社会,没土匪,天下太平,没捐税,只交公粮,公粮也不多。家中的粮囤又大了。碰巧,又有人卖地,卖四亩。那是个贫农,刚从地主那里分来的地,地名“百石仓”,是因为那人好吃懒做,庄稼没种成,没钱买酒,不能度春荒,才卖的。当时,允许土地买卖。父亲拿出家中的全部积蓄,又借一笔钱,买下了。父亲领我去“百石仓”,他以主人的姿态,骄傲地站在地当中,久久地端详脚下的地,一再说:“好地!好地!”我看见,他是那么强健有力,那么心高气壮,仿佛即使再有一顷地,他也能种好……(周同宾《土地梦》.《中华文学选刊》1999年第5期)
早有论者注意到,土改之后,毛泽东日益为农村中新一轮的分化而忧虑重重,并非仅仅因为他不懈地追求革命意识形态的纯洁性,或是他对于在分化中一部分再度被抛向了窘困境地的农民满怀着同情。
尤让毛泽东阢陧不安的是,在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3278亿斤,比上年增长10.6%,比1949年增长44.8%,也超过战前最高水平1936年3000亿斤的9.3%、堪称是一个大丰收年的1952年之后,中国的不少城市却为缺粮所困扰,到了1953年夏季,国库存粮已经所剩无几,各级政府声嘶力竭号召厉行节约,但也只够城里人维持两个月。虽然还有田间小麦尚可指望,但这个夏季,长江流域洪水肆虐为百年罕见,夏粮的减产已成定局。粮食部于6月2日呈报中央,经济专家和各省巨头齐集北京会商对策。对策没有拿出,拿出的只是一个“形势严峻,难以为继”的结论……
毛泽东的案头上,告急的报告还在纷至沓来。
从1953年7月1日开始的一个新的粮食年度里,京、津二市原本需要15亿斤小麦,可是收上来的只有10亿斤,而且从7月1日开始,三个月里已卖掉5亿多斤,尚剩下的4亿多斤,却要维持此后九个月的生计。9月4日,令人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私商在探得政府的焦头烂额之后,麇集一处火上加油,在两个小时内,把除去仓库里的粮食统统买去。他们还想断后,又蜂拥至徐州,抢购刚刚收上来的黄豆,一个叫王雨农的家伙,一个人便买去50万斤……
堂堂一国之都,那开国隆隆的礼炮声,和“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宣告,还回荡在耳边,现在却有可能站不起来了,不是被明火执仗的敌人,却是被一场粮荒所打倒。北京急电东北,需调42亿斤粮食火速进关,素有“粮仓”之誉的东北三省,因为也局部受灾,答复是只能调集14亿斤,而且不知何时才能启程。情势如箭在弦上!
造成粮食匮缺的局面,有着诸多的原因。
如农民放开了肚皮吃,1953年秋天,薄一波在华北作了十几天调查,他发现,过去山区农民一年只能吃上约十顿的白面,现在则每个月可以吃到四五顿,面粉需求量空前增大了。还有,由于发展工业的需要,城镇人口大量增加,除自然增长的以外,绝大部分来自农村,昔日他们是粮食的生产者,现在他们是粮食的消费者。此外,还有天灾的影响,以及私商们囤积居奇,待价而沽,与国家明中暗里斗法……
最重要的,仍然是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所面对的一个老问题:
一方面,农民总想将更多的粮食存在自己的粮囤里,如同地主总想把更多的土地集中在自己的名下。在他们眼里,这是一条载着他们渡过各种危机、并驶向发家致富彼岸的方舟。过去没有这条方舟的农民,一旦有了它,他们对于粮食的呵护更为精心,必要时,他们会在一番坚壁清野后,装出一副灶冷锅凉、可怜巴巴的模样……
另一方面,昔日乡村社会的结构性阶级——地主,日益变成抽去了骨头的软体动物,国家尚没有一个有效且强力的组织,对农民的生产活动进行全程的督促、监管,并让他们将所收获的粮食,按照国家经济建设的要求,老老实实地交出或卖出足够的数量。眼下,与农民打交道的,只是蝗虫一样密密麻麻活动于集镇与乡村之间的上百万粮贩子,后者又像蝗虫一样在疯狂吞噬共和国幼小的身架。农民却乐意把粮食卖给他们,因为他们给出的价格,高于国家征收的商品粮的价格。在1952年7月1日到1953年6月30日这个粮食年度内,全国农民共卖出粮食348亿斤,其中,国家和供销社只收购到近70%,私商则收购到了30%。
眼看一座座正在大出血的城市,毛泽东显然对列宁当年派出由武装的工人组成的粮食征集队下乡,多了一层理解。仅仅在土地改革结束一年之后,对当年用血肉之躯,还用独轮车和扁担,将中国革命推进了城市的农民,毛泽东的看法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在当年10月2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云详细分析了粮食购销的严峻形势,对八个应对方案的可行性逐个作了说明。他说:
我这个人不属于“激烈派”,总是希望抵抗少一点。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方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陈云文选》1949——1956年)
毛泽东深深地为陈云的话所震动,在会议最后,他讲到: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农民一切都是好的,农民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的一面;
现在是“青黄不接”,分土地的好处,有些农民开始忘记了;
这也是要打一仗,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不能打无准备之仗,要充分准备,紧急动员……(以上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
在陈云拟出的八个方案里,中央政治局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其中最为严厉的一个方案——统购统销。
所谓统购,即生产粮食的农民,应按国家收购的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字,将余粮售给国家。粮种和价格由中央统一规定。价格的规定,大体维持在当时城市出售价格的基础上,以不赔不赚为原则,并须长期固定,以打消农民囤粮待涨的心理。
所谓统销,即城市居民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数量、品种和价格购买粮食,其配给之数量,因人的性别、年龄、职业以及居住地区的不同而有不同。当时城镇居民大约组成了五千万户家庭,每户均有一个购粮本,凭本方能取得粮票。
粮票,此后又传宗接代,牵蔓扯藤,扯出了更多的票证:油票、布票、肉票、饼票、豆干票、糖票、烟票、酒票、煤球票、火柴票、肥皂票、工业券……头上纷扬着五颜六色票证的大雪,每一个城里人举步维艰,动辄掏票。无票,你就要饿死冻死,回到穴居时代;有票,你也不可能欢蹦乱跳,活色生香。这场将老百姓维持在最低生活水准的大雪,一直下了22年之久,大雪之中,则是政府高度膨胀了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管无所不服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