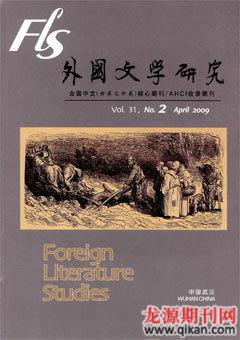论毕晓普诗歌中水意象的心理机制
徐 蕾
内容提要:水意象在伊丽莎白·毕晓普的诗作中频频出现并不断重复,这既是其诗歌创作的重要特色之一,也折射出诗人的主体意识和心理机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相关概念为从创作者心理机制的角度探究水意象的动机和内涵提供了依据。水意象在熟悉与诡异两极间的运动轨迹和内在张力指向诗人被压抑的童年创伤记忆、及其在想象空间中对家的渴望与困惑。毕晓普诗歌中丰富充盈的水意象,为诗人提供了在现实中无法获得的身份感和延续感,却难以弥补其生活与记忆中的永恒缺憾。
关键词:伊丽莎白·毕晓普水意象心理机制
作者简介:徐蕾,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语文学研究。
伊丽莎白·毕晓普(Elizabeth Bishop,1911—1979)是美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诗人之一,曾获普利策诗歌奖(1956年)、美国国家图书奖(1970年)。她凭借对日常生活充满想象力的观察和丝丝入扣的细腻笔触,赢得了约翰·阿什伯里、希默斯·希尼、奥克塔维亚,帕斯等著名诗人的高度评价。
在毕晓普总数并不算多的诗歌作品中,水意象出现的频率非常高。据统计,“在《诗歌全集1927—1979》(The Complete Poems 1927—1979,1983)中发表的一百一十首诗歌里,有四十四首或一半不到的作品或以水为背景、或将其作为主要的行文内容;此外,还有三十三首诗中提到了水——通常是很重要的一笔。这样,不算其它形式的流质,水浸润了诗人近四分之三的作品”(Goldensohn 35)。这里的水意象,系指广义的自然间液体,包括江湖河海里的水体、从天上落人人间的雨水、乃至生命感怀而流下的泪水。一些评论家已经注意到毕晓普诗歌中充盈的水意象,但他们或者在赏析某首诗作时对其中的个别水意象进行分析,或者认为这代表“一种思维的习惯”(Brett c,Miller,“The Prodigal”72),而对它在毕晓普诗歌创作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缺乏深度分析。笔者认为,水意象不仅显示了毕晓普在诗歌创作上的发展轨迹,更指向其意识和记忆的深处,值得研究者关注。本文将在西方学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心理机制的角度对毕晓普诗歌中的水意象进行深入探讨,试图构筑一个语言与意识、记忆与生活交汇融合的话语界面,以期在更为灵动的空间中把握毕晓普诗歌创作的内在逻辑。
一、诡异的重复
水意象的重复为研究者提供了进入毕晓普诗歌世界的重要通道。重复作为一种表现手法,对于小说和诗歌来说具有不同的意蕴。小说研究者关注重复,通常意味着阐释文学作品语言内涵的开端(Lodge 85),因为“任何小说都是由重复和重复中的重复,或以链接的方式与其它重复相连的重复构成的复杂组织”(J,Hilliss Miller 19)。诗歌中的重复则更具形式和结构上的重要意义,因为韵体诗歌强调以音韵、节律重复为基础的类音乐形式,诗歌中常见的副句或叠句(refrain)形式往往还是作品的重要成份。在毕晓普的诗歌中,重复不仅是形式上的,还承载着特殊而复杂的内涵。在其作品中频频出现的水意象,超越了音韵、节律、副句等形式和修辞的意义,它与诗人的童年记忆相勾连,蕴藏着深层心理动机,是理解毕晓普诗歌母题(motif)的一个重要线索。
诗集《旅行的问题》(1956)中的代表作“六节诗”(“Sestina”),将水意象的重复性在单篇诗作中发挥到了极致。在这首诗中,房屋、祖母、孩子、火炉、年历和眼泪是不断重复的核心要素。“九月的雨水落在房屋上。/昏暗的光线中,老祖母/和孩子一道坐在厨房里/小小的神奇火炉边,/一边读着年历里的笑话/一边又说又笑地藏起了眼泪”(Bishop,Com—plete Poems 123)。祖母试图隐匿眼泪,她以为“秋分时候的眼泪”和“年历中的预言”是她的秘密——只有她能够将秋雨和眼泪、忧伤和季节更迭联系在一起(Colwell 153)。然而,祖母的眼泪早就看在了孩子纯真的眼睛里。在接下来的诗节中,孩子用手中的画笔表现了他/她眼中的世界:眼泪出现在茶壶上,在火炉上疯狂地跳舞,盛满在祖母茶杯里,画上小人的纽扣和从空中坠落的一个个小月亮。祖母的眼泪在孩子的视野中恣意弥散。
屋外绵绵的秋雨和屋内无声的眼泪,将外部的自然空间与内部的家庭空间联通起来;而孩子的想象力又构筑了超越时空之外的新天地——心灵空间,泪水宛如飘忽不定的精灵,幻化出千种姿态。重复的水意象不仅是诗作韵律结构的重要组成单位,更构成了贯穿全诗的线索,让三重空间浑然一体。然而,水意象虽在形式上维系着三重空间的有机统一,却又在内容上彰显了三者间联系的“可疑性”——水意象与其出现的场域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协调性。美国诗歌评论家海伦·文德勒曾指出,虽然前五个存在再现了一幅典型的乡村家居生活即景,但是眼泪的出现却使得整座房屋变得“不自然”(Vendler 97),或借用原诗的字眼“inscrutable”——变得“难以理解”。“在所有令人难以理解的事物中,一个人的房子首当其冲”(Vendler 98)。当本应熟悉的事物变得难以理解、甚至神秘诡异时,这件事物便有了类似弗洛伊德所谓的“uncanny”的属性。这个词译自德语“unheimlich”,源自名词Heim,意即“家”;heimlich意为“家的,熟悉的,普通的”,unheimlich的字面含义则是“非家的”,引申为“不熟悉的”、“陌生的”、“奇怪的”、乃至“诡异的”。作为一种引发人们内心不安和恐惧的特质,unheimlich极具辩证色彩。弗洛伊德根据语义研究发现,heimlich与unheimlich虽然表面上意义相反,但前者的某些义项与后者完全一致,“heimlich因而变成了unheimlich”,“一方面它意味着熟悉和宜人的事物,另一方面它也是被隐藏和看不见的”(Freud,“The Uncanny”224-225)。
“六节诗”中的家庭画面,也呈现了从heimlich趋向unheimlich的运动轨迹,诗句描绘的日常生活即景在眼泪近乎强迫的重复中逐渐被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如果说第一节中的秋雨和第二节中祖母的眼泪是现实世界的水意象,那么从第三节开始,水便有了自己的意志和生命力。在第三节中,“茶壶上坚硬的小泪珠/在滚烫的黑炉灶上疯狂舞蹈/宛如雨水在房子上舞蹈一般”(Bishop,Complete Poems 123);到了第四节,茶壶上的泪珠变成了祖母茶杯中“深棕色的眼泪”;第五节里的孩子画了一个房子和一个男人,那男人的纽扣仿佛一颗颗泪珠;第六节泪珠般的小月亮从年历的页片间飞出,坠落在房间的空气里和孩子笔下的花坛里。茶壶上跳舞的眼泪或许还有其现实依据,眼泪与杯中红茶的关系就显得有些匪夷所思了,眼泪与钮扣间的奇特类比更是出乎人们的意料。眼泪渐趋离开其常规的人类情感语境,向陌生、奇异的物质想象空间飞去。
与此同时,穿越多重空间之后,水意象遭遇了本体论上的危机——其虚构性与实在性难
以界定。诗作的最后三行写道:“但当祖母悄悄地/在火炉边忙碌时/小小的月亮宛如泪珠/从年历的页片间坠落/到孩子仔细安置在房屋前/的花坛中”。水意象的活动场域从房屋内的真实空间延展到孩子画笔下的想象世界,并与房屋外真实的雨景遥相呼应。小月亮既可能是祖母眼泪的暗喻,也可以是孩子天马行空的想象。当这些小小的月亮落入画中的花坛时,它们又被画纸赋予了一定的真实性,并在与屋外秋雨的映射关系中获得了些许现实意义。此时此景中,水意象的真实性与虚构性彼此渗透、交融,难以剥离。原本熟悉、宜人的家庭画面,则因水意象对“被隐藏和看不见”之事物的揭示而变得神秘莫测。由此,我们被引向了诗人遥远的童年记忆和隐秘的内心深处。
二、压抑的创伤
“六节诗”中的水意象所开启的问题,提示我们沿着由“诡异”和“重复”所铺设的路标,继续向潜藏在诗行背后的诗人意识深处漫溯,揭开其间“被隐藏和看不见”的秘密。
弗洛伊德认为,“诡异”(unheimlich)与“熟悉”(heimlich)之间的语义重叠绝非巧合,而是隐喻着一种深层的心理结构。让人感到不安的事物其实源自童年时代的某种愿望或信仰,陌生、怪异的表象仅是一种错觉,其实质乃是在大脑中根深蒂固的熟悉事物的重复出现。这种“强迫性冲动的重复”(“The Uncanny”238)所指向的,恰是被意识多年压抑、本该隐藏却被公开的事物(“The Uncanny”241)。因此,“诡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心理压抑(repression)所带来的滞后效应(belatedness)。
毕晓普对“情感滞后性”和“压抑”的深刻理解,与她个人的童年记忆有着直接关系。毕晓普出生后八个月就失去了父亲,她的母亲从此失去正常理智,四年后被送进精神病院,直至终老。毕晓普在七岁之前,一直跟着外祖父母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一个小村庄里生活,没有父母的生活让她对于那些定期寄往某精神病院的包裹分外敏感。成年后,她也从未看望过住院的母亲。她对母亲的复杂情感可以从1970年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窥见一斑:“我和我母亲一道生活到我大约四岁半左右……没有父亲。一些富有爱心的姨妈和我的外祖父母拯救了我的生活,拯救了我——一个已经受伤的人格,但我的确得以幸存”(Harrison131)。目睹母亲的精神一步步陷于崩溃,对于一个正需要母爱的稚嫩孩子来说是无比痛苦的;而这伤痕以犯罪感的形式在毕晓普的心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我的生活一直笼罩在对母亲犯罪感的阴影下——不知何故,孩子们会有这样的念头:这是他们的错——或者只是我有这种想法。我对此无能为力,而她又活了二十年,对于我来说,这永远是一场噩梦”(Harrison 131)。这种复杂心理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让诗人自觉压制有关母亲的回忆,并在创作中摒弃任何相关的内容和主题。在1937年写给玛丽安娜-莫尔的信中,她甚至表示要永远放弃写关于母亲的主题:“母爱——难道不可怕吗。我渴望北冰洋的气候带,那里没有任何一种情感可以成长,当然君子之交的友谊除外”(Brett c,Miller,Elizabeth Bishop 125)。
但自觉的拒斥并不意味着对这段记忆的根除;相反,关于母亲和童年创伤的记忆时常以另一种特殊方式呈现在毕晓普的笔下。人们虽然可以将本能的心理典型事物排斥在意识之外,却会因此形成对某种事物或人的迷恋(fixafion),因为“压抑并不能阻止冲动代表继续存在于无意识中、进一步组织自我、产生衍生物并确立联系”(Freud,“Repression”149)。在毕晓普的诗作中,水意象既可以是温暖亲切的,承载着生命的慰藉和故乡的记忆;也可以是暴戾恣肆的,给人带来焦虑和恐惧、忧伤和绝望。经由对毕晓普诗歌中水意象的分析,我们得以接近诗人的隐秘往事和意识深处。
在毕晓普晚年创作的未发表诗作“酒徒”(“A Drunkard”,1972)中,可以瞥见水与被压抑的冲动间的潜在关系。该诗是目前仅存的诗人直接回忆童年时与母亲关系的作品,通过第一人称再现了她三岁时目睹的塞勒姆的一场大火。站在摇床里的幼童“我”注视着眼前的烈火,感到异常口渴,“但妈妈没有听见/我呼喊她。在草坪上/她和一些邻居在分发咖啡/或食物之类的东西,给坐船到达的人们/我隔一会看她一眼,看她一眼/然后喊哪、叫啊——可没人注意到我……我捡起一条女人的黑色长统棉袜。/满心好奇。我妈妈厉声叫道/把那放下!/我清楚地记得,清清楚楚地/从那天起,那句斥责/那个夜晚,那一天,那句斥责/我便有了一种反常的口渴感/我发誓这是真的——到了/二十或二十一岁,我就开始/喝酒——喝酒——就是喝不够/你一定已经注意到了/我现在已半醉了……”(qtd,inEllis)毕晓普在此诗中吐露了自己多年酗酒的动因,无论其中的因果关系是否完全成立,这段相隔58年的尘封往事定然包含着诗人对母亲最深刻的记忆。母亲的严厉斥责和自己“反常的口渴感”一起经历了岁月荏苒、斗转星移,顽强地留存在作者的记忆深处。两者间的偶然关系也因被长久压抑的寻求母爱的冲动而烙上了必然的印记。如果说诗人反常的口渴感隐喻了她对母爱的极度渴望,那么水与母亲、童年创伤记忆间的联系也就不言而喻了。
实际上,在毕晓普早期诗歌和散文作品中屡屡出现的水意象,已经隐晦地指向诗人与母亲的紧张关系。大学毕业后不久,毕晓普在几页草稿纸上写下了一个没有题名的故事片段。作品从一个孩子的视角,描写了他对母亲焦虑不安的心情。在这个几乎没有什么情节的故事中,母子二人走在被雨水淋湿的回家路上。雨后的空气清新湿润,孩子和母亲结伴回家的心情应该是愉悦的;然而被雨水浸透的地面湿滑、泥泞,孩子不得不一面小心翼翼地迈出每一步,一面紧紧跟上沉默不语的母亲。压抑的氛围悄然烘托出孩子内心深处的不安和对母亲的陌生感。诗作“在威尔弗里特涉水”(“Wading at Wellfleet”,1936)中的大海被评论家称为“令人永远惊恐的母亲海”(Bidney 501),颇为直接地表现了诗人眼中的大海/母性所具有的毁灭性力量。威尔弗里特是美国马萨诸塞洲科德角上的一个海边小镇,毕晓普在12岁到18岁期间每年都要参加那里的夏令营,在读大学期间还去过几次,可以说威尔弗里特的海水见证了她的成长岁月。而在诗人笔下,本该亲切的海水却成了“一箱刀子”,策划了一千个亚述战士也无法想象的一场战争;在这场人与海水的战役里,成败“完全取决于海浪”(Bishop,Complete Poems 7),战士们毫无反抗能力,最终只能成为大海的牺牲品。
对于“野草”(“The Weed”,1937)中“我”那停止跳动的心来说,水既创造着生命,也带来了生命中至深的伤害。流水催发萌动了落入心中的草籽,可茁壮成长的杂草只不过是要将“我”的心一次次分成两半。该诗中的水意象是条满载着往昔回忆的溪流:“几滴水珠落在我的脸上/和眼中,因此我可以看见/(在那阴暗的地方,我认为我看见)/每颗水珠里
都蕴含着一束光,/一幅照亮了的小小场景”(Bishop,Complete Poems 21)。有评论家认为,该诗表现的是“记忆的洪流可以给想象和创造带来新的活力”(Zhou 36);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洪流中裹携的记忆同时还带来了不断重复的痛苦。什么样的记忆会令年轻的诗人(时年26岁)感受到如此根深蒂固的痛苦呢?有学者分析此诗时指出,“出生大约是我们往昔最深的创伤”(Parker 20),野草与心脏的关系类似子宫与胎儿之间的关系,都具有相互依托又相互排斥的辩证色彩,因此他将创伤归结于胎儿与母体分离的一般事实。然对于毕晓普而言,这一分离不仅是母女肉体上的割断,更是两人情感与精神上的多年隔绝。伴随着分离的溪水一路从心中涓涓流出,那落在脸上和眼里的就成了泪水,照亮的一幅幅小小场景便是如影随形的童年记忆——毕晓普希望忘却、但又无法摆脱的心灵创伤。诗作展现的依稀带有超现实主义色彩的画卷,其实暗喻了一种在死亡和重生中不断轮回的意识结构,这与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对意识的理解相仿——意识的基础在于记忆,也是过去对未来的不断“咬啮”(gnawing)。诗中裹挟着记忆碎片的溪流给心灵带来一次次伤痛,也不断创造着生机——构成当下、推进着未来。因此,这首诗也可被视作创伤记忆对意识之冲击与塑造的寓言式再现。
现在重新回到“六节诗”,我们可以解答其中的疑问了:那神秘诡异的眼泪之所以无处不在,恰恰是因为屋子里有太多的“不在场”,在这个只有祖母和孩子的家,空缺的部分只能由季节的眼泪(秋雨)、祖母的眼泪和孩子想象的眼泪来填补。一如“野草”中照亮记忆长河里小小场景的溪水,绵延不绝的眼泪同样隐晦地言说着创作者心灵深处的秘密——长期被压抑的童年经历和创伤记忆。
三、“家”的困惑
由诗人的童年经历和创伤记忆继续追问,我们不难发现潜藏在水意象背后的另一重心理机制,那就是诗人在想象空间中对家的渴望与困惑。
毕晓普从1951年起定居巴西,开始了她一生中最稳定和幸福的岁月。远离故土的诗人打破以往对童年记忆的缄默态度,创作了大量关于“家”的诗篇——包括故乡加拿大新斯科舍的小村庄和她的新家巴西。巴西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诗人家乡的地理镜像,开启了她对童年生活的全部记忆(Brett c,Miller,Elizabeth Bishop 252)。水意象作为背景或前景,频频出现在毕晓普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又是诗人旅居国度的风景线与生命线,也成为她建构、重塑记忆之家与现实之家的重要元素。
1965年出版的诗集《旅行的问题》包括“巴西”和“其它地方”两部分。所谓“其它地方”指的往往就是新斯科舍。在这部诗集中,现实的家与想象的家、当下的家与记忆的家、异国的家与故土的家相互交织、相互映射,营造出一种“童年熟悉的异域风味”(Travisano 168)。“其它地方”中的“在村庄里(“In the Village”)被公认为诗人的自传故事。作品展现了“我”五岁时目睹母亲逐步失去理智直至被送往精神病院的经历,与之对应的是两组对立的声音:母亲拒绝脱下丧服时令人窒息的尖叫声,以及铁匠的打铁声和村里的河水声。在故事的开始,母亲的尖叫声无处不在,压抑着整个新斯科舍村庄和“我”无可逃遁的灵魂,那声音“飘荡在新斯科舍村的上空”,成为“我村里的音调。用你的指甲弹击教堂尖塔顶端上的避雷针,你就会听到那声音”(Bishop,Collected Prose 151)。随着时间的推移,铁匠清脆的钉锤声和河水潺潺的叮咚声最终在某个夏日午后送走了尖叫声。失去母爱的女孩转而“肯定生命的力量的替代源,即铁匠奈特的存在和大自然的慰藉”(Diehl 97)。所谓“大自然的慰藉”,指的就是一条蜿蜒的薰衣草红的小河。故事结尾处,去邮局给精神病院的母亲寄完包裹后,“我”在回家的一座桥上停了下来,被桥下流淌的河水深深吸引:河水里有自由自在的鳟鱼,有躺在河床多年、早已毁坏不堪的汽车挡泥板和闪闪发光的罐头盒子。生活就象这川流不息的河水,有充满活力的生命,也有积淀在脑海深处的残缺记忆。在认识到生命的真谛后,“我”最终摆脱了那曾经令人胆颤心惊的尖叫声。有学者指出,这首诗作勾勒了叙述者的心理成长轨迹,即“从最初面对抛弃自己的母亲而感到焦虑不安,叙述者通过在替代性媒质里寻找信心,逐步走向对母亲缺失的承认和情感的再生”(Diehl 104)。诗中潺潺的流水,正是可以抚慰孩子心灵伤痛的一种“替代性媒质”。前文论及的“六节诗”中另一种形态的水——眼泪,同样具有这种功能。
水不仅仅是毕晓普记忆中童年之家的重要内容,也是她新家园的核心要素。“旅行的问题”(“Questions of Travel”,1956)是毕晓普写下的第三首关于巴西的诗,诗中再现了一个充满瀑布、河流的水乡世界:“这里有太多的瀑布;拥挤的溪流/过于湍急地赶向大海/山顶上如此众多云朵的重压/让它们柔曼地往四周洋溢/就在我们的眼前变成了瀑布”(Bish0p,Complete Poems 93)。离开家也许是遗憾的,然而不能欣赏到这里的风景更是一种遗憾。随遇而安的毕晓普一度将巴西——沉浸在想象的水中的国度——当成了自己的家(schiller80)。在一次采访中,诗人把自己间或从巴西返回美国的旅程看作是“一个潜水员浮出了水面”(Ribeiro 14—15)。水之于巴西、之于诗人故乡感的意义呼之欲出。巴西雨水丰沛、云蒸霞蔚的地理气候环境不仅保障了毕晓普舒适的生存空间,更让她的心灵汲取着养分和慰藉。
毕晓普居住的内陆小镇佩特罗波利斯(Petropolis)的小家也是被水惠泽的地方。《雨季之歌》(“Song for the Rainy Season”,1960)以梦幻般的笔调展现了诗人与巴西女友在山间共筑的小屋。工作室窗外的瀑布显然激发了她的灵感:瀑布形成的云气把山间小屋更幽闭地与外界隔绝,而雾气散后的彩虹更增添了小屋的情致。虽然远离人群,静谧和谐小屋的世界依然有自己的“客人”:有白露和奶白色的日出,也有银鱼、老鼠、书虫和蛾子。炽烈的阳光是一种威胁,水却可以把热力阻隔在外,为生命提供一片清凉和宁静。水是这里的精髓,因为“没有水/大岩石将会瞪着眼/失去了磁力,光秃秃的/不再披挂/彩虹或雨水/那宽容的空气/和浓雾也散去”(Bishop,Complete Poems 102)。如果说大洪水后的彩虹象征着上帝与人类重新立约,山间岩石上浮现的彩虹就是这片土地与诗人的庄严约定——允诺给予心灵一块暂时的栖息地。
有评论者指出,巴西是毕晓普逃离童年时代被剥夺感和焦虑感的必要途径,尽管这一新生活仍然笼罩在过去的阴影下(Axelrod 279)。诗人在陌生的巴西找到了熟悉的故土气息,也透过眼前的异乡看到了记忆中遥远的新斯科舍;在由此产生的此在/彼在、现在/过去、旅行/家乡的关系中,看似对立的二元概念实际上不仅相互依存、更呈现出彼此转化的趋势。始终贯穿于两地风景间的水意象在这组辩证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跨越时空的隔阂,让
巴西的家和童年的家在诗歌文字中相遇、交叠。巴西的水释放了毕晓普自童年即萦绕心间的对爱与安全感的极度渴望,从而使陌生的异乡变得依稀故土;新斯科舍的水则寄托着诗人成年后回顾创伤记忆时些许想象的慰藉,在欲言又止之间给家庭画面罩上了一层神秘面纱。颇具吊诡意味的是,两个家因为相似而不同——共有的水意象有着不同的韵味;又因为不同而相似——不同韵味的水意象都表现出在heimlich和unheimlich间相互转化的倾向。
然而究竟何处是毕晓普所追寻的家呢?有人认为,在毕晓普的诗歌中,家依托于无法想象的想象之所,存在于熟悉与非熟悉的缝隙之间,它不是别处,而是不在任何地方(Fan 49)。也有人说,她的叙述者常常徘徊在某处落地生根的欲望和对稳定关系的信任缺乏之间,即便流浪者找到了“家”,它也要么空空如也,要么难以接近(Godwin 16)。水意象近乎强迫性的的反复重现,在某种意义上承载了诗人对家充满矛盾的追寻与想象。正如研究者所说,“如果自我是一面火车车窗里的瞬间影像,是覆盖一片移动着的黑暗的歪斜倒影,那么人们只能通过找寻相同的影像(或相同的风景),才会产生一种身份感和延续感”(Sanger)。在毕晓普的诗歌中,不断重复的水意象在想象的空间里提供了一种身份感和延续感,提供了一个在家的自我。然而,水意象终究只是个一个压缩的符号,或者如柏格森所说,是“介于‘事物与‘再现之间”的某种存在(Bergson viii)。它无法让诗人重获被剥夺的母爱,无法弥补家庭的缺失,也终究无法以异乡的水来还原故土的家。水意象的重复再现,不过是展现了瓦尔特‘本雅明所说的“模糊相似性”(opaque similarity),一种梦境世界的深层然而依稀的相似性(Benjamin 200)。
毕晓普的诗歌虽因语言明晰、简明易读而常被列入美国大学文学课程的阅读内容,但对于研究者而言,充分理解她的作品却并非易事。美国女作家玛丽·麦卡锡就曾把阅读毕晓普的诗歌比喻为捉迷藏的游戏,称自己“嫉妒隐藏在她文字中的心灵,就仿佛是一个数到一百、等待被发现的‘我”(McCarthy 267)。和同时代的美国自白派诗人不同,毕晓普往往喜欢隐蔽自我,越涉及个人生活,笔法越间接隐晦(Marks 213)。纵观其一生的诗歌创作,让她始终难弃的水意象可算是引领读者通向诗人主体性的重要路标。英国评论家I,A,理查兹说过,“产生一篇诗作的大部分动机当然是无意识的,而这些无意识的过程极有可能比有意识的过程更为重要”(Richards 29)。本文从心理机制角度对毕晓普诗歌中水意象所作的分析,或可成为循此路径将毕晓普诗歌研究推向深入的一次有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