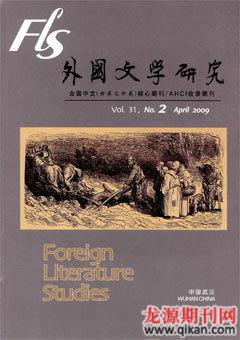《蝇王》:启蒙现代性方案的解构
李 丹
内容提要:本文运用了格雷马斯的叙事语法分析戈尔丁《蝇王》的角色模式及其深层意指结构,认为《蝇王》中的人物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单位,他们之间的对立和斗争隐喻了启蒙过程的展开及其结局。在《蝇王》中,真正使孩子们得救的并不是拉尔夫代表的“理性”,而是巡洋舰的“偶然到来”。因此,“理性”被“偶然”反讽性置换,《蝇王》构成了对启蒙现代性方案的解构。
关键词:戈尔丁《蝇王》启蒙现代性解构
作者简介:李丹,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荒岛小说”堪称西方文学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18世纪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19世纪巴兰坦的儿童小说《珊瑚岛》都是英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荒岛小说。在这两部小说中,知识战胜了愚昧,文明征服了野蛮,理性征服了非理性,由此折射出人类开拓进取、昂扬乐观的启蒙精神。但是,当20世纪英国小说家戈尔丁在《蝇王》中再次以荒岛作为背景的时候,却对此前的荒岛小说所展示的启蒙现代性方案予以了反讽和解构。可以说,《蝇王》有着更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阐明了当今世界人类的状况,揭示了启蒙现代性的方案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是如何被扭曲和异化的。
评论家们常常把《蝇王》看作是“寓言”或“神话”,戈尔丁的本意也是通过《蝇王》复制一部袖珍版的人类发展史。小说的象征性、隐喻性显而易见。其中出现的人物、实物等,都可看作是具有象征隐喻意义的符号。
在小说中,拉尔夫是一个英俊的金发少年。他最早发现了海螺,并把它作为团结、组织岛上孩子们的工具。在荒蛮的海岛上,他力图维持一种文明而有秩序的生活。他组织大家通过吹海螺来召开民主会议,共同协商事情。谁拿着海螺谁就有发言的权力。拉尔夫始终都富于理性,体现了文明和传统的力量,可以说是启蒙思想家心目中理想的人的化身。可以说,“拉尔夫”和“海螺”,隐喻了启蒙思想体系中的“理性”和“民主”。
小说中的猪崽子是拉尔夫的忠实的支持者。他头脑聪明,带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他始终维护海螺的权威,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相信科学,他的眼镜片的聚光为孩子们带来了至关重要的火。当孩子们害怕夜晚的鬼怪的时候,他坚信世界上是不可能有鬼魂的,并力图消除孩子们的恐惧。于是,猪崽子和眼镜,也获得了更为抽象的意义,即启蒙思想体系中的“科学”与“文明”。
小说中另一个主人公西蒙,是一个腼腆正直的孩子。他喜欢思考,带有形而上的气质,有着非凡的洞察力,并富于道德良知。当孩子们在为野兽所恐惧时,他最早意识到“大概野兽不过是我们自己”。为了搞清楚野兽的真相,他还爬上山去想看个究竟。在林中空地上,他看到了杰克等人献给野兽的贡品——一只爬满苍蝇的野猪头。恍惚中,野猪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苍蝇之王,对着西蒙说:“别梦想野兽会是你们可以捕捉和杀死的东西……我就是你的一部分”(218)。这正是作者力图揭示的人性中兽性的、恶的秘密。而西蒙则象征着不断探求真理的“美德”。
与拉尔夫、猪崽子和西蒙相对立的是杰克。他意志坚强,有着极强的权力欲,始终都在和拉尔夫争夺领导权。一开始他还遵守着文明社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后来他在脸上涂抹上了五颜六色的面具,摆脱了羞耻感和自我意识,嗜血的兽性大发作。他利用孩子们对猪肉的垂涎和对野兽的恐惧,吸引了大批的孩子,夺取了拉尔夫的领导权。从捕杀野猪到残杀同伴,他实行了野蛮的专制统治。杰克象征着野蛮、专制和人性中的恶。
按照启蒙思想家们的启蒙现代性方案,这个故事的结局应该是:以拉尔夫为代表的理想的人,以“理性”为最高的指导,以“民主”、“科学”、“美德”战胜“野蛮”、“专制”和人性中的恶,最终得救。然而,戈尔丁展现的这个故事却是:以杰克为代表的野蛮专制派完全战胜了以拉尔夫为代表的科学民主派,海螺被砸碎,眼镜被偷走,西蒙被残杀,猪崽子的脑袋被砸得脑浆迸裂,拉尔夫本人也受到追杀,险些毙命。孩子们完全堕落为丧失理性和文明的野蛮人。最后,杰克等人为了烧死拉尔夫而纵火烧岛时,烟火引来了一艘巡洋舰,把他们带回了成人世界。
如果采用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家格雷马斯的叙事语法来分析《蝇王》的角色模式及其深层意指结构,那么,我们对作品主题的把握将会更加深刻。
角色模式,是格雷马斯在普罗普总结的民间故事七种行动范围的基础上,进一步简化提出的叙事文中所包括的六个行动位的模型。这六个行动位是:主体、客体、发出者、承受者、帮助者、反对者。根据格雷马斯的观点,叙事文中追求某种目标的角色与其所追求的目标之间构成了“主体”(subject)与“客体”(0bject)的关系。主体既然要追求某种目标,那么就可能存在着某种引发其行为或为其提供支撑的力量,格雷马斯称之为“发出者”(sender)。发出者很多情况下可能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也可能是某种抽象的力量。而获得目标的人称为“承受者”(Receiver)。主体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可能得到朋友的帮助,也可能受到敌对势力的阻挠,格雷马斯分别称之为“帮助者”(Helper)和“反对者”(0pponent)。据此,《蝇王》的角色模式如下:
主体:拉尔夫
客体:得救
发出者:理性
承受者:孩子们
帮助者:海螺、眼镜、猪崽子、西蒙
反对者:杰克、“野兽”
格雷马斯还提出了著名的研究文本深层意指结构的“符号矩阵”。它是对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命题与反命题的扩展。格雷马斯认为,文学叙事模式源于x与反x的对立。随着叙事的展开引进了新的因素,有与x矛盾但不一定对立的非x,有与反x矛盾但不一定对立的非反x。当这些因素及其之间的关系充分展开,文学叙事便得以完成。符号矩阵位于文本结构的深层,与特定的意识形态内涵相连,标明了文本的意义系统。
在《蝇王》中,拉尔夫代表启蒙思想体系的核心——“理性”,杰克野蛮、专制、疯狂地嗜血残杀,始终与拉尔夫作对,代表“反理性”。一大批出于对野兽的恐惧和对猪肉的垂涎而支持了杰克的一帮孩子,代表“非理性”;猪崽子和西蒙象征着科学、民主和美德,代表“非反理性”。于是,孩子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就构成了理性与反理性之间的斗争,进而隐喻了启蒙过程的展开及其失败的过程。
在《蝇王》中,理性精神显得如此虚弱无力,它无法拯救孩子们,无法约束他们的兽性。在远离文明的孤岛上,人性中固有的非理性的、恶的因子被饥饿、恐惧充分地激发。孩子们涂上脸拿着长矛像野人一样的嚎叫,疯狂地嗜血残杀。他们追杀野猪,甚至在雷电交织的傍晚,在恐惧和狂舞中杀死了善良的西蒙。在此,戈尔丁解构了此前的荒岛文学,一反理性必然战胜非理性,文明必然战胜野蛮的信念,让理性彻底失败,让野蛮毁灭了文明。
当然,在小说的最后,巡洋舰突然来了,孩子们还是得救了,目标还是达到了。但这个目标的达成更带有讽刺意味。因为在格雷马斯的角色模式中,发出者“理性”才是支持“主体”拉尔夫追求“客体”“得救”的决定性力量。对启蒙思想家来说,理性是整个启蒙思想体系的
核心,是拯救人类的新的上帝,是绝对的权威,也是必然的胜利者。而在《蝇王》的结局中,最后真正使孩子们得救的,并不是拉尔夫代表的理性,而是巡洋舰的“偶然到来”。至此,启蒙思想中至高无上的“理性”被小小的“偶然”置换,其中的反讽意味是明显的。
那么,启蒙现代性的方案是如何被扭曲、异化并最终失败的呢?作为一个现代性寓言,我们不得不再次考察小说的三个基本隐喻:海螺、眼镜和野兽。海螺主要体现价值理性,代表民主、正义的价值观念,与象征专制、邪恶的野兽相对立。眼镜是维持火堆所必需的工具,它一直是孩子们得救的希望所在,象征着科学在人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小说中“眼镜被抢”的情节显然具有某种象征性。在一个夜晚,已经另立山头,堕落为野蛮人的杰克一派抢走了猪崽子的眼镜。不是用它来维持火堆发出求救信号,而是用它来点火烧烤野猪。此后这副眼镜一直炫耀性地挂在杰克这个专制者的腰间。眼镜作为科学的象征,代表工具理性。它价值中立,遵循功效原则,既可以与海螺互补(前期它一直挂在猪崽子的脸上),也可以与野兽互补(后来它挂在杰克的腰间),并且制造出更大的恶(杰克放火烧岛,要烧死拉尔夫,毁灭整个岛屿)。无可否认,科学是启蒙精神最重要的内涵之一,正是科技的发展使得现代性的诉求得以实现,但科技在促进人类发展的同时也隐藏着巨大的危机。小说的结尾,巡洋舰救了孩子们。这个结尾的象征意义在于,巡洋舰是对眼镜的替换,它代表着更强大的工具理性。它可以救人也可以杀人:它把孩子们从岛上的争斗中解救出来,却是带向了成人世界更加残酷的争斗之中。
同时,工具理性使猪崽子迷信科学的力量,却缺乏对人性黑暗的体察。他和拉尔夫都在雷电交加的夜晚,在迷混的状态下参与了杀害西蒙的狂舞。但事后拉尔夫受到良心的谴责。猪崽子却坚持认为这只是一场意外。我们似乎感受到了缺乏人文关怀的工具理性的冰冷。
事实上,戈尔丁在此表达了对科技、对工具理性的反思。工具理性的片面发展,可能导致整个启蒙现代性方案的扭曲和异化。一旦工具理性压倒、宰制了价值理性,两者出现了分离和对立,世界将变成一只“铁的牢笼”。
由此,我们更深地理解了小说中的“野兽”到底是指什么?从小说对孩子们毁灭文明,堕落为野蛮人的描写来看,“野兽”隐喻着人性中潜伏着的兽性。兽性不仅存在于岛上的孩子,也存在于岛外的成人世界。正是成人世界野蛮的核战争把孩子们带到了荒岛上,而他们在荒岛上的经历又重现了使他们落到这种处境的历史的全过程。可以说,巡洋舰意味深长的出现和核战争恐怖的背景表明:兽性正是工具理性过度膨胀,人们的道德自律变得虚妄,价值取向失去了规约之后所导致的疯狂。从这个角度看,《蝇王》所展示的就不仅仅是野蛮战胜了文明、非理性战胜了理性,而是文明的本质中深藏着野蛮,理性的内核中深藏着非理性。
小说的结尾是一种带着希望的绝望。军官的到来拯救了拉尔夫和孩子们。启蒙思想家心目中理想的人仍然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在这里戈尔丁似乎给读者留下了关于一个未来世界的幻想。这让人想起哈贝马斯的论断:“现代性计划”——“启蒙计划”还没有完成,还有着巨大的未实现的潜能。想起他以“交往理性”来重新整合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审美伦理理性的努力以及他对“新理性”图景的重建。也许这是一个新的乌托邦。但无论如何,对理性的反思,而不是对理性的迷信,才意味着真正的“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