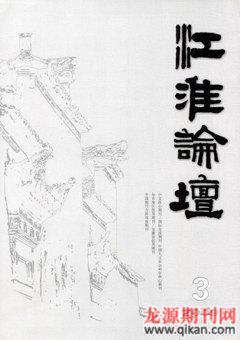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道德精神
余京华
摘要: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有一种强势研究误区,即把马克思唯物史观视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真理学说,忽视甚至否认其“真”背后的“善”的价值取向。实际上,马克思唯物史观不仅是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的学说,也是批判资本主义、诉诸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的“善”的学说,内蕴深厚的道德关怀精神、科学的道德批判精神和强烈的道德实践精神,是真与善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马克思; 马克思唯物史观; 道德精神
中图分类号:B019.1文献标志码:A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石。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一生中有两大发现,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1]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唯物史观仅仅视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真”的学说,而忽视甚至否认其的“真”背后的“善”的价值取向。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正统派”理论家由于片面的经济决定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倾向,把唯物史观只当作一门严格的科学,否认它的价值性,特别是其对无产阶级和人类的道德关怀精神。1918年考茨基在《伦理学与唯物史观》中写道:“甚至连作为无产阶级组织的社会民主党在其阶级斗争中也不能没有反对剥削和阶级统治的道德理想和道德义愤。但是,这种理想在科学的社会主义中是找不到的,而科学的社会主义是为了认识无产阶级斗争的必然趋势和目标而对社会有机体的发展和运动的规律所作的科学考察。”[2]伯恩斯坦强调,作为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基础,唯物史观需要用新康德主义伦理学加以补充,唯物史观只有经过伦理道德因素的改写才能有效。时至今日,国内外很多学者仍在不同程度上忽视甚至否认唯物史观蕴涵的道德精神。
今天,在唯物史观研究领域,学者们多从哲学、经济学、法学或史学角度来认识唯物史观,亦或从本体论、认识论或方法论视角来理解唯物史观,其共同特征是普遍关注对唯物史观的科学维度的把握,忽视了对唯物史观中与科学维度相辅相成的另一个基本维度——道德维度的把握。国内外学界至今还没有一部独立、系统地研究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道德精神的书籍问世。论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道德精神的文章也是屈指可数。这是唯物史观研究的不足,也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缺憾。实际上,如果我们系统研读唯物史观的经典文本,深入反思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认真剖析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社会功能,就不难发现,唯物史观不仅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真”的学说,也是批判资本主义、诉诸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的“善”的学说,内含着深厚的道德精神。
一、马克思唯物史观是历史发展规律与终极人类道德关怀的统一
唯物史观是否具有对人的道德关怀精神?正确回答这个问题,要求我们深刻分析唯物史观的创立目的。一种理论体系的创立目的直接决定该理论的性质与特点。马克思早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说过:“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4]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他明确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5]18-19在和恩格斯共同创作的、第一次完整表述他们的历史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巨著中,他写道:“人是人类全部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基础。”[6]恩格斯也指出,人是一切活动和一切关系的基础。哲学的出发点、前提和根本立场取决于对人的理解,哲学的发展状态取决于人的发展状态。马克思的哲学创造活动的全部努力集中在以“人类世界”为中心、以“实践”为本体,构建一种科学性与价值性(包括道德价值)相统一的哲学形态。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高举着“为绝大多数人(包括其中的每一个人)谋利益”的旗帜,亦即实现每个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的发展,这是人类一切道德诉求的制高点。
马克思反对所谓的“道德中立”论,反对隐藏或削弱自己学说的积极性和道义性,毫不掩饰自己对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道德诉求。我们只要读一读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致卢格的信以及《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就能知晓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目的和使命。他看到了政治解放的局限性,指出“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7]435把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联系起来,提出了“人类解放”的口号,把对无产阶级的道德关怀升华到了人类的道德关怀的崇高境界。正如梅林所言,历史唯物主义不但不否认道德力量,甚至还是最先使人能够解释道德力量的。唯物史观不能归结为人道主义,但却包含着有史以来最人道的精神,终极人类道德关怀则是其人道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
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不是为了纯粹地揭示社会发展规律而去科学地解释客观世界,不是为了建立某个历史学派或哲学流派,也不是出于纯粹的理论兴趣,而是为了变革旧世界,建立一个“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人道化社会,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人类的解放、自由和全面发展是最根本的道德理想,是一种终极人类道德关怀。它与宗教所宣扬的终极道德关怀有着质的区别,后者把宗教信仰作为基础,以上帝为最后的精神寄托,以抽象的人为出发点,是非理性关怀形式。它使人沉湎于对未来处境的幻想,不可能真正解决现实问题;而唯物史观是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以社会发展规律为依据,以革命实践为手段,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的终极道德关怀,是对人类的理性关怀形式。它激励人通过革命手段去摆脱需要幻想的现实处境,为解决人的存在问题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唯物史观不是空洞的人道呐喊,不是把对人的道德关怀建立在公平、正义、人道、良心等道德范畴的基础之上,而是把崇高的道德追求和价值追求隐含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冷静的剖析之中。在马克思看来,一切有悖于人的解放、自由与全面发展的社会制度,都是不道德甚至反人道的社会制度;建立理想的道德社会,必须建立人性化的社会制度,这需要首先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对人类生存与发展模式进行理性思考和道德反思。他强调要以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为依据来论证资本主义存在的暂时性,探索人类解放的可能性、必然性和现实途径。唯物史观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揭示,科学预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趋势,也就是揭示建立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的人道化的社会制度的可能性与必然性。[8]可见,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和对人类的终极道德关怀是唯物史观的一体两面。前者是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基础,而后者则是它的核心和目的。
唯物史观虽然是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学说,很少直接述及伦理概念和道德判断,但只要认真分析就会发现,其科学判断蕴涵着以科学判断为依据的道德判断,它既是一种严谨的“科学”,又是一种“人性”、一种“道德哲学”。马克思在唯物史观的创立、发展和完善过程中,运用科学实证的分析方法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运用价值分析方法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意义,把人的本质、价值实现,把对人的终极道德关怀建立在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这样,唯物史观既不是丧失人情味的冷冰冰的纯“科学主义”,也不是离开社会规律的道德空谈或抽象的人的价值悬设,它既使社会规律具有“为人”的人学价值和意义,也使诉求人类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道德理想具备了科学的理论形态,实现了历史发展规律与终极人类道德关怀的有机统一。
二、马克思唯物史观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科学的道德批判
要实现对人类的道德关怀,必须对反人道的资本主义现实作深刻的批判。德里达曾说:马克思最可贵的精神是批判精神。时代需要马克思,就需要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早在青年时代马克思就宣布,“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并公开申明“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7]416。
马克思主义以批判资本主义的面貌出现,批判的主要武器就是唯物史观。在唯物史观创立之前,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无情的道德批判,对马克思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具有重大启发意义。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时汲取了这种道德批判精神,但唯物史观批判又明显不同于以往的道德批判,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双重维度:道义与生产方式。它把道德批判建立在经济批判的基础之上,成为道德批判与科学批判相结合的完美典范。
一方面,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无情的道德批判。它从道义上强烈地谴责资本主义:“资本来到人间,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0]“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地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地‘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10]37它揭露资本家的贪婪,揭露利己主义是资产阶级道德的基本原则,批判资产阶级金钱道德的虚伪和丑恶,谴责资产阶级用公开、无耻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的剥削,进而抨击资本主义社会毁灭了人类既有的温情,使人类陷入一场赤裸裸的金钱与物欲的战争。正如《形态》所言:“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明显地呈现出社会是个有机体,暴露了社会的内在矛盾和辩证运动,而且由于撕去一切宗法的、宗教的含情脉脉的面纱,赤裸裸地显示了物质利益的作用。”[10]38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丑恶及不公正现象的道义批判无疑是辛辣而深刻的。
另一方面,唯物史观没有停留于一般的道德批判,而是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把道德批判建立在生产方式批判的基础上,实现了经济批判与道德批判的有机统一,彰显出其道德批判精神的道义性和科学性,避免了重蹈空想社会主义只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单纯的外在伦理批判的覆辙。马克思认为,对待资本主义只进行人文主义的道德批判终究是软弱无力的,它既不能真正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根源和运行机制,也不可能切实地找到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道路。恩格斯也曾指出:“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而只能看做象征。”[11]要达到对资本主义的深刻而清醒的认识,不能只诉诸道德批判,必须走向现实,研究那些被以往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们所忽视的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活动,“所以马克思从来不把他的共产主义要求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的、我们眼见一天甚于一天的崩溃上。”[12]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使“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0]36,但造成这种贫富分化的原因不在于生产力本身的高度发展,而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10]40不合理的生产方式造成工人劳动的普遍异化,工人生产的越多,得到的却越少、日益贫困,“自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产生以来,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从整体上来说,是变得更悲惨”,“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神奇地发展了社会的生产力,但是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它同自己所产生的社会生产力是不相容的。它的历史今后只能是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的历史。”[13]马克思正是在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中将资本主义的反人道性质一点一点地揭露出来,提出 “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科学判断,强调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彻底变革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切腐朽、落后和反人道的社会现象才会消失,人类才能真正获得解放,人道化的理想社会才能最终实现。唯物史观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科学地揭示出资本主义反人道的经济根源。它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只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外在伦理批判的抽象性、人文性和浪漫性,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科学的道德批判。
三、马克思唯物史观是超越理性的实践道德
实践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源头活水,唯物史观源自实践、关注实践又指导实践,主张通过群众实践来创造人性化的共产主义社会。它是超越理性的实践道德,内蕴强烈的道德实践精神。
1. 马克思唯物史观在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实践中彰显其道德诉求。关注人类生活与幸福的道德诉求如果脱离物质生产实践,不扎根于现实土壤,只是一种“真空”理论,在现实的人类实践中终会因窒息而自行消亡,或只能作为一种纯理论诉求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永远无法付诸实践。康伯内拉眼中的太阳城、托马斯·莫尔心目中的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者构想的理想社会模式,都因脱离现实、流于纯粹的道德批判而成为空中楼阁、海市蜃楼。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施蒂纳时说:“共产主义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14]50唯物史观与以往社会理论的重大区别在于,它不屑于纯粹的道义谴责,而是转向了现实的人类生活和生产实践,在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实践和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抓住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从现象到本质对资本主义进行层层剥离,剖析资本主义生产内在不可克服的矛盾以及资本统治活劳动的不合理性,在规律的层面上探讨资本主义产生的根据和被超越的根据,[15]在分析物质生产实践中展现伦理道德的内在经济本性,揭露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非道德性。它还从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来理解人的存在、本质和价值实现,首次赋予人类物质生产以人学的意义。唯物史观通过对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实践的内在矛盾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和未来发展趋势,将资本主义的反人道淋漓尽致地再现出来,将共产主义胜利的必然性公之于世,在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中彰显自己的道德诉求。
2. 马克思唯物史观在人的生存实践中寻求人性化社会的合理性根据。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虽然把人从上帝中解放出来,却只在“爱”的宗教中寻求人性化社会的合理性根据,“他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14]256 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虽然口头上也讲人的生存现实与状态,却从来没有深入人的生存实践去寻求未来社会的合理性根据,只是努力去探讨完善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途径,企图缓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削弱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自由解放的斗志。西方伦理学家始终只是从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或认识论角度逻辑地领会人的现实生存状态对于探求人性化社会的重要性。他们虽然也关怀人的存在状态,却将这一关怀彻底抽象化,只去探究主体内心道德体验应该指向善良还是指向幸福,而根本不考虑现实中人的特定存在状态是否道德和幸福;只关心人的存在的理想状态,即善良与幸福的概念化状态,而根本不关心现实中的人遭遇的种种不幸命运,如贫困和苦难。[16]与之相反,唯物史观的前提“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17]66,它重视既作为人性生长土壤、又作为人性现实内容的现实生活世界,重视人在现实中的“活法”。唯物史观所理解的人类存在的理想状态,决不是先验主体关于道德原则的某种“想法”或纯粹内心体验,而是人的现实生活状态的道德和幸福指向。它在关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特别是无产阶级的生存实践中去揭示现存社会的不合理性,寻求建立人性化的理想社会的合理性根据,力求从制度精神、生产方式变革和社会客观生存模式的角度来探索真正合乎人性发展的社会形态,探求适合新道德滋生的土壤,探究未来人性化社会的道德基础。马克思通过创立唯物史观,不仅要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且要确立一种关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道德标准,并以此为依据来改善人的现有的生存状态。
3. 马克思唯物史观在革命实践中谋求理想社会实现的现实路径。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7]61如何改变世界?以往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只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作出一般的道义谴责,没有对该制度进行深刻的经济学分析,因而无法找到颠覆这种制度的现实路径。马克思没有停留于一般的道义谴责,而是把以往思想家的纯道德批判转化为对不合理现实的经济学批判,转化为对人类生产方式的研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意识到实践对改变世界的重要性,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实现道德理想的提供了正确的途径。正如陈先达先生所言:“在人类历史上为穷人说话表示哀怜的思想家并不少,惟有马克思不是用怜悯,不是用眼泪,不是用抽象人道主义原则表示同情和抚慰,而是真正用科学理论揭示他们的处境和获得自身解放的途径”[18],这一途径正是实践,“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7]60马克思强调人的实践在改造不合理世界中的地位及作用,指出:“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达到目的本身,都必须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5]76-77唯物史观不满足于一般的道义批判,主张将道义批判化为人们的革命实践,在创造新生活世界的积极行动过程中使人自身获得自由解放。[27]这不是对道德的否定,而是对道德的扬弃,是从形式道德向实践道德的飞跃。唯物史观超越了资产阶级的抽象人道主义和费尔巴哈以“爱”的宗教为基础的抽象人本主义,也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忽视实践批判的纯道义批判,成为具体性、人民性和实践性相结合的实践人道主义,它实现了哲学历史观的伟大变革,用科学理论提供了人类道德关怀的实践模式。
四、结语
我们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学”学者及国内部分学者把马克思唯物史观归结为人道史观,反对他们把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化并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劝世箴言,但我们不能忽视或否认唯物史观所内蕴的深厚的道德精神。唯物史观本身是揭示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哲学学说而不是独立的道德学说或伦理体系,它没有排斥对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道德关怀,没有排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批判和对未来理想社会的道德诉求,更为重要的是,它不屑于空洞虚幻的人道关怀和抽象思辨的道德批判,而是将对人类的道德关怀、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道德诉求建立于实践基础之上,强调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必须通过革命实践来颠覆资本主义制度,实现自身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彰显出其道德精神的强烈的实践品质。因此,唯物史观是真正的实践人道主义、人民人道主义和科学人道主义。它越是科学,就越能转化为激励被压迫者起来为争取自身自由解放而奋起抗争的巨大道义力量。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石。马克思主义伦理道德思想的基本精神集中于唯物史观。深入研究唯物史观的道德精神,在理论上有助于丰富和拓展唯物史观的研究视域,突显道德价值在唯物史观中的重要地位,为解决当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与价值研究之间的矛盾和分歧提供理论依据,有助于深化和拓展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在实践上有助于我们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科学地实践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真实而科学地实施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强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德信仰,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和谐世界的构建。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6.
[2]转引自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慎之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139-140.
[3]李宜青.阿尔都塞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151.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7.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18.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8]胡贤鑫.《资本论》伦理思想研究[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7.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9.
[10]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9.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09.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43.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5]吕世荣、周宏.唯物史论的返本开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
[16]张盾.马克思哲学革命中的伦理学问题[J].哲学研究,2004,(5).
[17]马克思恩格斯先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8]陈先达.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
[19]高兆明.马克思的唯物史论与道德观三问[J].道德与文明,2007,(3).
(责任编辑庆跃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