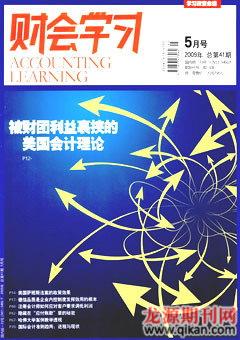中信泰富衍生工具损失案分析
杨荣华 李明辉
2008年10月,中信泰富公司因为从事澳元杠杆式远期交易而发生巨额损失,成为又一起衍生工具灾难。从表面看来,导致中信泰富巨额损失的原因是由于澳元兑美元汇率发生异常波动而导致的市场风险,但事实上,乃是由于该公司内部控制失控而产生的操作风险。在现实中,操作风险往往是衍生工具的核心风险。要有效地管理衍生工具的风险,必须要建立健全相关的内部控制。
◎事件的经过
中信泰富有限公司(Citic Pacific Ltd.,简称“中信泰富”,港交所:0267,OTCBB:CTPCY)于1990年在香港注册成立,2007年10月17日,公司在香港交易所上市。公司最大股东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香港集团)有限公司,其业务以基建为主,包括基础设施、能源项目、环保项目、航空以及电讯业务。
2008年10月20日上午,中信泰富突然停牌,下午5时发布盈利预警称,为对冲澳大利亚铁矿项目汇率风险,该公司自2007年底起签订了多份累计杠杆式外汇买卖合约,名义金额的总数达到94亿澳元之巨。由于2008年9月之后,澳元对美元的汇率大幅下跌,此项亏损将达其净资产600亿港元的近1/4,比2004年新加坡中航油集团5亿美元的亏损高出近4倍,为投资期货亏损最严重的事件。公告一出,市场哗然,投资者纷纷抛售该股票。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发布个人声明说,中信泰富目前正在澳大利亚建一个铁矿石项目,为了支付从澳大利亚和欧洲购买的设备和原材料,中信泰富需要澳元和欧元。而为了锁定美元开支的成本,中信泰富签订了一些外汇合约。但是,这些外汇合约的签订,没有经过合理的授权,而且这些合约中潜在的最大风险,没有被正确的估计到。在随后的相关公告中,中信泰富称,此次衍生工具巨额损失事件源于集团财务董事张立宪在未经主席批准下,进行有关外汇交易,张立宪连同财务总监周志贤已经请辞,并由莫伟龙接任财务董事。
2008年12月2日,中信泰富在港交所发布的股东通函首次披露公司与花旗银行、汇丰银行等13家银行签订的外汇累计期权合约细节。通函显示,中信泰富2007年8月至2008年8月间,分别与汇丰银行、花旗银行、摩根士丹利资本、美国银行、巴克莱银行、瑞信国际、法国巴黎银行等13家银行签订24份外汇累计期权合约,合约币种涉及澳元、欧元及人民币。股东通函还显示,由于澳元进一步走低,中信泰富外汇衍生合约变现亏损及公平价定值亏损总额已由11月12日公告中的168亿港元,扩大至186亿港元。
案件发生后,香港证监会自2008年10月22日起正式对中信泰富展开调查。目前尚未公布正式调查结果。
◎中信泰富巨额损失的原因:衍生工具内部控制失效
导致中信泰富发生巨额损失的,是该公司从事的澳元累计目标可赎回远期交易,该合同为澳元杠杆式远期合约,与欧元兑美元、澳元兑美元汇率挂钩。其实质,是一种累进期权交易(Dividend Accumulator Warrant,简称Accumulator)。累进期权一般由欧美私人银行出售给高资产客户。这种产品可以和外汇或者股票挂钩,通常合约期限约一年,最低投资额为100万美元(800万港元)。在Accumulator合约下,发行商(银行)锁定股价(或汇价)的上下限,并规定在一个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以低于目前股价水平为客户提供股票。通常情况下,银行向客户提供较现价低5%~10%的行使价。但当股价升过现价3%~5%时,合约就自行终止;而当股价跌破行使价时,投资者必须按合约继续按行使价买入股份,有些银行会要求投资人双倍甚至三倍的吸纳股份。因此,这种合约可以分解成两种障碍期权组合,一种是向上敲出的看涨期权;另一种是向上敲出的看跌期权,两者的条款一样。通常这种合约在签订之时,双方没有现金支付。投资人可以获得1个向上敲出的看涨期权,但应同时支付约定杠杆倍数的向上敲出的看跌期权给银行作为对价。在Accumulator合约下,投资人在牛市时可以以折扣价买入股票或者外汇,但在熊市时也必须按协议价格买人,因而风险极高,属于一种“锦上添花,雪上加霜”的产品。由于Accumulator这种在牛市中放大收益、熊市中放大损失的杠杆效应,其被香港投行界以谐音戏谑为“I kill you later(我迟些杀你)”。
据披露,中信泰富在2008年7月与多家外资银行签署了多份每月累计外汇远期合约,合约杠杆倍数绝大多数为2.5倍,行权价格为0.87美元。这意味着,中信泰富以0.87美元的价格购买一个澳元兑美元的看涨期权需支付2.5个看跌期权。当澳元汇率高于0.87时,中信泰富以低于市场价的0.87美元每天买入1个单位外汇而获利,但当汇率下降到0.87以下时,中信泰富必须每天以0.87美元的高价买入2.5个单位外汇。据中信泰富的公告称,该公司之所以要签订这些累计外汇远期合约,是因为其在澳大利亚建一个铁矿石项目,为了支付从澳大利亚和欧洲购买的设备和原材料,中信泰富需要澳元和欧元,因此,财务董事张立宪达成了一笔外汇衍生交易。只要美元兑澳元继续走弱,这项交易就能获利。然而现实是,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澳元兑美元不但没有走强,还大幅走弱,2008年7月到10月间,澳元兑美元下跌了约29%,从而造成公司巨额亏损。因此,中信泰富管理人员对澳元汇率的错误估计,是导致巨额亏损的直接原因。然而,从目前已披露出来的信息来看,中信泰富内部控制不完善,乃是导致这次事件的根本原因。
具体而言,中信泰富在衍生工具内部控制方面存在以下问题:
1、缺乏明确的授权。据中信泰富审核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此事是由于财务董事未遵守集团对冲风险政策,且在进行交易前未按规定取得主席批准,超越其权限所为而导致的。然而,作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上市公司,为何一个财务董事在未取得主席批准的情况下竟能签署如此巨额的合约?此外,在衍生工具交易中,前台、中台、后台部门必须相互牵制,而不能由少数人掌控整个交易过程,尽管目前案件尚没有完整的调查结果,但据称交易的原始材料上签名只有张立宪和另外一个交易员。这是否表明,中信泰富内部缺乏起码的授权与职责分离机制呢?
2、为投机目的盲目从事杠杆式衍生工具交易。(1)交易金额远远超过套期保值需要,投机成分重过套期保值。按照中信泰富的说法,签订相关合约是为了套期保值。但如果仅是套期保值,衍生品的合约头寸应与实际的业务头寸相接近,这样,当澳元汇率出现波动时,一边盈利、一边亏损,两相总计最终应相差不大,不可能出现巨额亏损。实际情况是,中信泰富通过签订杠杆式合约所得到的澳元远远超过其澳洲铁矿项目所需
澳元资金。据披露,预计铁矿项目直至2010年的资本开支,对澳元的需求为16亿澳元,而每年营运开支估计需要10亿澳元。因此,中信泰富合计对澳元的需求为26亿,然而,在澳元累计目标可赎回远期合约、每日累计澳元远期合约及双货币累计目标可赎回远期合约下(假设澳元为较疲弱货币),公司须接取最高总金额为94.4亿澳元。中信泰富现时预计铁矿项目之资本开支对欧元的需求为8500万欧元,而在双货币累计目标可赎回远期合约下(假设欧元为较疲弱货币),公司须接取的最高总金额达1.604亿欧元。因此,这一交易明显带有很强的投机性,绝非为套期保值目的而交易。(2)交易品种选择错误。Accumulator是一个高风险的投机产品,而不是用来套期保值的。中信泰富选择这样一个奇异衍生工具来套期保值(姑且认为该公司确实是为套期保值目的而签订这些合约),加之对外汇的走势判断失误,无异于自寻死路。事实上,中信泰富完全可以利用一般的外汇远期等衍生工具来达到套期保值目的。(3)合约条款明显不利于公司。根据合约,在澳元兑美元汇率高于0.87时,该公司可以以0.87美元的价格买人澳元,从而赚取差价。但这些合约每份都规定有最高利润上限,当每份合约达到最高利润(150万美元~700万美元之间)时,合约将终止。中信泰富手中所有的澳元合约加起来,理论上的最高利润总额仅为5150万美元,约合4亿港元。但是,如果该汇率低于0.87时,却没有规定自动终止协议。根据合约,中信泰富的澳元合约所需要接受的澳元总额高达90.5亿澳元(超过485亿港元)。这意味着,只要澳元兑美元不断贬值,中信泰富就必须不断高位接货,直到接货总量达90.5亿澳元为止。有人利用蒙特卡罗方法、按汇率历史波动率模拟发现,中信泰富在签订这笔外汇合约当时就亏损了667万美元。其原因在于中信泰富得到的1个看涨敲出期权的价值远远小于其送给交易对手的2.5个看跌敲出期权的价值。之所以会签下这样的条款,可能的原因是当时澳元兑美元的汇率坚挺,导致交易人员只考虑对冲相关外币升值影响,而未考虑相关外币的贬值可能。从这一点上,可以反映出交易人员风险意识的缺乏和从事衍生工具交易专业能力的不足。
3、没有制定严格的限额控制。一方面,在签订的合约中,只规定有盈利的上限,却没有规定止损点;另一方面,该公司没有对衍生工具头寸及其风险限额进行严格的限制,从而为巨额损失埋下了隐患。如果该公司规定有严格的交易限额,即便存在杠杆效应,损失也不会如此巨大。
4、没有及时止损。在衍生工具交易中,投资者需要随时关注市场因子的变化,并及时采取风险应对措施(包括终止合约、重组合约等)来控制风险。澳元自2008年7月中下旬便开始下跌,在以后长达3个月里,中信泰富一直没有及时制止进一步亏损。即便在事件发生后,中信泰富也没有及时平仓,其原因可能是寄希望于澳元兑美元出现回升。根据敏感性分析,事件发生时,澳元兑美元每贬值1美分,中信泰富就亏损9400万美元,每股就亏损0.33港元。如果澳元兑美元汇率进一步下滑,中信泰富的亏损还将继续扩大。
5、缺乏有效的风险识别与评估机制。(1)在交易之前缺乏风险识别与评估。企业在进行衍生工具交易前,务必要识别相关的风险并对其损失进行评估。尤其是,杠杆式外汇交易属于高风险品种,更要对其风险进行完整的评估,以确信其处于自身可接受范围之内。必要时,还需要聘请专业人士来帮助企业进行风险识别与评估。而据该公司审核委员会及荣智健的相关公告,由于早前澳元汇率急升,相关人员在交易之前没有评估澳元贬值所构成的风险。另据披露,张立宪和另外一个交易员在签订合约时,有事出差在外地,边打电话边下单,而没有详细检查和评估合同风险,也未请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查看合同详情。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公司整个企业风险理念的缺乏。此外,中信泰富签订的合约条款表明该公司交易人员只预期澳元汇率会涨,根本没有考虑澳元汇率会跌,在做出如此巨额的投资决策之前不考虑潜在的风险,对于一个担任重要财务职位的高级管理人员来说,幼稚至如此,是不可想象的。另外,中信集团事后披露,在中信泰富以往的有关交易中,一些银行存在误导可能,银行在推销产品时,没有将风险彻底向中信泰富解释清楚,无合适警示。但对企业而言,从事衍生工具交易之前不详细了解该交易品种的相关风险,而一味听信交易对手的推销,只能怪自己风险意识的缺乏。(2)在合约持续期间,企业也应当不断地关注风险因素并对其发生的概率和损失的金额进行评估。就此项交易而言,企业必须要关注影响澳元兑美元汇率的各种政治、经济、法律事项。在金融危机已经波及众多国家、澳元汇率不可避免地要下行的时候,企业交易人员以及相关的机构一直没有采取措施,而是赌博澳元汇率会上升,充分说明该公司风险识别与评估机制的缺乏。
6、风险管理机制不健全。即便是如中信泰富所言,该交易是少数管理人员越权所为,但这些合约在澳元汇率低于0.87时,必须要定期进行结算,也就是说,公司的相关部门应当能够很快知悉此项交易。那么,公司的内部审计、风险管理机构在较长时间内为何一直没有发现此项交易的风险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公司的风险管理机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7、信息披露不透明。(1)内部信息不畅。据披露,中信集团事前对此交易并不知情。据称,这与中信集团采用分散式风险管理模式有关。但即使这样并不等于集团(母公司)可以不关注子公司的风险事项,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该公司乃至整个中信集团内部信息与沟通机制不健全。(2)对外信息披露不透明。中信泰富在公告中宣称,2008年9月初,公司即已察觉到合约的风险所在,并中止部分合约,实时损失8亿港元。但直到10月20日,公司才披露巨额损失。在半年报中,也没有提及这项业务。中信泰富将推迟披露归因于金融海啸导致公司没能及时将部分合约平仓以及需要进行内部调查。笔者认为,中信泰富不能以需要平仓或者需要调查为由来延迟披露。毕竟,及时向投资者披露重大事件并要求投资者注意可能的风险,是公司的责任。法兴银行事件当中,法兴银行在公开披露之前对违规头寸进行平仓,也受到了投资者的诉讼。这更警示,企业在进行平仓之时,也应依照相关信息披露要求进行披露,以维护投资者的知情权。
◎对衍生工具内部控制的启示
可以说,中信泰富发生巨额损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金融危机引发澳元汇率下跌产生的市场风险,但更重要的是该公司内部控制不严而形成的操作风险。这充分说明,企业在从事衍生工具交易时,务必要完善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机制,尤其是要强化授权、职责分离、限额控制、风险识别与评估、内部报告等制度。此外,在观念上,企业管理层和交易人员必须要强化风险意识,避免盲目乐观,忽视市场中随时潜伏的巨大风险。并且,需要牢记,衍生工具的首要功能在于避险,而不是投机。
中信泰富案中,该公司从事的是杠杆式外汇交易。投机性强、风险高、杠杆率高是此类业务的最主要特点。我国一些银行曾开办杠杆式外汇交易,如交行的“满金宝”、中行的“保证金外汇宝”和民生银行的“易富通”。还有一些银行继续筹备并准备开办外汇保证金交易业务。但据银监会调查,参与这项业务的普通投资者,80%甚至90%都处于亏损状态。这种参与者高损失、低盈利的概率状况已近似于“赌博”。因此,2008年6月6日,银监会发布《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办外汇保证金交易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开办或变相开办外汇保证金交易业务;已开办的,应在通知印发后5日内,将已从事此业务客户数量、保证金总额、交易头寸总额、客户总体盈亏状况及目前已采取的相应风险管理措施等情况以书面形式一式两份报送银监会。此后在每月初5日内将上月情况逐月报送,直到已从事此业务客户完全结清交易仓位为止。透过中信泰富案及其他因从事杠杆式外汇交易而导致巨额损失的案例,我国投资者应当加强自身的风险观念,避免盲目投机。从监管部门的角度而言,则应当加强对衍生工具交易品种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