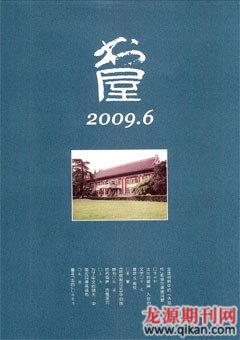香港的《字花》与文学的可能
张春田
面对今天总体上愈来愈困难的文学处境与颓败无力的文学生产现状,很容易就会想起希利斯·米勒当年极具震撼性的追问:“文学死了吗?”何况当你环顾周围,发现文学似乎不再那样吸引本应与它保持天然亲近的年轻人,“文学青年”成为带有反讽意味的称呼,与青年文学想象连带着的真诚、美好、激动、崇高、希望,甚至不安、忧郁、痛楚等等情感质素,在彻底商业化的“七零后”、“八零后”文学里几乎难觅踪影,这时,你的失望一定会更加强烈,也怀疑起中国文学的前途来。
可是,如果你相信文学如梦一样,只要人类还存在,注定要跟我们相伴前行;更重要的是,如果你不纠缠在怀旧:感伤和抱怨之中,而是细心地注意到身边日渐涌现出的那些年轻人的文学团队、刊物和作品;你就会感到其实并没有那么糟糕,在放逐文学的资本化时代里,新的文学空间、书写形式以及文学言说的可能性,却也在一点点艰难然而坚韧地生长出来。这种尝试和努力,正一步步获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关注和支持,香港的《字花》正是其中的代表。
《字花》是由一群在香港关怀着文字和书写的人组织起来的,他们年轻——都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业余——都有各自的工作;无名——都不是什么成名作家,但他们却都真切地关心着:“香港文学如何可以在更良好的土壤上开出出人意表、令人不敢逼视又难以漠视的花朵。”在一个往往被轻视为“文化沙漠”的地方,他们要为香港作证,他们愿意有更多的人能够分享学习和创作文学的乐趣,更期望以追求反叛、省察的文学与发生着激变的社会保持互动,撑开精神空间,来对抗庸俗、虚伪和各种宰制的压抑。从他们的理念上,也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满意主流的“七零后”或“八零后”文学想象力与创造力上的委顿,而试图开辟出另一片文学土壤,表达一个群体甚或七十年代末以后出生的一代人经验和记忆的全部真相。已经出版的杂志,都显示出他们致力于关注和言说出这一代人的经验。这里面凝聚了这代人文化创造的冲动和表达的迫切。从他们的杂志中,一种久违了的创作的困难与挣扎,还有对创作抱持的神圣感,频频可见。尽管他们现在才刚刚起步,并不成熟,但那种可贵的认真、执著和凌厉,让人根本无法漠视。
《字花》(Fleurs des Lettres)双月刊从2006年横空出世到现在,厚厚的十多期杂志,每期都会设定一个主题,比如,“买”、“恶”、“爽”、“假”、“色”、“乐”、“烂”、“木”、“热”、“咬”,等等,相当别出心裁。而这不仅是征稿主题,更是一个鼓励别人参与的创作过程。对于主题的诠释和铺展,将由广泛的创作上的互动来完成,这显然不同于相对封闭、单向的传统文学生产模式。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的是对创作的热忱和对自我的要求。无论是“喧嚣与躁动”下的犀利评论,“植字练习”给初写者提供的可以天马行空的舞台,抑或是“漫画奇劫文学”、“文学星座”中对于文学与图像、星座的“后现代式”嫁接,《字花》完全突破了一般文学杂志平板、单调和陈腐的格局,展现出“新”文学杂志的冲击力。对于《字花》而言,设计风格“不是外在末节,而是表达态度的核心”,每期充满创意的美术设计和视觉呈现,总是会让人眼睛一亮,文学杂志原来也可以做得如此缤纷漂亮、有型有品。但《字花》又并不让人觉得花哨,因为它的设计与文字,与杂志精神确实是贴合无间的。也许正是这些特色,让《字花》在短短两年里已经在香港年轻人中赢得上佳口碑,站稳脚跟,拓展到台湾,也受到不少大陆书友们的热烈欢迎。
我觉得,《字花》的创作、评论和设计,切入了当下年轻人的情感结构,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耐心地读下去,会发现就在那些对于成长痛楚、性别焦虑、边缘生存和情感状态、奇幻幽秘世界的书写背后,包藏着一代人碎片化了的精神史,甚至表征着这个“大时代”的症候图像。而且,他们又是以新的语言技术、视觉冲击来进行这种经验描述和表达的,挑战一般阅读期待视野的同时,也分明体现出他们更新审美理解和“文学观”的诉求。《字花》印刻下这群“文青”们重新定义“文学性”以及创造新的表达形式的卓越探索。这一方面证明香港的文学创作对于华文书写所具有的不可忽视的贡献;另一面,《字花》立足于置身的城市与时代,重建文学与在地历史、文化和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密切关联的行动,格外凸显了文学的尊严及其所集聚的能量。而这些,正是今天很多以“纯文学”为幌子的写作所缺少的。
描述自己的经验,创造新的艺术形式,说起来好像很容易,但实际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其中包括“隔阂”。比如,不是已经有太多这样的批评了吗:他们的成长中哪会有那么多奇怪的灰暗和痛楚,不可思议;写来写去都是迷惘哀伤的个人情调,没有大的抱负那些的文字和图片,根本看不懂;把杂志设计成那样,不过是靠拢时尚读物罢了……可是,在我看来,如果只是躺在庸俗的成功迷梦和僵化的文学观念中,不能正视今天年轻人与前人有着极大不同的生活经验和精神关切,不能理解文学在他们的生活世界里新的位置和功能,那么,所有过于轻易地批评,不仅是不及物的,也是毫无生产性的。在这个告别崇高的消费时代,如何去触碰来自于经验的无法承受之“重”,正是有追求的青年文学所不容回避的使命。从《字花》中,我看到了朝着这个方向的探索,以及所释放出来的能量。既然这样的能量能由他们释放出来,而且已经让更多的人感应到这种能量,那我们对于在青年文学中建立起刺穿或逸出主流意识笼罩的可能,不是应该更有信心一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