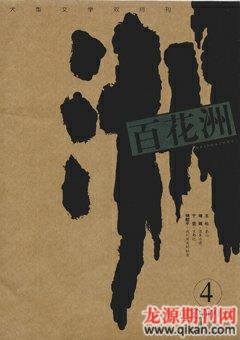打开小说之门
■在废墟上复活的生活细节
——谈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
对日常事物的精确书写,并不在于刻画事物的尺寸、大小、位置和样式。帕慕克的回忆告诉我们还原事物最重要的方式在于细节,在于使事物恢复它们当初的状态,一种旧时的状态。这就是小说家的伟大之处。《伊斯坦布尔》显然是一部不朽的杰作,与其说这是在回忆一座城市,不如说这是在回忆一个人,一个城市中的人,他到底是如何记下了这座城市。处于欧亚交界的伊斯坦布尔,在博斯普鲁斯的海峡岸边居住的人们,帕慕克这么贴近地在当代生活中如此巨细地书写了他曾经的生活、他曾经的时光。这不仅记录了城市,实际上是记录了一整个时代,或者说也记录了时代的所有可能,一个往前往历史那里一直向下去的时代。这是帕慕克式的趣味,只有读《伊斯坦布尔》,才能更好地了解他是如何写出《我的名字叫红》、《雪》这样经典的长篇。
看了这本城市书,我可以断定帕慕克一定是一位不朽的作家,这最大的不可取代之处便在于他关注了人的真正的存在境遇。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帕慕克是现在地球上所有人的同时代人,但是帕慕克真正回忆的并不是一个浅表的时代印记,他要书写的是人的经历,人的普遍历程,因此他必须提供他真实的关键词。这个词他自己说叫“呼愁”,直接讲出来便是忧伤。
好了,让我们跟帕慕克一起到伊斯坦布尔城里去吧。这是一个行将崩溃的帝国之城的遭遇,同时所有的光荣,绝不是可以恢复的模样。一种最大的模糊在于伊斯坦布尔很难被改写,它的城市趣味正在于它的失落、低沉、繁杂、坍陷、委靡,低首和收缩。它所有的城市形象,城市生活以及它的艺术处于一种自我的无止境的下坠和堕落,这是一种文明的忧伤。
这里的拜占庭建筑和回民建筑一样,始终有可能被剥离那层建筑的“铅”,几百年不再喷水的龙头,使我们从相反的方向追忆那曾经的喧哗。这千年似的沉寂,其实往往含有人类本身的矛盾,各种异质力量的角逐,以及处于亚欧交界这种地理位置本身的后果。实际上,伊斯坦布尔那近千万人口的现代城市风貌仅仅是一种短暂支撑起来的繁乱。
一个经过半个世纪的作家,叙述他自己的生活,你才会发现,那些“上等”的土耳其人,实际上对于西化有着强烈的渴望,对于宗教极端势力充满不屑,这正是土耳其最真实的现实——是欧洲,还是亚洲?是新文化,还是伊斯兰?处于十字路口的伊斯坦布尔虽然颓废,但不乏激情,尽管这激情本身更像一种迷惑。帕慕克是伟大的,他是一个独立的书写自己城市记忆的作家,他的忧伤是真切的。实际上他构筑的记忆中的废墟景象,有一种更强的道德力量,那便是废墟本身不再有浩劫和新动向。这正好反映了历史的现实,以及土耳其真实的现代化向度迷失。
■黏稠的第三世界
——读阿切比的《崩溃》
《崩溃》这部小说,在全世界有着极高的发行量,近年在国内引来众多读者。其实小说成书已有几十年,按照那些批评家的话说,是世界范围内,关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兴起,才使得阿切比的这部小说长期引人关注。但我读《崩溃》,并没有真正被所谓的后殖民理论所影响。我看那种理论对于小说以及小说中的现实,很难起到阐释的作用。《崩溃》的成功,其实并不在于别人所提到的从后殖民的视角去看待非洲传统和非洲文化的问题。我敢肯定地说,《崩溃》真正的意义恰恰不在于有了后殖民视角所取得的非洲传统的凸现,《崩溃》的最大意义在于非洲本身,在于传统本身的叙事,在于非洲自身。更直接的说法应该是,它是第三世界自身的真实在叙事中架构了非洲英雄的一生。
阿切比,长期居住在美国,用英语写作,有西方背景,在小说技法上,虽然也使用了一些西方现代派的技法,但总体上讲,阿切比还是非常“非洲”地讲述了一个非洲领袖的一生。而这个奥孔克沃的一生,由于时代环境的客观变化被分成了形式上的两大块,一部分是非洲内部的自足的英雄的成长和生活史,另一部分不可避免地涉及在白人文化和白人力量入侵后这位领袖的遭遇。我想跟读者强调的便是阿切比在描写奥孔克沃在非洲内部的成长史那一部分,我认为只有这一部分是这部小说真正的意义所在,我们发现在阿切比的叙事中,非洲部落、非洲传统、非洲的生活方式,是以它完整的自足的世界图景出现的,包括借种子、恶林、避祸、驱魔、部落冲突等。这些叙述段落,在非洲土地以上,在这种非洲自我的图解方式上,奥扎克沃,拥有他的妻儿,邻居,拥有他的同乡、追随者,同时他拥有了一份信念,这一切都完全陷于非洲内部的一种氛围之中。我把这种氛围称作“黏稠的第三世界”。
说它黏稠,是因为阿切比在这一部分里让奥孔克沃按照非洲的神性来处理土地上的一切行为,他所有的成长和事业,是不会折断的,是不会退缩的,是不被拆解的,它是一种精神。为什么是第三世界呢?我想读者会明白,阿切比是用英语写作,《崩溃》的成功是世界意义上的。《崩溃》的流行和可读,实际上和它的第二部分紧密相关,因为阿切比写到了白人和白人的入侵,两种异质文明在强弱悬殊的对比中交互作用。阿切比和这个世界,最终都要承认,“非洲”的崩溃,说的仍然是非洲在白人力量和白人文化的入侵中,它那受损害的部分的崩溃。这种崩溃,是非洲对于西方的整体的塌陷。而我更愿意指出的是,作为一种记忆,作为一种英雄,非洲的整体在它的内部、在它的信仰上,它仍然是黏稠的。所以我说奥扎克沃的一生,其实更应该是白人到来之前,“非洲”并没有崩溃之前的一生,那是黏稠的一生,不可折断的一生。
处于人类的底处,我坚信,任何一种文明和信念,它和它的人民之间,始终是内部的关联、始终是暗中的成长,崩溃的更重大的解释应该是一种陷落,是一种标差和身份的异质的说明。在它民族的英雄史诗中,它仅仅是呈现了一种最新的现实而已。
■塞林格的冰山
——读J.D.塞林格的短篇小说集《九故事》
我要称赞这部《九故事》,这是最好的故事,是最好的短篇小说,当然我曾读过的《都柏林人》很好,艾·辛格的短篇小说也很好,然而这些不是同一回事。我看重这个《九故事》的完整性,他们是塞林格的作品,他们是九个故事,是九个篇幅有限的故事。深夜我还在阅读,并在早晨5点写出对这个《九故事》的印象,我都不愿说是对它的评论了,它们确实是太过优秀了。这些故事到底是什么?好了,我先说,这个九故事潜藏的东西可能要超过海明威在《白象似的群山》里所做的,因为塞林格差不多在这样的短篇里,埋下了另一种永远不会被发现的可能,也许是世界本原的某种迹象,也许是只可用感知去够着的一点隐情。当然,叙事的遮蔽,无论有意无意,叙事无法穷尽真实,真实在《九故事》里以另一种特别的唯一的方式被连接在故事中,甚至是超越了真实,它回到了叙事的整个结构的缝隙。
好吧,我们看看是些什么故事。《笑面人》实际上很能说明塞林格的想法,一方面我们在听一个故事,同时故事中的人可能在组织一个故事。这个套路不仅仅是一种双重性,同时它也反对象征性。它是一种事实,只不过《笑面人》通过男孩回忆打捧球听教练讲故事的一段经历,回顾了记忆中的一点感性的认知,关于教练和他的女友的。然而《笑面人》更是那个有趣的笑面人故事本身,那个童年听故事的体验决定了童年真实的状态,这是最重要的。当然《笑面人》浮出来的东西还是够多的。当你阅读《就在跟爱斯基摩人开战之前》,你会发现女孩吉尼到塞利纳家要钱的故事其实本身是线性的,但当塞利纳哥哥说出了他与吉尼姐姐的一段无果往事之后,故事本身被抽离到纯粹与现实焦虑对抗的另一种精神状态里去了,这是塞林格的天才。
其实在《为埃斯米而作》中,这种叙事的隐形和浮托的均衡制造能力达到了一种巅峰,他把一个士兵×与十六岁女孩埃斯米之间有可能的人间情感状态压制到了一个近乎绝佳的水平,使得读者坚信十六岁的埃斯米有着全世界无可取代的美丽、纯真以及一种普遍化的情爱隐匿实质。她给士兵×的信,差不多能代表塞林格脱开小说家身份所能表达的对于人生最深情的眷顾了,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女孩会比爱斯米有更少的真情实感,而同时又不会有任何一个女孩能比爱斯米幸运,占据那最准确的叙事文本。在《威格利大叔在康涅狄格州》中,塞林格看起来是写两个老同学玛丽和依洛斯的喝酒聊天,实际上这个小说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塞林格对于个人史与历史关系的一种超凡脱俗的处理。这种方式是以玛丽一直劝慰依洛斯将曾经的故事告诉她丈夫,但依洛斯始终回避的纠结。这个叙述过程反映了一种美国式的叙事伦理,世界上的人可能很少真正有人像美国人那样如此单纯地看待个人史,如此将个人史看作一个人真正的成长史。在《威格利大叔在康涅狄格州》以及《嘴唇美丽而我的双眸清澈》中,塞林格显然以不同的视角真正道出了一种新大陆的忧伤和迷茫。这些差不多算是后青春时代的迷茫与《就在跟爱斯基摩人开站之前》的青春期迷茫一道,构成了塞林格独一无二的青春性审美伤感和一种艰巨的对于某种道德神经松弛的近乎告慰式的宣泄与惦念。
《九故事》是伟大的,然而在《特迪》中,塞林格有些出其不意地塑造了一个特殊少年特迪。当然关于冥想和清除,那是观念化的叙写,最重要的在于特迪和他父母以及妹妹的对话中,塞林格实际上是为我们还原了一个奇特少年的简单逻辑。正因为简单,所以当特迪与尼科尔森谈起那复杂的录音和预测时,我们才发现小说从第一个细节开始便是还原一种独立的发现式的生活方式。
塞林格是伟大的,他是一种美国式的伟大。当然从《九故事》里,我们还无法在美国历史现实和美国人的故事特质中间寻找到一条准确的观察途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必须简约的地方,塞林格是坚决把叙事的真正深层的动因压制到水面以下的,那是塞林格式的冰山。那《笑面人》一般双重结构的关照仅仅是我们的一种粗放的认知。对于塞林格而言,最重要的恰恰在于在那个被摁在水面以下的部分,它们有着更为深层的迷失和突围。这几乎是另一种本真的力量,与历史、事实和真相无关,是一种与叙述并行的不可更改的坚定的叙事热情和一种小说式的精神亢进与呼吸。在《嘴唇美丽而我的双眸清澈》中,灰头发与阿瑟的对话,实际上完整地再现了一种生活现实。在这个现实中,任何历史与宏观结构都已经消失、终结、退位和坍缩。对话中我们发现阿瑟对其妻子的担忧,实际上恰恰是这个世界最荒诞的一种絮语,它反映在一个人对自身高度清醒的认知中,一种语感上的恣意挥霍,一种在讲话中所渗透的对于叙事的一种近乎无节制的疯狂旋转。然而妻子回来了,他不忘跟老朋友说起他工作的案子的事情,这仍是一个双重结构,也可以说这个双重结构因为他在絮语中叙事,使得这个双重性,一直也是多重的,这本身也构成了一种叙事的迷茫。
通过《九故事》,特别是《为埃斯米而写——既有爱也有污秽凄苦》中爱斯米的形象,我们发现塞林格差不多是美国作家中、也是世界作家中,少有的真正有着青春体验的小说家。这种青春体验,甚至不是青春本体的,也不是主体本位的,它是一种跨越,是在一种叙事的疯狂与节制的天才控制中,从叙事的亢奋与哀婉并存的气质裂隙处看到的青春的放荡却谨慎的阴影。这便是一个十六岁少女爱斯米,她差不多是塞林格《九故事》里一个最不朽的形象。
■忧伤是他唯一的诗意
——读纳博科夫的《普宁》
《普宁》无疑是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尽管它的篇幅并不太长,但它那强烈的散文化的风格,它那流畅的叙事,以及那种浮现在任何一段文字里的忧伤的流亡者的气息,都使得这部作品具有不容争辩的经典性。与另一部《玛丽》相比,倒是《普宁》更加彻底地流亡化了,或者说在流亡这一本质性的情节书写上,普宁这个人物似乎比《玛丽》中的流亡者具有更大的承担性,只不过,此时的普宁不再是承担一种风险或追问,也不是承担对于那个他所出逃的社会现实的责难。相反,普宁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现实性,因为小说如此真实巨细,跌宕而又平静地讲述了教员普宁的现实生活,所以使得普宁即使在他的真实处境之内,也在他的流亡者的身份中,更加深刻地铭记着他在现实中的悲哀的印记。
实际上《玛丽》已经足够伟大,能够把一个流亡者等待过去妻子的那个有限的时间叙述得那么细微,已经使得流亡获得了它那普世的伤感的美学哀愁。但《普宁》实际上要更进一步。尽管《普宁》可能并不那么放肆与挥霍一个俄罗斯流亡者对于过去的追忆,但最为可贵的是,纳博科夫拥有超越一切写作者的异乎寻常的力量,将普宁的生活,以一种罕见的入微的嵌连事物深处的深沉的细密的交融,呈现出他在美洲的实际境遇,这似乎有时也暗示了一个从俄罗斯经欧洲巴黎再至美国的一个流亡路径。然而强大的青春化的美洲,却在真实的生活遭遇面前,呈现出它与流亡者气息之间那种无法沟通的基本的裂隙。这一裂隙也就决定了普宁的生活的每一步,都必将是有些危险的。这危险已经越过身份这一基本认同,实际上是他的生存,他的俄罗斯情感、俄罗斯形式、俄罗斯个人史,处在一个无法解释、无法告示、也无法现实化的绝境中。
《普宁》应该是遇到了哈根、劳伦斯、王京、贝帝等一些通融温情的美国人,但这也无法割除一个流亡者那长长的忧伤的影子。更为严重的是他的腔调,是普宁的腔调,一种极为温存、缓和的尊严,始终在被世界性的力量推残着、撕裂着、降低着,同时也在逐步地毁灭。普宁和丽莎的爱情与婚姻,这个流亡者与另一个流亡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普宁的好人性格的关系,使得俄罗斯温情获得了有限的保留,尽管这种保留恰恰对他的社会性存在构成了一种绝妙的反讽。普宁是个不错的男人,这一点很快获得了普遍的好感。但是仅仅在于他和他的事物之间、他和他的朋友之间,他那现实的最低限度的快感,也不过仅仅是让生活成为生活本身,生活无法获得还原,一切都和最简单的椅子、晚餐、烧酒和几近熄灭的情欲一样,都是无法再细分和追究的实际存在。普宁仅仅成了普宁,他永远失去的除了故乡,还有对那种记忆的可怕的触动。
陈家桥,1972年生于安徽六安,1990年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已发表出版小说作品三百万字。代表作有《爱情三部曲》《男虚》《女疼》《别动》《坍塌》《全贞谱》等十几部长篇。现从事媒体策划工作。
责任编辑 刘伟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