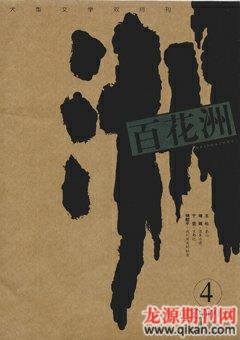王松的儒雅与野性
黄桂元
王松通常给人的印象近乎儒雅,这不是错觉,但也绝非其真相的全部。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刚读到王松两个中篇《数学系的大学生》和《黑旗镇》,就预感此君的小说路数诡异,将来定成气候。如今王松的小说风景已是森然万象,言行举止亦愈发气定神闲,却毫无“木秀于林”的得意。于是我常想,智性的雅者王松,与野性的锐者王松,哪一个更加真实?
说王松的智与雅,自然有小说为证;说王松的野与锐,依然可见证于他的小说。王松本是个血性之人,年轻那会儿骨子里时时律动着野性,甚至可以用“火暴”形容,这一点他自己也不讳言。当年在农村插队,一次因不甘凌辱,血气方刚的王松红着眼珠子竟抡圆了锃光瓦亮的尖锐铁锨,冲着一只脑袋削将过去!王松说那人太坏,专门欺负知青中的弱者。他手里的那把锨头比杀猪刀还要锋利,若不是那人闪得快,脑袋早就告别了肩膀。事后他也挺后怕,但实在忍不下这口气,也就不管后果了。那只脑袋从此受了刺激,一见了亡命徒王松的影子就躲。带着这股子野性,王松考进了大学数学系,安安静静读了四年书。然后他被分配在中学执教,同时也开始了完全不搭界的小说创作。再然后进了一家艺术杂志,我们成了同事。一天上午我照常上班,听到头儿的办公室传来一阵波涛汹涌般的激辩声。原来王松的一封私人信件被头儿拆开了,头儿说是把一摞信件捏在一起用剪子剪开的,王松的信不幸就夹在其中。无论这个解释是否成立,一般人自认倒霉也就算了,头儿毕竟是头儿,但王松认为这关系到对一个人最起码的尊重问题,非要验证这种事究竟有多少可能性,搞得头儿大光其火,事情便有些不好收拾。但王松终于没有失控,若依他年轻时的脾气,搞不好头儿的什么部位就会伤残的。
之后王松选择了调离,让自己距小说氛围更近一些。曾经研习的大学高等数学锻炼了王松思维的缜密、行文的精细与坚忍的耐性。人们发现王松变得用功了。其实王松的用功也只是近八九年的事。王松曾一度“混迹”于浮华、喧嚣的京城影视圈,写歌词,写舞台脚本,写相声段子,也导过北京电视台的综艺晚会,每日吆五喝六,烟酒相伴,光环闪烁,声色犬马,但他心里很清楚,那绝不是自己所希望的生活。上世纪末,王松放弃京城影视圈而回到天津居所专事所谓的纯文学写作,很为世俗不解。那劳什子已被社会主流文化挤到了边缘,能为他带来什么呢?神奇的是,从京城影视圈悄然消失了的王松,却令人瞩目地浮出文坛海面,被公认为中篇小说写作领域的一位高手。
今年仲夏的一个傍晚,我陪旅美作家陈九先生去王松家拜访。远在纽约的陈九曾细读过王松的部分小说,像《红汞》《双驴记》更是曾被他饶有兴味地“大卸八块”过,于是在那个傍晚陈九完全是一副有备而来的架势。在王松那间集书房、花室、会客厅和小说生产基地诸多功能于一体的“木华榭”里,两人脸对脸端坐于一条茶几的两侧探讨小说,一问一答皆京腔京调,只见两对镜片闪闪烁烁,然后似乎在瞬间定格了。我陷在两米远的沙发里看着王松,竟觉得有些恍惚。常年以小说写作为伴,使他看上去很像一幅剪影。王松在爱女萌萌的记忆里就永远是一幅寂寞剪影。小时候受爸爸的影响,萌萌也曾有过当作家的理想,之所以放弃,是因为她发现每天一早离家上学时,爸爸已经坐在电脑前写作了;黄昏时放学回家,朦朦胧胧之中看见爸爸还在电脑前凝然沉思,连坐姿都雷同得令人沮丧,就觉得写小说太单调也太辛苦了。王松不禁报以苦笑,那一脸的纹路也随之显露出深深浅浅的沧桑。王松第一次见到年轻同道红柯那一脸的“沟壑”,便不由得生出了一种惺惺相惜。他说皱纹常常构成了小说家的标志性相貌,长年累月、日复一日对着电脑屏幕敲字,内心随着没有终旅的小说故事延伸、人物命运起伏和形形色色的悲欢离合而抽搐,表情也被一刻不停地来回扯动,若不在脸上留下刻痕就说不过去了。
王松的小说叙述腔调也极为讲究,显得雍容典雅,绝不肯让哪怕一点点污痕脏了自己的语言。那样的雍容典雅其实是以血色为溶剂的,弥漫着生命的野生气息,同时饱含了成色十足的寓言智慧。无论凝结童年创伤记忆的“三红一血”(《红汞》《红风筝》《红莓花儿开》《血疑》),还是“后知青”系列的《双驴记》《后知青的猪》《眉毛》《哭麦》,皆深化了特殊年代里由“复仇”情结为精神引力的人生成长主题,充满了尖锐的艺术张力,富于鲜明的原创品格。这是王松的独门绝技,在当代文坛仅此一家,别无分店。
责任编辑 许 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