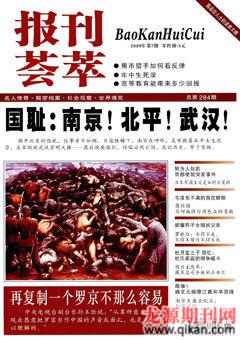“文革”中的知青典型怎么了?
刘小萌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纷至沓来,席卷城乡。许多知识青年,首先是那些典型人物,曾自觉或不自觉地投身其间。“文革”后期崛起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潮流”典型,更是深深卷入到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文革”结束以后,如何对待这些知青典型,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
“反潮流”典型的下场
在众多知青典型中,有极少数人如张铁生、朱克家辈是经“四人帮”亲自选拔而一跃成为政坛新星的。“文革”结束后,他们被定性为“帮派体系骨干分子”、“新生反革命分子”而分别受到法律惩处。
“白卷英雄”张铁生是最先受到点名批判的知青典型之一。1976年11月18日,《山西日报》发表《二月里的反革命噪音》的文章,揭露张铁生于当年2月在山西省煽动“层层揪”所谓“党内走资派”的言行,拉开了揭批的序幕。11月30日《人民日报》又刊载《一个反革命的政治骗局——“四人帮”炮制(答卷>作者这个假典型的调查》。调查揭露了“四人帮”制造这个“反潮流典型”的经过及用心。此后,各地报刊纷纷撰文批判这一事件对教育工作和对青少年思想造成的危害。
但张铁生的主要问题还在于他与“四人帮”的政治关系上。1977年9月中共中央37号文件将王、张、江、姚专案组编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下发全国。其中公布有“新生反革命分子张铁生的材料”,包括“白卷”影印件,中共辽宁省委关于张铁生的审查情况报告。报告称:审查证明,张铁生是“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和亲信毛远新等人一手炮制的假典型,真右派,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个反革命打手。报告在列举他“疯狂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主要事实(恶毒攻击毛主席;反对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恶毒攻击周总理、华国锋同志、叶副主席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对党的老干部怀有刻骨仇恨;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四人帮”被粉碎后策划上山打游击,搞反革命武装暴动)后得出结论说:“大量的确凿的事实证明,张铁生是一个死心塌地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报告最后举出张铁生生父的历史问题,以证明他堕落成现行反革命,是有深刻阶级根源的。
1975年12月张铁生在法库县作报告时曾慷慨自誓:“不怕当少正卯”。又说:“现在我在政治舞台上讲演,很可能有一天把我推到历史审判台上批判,这是我早就考虑到了的。”此话或出于一时心血来潮,最终却完全应验了。1983年3月,锦州市中级法院组成合议庭公开审判张铁生反革命案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张铁生没有委托律师辩护,拒绝法院为他指定辩护人。他在辩论发言时称自己只是一个不明真相的“小将”,在复杂的路线斗争中,犯了该宽容和谅解的“错误”。他还自我辩解说:“我那时头脑简单得像个牛犊子,只会鹦鹉学舌。别说野心,连私心我都严格控制着。我的目的正好与‘四人帮相反。反革命的帽子怎该扣到傻小子头上呢?”法院的判决书则确认,被告人积极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为目的,猖狂地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策动武装暴乱,妄图把辽宁变成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的基地,被捕后拒不认罪,继续坚持反动立场,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并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张铁生不服判决,以没有反革命目的,构不成反革命犯罪为理由,上诉辽宁省高级法院。终被驳回,维持原判。
1977年5月,张铁生的“知青战友”吴献忠、刘继业同时被捕。5月18日《辽宁日报》讯:锦州市和铁岭地区分别召开批斗、逮捕新生反革命分子吴献忠、刘继业大会。两地各有170万群众收听了大会的实况广播:那个一向以“彻底决裂旧传统观念”相标榜,敢于向老将挑战的著名典型柴春泽也在1978年4月锒铛入狱。9月13日《辽宁日报》发表署名共青团辽宁省委大批判组的文章《毒汁四溅的反革命黑信——批判柴春泽利用书信大造反革命舆论的罪行》。柴春泽同样被冠以“新生反革命分子”的政治帽子。
与此同时,曾为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器重的上海知青典型朱克家成为云南省揭批“四人帮”运动中的重点对象。1977年3月1日,云南省级党群系统召开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大会,集中揭批他“大搞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当日《云南日报》的报道,曾用“心惊肉跳,狼狈不堪”八个字刻画他在接受批斗时的神态。以后,他被当作江青集团在云南的亲信和代理人受到关押审查。如上所述,在1977年至1978年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这些知青典型均被当作“四人帮”的亲信和爪牙,按敌我矛盾作了处理。但在以后年代里,他们的经历和处境却由于种种原因而各不相同:吴献忠入狱有年,因牢房条件太差,几乎瘫痪。出狱后分配到锦州市农业研究所工作,与一位比自己年轻的农村青年结了婚。相比之下,朱克家则较为幸运。有关部门考虑到他犯错误的历史背景,最终对他进行了宽大处理,后来留在云南沾益的一个煤矿工作,从此销声匿迹。最富戏剧色彩的还是柴春泽命运的大起大落。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着手对历史遗留的各种积案进行清理,国务院知青办出面,提出对“文革”中犯过错误的知青典型予以解脱,让他们重新工作。接着,各省开始落实对知青典型的政策。这时,赤峰市所在的昭盟已划回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研究了柴的问题,认为他不够“新生的反革命分子”,于1979年12月宣布“无罪释放”。接着,他被恢复了党籍,公安部门同时宣布,当时逮捕他是错误的,给予平反。1982年他考入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赤峰分校,毕业后留校任教。
在当年名噪天下的“反潮流”知青典型中,张铁生是受惩处最严厉的一个。他在监狱中度过了漫长的刑期。1991年刑满出狱。当时,他对世间的巨大变化恍若隔世。最初想依靠有关部门分配“端个铁饭碗”,奔波数月劳而无功。想开个体医疗门诊,又苦于没有职称。后来进入兴城某饲料公司担任办公室主任,终日忙于工作,还学电脑,搞经营,事业上有声有色。他决心要“重新踩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路”。
事过境迁,20年后的今天,已没有多少人会再纠缠这些知青典型误入歧途时的个人责任,而会更多地探究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的社会原因。显然,将这些青年人陷入政治泥淖的原因简单归结为“四人帮”的教唆还是远远不够的。“文化大革命”本身不就是一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的颠倒是非的运动吗?中共十大制定的党章里不是堂而皇之地载入了“反潮流”的内容吗?再进一步讲,这些青年在政治上表现出的愚昧与盲从,偏激与狂热,与他们在学生时代所受的政治灌输又
何尝没有联系?我们不妨以吴献忠为例进一步剖析一下这个问题:
根据“文革”中有关她的事迹的报道,可知这个出身工人家庭的女青年在读小学时曾经爱好文艺,当时的憧憬是将来成为歌舞演员。小学毕业时获得全优成绩,于是放弃当演员的初衷,立志上大学。“文革”中,她曾怀着忏悔的心情回忆及当年的志向,认为这是“由于旧学校里资产阶级成名成家的思想熏染”,同时以感激涕零的语气回顾60年代初轰轰烈烈开展的学雷锋运动,认为正是那场运动的冲击,使她头脑中关于上大学,即“追求个人的所谓前途”的错误思想消失殆尽,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理想和前途。到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这个工人的女儿终于找到了实现自己理想和前途的最佳路径,那就是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接着,她以“闹而优”的战绩在同辈人中显山露水,被提拔为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和红代会主任,成为全校红卫兵的负责人吴献忠,《当一辈子农民开创一代新风》,《扎根农村大有作为》,人民教育出版社1973年版。这就是吴献忠下乡以前的成长轨迹,循着这条轨迹,才能把握她日后在政治陷阱中不能自拔的来龙去脉。总之,脱离“文化大革命”的特定政治背景,脱离“文革”前政治教育的偏颇,也就不可能理清一些知青典型之所以堕入政治深渊的头绪。
李庆霖虽不是知青,他的沉浮荣辱却与上山下乡运动紧紧连在一起。“文革”中,他大胆为困境中的知识青年鸣冤叫屈,当国家给知青落实政策的同时,他的命运也在不断改变,从小学校的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到县知青办副主任和县教育组副组长直至福建省高招办副组长和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随着地位上升,他深深陷入那个年代的政治漩涡中。从1973年底选上全国人大代表到,1977年初被隔离审查,他大红大紫的时光只有3年多。经历10个月的批斗审查后,1977年11月14日下午,他在福州被正式逮捕。这是经福建省委研究决定,“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批准”,在全省有200万人收听的实况广播大会上当场逮捕的。大会的批斗发言说他:“在历史上一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党对社会主义怀有刻骨仇恨。”认定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漏网右派”。这样一来,当年被省委第一书记亲自拔掉的“白旗”又重新插到他的头上,而且不仅是“白旗”,进一步升级为“漏网右派”。
在逮捕了一年零七个月后,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李庆霖“反革命案”作出判决。1979年法刑初字第001号的《刑事判决书》说:被告李庆霖积极投靠“四人帮”,多次写信给“四人帮”,诬陷中央、省、地、县委领导。1975年在北京受到江青的接见和赞赏。以后又与“四人帮”亲信派来福建的“联络”人员相勾结。串联“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提供了大量颠倒是非的材料,诬陷省、地、县委负责人,诽谤福州军区领导人,狂叫要与省委“对着干”,要改组福州军区和福建省委。1976年10月上旬被告在一次会上竟数十次以极其恶毒的语言点名攻击中央领导人。“四人帮”利用了被告诽谤的材料,打击、迫害省委领导。
判决书还认定他犯有“大搞篡党夺权”;“极力为坏人翻案”;非法建立“民兵指挥部”,“在各地刮起打砸抢妖风”;“在粉碎‘四人帮后,仍坚持反动立场”等罪行。
判决书认为,被告李庆霖积极投靠“四人帮”,是“四人帮”在我省的亲信,是猖狂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分子。罪行极为严重,民愤极大,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应从严惩处,但归案后尚能认罪。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十条(二)、(三)款之规定精神,判处反革命犯李庆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李庆霖不服判决。他承认有严重错误,但认为是按照上面部署干的,不应判无期徒刑这样的重刑。这种态度当然于事无补,等待他的将是漫漫刑期。
(二)为知青典型落实政策
除了前面讲过的一些经“四人帮”及其亲信赏识拔擢的“反潮流”典型外,其他一些著名知青样板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也多多少少受到冲击。如河南省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的薛喜梅,“文革”中在极左势力的影响教唆下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粉碎“四人帮”后,薛喜梅深感自己问题严重,多次写材料,并在大会小会上进行检查,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她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但仍长期未予解脱。为了及时解决自己的问题,薛喜梅曾多次给河南省委领导写信,均无下文。她又亲自到郑州找省委负责人,等了八天,没人理睬,只得失望而归。她的错误,还影响到妹妹人不了团,并连累了一些同学和他们的家长。一次,薛喜梅途遇一个同学的母亲,被拉到家里坐了一会儿。不料想,这位母亲所在单位即责成她交代与薛喜梅的关系。这种处境,使薛喜梅十分苦恼,感到自己似乎成了“瘟神”。
一些地方的“派性”加剧了知青典型的窘迫处境。到山西杜家山插队的北京女知青蔡立坚,是闻名全国的典型。“文革”结束后,山西仍旧有“派”,“反大寨”的一派被顺势挂到“四人帮”线上,一些干部为此被关押起来。蔡立坚也被莫名其妙地划入其列,于是新账旧账一起算。地区报纸拿出版面对她进行批判;地区知青办、团委联合召开批判会,中心议题是她怎样由红心变黑心;县委揭批查办公室提出给她以严重警告处分。她的县委常委、省团委常委、省革委委员等职务也被罢免。问题多年得不到澄清。
1979年初,辽宁省一些下乡知青中的老典型到省委上访,反映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对他们的定性和处理偏严过重,要求重新作出结论。知青典型高晓天在给省知青办的信中写道:
向党组织说说我的心里话。在我任职(注:高曾任生产队长)期间,和贫下中农一起大于,我们小队的粮食产量逐年提高,由过去的亩产一百八九十斤,一年达到八百一十斤,以后又增加到亩产一千三百斤。我对贫下中农和各级领导干部是热爱的。“四人帮”迫害老干部时,我做了抵制。七六年六月“放炮会”,毛远新一伙妄图利用青年整老干部,我一言没发。我由于疲劳过度患腰肌劳损,但自己咬着牙继续大干。七四年毅然放弃了升学。女朋友抽回沈阳时,我坚持留在农村,牺牲了个人利益。
“四人帮”及其死党出于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妄图把知青作为借用力量,我当时也被他们搬上了银幕、电台、报纸。对于他们别有用心的那一套,自己缺乏识别能力,没有抵制,也说过一些错话。回想起来很痛心。但我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应该一分为二。
十二月二十日,开原县清查办来了两个同志,向我宣布结论:“犯
有严重错误,是四人帮党羽亲信器重的人物,是他们极力培植的一个典型……”看了这些我想不通。说我是典型不假,但我是被他们称为“唯生产力论”的典型。难道我们生产队连续三年超千斤,多打粮有错吗?为什么一些搞清查的同志,不尊重客观事实,无限上纲?党中央一再提出要正确对待因受“四人帮”影响而犯了错误的青年,为什么基层老是落实不了?我要求组织把我的问题调查清楚,做出正确结论。
高晓天的信写得很诚恳,反映的问题也带有一定普遍性。这类知青典型长期生活在农村基层,在领导农业生产中取得了一些成绩。当然,由于政治上的幼稚和愚昧,在极左势力甚嚣尘上的日子里,他们中不少人也曾随波逐流,或盲目执行“上级指示”,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对此是应该谅解的,而不应小题大做,无限上纲。
辽宁省委对高晓天信中反映的问题很重视,主管知青工作的书记在他的来信上批示:对知识青年中老典型的处理,一定要注意政策。不能随意作“假典型”的结论,犯一般错误的知识青年一般也不要作结论。省委另一位负责人也批示说:“对毛远新、‘四人帮路线影响下树的一批典型,要作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要看他们的基本方面,不要过高地上纲上线。必要时可发一通报,使各地注意这一问题。”根据辽宁省委的指示,省知青办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对运动中处理的知青典型认真进行一次复查,重新处理,正确作出结论。
辽宁省是“四人帮”集团重要成员毛远新长期控制、经营的地方,知青典型为极左派领导人蒙蔽、教唆、利用的现象也最严重。辽宁省委提出给知青典型落实政策问题,对全国的知青工作都有借鉴意义。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不少知识青年中的典型人物给国务院写信或上访,反映对他们的处理过重。为此,国务院知青办曾在《情况简报》1978年第21期中以《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正确对待犯错误的知识青年》为题,专门介绍了辽宁省彰武县正确对待犯错误的知识青年的经验。1979年3月,《情况简报》增刊第14期又发表了辽宁省委正确对待下乡知青典型的报道。同时强调指出:对待知青典型,要做客观的、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他们中间,确有一些是搞“闹而优则仕”起家,靠追随“四人帮”爬上高位,成为帮派体系骨干分子的,如朱克家、张铁生之流,也有一些堕落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和民愤很大的刑事犯罪分子,对他们一定要彻底揭发批判,以至给予必要的党纪国法制裁。这只占极少数。绝大多数知青典型,包括那些下乡早、有干劲、成绩大,但又犯了某些错误,甚至犯了严重错误的知青典型,要注意保护。国务院知青办的文章还规定了保护知青典型的几条原则:可处分可不处分的,不要处分,不要追究个人责任,不要作“假典型”的结论。错误特别严重需要做组织处理的,也要采取“冷处理”的办法,或者调离领导岗位,或者下放基层锻炼,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再按照本人的表现做最后的组织处理。
1979年5月23日《人民日报》在刊载本报记者来信《老知青薛喜梅应该解脱》时,发表了编者按。编者按指出,正确对待下乡知识青年典型人物的问题,值得重视。对他们的错误,应该进行历史的分析。对他们说过的错话,不应该揪住不放。只要他们把问题说清楚了,有了认识并以实际行动改正自己的错误,就应该欢迎进步,为其解脱,做出妥当的处理。这样有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有利于巩固上山下乡的成果,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归根结底,有利于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在此前后,其他一些报刊也发表了同样内容的文章。
应该看到,提出给知青典型落实政策的问题,不单纯是为了纠正前一段揭批“四人帮”运动中出现的过火行为,同时也是出于“巩固上山下乡的成果”的现实需要。当时,全国知青的返城风已经如火如荼。不久,一些知青典型获得了再度辉煌的机会。
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虽然给了知青典型以放下包袱、轻装前进的机会,但至少对其中一部分人来说,他们因成为典型而付出的代价是无法补偿的。
典型人物多是年纪轻轻,下乡不久,即被领导看重,多方培养,并委以重任或加以桂冠的。然而一旦形势陡变,身份地位则难免不一落千丈。最令人触目惊心的还是1976年前后历史车轮的急遽转折,一些志得意满时人物因此被狠狠甩了出去,后悔莫及。与普通知青相比,典型人物的经历通常更坎坷,自不待言。
政治上大起大落是知青典型的普遍经历。不但昙花一现的“反潮流”典型如此,像邢燕子、侯隽这样的老知青样板又何曾例外?上山下乡运动处于高潮时,两人总是身兼高职,频频亮相于广播新闻中。1976年,侯隽被提升为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专职副组长,7月份调到国务院知青办工作。这中间,仅仅经过三个月,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她作为“有牵连的人和事”,受到审查。起因是,她任职期间,国务院知青办领导小组起草了一份《知青工作调查报告》,主持文件起草工作的是正组长和知青办主任,她作为副组长也参与了其事。粉碎“四人帮”后,中央领导人指出这份报告符合“四人帮”口味。侯隽的问题查清后,被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回原单位工作。1977年底,她回到阔别多时的宝坻县窦家桥,仍旧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
董加耕的名字,在60年代几乎家喻户晓。60年代初,他高中毕业后立志务农,被树为全国的知青典型。他的名言:“身居茅屋,眼看全球,脚踩污泥,心忧天下”成为教育青年学生时经常引用的座右铭。他的形象曾鼓舞许多青年喊着“学习董加耕,一心下农村”的口号投身于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与其他同时代的弄潮儿比,他以后的命运更显得坎坷。“文革”初,他受到冲击,多次受审查,特别在深挖“五一六”运动中被关押三年之久。以后在周恩来亲自过问下才获解脱。他先后担任过团地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共青团九大中央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1975年上调北京任共青团十大筹备组副组长,接着又被任命为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四人帮”心腹谢静宜是共青团十大筹备组的正组长。福祸相依,“四人帮”垮台后,董加耕顺理成章地成了被殃及的“池鱼”,受到审查。1977年秋才允许重返盐城。
1974年,因率领119名旅大知青奔赴昭盟草原而被树为典型的女知青王冬梅,在“文革”结束后,怀着沉重的心情谈到“典型人物”的“代价问题”。为了符合知青典型的“光辉形象”,唯有一次又一次地放弃上调的机会,关于当年的内心活动,她后来在回忆文章《被埋葬的青春梦》中这样写道:
我想上大学,想得发疯,但我心甘情愿不去,我不想扎根农村,我害怕嫁给牧民,但我心甘情愿留下,并且准备在这荒芜、落后、愚昧、贫穷、边远的地方呆一辈子。谁也没强迫我,我自己愿意,我堵死了自己上大学的路,还以为自己是个悲剧的勇士。
几乎每个知青典型都有过放弃上调机会的经历,换言之,没有这种经历也就很难取得典型的资格。他们的理想与追求,没等开花结果,已在一种窒息个性发展的氛围中过早凋谢了。为此王冬梅曾反问道:
我是那个时代的宠儿、骄子,但这些难道不是那个时代对我的伤害,对我灵魂的深深伤害吗?
当然,并不是知青典型在痛定思痛之余都有王冬梅这样的悟性。就王冬梅个人而言,她所付出的代价远远不止失去上调的机会。由于她的典型身份,父母必须一次次扮演“革命家长”的角色,在报纸广播中不断抛头露面,向广大知青家长进行现身说法。不但违心地将二女儿王玉梅也送往昭盟,最后,连自己也被迁到偏僻的赤峰。由于典型的身份,她本人付出了沉重代价。像她这样的典型,本来就是被时事“制造”出来的。要求上山下乡时,她年仅17岁,1976年受到批判、审查时也不过20岁,1979年才被解脱。多年后她深有感触地指出:知青典型,作为一种“政治道具”,被利用者高高举起,名声显赫。一旦风云变幻,立刻打翻在地,大批特批。而我们在心灵的大起大落中仅仅学到一点政治常识。这,就是典型的悲剧。值得庆幸的是,与其他知青典型比,王冬梅毕竟年龄很轻,这使她在身世浮沉之后,来得及重新设计自己的人生,1979年她考入了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记者。有的知青典型,至今不改“青春无悔”的旧调,王冬梅则不然,在回忆当年的那段经历时,她感到的只是“痛悔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