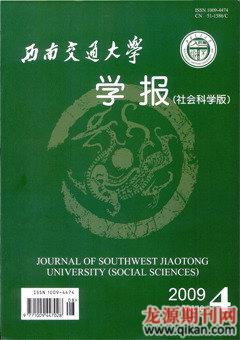论以意逆志对常州词派词学阐释学的影响
祝 东
关键词:以意逆志;常州词派;张惠言;周济;谭献;词学阐释学
摘要:孟子“以意逆志”说对中国古典诗学阐释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并辐射到词学阐释学领域,清代常州词派的词学阐释理论就是导源于这一阐释传统的。通过考察常州词派的词学阐释理论,发现自其创始人张惠言至谭献等人之间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他们逐步完成了将“以意逆志”之“志”由“作者之意”向“读者之意”的转换,最后将阐释的主动权完全交给了读者,给读者理解文本以充分的自由,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学阐释学理论的发展。
中图分类号:I207.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09)04-0015-05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被誉为中国诗歌阐释学的开山纲领,对后世的诗学阐释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云:
成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
孟子此处正式提出“以意逆志”之说。关于孟子此处提出的“意”,历代学者多有论述,大致有两个方面的解释,一派以为是读者之意旨,一派以为是作者之意旨。纵观两派观点,结合文本实际,笔者倾向于前种解释,因为它更符合孟子的原意。东汉赵岐在注解《孟子》时就是这样解释的:“意,学者之心意也”,“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因为人心是相通的,所以读者可以用自己之意去揣摩作者之意。宋人朱熹亦是这么认为的:“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近人朱自清也有同样的理解:“以己之意‘迎受诗人之志而加以‘钩考”。他们都认可“意”为读者之意。
孟子的这种阐释学思想给中国古代阐释学开创了较大的理论空间,“一方面,他肯定作者之志是一切阐释的目标,提倡一种所谓‘意图论的阐释学;而另一方面,他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却依赖于读者的主观推测,这就意味着承认不同读者的推测都具有合法性,从而成为一种‘多元论的阐释学”。正是因为这种阐释承认了读者的主观能动性,肯定了读者在重建文本意义中的重要性,故而乐于为人所接受。其对诗学阐释学的影响自不必云,还渗透到词学理论中来,不仅使有志于提高词体地位的人找到了佐证,而且对词学阐释学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在清代常州词派的词学理论中表现得尤为显著。
常州词派兴起于清代乾嘉之际,常州张惠言、张琦兄弟等人论词,首倡比兴寄托之说,其理论经嘉道之际周济、宋翔凤等人的进一步发挥,复历同光时期谭献、陈廷焯等人的深化和总结,最终形成了一套系统较为完整的词学阐释学理论。然考其精神内核,追根溯源,则还是对孟子“以意逆志”的诗学阐释理论的演绎发展。
一、引申自有无穷意,端赖张侯作郑笺
张惠言按其本意,并不是要以词学名家的。确切地说,他应该是名经学家,长于治虞氏《易》,又是阳湖文派的重要作家。考其治词,则为晚年余事耳。但是由于历史和时代的选择,他被推上了常州词派开山人物的高位,这一切源于他设帐安徽歙县金榜家为教学编选的一部《词选》,并做了一篇《词选序》:
叙曰:词者,盖出于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其词,故日词。《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然以其文小,其声哀,放者为之,或跌荡靡丽,杂以昌狂俳优。然要其至者,莫不恻隐盱愉,感物而发,触类条鬯,各有所归,非苟为雕琢曼词而已。自唐之词人李白为首,其后韦应物、王建、韩翃、白居易、刘禹锡、皇甫松、司空图、韩偓并有述造,而温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闳约。五代之际,孟氏、李氏君臣为谑,竞作新调,词之杂流,由此起矣。至其工者,往往绝伦。亦如齐梁五言,依托魏晋,近古然也。宋之词家,号为极盛,然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张炎渊渊乎文有其质焉。其荡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黄庭坚、刘过、吴文英之伦,亦各引一端,以取重于当世。而前数子者,又不免有一时放浪通脱之言出于其问。后进弥以驰逐,不务原其指意,破析乖刺,坏乱而不可纪。故自宋之亡而正声绝,元之末而规矩隳。以至于今,四百余年,作者十数,谅其所是,互有繁变,皆可谓安乖蔽方,迷不知门户者也。今第录此篇,都为二卷。义有幽隐,并为指发。几以塞其下流,导其渊源,无使风雅之士惩于鄙俗之音,不敢与诗赋之流同类而风诵之也。
由于乾嘉时期,浙西词派末流将词坛弄得萎靡不振,使得“淫词”、“鄙词”、“游词”充斥词坛。张惠言为了提高词的意格,引经据典,在经学中找到了“意内而言外谓之词”这个解释,进而论证诗词本是同源的,打破了词为小道末技的陈见,把词抬高到了儒家认同的正统文学的地位。既然诗词同源,就可以用解诗的办法解词了,于是张氏率先提出了用“比兴寄托”这一本属于诗学领域的阐释方法解词。在他看来,诗词一理,词中蕴含的比兴寄托与《诗经》、《楚辞》是一样的,看似描写风花雪月用资羽盖之欢的词作,实则继承着文学史上的香草美人传统,蕴藏着作者的别样情怀。这样解词就有章法可循,“触类条鬯,各有所归”,使得“义有幽隐,并为指发”,将隐藏在艺术形象之中的深刻寓意逐一剥离出来。如其评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
此感士不遏也。篇法仿佛长门赋,而用节节逆叙。此章从梦晓后,领起“懒起”二字,含后文情事,“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意。
评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
“庭院深深”,闺中既已邃远也。“楼高不见”,哲王又不寤也。“章台”“游冶”,小人之径。“雨横风狂”,政令暴急也。“乱红飞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为韩、范作乎。
评辛弃疾《祝英台近·宝钗分》:
此与德祐太学生二词用意相似。“点点飞红”。伤君子之弃。“流莺”,恶小人得志也。“春带愁来”,其刺赵、张乎。
以上皆是以己之“意”去逆作者之“志”的经典例子。如上面解读温庭筠的那首词时,张氏正是带着自己寒士阶层不遇之“意”,去逆“蛾眉”之“志”的,最后得出的结论正是“离骚初服之意”。正如叶嘉莹所说的,“任何一个人的解释都带着自己的色彩和文化背景”。每个解词者都带着自己独特的情感体验和文化背景去读词,所得出的结论当然是不完全相同的。同理,张皋文评冯延巳三首《蝶恋花》恋情词时亦是带着自己乾嘉之际寒士之意去逆词作之“志”的,其所得之“意”实际上是皋文自己
赋予作品的,只是他没有承认,而坚持认为这个就是作者之“意”,故而显得牵强附会,亟待修订。与此同时,张惠言的弟子金应珪在《词选后序》中也进一步论述了这种解词方法的历史性与合理性:
乐府既衰,填词斯作,三唐引其绪,五季畅其支。两宋名公,尤工此体,莫不飞声尊俎之上,引节丝管之间。然乃琼楼玉宇,天子识其忠言;斜阳烟柳,寿皇指为怨曲;造口之壁,比之诗史;太学之咏,传其主文。举此一隅,合诸四始,图归所会,断可识矣。
宋神宗由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读出东坡的爱君之情,宋孝宗由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读出稼轩的怨君之意,都是以意逆志解词方法的具体体现,从而证实了这种词学阐释传统的历史性。在他们看来,既然历史上早就存在,那么现今的这个阐释方法就有其合理性了。
张惠言的另一位弟子宋翔凤,也十分推崇其师以“比兴寄托”解词的主张。他在《洞箫楼诗纪》卷三《论词绝句》中,高度评价张惠言《词选》解释温庭筠词的方法和意义:“风雅飘零乐府传,前开太白后《金荃》。引申自有无穷意,端赖张侯作郑笺”。充分肯定张惠言对温庭筠词阐扬的功绩,而且将张惠言解释温词与汉代郑玄笺注毛诗相提并论。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张惠言先是在词体上做文章,把词体上升到诗、骚的高度,使得借用诗学理论来解词顺理成章,进而正式抛出了“比兴寄托”解词的理论主张。然而张氏的词学阐释理论未能事先肯定读者参与作品意义建设的合理性,而是单刀直入,硬是将读者之意说成是作者之意,且解说多附会政治教化,故深受诟病。如王国维言:“固哉,皋文之为词也!飞卿《菩萨蛮》、永叔《蝶恋花》、子瞻《卜算子》,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故而张氏的理论还有待充实完善。
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如前文所言,正是由于张惠言论词提出了比兴寄托理论,肯定了词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读者是可以以己意去迎取的,从而“触类条鬯”、“并为指发”,给词学阐释开创了理论空间,故常州词派后学乐于继承接受并重新阐发。嘉道时期的周济和宋翔凤依此提出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词学阐释理论就是对张氏理论的发展和深化,常州词派也正是由于他们的阐发推扬而大显于世的。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率先提出此一词学阐释方法:
初学词求空,空则灵气往来。既成格调求实,实则精力弥满。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宜,斐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知者见知。
同期稍后的宋翔风在自注论词绝句“引申自有无穷意,端赖张侯作郑笺”时也提出了这一词学阐释方法:
张皋文先生《词选》申太白、飞卿之意,托兴绵远,不必作者如是。是词之精者,可以仁者见仁知者见知也。
两人先后都依照张惠言的比兴寄托理论生发开去,提出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词学阐释方法。先看周济的论述,在这里,周济(保绪)重点强调了两个问题:其一,即是作者的创造问题,填词时做到语言形象和思想内容水乳交融,使之相得益彰,这样才算是好词,才是“无寄托”的作品。无寄托不是没有寄托,而是将思想感情融入到语言之中,达到化境,没有寄托的痕迹,浑化无痕。其二,正是因为有了“无寄托”的词作,读者在理解方面才可以依照自己的情感体验,以意逆志,进而见仁见智。
宋翔凤也是先陈述了张氏的寄托之论,但是马上笔锋一转,指出“不必作者如是”,一方面承认张惠言解词是掺杂着自己的意旨而有所发挥的,但是他用了一个以退为进的策略,即是承认这种解词方法主观色彩太浓,甚至穿凿附会。但是宋翔凤比张皋文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将张氏追求的“作者之意”置换为“读者之意”,尽管作者不一定有这样的意旨,但是读者不必拘泥于作者之意,故而“托意绵远”的作品读者可以以己意逆之,达到见仁见智的理解阐释效果。这就初步将阐释的主动权交给了读者,乐为常州后学继承发扬,此将在后文深入论述。这样两人就从理论上修订补充了张惠言词论的不足,为以意逆志的词学阐释理论进一步扩宽了道路。如周济评周邦彦的词:
美成思力,独绝千古,如颜平原书,虽未臻两晋,而唐初之法,至此大备。后有作者,莫能出其范围矣,读得清真词多,觉他人所作,都不十分经意。钩勒之妙,无如清真。他人一钩勒便薄,清真愈钩勒愈浑厚。
评吴文英的词:
梦窗每于空际转身,非具大神力不能。梦窗非无生涩处,总胜空滑。况其佳者,天光云影,摇荡绿波,抚玩无皲,追寻已远。君特意思甚感慨,而寄情闲散,使人不易测其中之所有。
周济推崇此二人之词作,正是因为符合他的浑化无痕的词学审美思想,这种浑化的词境“使人不易测其中之所有”。但正是词作的寄意没有被坐实,才使得人人都可以以己意逆词作之意,可自成一家之言而不易遭人批评,从而使张惠言以取类比附说的词学阐释理论大为改观。常州词派也正是到了周济这里才真正开始领导词坛,这与周济等人对常派词学阐释理论的修订完善是分不开的。
三、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
由张惠言等人的比兴寄托到周济诸人的见仁见智论,常州词派的词学阐释理论处在不断修复完善之中,但仍然存在不足,常州词派阵营里的谭献就深明这一点:
常州派兴,虽不无皮傅,而比兴渐盛。故以浙派洗明代淫曼之陋,而流为江湖;以常派换朱、厉、吴、郭佻染侄仃之失,而流为学究。
谭献指出了常派比兴说词所存在的牵强附会之病,这一点是常派的软肋,容易遭人诟病。如当时词学思想比较独立的谢章铤就曾指斥常派道:
皋文《词选》,诚足救此三弊(按:指淫词、鄙词、游词)。其大旨在于有寄托,能蕴藉,是固倚声家之金针也。虽然,词本于诗,当知比兴,固已。究之尊前花外,岂无即境之篇,必欲深求,殆将穿凿。夫杜少陵非不忠爱,今抱其全诗,无字不附会以时事,将漫兴遗兴诸作,而皆谓其有深文,是温柔敦厚之教,而以刻薄讥讽行之,彼鸟台诗案,又何怪其锻炼周内哉。即如东坡之《乳燕飞》,稼轩之《祝英台近》,皆有本事,见于宋人之纪载。今竞一概抹杀之,而谓我能以意逆志,是为刺时,是为叹世,是何异读诗者尽去小序,独创新说,而自谓能得古人之心,恐古人可起,未必任受也。前人之纪载不可信,而我之悬揣,遂足信乎。故皋文之说不可弃,亦不可泥也。
这段话直指以意逆志解词的片面性。盖自皋文到周济诸人,未能在理论上全面肯定读者之意的重要性,即读者在参与作品意蕴重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每一位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都存在他本人独特的期待视野,这种期待视野是以他个人的文化经历为背景的,故而提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阐释方法的前提是肯定读者的意义。故谭献申述道:
献十有五而学诗,二十二旅病会稽,乃始为词,未尝深观之也。然喜寻其憎于人事,论作者之世,
思作者之人。三十而后,审其流别,乃复得先正绪言以相启发。年瑜四十,益明于古乐之似在乐府,乐府之余在词。昔云:“礼失而求之野。”其诸乐失,而求之词乎。然而靡曼荧眩,变本加厉,日出而不穷,因是以鄙夷焉,挥斥焉。又其为体,固不必与庄语也,而后侧出其言,旁通其情,触类以感,充类以尽。甚且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言思拟议之穷,而喜怒哀乐之相发,向之未有得于诗者,今遂有得于词。如是者年至五十,其见始定。
此文回忆了其近三十年的学词经历,最后得出“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的深切体会,并且一通百通,始成定论。在此,谭献肯定了读者在阅读理解过程中的积极能动作用,认为词作不一定有寄托,但是读者在对词作的阅读、体味、联想、加工的过程中,可以以己意逆词之“志”,而这个“志”也不一定是作者的,读者可以见仁见智。这就在理论上第一次明确肯定了读者的主动权,摆脱了文学批评史上一直以来对作者之“志”的纠缠,由此再依照周济诸人的解词方法去阐释各种词作,就显得积极主动而不受羁缚了。如其分评冯延巳《蝶恋花》四阙道:
金碧山水,一片空濛,此正周氏所谓有寄托入、无寄托出也。此阕叙事。行云、百草、千花、香车、双燕,必有所托。宋刻玉玩,双层浮起,笔墨至此,能事几尽。
评苏轼的《卜算子·雁》:
皋文《词选》,以《考菜》为比,其言非河汉也。此亦鄙人所谓“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
他明确肯定读者之意而使阐释显得游刃有余,给读者以解读的主动权,使得常州词派比兴寄托、见仁见智的阐释理论得以巩固,免除了牵强附会的讥讽,修正并完善了常州词派自“以意逆志”繁衍而下的词学阐释理论。
总之,孟子的“以意逆志”的诗学阐释理论充分肯定了读者之意在参与作品重建中的积极能动作用,对中国诗学阐释传统产生了重要影响,并辐射到词学阐释理论之中,给常州词派的词学阐释理论以很大的启发。由张惠言张其绪,以比兴寄托说词,指出了读者之意在参与理解作品过程中的可能性,为常州词派后学建立了一个大体的理论框架,至周济、宋翔凤诸人则进一步将读者之意的重要性提高。但是他们没有分清读者之“意”和作者之“志”的关系,在阐释过程中易于将读者之“意”强加于作者之“志”上,显得生硬不适,直到谭献、陈廷焯诸人才将这一矛盾解决。他们给读者以充分的权力,将文本的解释权完全交给了读者,明确提出读者之意可以与作者之志无关,使得词学阐释的自由度大为提高,并有了充足的阐释空间,这样就维护并深化了张惠言的比兴寄托的词学阐释学理论。纵观常州词派的词学阐释理论,虽导源于“以意逆志”之说,但是又超越了这种阐释理论的范围,将中国古代一直以来以作者、作品为中心的文学阐释理论逐渐转向以读者为中心的文学阐释,推进了中国古代阐释学理论的发展,以至于和西方的接受美学理论达到了超越时空的暗合。
注释:
①见清代宋翔凤《洞箫楼诗纪》卷三,浮溪精舍丛书本。
参考文献:
[1]赵岐,孟子注疏[c]∥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2735,2735。
[2]朱熹,孟子集注[c]∥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306。
[3]朱自清,诗言志辨[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76。
[4]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7-48。
[5]张惠言,词选序[c]∥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1617—1618。
(6]张惠言,张惠言论词[c]∥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1609,1613,1615。
[7]叶嘉莹,清词丛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269。
[8]金应珪,词选后序[c]∥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1618。
[9]况周颐,王国维,蕙风词话,人间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233—234。
[10]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c]∥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1630,1632,1633。
[11]谭献,范旭仑,整理,复堂日记[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72。
[12]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c]∥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3485—3486。
[13]谭献,复堂词话[c]∥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3987—3988,3990,3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