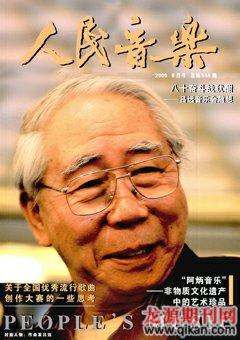“情境逻辑”:声乐表演艺术理论研究
程 军
在以往有关声乐艺术表演的文献之中,“情感性”和“炫技性”始终是作为表演的核心要义,高居于评判标尺之上。似乎歌唱的最终目的,终将只是指向对聆听者“情感”的引发。此般理论,在中西乐事中比比皆是,不一而足。譬如以歌剧为例,西方自十八世纪初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中的“美歌”时代(Bel canto),阉人歌手们为了能够毫不费力地演唱无比辉煌的华彩乐段,而进行种种精心训练,但这种对音色感观的极端追求,其结果却只是导致华丽之后的情感真空;而在浪漫主义时代,声乐体裁本身似乎便是为了担负“情感陈述”的职责,情感便是一切,常常自顾脱离歌剧文本的语境前提,最终因毫无节制的情感滥用而破坏了歌剧艺术综合美的有机性。歌剧史历经格鲁克、蒙特威尔第、莫扎特及至先锋派贝尔格、布里顿等大师的种种革新,其最终的目的,也正是为解答一个谜题:音乐和戏剧,究竟谁才是歌剧的逻辑。对优美音色和灵敏技巧的渴望、对充沛的情感渲染力的追求,在声乐艺术表演中,固然极为重要。但作为一门艺术,表演家们还应该有着更为清醒的主体意识。本文要旨,正是意在尝试提出一个声乐表演的理论概念,即:将“情境逻辑”作为声乐表演——尤其是歌剧表演艺术的依据之一。文中观点当属个人一孔之见,偏颇遗漏在所难免,敬请各位方家指正。
一、“情境逻辑”之学理界定
所谓“情境逻辑”,乃是英国美术史大师E.H.贡布里希于其煌煌巨著《理想与偶像》中,分析艺术发展动因时所提出的一个学理概念。他认为,“社会科学中有一种客观的方法,也许可以称为客观理解的方法或情境逻辑。一門客观理解的社会科学可以不依赖任何主观的或心理学的思想而独立发展。这就在于,详尽地分析行动的人们的情境,以便从情境中解释行动,而不必借助心理学。客观的‘理解就是,我们认为行为客观上符合情境。换句话说,尽可能广泛地分析情境,使那些最初像是心理学因素的东西,如愿望、动机、回忆、联想等,都变成为情境因素。把一个有这样或那样愿望的人变为一个处于追求这样或那样目标的情境的人。把一个有这样或那样回忆或者联想的人,变为一个处于用这种或那种理论或者这样或那样的信息装备起来的情境的人”①。
可见,“情境”二字绝非等同于“情节”、“主题”、“歌剧脚本”或者“舞台背景”、“作品风格”诸般概念。在歌剧的实践美学中,它意味着一个更为综合的理念,要求表演者对角色做更综合层面上的揣摩和把握。所以,“情境逻辑”作为一种分析视角,强调的是从客观的角度出发,从而避免空洞的抒情和盲目的炫技。对于现实表演而言,“情境逻辑”已经化为一种“语境”,我们可以从歌剧中角色的形体语言以及歌唱两方面,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首先,“形体语言”与“情境逻辑”之间的关联。歌剧中的动作行为,其比重虽不如话剧,但仍然担负着不可取代的戏剧使命。优秀的歌剧表演家除了能够发出自如优美的声音之外,还须妥帖地依从剧作情境,设计动作样式。这里的“情境”被理解为制约角色行为选择的“客观环境”,据此引发人物的行为选择。丝丝入扣于“情境逻辑”的形体语言,能够更好地推动戏剧情节的“起承转合”,使人物的形象刻画更为传神深刻。格鲁克在著名的《阿尔切斯特》前言(Preface to Alceste)这篇经典文献中对“动作必须贴和情境”的问题洞之若烛,他说道:“用音乐表达感情,遵循剧情的发展,不用无价值的浮夸装饰去打断动作或抑制动作。”②正确、真实的动作才能够和歌唱的内在激情相互配合、相互促进。《茶花女》第二幕中薇奥莱塔和阿芒的交锋便能深刻地说明这一点。剧中薇奥莱塔面对阿芒突如其来的造访,首先表现出一种优雅的敬意,因为他是爱人的父亲,但当阿芒粗暴无礼地要求薇奥莱塔离开他儿子,并谴责薇奥莱塔贪慕虚华引诱其儿子时,薇奥莱塔在形体语言上经历了从“凛然对抗”、“断然拒绝”到“痛苦挣扎”的动作形态。当阿芒终于知晓事实的全部真象,对薇奥莱塔报以同情之时,薇奥莱塔却又表现出一种“原谅”的神情。这种种形体语言,无不深深刻画出她虽为风尘女子但却无比高贵的内心,从而使观众对茶花女的悲剧报以更深刻的同情和怜悯。
世界著名的歌剧表演家们,除了拥有令人叹服的嗓音技术之外,也多能够从剧作本身的情境逻辑出发,去进行形体语言的塑造。比如《唐•卡洛》中因饰演伊丽莎贝塔而闻名的女高音格蕾•布鲁文斯蒂恩(Gre Brouwenstijin);男中音布林恩•特菲尔等等。传奇女高音琼•萨瑟兰女爵曾对年轻演员语重心长地告诫道,“有些年轻歌唱演员一上来就唱《安娜•波列娜》的终场,对我来说,这段不是入门者唱的,因为你得经由整部歌剧才能导向这个最终的场景”③。在这里,“整部歌剧”作为一种“情境逻辑”,制约着角色人物行动的发出,以及情绪的变化。萨瑟兰爵士隐约道出了歌剧艺术表演的一个真谛。 需要强调的是,注重台本的揣摩,虽然几乎可算是所有表演家耳熟能详之语,但对于真正把握“情境逻辑”而言却绝非仅此而已。正如美国著名音乐学家保罗•罗宾逊(Paul Robinson)所言,“文辞和故事仅仅是个开始。如果只是谈论文辞和故事,或许我们会总结出许多启发性的联系,但这些结论最终缺乏解释的力度,因为这种结论没能与音乐——区分歌剧与戏剧的主要因素——发生关联。歌剧首先是一个音乐现象,它的歌剧性妥协不会使我们脱离音乐的上下文”④。在歌剧中,音乐其实负载着更多的它真正想要表达的思想——无论是作曲家还是剧本情节本身的。这要求表演艺术家们,除了认真揣摩脚本角色和对生活经验的点滴积累之外,核心之处在于要能够把握住歌剧的观念所在。这其实也就是我们所一直在谈论的“情境逻辑”。譬如,要想真正把握住瓦格纳的《飞行的荷兰人》中角色的漂泊、彷徨之感,表演家们最好能够知晓这出歌剧和海涅作品之间的思想关联。
其次,情感的流露与“情境逻辑”之间的关联。“以情带声”已经是声乐艺术的权威信条,无人能够反驳。事实的确如此。问题在于,“情感的流露”是在“情境逻辑”的制约之下,即,只有依据“情境逻辑”,才能获得“真实的情感流露”,否则便是矫情,观众也很难理解这些情感的内涵。世界一流男低音马尔蒂•塔尔韦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当声音一进入良好的状态,音色立即呈现出来,而你在想的是唱的内容。声音是歌唱者的仆人,很多时候我有目的地唱一个重声音,因为声音只是仆人,而我们必须告诉我们意图表达的内容。一个歌手不能只是一口空摆着的钟。必须有钟声传达讯息”。可见,情感的释放必须具有一种“意图性”,它有自己的“情境逻辑”,而不是漫无来由的“滥情主义”。一位优秀的歌剧表演艺术家,将能始终保持着一种主体克制意识,小心谨慎地处理自己的主观情感和音乐本体之间的关联,绝不会过度沉溺于一种危险的狭小个人情绪之内。否则,对于作品的诠释,经不起审美的细致推敲和听觉考验,令人听而生厌,兴味全无。
二、“情境逻辑”的组成要素:以《费加罗的婚礼》为例
笔者认为,在歌剧表演艺术中,“情境逻辑”主要应该涵括下列两个部分:“戏剧本体”的“情境逻辑”、“音乐本体”的“情境逻辑”。前者具体而言,包括情节展开、人物关系和矛盾冲突、戏剧观念;后者则主要旨涉音乐主题、情感内涵、表现手段(音乐语言和技法)。“从美学层面上看,戏剧的本性主要在于它的空间性、造型性或曰再现性,而音乐的本性则在于它的时间性、抒情性或曰表现性。当这两者作为构成元素同时进入歌剧综合体之中时,一种神奇的对比互渗效应也就随之发生,于是便产生出一种新质,一种任何单一艺术所不可能具有的综合美感,于是便造就了歌剧艺术在美学品格上空间性与时间性的统一、造型性与抒情性的统一、再现性与表现性的统一、造型性与抒情性的统一、再现性与表现性的统一。”⑤这意味着,当使用“情境逻辑”去分析歌剧角色和内涵时,演唱者应当在保持清醒的主体意识之下,根据戏剧所提供的人物、情节、动作、冲突等等,去进行一种空间性和视觉性的描绘和构思,这体现为演员的形体语言、面部表情、台步的走法等等;而音乐作为一种主情的要素,将担负着以直入心灵的方式去揭示歌剧人物内心世界最微妙、最精细、最隐秘的情感活动和心路历程,总之,戏剧所未能言及之处,音乐皆能补充,二者唇齿相依、不可偏废。只有充分理解上述情境,表演者才能恰如其分地诠释出歌剧的观念和意图所在,在舞台上展现出无与伦比的风采和吸引力。笔者在此试图以莫扎特的四幕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的“费加罗”形象为例,简要概述“情境逻辑”分析法对于歌剧表演的重要性。
首先,从“戏剧本体”的情境逻辑而言,关于该剧的性质、情节、观念,业界已经达成共识:这是一部社会喜剧,足智多谋的费加罗巧妙地惩罚了放荡不羁的伯爵,使其不能行使贵族陋习中领主特有的初夜权,体现了18世纪启蒙运动关于“理性”的思想潮流。这是一部人物众多、人际关系异常复杂的歌剧,所以,人物间的“冲突关联”是诠释角色时所要考虑的“情境逻辑”之一。比如费加罗和伯爵的冲突在于,荒诞放荡的伯爵意欲对未婚妻苏珊娜行使初夜权;伯爵和罗西娜的冲突则在于爱与背叛;费加罗和苏珊娜的冲突则在于忠诚与误解;伯爵与凯鲁比诺的冲突则在于爱与嫉妒。如此多的冲突,却在终场都达成和解,伯爵夫人的宽恕,使事件导向于“大团圆”式的结局。所以,我们可以将整部戏剧的思想观念具体分析为,莫扎特创造了一种真相与爱情的音乐论证,对人性的恶与社会的不公抱之以深切的人文关怀。于是,这里所谓的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在剧中情境,变具体化为“一个关于公正社会的幻想:每个社会成员既能实现自己的渴望,又不至于摧毁他人的梦想”⑥。
根据上述情境,费加罗这一人物的形象特征便将清晰起来。他是一个足智多谋、风趣诙谐的角色,否则也不可能帮助伯爵得到罗西娜,又如愿以偿地解脱苏珊娜的困境;他是一个傲慢自负的男人,否则他也不会误解苏珊娜真的和伯爵有染;他还是一个狂放不羁、情感强烈、自信无比的人物,否则他也不会常常用一种甜蜜而冷淡的语气,轻蔑地称呼“Signor Contino”(我亲爱的伯爵),给人一种颠覆既定阶级关系、仆人控制了主人的情感效应。如此种种,成为歌剧演员塑造“费加罗”这一形象时,所必要了解的“情境逻辑”,据此来揣摩、选择人物的动作、表情等等行为语言。
而“戏剧本体”中所未能揭示的种种人类间的微妙情感,则交由“音乐情境”来完成。笔者在此,主要拟选取重唱段落为例,剖析“音乐情境”和“戏剧情境”相互促进的效应。莫扎特天才般的音乐笔触,用重唱这一方式,绝妙地描绘出人物间错综复杂的关联、揭示了冲突下各个人物复杂的心绪和情感、推动着角色动作的进展和发出。比如,第三幕中的第十八分曲中的“Sull mandre”(他的母亲)“六重唱”,它是由发现费加罗是玛尔切利娜与巴尔托洛之子这一事件引起。“正如科尔曼所言,六重唱虽然是个玩笑,同时也是个和解的时刻:儿子和父母团聚,一个曾经受到奚落的未来儿媳也得到未婚夫的认可。”在六重唱戏剧冲突巅峰的时刻,即费加罗和其母亲拥抱,苏珊娜进来,在不明就里之下打了费加罗一耳光的时间,音乐的主题突然滑到下属小调,弦乐出现了不安的抖弓,帮助点明了此处的紧张情绪,“六人此时同时唱出不同心态——费加罗、玛尔切利娜和巴尔托洛表示理解苏珊娜的愤慨是出于爱情,伯爵和库尔乔仍是满腹气恼,但多少有点幸灾乐祸;苏珊娜当然是怒不可遏。他们六人重唱的丰满织体将音乐推至高点,并将音乐稳定收束在属调性C大调上——至此呈示部结束。”⑦敏锐的歌剧演员,在此处必定能够感受到音乐情境和戏剧逻辑的内在一致性,以此来调节自己的动作发出和转换,在情感的揭示上,也将采用一种真实自然的抒发和流露。因为,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情感,演员必须首先学会为情感的来由找到正确的通途。
结语:将“情境逻辑”作为声乐艺术
表演的语境
综上所述,“情境逻辑”对于歌剧艺术表演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在“戏剧本体”上,是诠释人物行为动作、思想观念的“情境依据”,又是“音乐本体”上进行情感塑造和表露的“客观尺度”。它具有一种“语境”力量,成为表演家们平衡情感抒发和理性控制二者关系的“调节器”。事实上,将“情境逻辑”作为声乐艺术表演理论概念提出,正是为了提醒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演唱虽然是一门主情的艺术,但是“情感”不可脱离于“音乐和戏剧”的“情境逻辑”。事实上,歌剧的“情境逻辑”研究还有很多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比如:在面对声乐单曲时,“情境逻辑”的解析方式如何执行?有没有可能提出更为全面和具体的“情境逻辑”分析方式?总之,歌剧是一门如此深奥的艺术,一位成熟的歌剧演唱者,只有不断地开掘戏剧之情境逻辑的各项要义和内涵,才能够在舞台上大放异彩、塑造出各种令人难以忘怀的经典角色。
①[英]E•H•贡布里希《理想与偶像——价值在历史和艺术中的地位》,范景中、曹意强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94-95页。
②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London:Macmillan Publisher limited, Vol.7,1989, p467.
③朱墨青《年屆八十的神奇女高音》,《人民音乐•留声机》2006年第12期。
④[美]保罗•罗宾逊《歌剧与观念:从莫扎特到施特劳斯》,周彬彬译,上海音乐学院2006级硕士论文。
⑤居其宏《歌剧美学论纲》,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⑥[德]沃尔夫冈•维拉切克《50部经典歌剧》,黄冰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8页。
⑦杨燕迪《莫扎特歌剧重唱中音乐与动作的关系(续)》,《音乐艺术》1992年第3期,第65页。
程军 西安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 张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