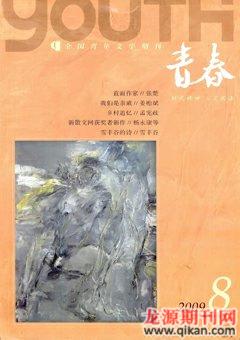仇人自远方来
屋子里都已收拾妥当,香也上好了,发出一股森幽绵远的气味来,暂时过滤掉了我们祖辈流传下来的贫穷和腐昧,母亲背靠在粮仓前还在擦拭着瓷器,喜得合不拢嘴,泛着老年人的贪婪的光。
我来到院子里像一名将军,检阅着眼前这繁杂庞大的军队,葡萄藤架起的庭院里,庭院里有的磨刀霍霍杀向猪,有的揎拳攘臂向酒坛,孩子们蹲在爆竹前张着耳朵,一旦有任何的声响,撒腿就跑,因为他们也不知道糖果放在哪了,跑是唯一的机会,爆竹一响,喜糖就撒在了地上。往高处看,彩色的灯盘旋在每一颗树上都乐开了花,极好地配合了我脸上的光辉,万事俱备只等我振臂一挥,锣鼓喧天,爆竹齐鸣。但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抬头望了望天,大海的蓝吹进了棉花的白里,阳光还不烈,至少还没有到眩晕的地步,所以细环还应该磨磨蹭蹭在梳妆台上。
细环是我的女朋友,我们青梅竹马地长大,等的就是这一天,这一天我提心吊胆地等了二十三年,这过去的二十三年里的每一天我无不是在恐慌和胆怯中度过的,没有欢乐,没有歌声,即使是赶路人的随便一声吆喝也会把我推进恐惧的深渊当中,久久爬不上来。
作孽啊,我的妈妈常常捶打着她的膝盖这样哀怨、叹息,随后抽泣起来。因为没钱,我也最终没有去成少林寺,就连城里面的奥林武校也没有去过。在我八岁的时候我曾经跟随过陈大力一段时间,陈大力是村子里唯一懂得习武之道,手脚稍微好点的人,主要是他长得还年轻,年轻就可以力壮,所以我指望就在他那学点东西,不再眼高手低了,但是在我跟随他的半年时间里他除了让我倒垃圾,端洗脚水之外,连马步都没有教过我,起初我还以为他是有意考验和激发我,但后来我才知道是我的电视剧看多了,他根本没有教我的意思,他还指示我去偷细环家的鸡,我当然没偷,我虽然没有学上武艺,但也不至于让我智力倒退,这是违法的事,何况那时候我就喜欢上细环了。
后来陈大力和他的徒弟们被逮了起来,我幸免于难纯粹是因为我的手脚既不麻利,头脑也不灵活。陈大力那天没有带我去,据说,他们那天劫上的偏偏是镇上武装部的部长。那部长一脚踢飞一群,其动作之娴熟,套路之简练,用放牛归来恰好路经此地的秀山的话说比看武侠小说还过瘾,当时,我妈妈特意给我装上了一篮子的草鸡蛋还封了两盒匣果,让我去找那个一脚踢飞一群人的部长。那个部长在听了我的来意之后,笑弯了腰,然后抚摩着我的头说,傻孩子这是什么社会了,快回去好好学习吧!祖国正需要你呢!然后我就回到了爨下填柴火烧饭,我的妈妈又开始抽泣起来,作孽啊,生了个儿子作孽啊,我觉得这是故意说给我听的,但我什么也不想说,嘴角动都不想再动了,这二十三年来,我已经习惯了。
二十三年前的一个蜜蜂满天飞的春天,我的哥哥一眼就爱上了面若桃花、长发如云的名叫桃云的女子,这个女子刚进村子就被我哥哥看上了,但问题就出在这个女人并不是来找我哥哥的,她是我堂哥黑粪的女人,并且马上就要结婚了,但我哥不管,那个女人也不管,于是那天晚上他们就用眼睛约好了似的来到村北面白花花的梨树林子里,在月光的鼓舞下,私奔了。
那是怎样的一晚啊,失去了未婚妻的黑粪一怒之下把我们家的房子点着了,火光冲天,噼里啪啦地他把他的爱情也烧成了灰烬。房子烧得那么旺,那么彻底和干脆,我的爸爸和妈妈索性连扑火都不想扑了,光着脚,流着泪,在火光的掩护下,在月光的鼓舞下,也逃跑了。
该怎么说呢,我得感谢我的哥哥,他沓无音信地离去,让我得以有幸降临人间,当我的爸爸知道他的儿子将再也不可能回来的时候,于是决定产出我这个替代品,以此延续香火。那时候我刚刚成型,我的爸爸以为一切风平浪静回家探视的时候,正好被黑粪一把抓住,两人迅速扭打在一起,可我的爸爸怎么是黑粪的对手,他被黑粪按死在了冷水缸里。黑粪也开始了他长达二十三年的牢狱生涯,临走的时候他还信誓旦旦地扬言,二十三年后他要让我们家还他一个老婆,一个面若逃花、长发如云的老婆。
可是到哪找去呢。几年之后,一个叫细环的女孩像一簇莲花不知不觉地那样开了,而且越开越水灵,七里八村的人都专程跑过来参观,我的妈妈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及时地把眼睛投向了细环,从此只要家里有点好吃的我的妈妈总是首先想到她,她已经完全忘记了我的存在,但每次从细环家回来她还是要扶着门框上长叹一声,作孽啊生了个儿子。起初我以为她说的是我哥哥,但后来我错了。他不停地催我北上少林,南下武当,而不是像其他父母那样送到幼稚园里,从大象的鼻子里滑出来,我每天所面对的只有硬邦邦的沙袋,尽管如此我还是体瘦如柴,力不从心,她说,我们就一起束手待毙吧。
我当然知道她的意思,如果找不到黑粪动心的女人,我们都将死在黑粪的手里,就连我的师傅陈大力都不是他的对手都怕他,那么村子里还有谁呢,除非我把他的桃云找回来,顺便找回那个让我有幸降临人间又让我极度厌倦了人间的哥哥,我倒想看看他到底哪方面有过人之处,让桃云迷得只能选择一起远走高飞。但找回他们已不是可能的事,他们肯定已不呆在镇子上了,现在整个镇子就数细环最漂亮,这已是公认的事实,所以桃云肯定是不在了,作为镇上公认的最漂亮的女人细环,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喜欢上我,就像人们也不知道桃云为什么会喜欢上我的哥哥,我们两个兄弟把这个镇上百年不一遇的美人都遇上了并且占有了,还有什么比这更光荣的呢,但我的妈妈就是没有想到这一点,她只知道生出来的是作孽的儿子,一个不学武术的儿子。
院子里,猪肉已经挂上了葡萄藤子,孩子们还在像狗一样趴着搜寻着糖果,我看了一眼天上,阳光有点刺眼了,我的细环应该已经出门了。
我回到里屋,戴上胸花,重新用水抹湿了头发,这样一来我精神多了。你知道怎么说了吗?我的妈妈把一些红枣花生桂圆瓜子塞进屋子里的每一个桌洞里,看着我。什么,我咕噜着一声。你准备好和细环怎么说了吗?她大了一点嗓门说,声音之突兀像破碎的冰渣。知道了,我不耐烦地说。我的妈妈刚想掠起袖子拍向她臃肿的大腿,继续她的那句经典台词,被我当场拦下,我说妈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别哭了好吗?我的妈妈沉重地叹息了一声,就抓起一把糖果出去了。
孩子们一片混战,在糖果的吸引之下,把高潮及早地挑起,就差爆竹和锣鼓的加入了。我的妈妈随后振臂一挥,像花木兰一样英武,响,于是天翻地覆的爆竹响了起来,乐队也开始了排山倒海的嚎叫,如五十弦翻塞外声,一时间,我们的庭院气吞山河不仅具备了沙场秋点兵的壮观,更弥漫着红装素裹的妖娆,我举手示意,新娘还没有到,但没有人理会我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男人,似乎他们才是今天的新郎,该吃的吃,该叫的叫,只有我一个人埋在葡萄架下的阴影里,心一点点地凉了。酒足饭饱的人们打着饱嗝,相互搀扶着,像垂败下来的军队,有气无力地在我的身旁走来走去,不断地有人把吃剩的东西带走,满地的糖纸,满院的风,一地破碎的阳光,就是没有我的细环。
我再次张望起天空来,日头上了栏杆,白云急速流转,我突然可怜起我的女人细环来,我什么都不能给她,连一场象样的婚礼都不能,现在算是什么样子,二婚都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我在鸡窝里找到我的妈妈,我说妈你不应该这样,我们说好的。什么说好的,你根本就没准备给细环讲吧。说了我说了啊,你就成全我们的婚礼吧。成全你们?你好好想想吧,你掰开手指头算算,今天是什么日子,黑粪马上就要来了,怎么成全?已经不错了,亲朋好友都来了席也开了,你还想什么!
院子里该走的人都在走,留都留不住,天好像要下雨,我闷得慌,走出门去。街上和我家的情况是一样,连小孩都没有,和早晨完全不是一种气氛。秀山还是一如既往地匆匆往家赶,但他的牛并不听话死赖在地上,很久才挪开一步。我说秀山你今天怎么没来喝我的喜酒啊,他们都喝完了,你晚上来找我喝好不,我晚上请你。秀山低着头,不理我,继续拉他的牛。我说你怎么了秀山,要不要我帮你。秀山红着脸气愤地说,走开,黑粪马上来了!说完,牛也不用拽了,直接把秀山拉起来跑了。
我重新在鸡窝里找到我的妈妈,院子里的杂务收拾的差不多了,干干净净的,连帐篷都拆了,我说妈黑粪真的是今天出来吗?不是一直说明天吗,我小心翼翼地问。他几时出来也不是我们说的算啊,有法官呢。我再问,那法官当时是说几时出来?她没再理我,掉头走了。
但细环还是来了,细环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没有喜烟喜酒喜糖,连证婚人都没有,她竟然也没生气,蹦跳着说真好,这样的安静真好。我不置可否,低着头,很怕看到她内心里的阴影。细环继续念叨,不被人打扰的婚礼才最纯净嘛,那就让风来做我的伴娘吧,让雨做我的伴郎,让雷声做我们的乐队,让这满架的葡萄装点我们的洞房吧,啊。
对细环的抒情,我有点不耐烦了,我知道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必须像一个旁观者那样尽可能平静而迅速地把问题的严重性、艰巨性和紧迫性阐述清楚,就像一个越狱者挖地道那样一刻也不能停。
细环,我有话想给你说。
怎么了?
你知道我爸爸怎么死的吗。
知道啊,村子里的人每天都在谈论,谁可能不知道呢。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都死了二十多年了,你还提这干什么。
他死了但是黑粪没死。
他不是被抓到牢里去了吗。
但是他早晚会出来。
你想怎么办呢?
报仇!
你要找黑粪报仇?
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可我都等了二十多年了,再不报我还是人吗。
我们好好过日子好吗,你看他也没了桃云,一辈子也就那样了。
不,你一定要答应我报仇。
我能帮你什么呢?
你来和他结婚。
谁?你说谁?
黑粪,你来和黑粪结婚。
疯子,你这个疯子,你是不是疯了,把自己的老婆拱手给别人。
别吵,不要吵!我这是计谋,是假的。
别跟我说什么真的假的,假的也不行,我不会做的。
我激动起来,一把按住细环的肩膀,别吵,听我讲完。屋子里的安静让我顿时意识到了自己的粗鲁,对不起,你听我讲完好吗。你就当和他参加一场百米比赛,陪他跑到村北口的梨树林,回来的时候我再想办法,好不好,他现在只想体验一番私奔的那种感觉。我把手放下来,把头趴到她的腿上,我跪在了地上。
我妈这时走了进来,她说细环啊,你就陪着他感受一下嘛,他现在已经想桃云想疯了。是啊,一起感受感受,我在一旁小声附和着。细环瞪了我一眼,我吓得赶紧把我的眼睛停到了她的腿上,不再与其对视。我的妈妈说,闺女啊,好歹你现在也嫁过来了,我们还能不承认?你就放一万个心去吧,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会讲究信用的,去吧,啊(请读二声)。
细环不语,连空气都在耗着,天一点点地黑了起来。院子里有了嘈杂的人声,有点吵,我迈出屋门,外面到处是人,我妈妈也出来了,她颤抖着嘴唇说,是黑粪来了,快去叫哥!
我来到带院子里,我说哥,你回来了。
他没有答应,扫视着我们一家,眼神空洞,神情严峻,他的鼻子也在嗅,浑身散发出稻草般的霉味,我的妈妈赶紧把细环推了出来,他哥这是给你娶的,你看中意不。黑粪瞥了一眼细环,眼里逐渐放出微弱的光,有了一丝人的气息。他往前挪了一步把手伸了过来,放到细环的胳膊上,问,你叫什么名字。细环。
黑粪在一旁琢磨着这个名字,来回踱着步子,突然嘿嘿地笑了起来。我说哥你中意不,黑粪终于看了我一眼,说,那就赶快办了吧。嗯!这声音像把刀子几乎是从我妈妈的胸腔里飞出来的,割破了暂时的平静,有点像叹息,也有点像尖叫,更像一响贪欢后的呻吟。
黑粪拉着细环的手,指着看不见的梨树林说,就是那边,你陪我跑到那边去,我们再来完婚。细环扭捏着身子不说话,点了点头。我把床底下的汽油提了出来,屋前屋后洒了个遍,然后我掏出打火机,我说哥要不要给你来把火,让你找找感觉,噼里啪啦地跑起来可带劲了。黑粪摆了摆手示意我不要再说了,他似乎察觉到了什么,黑粪说你哥走的时候是不是带了一瓶桂花香水?我也像我妈一样嗯了一声,舒服极了。于是他就进屋翻找桂花香水去了,我趁势把锁一按,把火机点上,戳到窗棂上,轰的一声火舌窜至树梢,整个屋像一顶纸轿,不要命地烧着,我拉起细环不要命地跑,像当年我的哥哥那样,也在村北面的梨树林回了一下头。只一下,远方便传来一阵苍声,作孽啊,生了个儿子,我知道那是我的妈妈向命运做最后的抗争。
责任编辑 裴秋秋
作者简介:
李子悦,1983年生人,已出版长篇小说《我该找谁去告别》《盛世荒年》,有作品发于《青年文学》《西湖》等,现为南京市文联签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