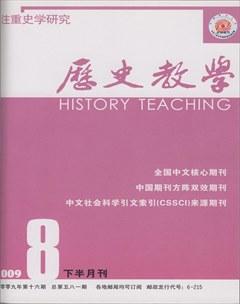清初对江南缙绅的政策及其变化
宫保利
[摘要]清初,降清的大批故明汉官成为清朝入关后政治、军事不断取得胜利和稳固统治的重要力量,清朝统治者一方面依靠、任用汉官,将其视为统治集团中的一员,另一方面在涉及满汉矛盾和动摇满洲贵族集团根本利益问题上,毫不犹豫地惩治汉宫中异己分子。顺治帝亲政后大胆任用汉官,同时对降清汉官始终保持高度警觉,特别是对江南籍汉官的猜忌和打压尤为明显。严厉惩处江南籍汉官和严禁结社订盟的政策,表明顺治帝对江南文人崇尚气节:复明排满情绪以及可能出现蔓延之势的极度忧虑和恐惧。清初对江南缙绅的猜忌、提防和弹压,是在清朝入关后相当一段时期内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社会风俗冲突的反映。随着清朝统治的日臻巩固和关外守旧满洲贵族的逐步消失,面对新形势,清统治者对江南缙绅的政策也产生了某些变化。
[关键词]顺治帝,江南籍汉官,猜忌
[中图分类号]K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9)16—0019—08
一、顺治帝对汉官的笼络及其局限性
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帝开始亲政,虽然清朝在军事上不断取得胜利,在平定了江西金声桓、广东李成栋、山西姜瓖的叛清活动后,全国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得到清朝的控制,但是满汉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特别是针对汉人的剃发、易衣冠以及维护满人利益的圈地、投充、逃人法三大恶政的推行,更是加剧了满汉间无法调和的对立,且积压在广大汉人内心的愤懑已成愈演愈烈之势。顺治帝作为清朝最高统治者既要维护满洲贵族利益,更要处理好君臣关系,依靠广大汉官建立稳固而有序的统治,促进社会安定和经济恢复。而作为偏居一隅又比较落后的满洲,如何处理好与广大汉人的关系,如何面对较先进的汉文化,特别是如何统治文明程度较高的江南地区,成为一国之君不能不面临和处理的问题。
顺治帝亲政后,为了减少国内广大汉人排满、反满情绪,缓和民族矛盾,一方面努力亲近汉文化,以此笼络广大汉人。他命人翻译五经,主持编修《资政要览》《劝善要吉》《范行恒言》《人臣璥心录》等著述,亲自撰写序言,设馆编成《顺治大训》一书,并说:“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另一方面,顺治帝千方百计地笼络广大汉官,努力消弭汉官与满人的隔阂。他越来越感觉到满汉和谐对维系统治的重要性,决心改变“各衙门奏事,但有满臣未见汉臣”的现象。顺治十六年,他告谕吏部:“向来各衙门印务,俱系满官掌握,以后各部尚书、侍郎及院寺堂官受事在先者,即著掌印,不必分别满汉。尔部即传谕各衙门一体遵行。”汉官可以和满人共同掌管印务,不论实际执行情况如何,这是自满洲政权建立以来破天荒的决定。顺治帝在位期间还一再要求满汉官员和衷共事,要求“凡会议政事,原应满汉公共商榷,斟酌事理,归于至当”,“不拘满汉皆可具稿”,希望不要再出现“满汉两议”的现象。
对洪承畴的重用,更突出地反映了顺治帝重用汉人的勇气。顺治帝为迅速结束西南战事,消灭永历政权,顺治十年五月二十五日,特升洪承畴为太保兼太子太师、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理军务兼理粮饷”,并破格授予“假以便宜”之权,许其“听择扼要处所驻扎,应巡历者随便巡历,总督应关会者必咨尔而后行;尔所欲行,若系紧急机务,许尔便宜行事,然后知会。巡抚、提督、总兵以下听尔节制,兵马钱粮听尔调发。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副将以下有违命者听以军法从事。一应剿抚事宜不从中制,事后具疏报闻”“事关藩王及公者,平行咨会,相见各依宾客礼。文武各官在京在外,应于军前及地方需用者,随时择取任用;所属各省官员升转补调悉从所奏;抚镇道府等官有地方不宜、才品不称应另行推用者,一面调补一面奏闻,吏兵二部不得掣肘;应用钱粮即与解给,户部不得稽迟。归顺官员酌量收录,投降兵民随宜安插”。如此委以重任,这在当时是对汉官从未有过的信任。顺治帝又亲自对洪承畴说:“卿练达民情,晓畅兵事,特假便宜,往靖南服。一应调度事宜,悉以委托。距京虽远,眷注弥殷。务殚忠猷,副兹信任。凡有奏请,朕靡不曲体。”
顺治帝为了达到笼络汉官的目的,汉人大学士党崇雅告老还籍时,他两次破格召见,赐坐,赐衣帽、靴袜、茶饭,“温语慰劳良久”,还特命满洲大学士车克送行。顺治十五年,翰林院修撰、状元孙承恩英年早逝,顺治帝“深悼惜之,赐白金三百两归其丧”。
顺治帝对汉官的任用与笼络的政策,既是他的勇气与魄力的反映,更是满洲统治广大汉人地区必须做出的政治选择。顺治帝作为满洲贵族的最高利益代表始终也未改变清朝“首崇满洲”的既定国策,在关键问题和重要决策上他的意识和利益天平本能或自觉地偏向维护满洲贵族利益和偏袒满人。
顺治十年二月初九日,顺治帝巡幸内院,当看到少詹事李呈祥请于部院衙门裁去满官专任汉人的奏疏时,大为恼火,对身边的大学士洪承畴、范文程等人说:“李呈祥此疏大不合理!夙昔满臣赞理庶政,并有畋猎行阵之劳,是用得邀天眷,大业克成,彼时可曾咨尔汉臣而为之乎?朕不分满汉,一体眷遇,尔汉官奈何反生异志?若以理言,首崇满洲固所宜也。想尔等多系明季之臣,故有此妄言耳!”几天后,顺治帝便将李呈祥革职,流徙盛京。
清初“三大恶政”造成广大汉人流离失所,沦落为奴,社会极度恐慌混乱。对于野蛮而残暴的逃人法顺治帝不仅从不触动,甚至为了捕获“逃人”还批准兵部设立督捕衙门,并以“逃人逃多获少,不行严察”为由,严惩兵部督捕衙门官员。就在顺治帝三番五次下诏广开言路,要求臣下“极言无隐,如有未当必不加罪”的谕旨发布不久,兵部右给事中李褶针对当时逃人法的种种弊端,于顺治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上疏建议修改逃人法。他奏言道:“逃人一事,立法过重,株连太多。使海内外无贫富、无良贱、无官民,皆惴惴焉莫保其身家,可为痛心者一也;法立而犯者众,势必有以逃人为奇货,纵令絷诈,则富家立破,祸起奴婢,则名分荡然。使愚者误陷而难解,智者欲避而不能。可为痛心者二也;犯法不贷,牵引不原,即大逆不道,无以加此。且破一家,即耗朝廷一家之供赋,杀一人,即伤朝廷一人之培养。古人十年生之,十年教之,今乃以逃人一事戕之乎?为痛心者三也;人情不堪相远,使其安居得所,何苦相率而逃,至于三万之多,如不以恩意维系其心,而但欲以法穷其所往,法愈竣,逃愈多。可为痛心者四也;即自捕获以后,起解质审,道途骚扰,冤陷实繁,藤蔓不已,生齿凋敝,夫孰非皇上之赤子乎?可为痛心者五也;且饥民流离,地方官以挨查逃人之故,闭关不纳,嗟此穷黎,朝廷日蠲租煮赈,衣而食之,奈何以酷法苛令迫而毙之乎?可为痛心者六也;妇女踯躅于原野,老稚僵仆于沟渠,其强有力者,东西驱逐而无所投止,势必铤而走险,今寇孽未靖,方且多方招徕,何为本我赤子乃驱之作贼乎?可为痛
心者七也。”奏疏言真意切,字字肺腑,句句属实。但由于上言触及满洲贵族集团的根本利益,因此奏入后,李褶被顺治帝流徙东北尚阳堡。
同年三月,顺治帝因逃人甚多,缉获甚少,而向臣下征询既不累民,又能速获逃人的良策。户部右侍郎赵开心以饥民流离可悯,再请朝廷暂宽逃人之禁,他说:“闻近畿流民载道,地方有司惧逃人法严不敢容留,势必听其转徙。若将逃人解督捕衙门,暂宽其隐匿之罪,以免株连,则有司乐于缉逃,即流民亦乐于举发,而逃人无不获矣。”但是顺治帝却认为:“逃人之多,因有窝逃之人,故立法不得不严,若隐匿者自当治罪,何谓株连?”遂以赵开心“不思实心为国,辄沽誉市恩,殊失大臣之礼”,将其“著降五级调用”。
当时朝中的多数汉官对隐匿逃人治罪过严不满,尽管上疏者均受到严厉惩处,但言者仍不断涉及放宽逃人问题。顺治帝认为此种言论实属“胸怀偏私”,“但知汉人之累,不知满洲之苦”。斥责请宽逃人令的汉官“偏护汉人,欲令满洲困苦,谋国不忠”,遂于十二年三月初九日下令:“凡章奏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决不轻恕。”顺治帝反复征询良策,诏令大臣广开言路,但只要触动满洲贵族利益的疏言,无论其对社会安定与进步是否有利,一律视为与满人为敌的言论,索性关闭言路了事。
顺治帝对朝中汉官的有限任用与对满洲官员过分偏袒,甚至导致了汉官受辱被迫自杀的事件。
顺治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直隶、河南、山东三省总督张悬锡因受辱而激愤自刎,因家丁急救而自杀未遂。他在遗言中称自己:“直道难行,清白招忌,家无余蓄,亦无良田美宅,不收一钱以负上恩。”事件发生的原因,是顺治十四年年底,顺治帝因孙可望于洪承畴军前投降,特封其为义王。十五年年初特命满洲大学士麻勒吉为特使,专程前往赍送敕印,并偕其来京。在返回京师途中,总督张悬锡于顺德迎接麻勒吉一行。麻勒吉“始而倨傲之不与见,既而鄙薄之不与坐、不与言,侮辱情状,诚所难堪”,并向张悬锡明言索贿,要求“馈送驼赢”。张悬锡以贿赂为朝廷首禁之条,拒不纳贿,“宁就死,必不敢从”。但又害怕日后受到迫害而日子难熬,因激愤而自刎未遂。
顺治帝得报后反而斥责张悬锡“殊失大臣之体”,将其降三级调用,“以听勘诣京师,居僧寺”。在勘察录取口供时,张悬锡不敢尽吐实情,质审诸大臣亦“瞻循麻勒吉等,不行详察”。顺治帝遂令吏部详察议奏,六月二十五日张悬锡在说出了麻勒吉“苛索”的真相后,不久,自己便于京师圣安寺自缢身亡。满洲大学士麻勒吉公然索贿,导致总督惧怕迫害而被迫自尽,事发后,九卿科道会议遂议麻勒吉应革职,籍没家产并鞭一百为奴。议上,顺治帝下令“麻勒吉革去所加之级,再降三级,仍留原任”。这样一来,实际上等于没有处分。在如此骇人听闻的事件上,顺治帝竟同自已作对,自乱章法,这是他从根本上偏祖满人所造成无法克服的政治失明。
二、降清汉官党争及顺治帝对江南籍汉官的猜忌
清军入关后,特别是占领北京、南京后,自顺治元年至三年间大批故明官员纷纷降清,以各种形式效力新朝,众所周知如宋权、骆养性、冯铨、柳寅东、曹溶、谢升、王鳌永、金之俊、李若琳、孙之獬、钱谦益、陈名夏、陈之遴、龚鼎孳等等。这些故明降官或沿袭旧怨,或攀援满人,或因争宠新朝等诸多因素,在降清后仍继续因循明末党争旧径。清初朝中也常常发生汉官党争现象。顺治二年,多尔衮在总结明亡的教训时颇有感触地说:“明季诸臣,窃名誉,贪货利,树党羽,肆排挤,以欺罔为固然,以奸佞为得计,任意交章,烦渎主听,使其主眩惑,用人行政,颠倒混淆,以致寇起民离,祸乱莫救,颠辙在前,后人炯鉴。”说明清初统治者对明末党争的危害是清楚的,并有所警觉。
冯铨在明朝天启年间追随魏忠贤,为阉党骨干,曾任礼部尚书、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崇祯初年,因涉阉党,论杖徒,赎为民。清军占领北京不久,多尔衮即书征冯铨至京,冯铨闻命即至。顺治二年二月,清廷定部院官制,授冯铨弘文院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同年八月,御史吴达、李森先、王守履、桑云和给事中许作梅、庄宪租、杜立德等群起参劾大学士冯铨并词连李若琳、孙之獬。御史吴达上疏言道:“冯铨为逆党魏忠贤干儿,故习不移……平日揽权纳贿。”且“纵子往来贵要,招摇纳贿又可知。请罢黜,以肃政本”。给事中许作梅、庄宪租、杜立德,御史王守履、罗国士、邓孚槐等,亦交章参劾冯铨揽权纳贿。御史李森先又上疏大呼“奸相冯铨误国……招摇纳贿”,并援引明末阉党事例,谈及魏忠贤“当日杀戮贤良,通贿谋逆,皆成于铨一人,此通国共知者”,坚决反对清朝再重用冯铨,应“戮之于市”。多尔衮遂召集廷臣及科道各官,令刑部当面质问。刑部认为科道官员所劾不实,应反坐。给事中龚鼎孳现场指责冯铨为“党附魏忠贤作恶之人”。冯铨亦斥责龚鼎孳曾降流贼李白成。多尔衮面对这场风波非常恼火,说道:“明季诸臣党害无辜,以致明亡。今科道各官仍蹈陋习。陷害无辜!”多尔衮肯定冯铨最先投诚清朝的贡献,对龚鼎孳等人加以申戒,并将李森先、许作梅革职。多尔衮之所以对冯铨多有庇护,主要出于清朝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他认为:“因冯铨自投诚后,剃发勤职,孙之獬于众人未剃发之前,即行剃发,举家男妇皆效满装,李若琳亦先剃发,故结党同谋陷害。”不难看出,多尔衮一方面对明末党争旧习深恶痛绝,一方面将对冯铨等人的纠劾视为对效忠清朝汉官的迫害。
在清初,降清汉官中逐渐形成冯铨为首的“北党”和陈名夏为领袖的“南党”,他们在勾结讨好满洲统治者,并借助手中权利巩固朝中地位,培植故交党羽上是完全一致的。冯铨是顺天涿州人,陈名夏是江南溧阳人,二人能在清初朝中得势,同是谄媚多尔衮的缘故,但是他们意见不合,就相互倾轧,分成南北两派。
顺治八年,多尔衮被迫罪后,顺治帝因冯铨依附多尔衮将其罢职:认为他“七年以来,毫无建明,毫无争执”。冯铨被赶出朝廷后,陈名夏、陈之遴“相继入内院”。同年五月,外转御史张煊指控陈名夏“结党行私,铨选不公”,列举他十大罪状,有依附邪党一款。陈名夏“厉声强辩”,且“自诉投诚有功”,加上满洲吏部尚书谭泰的极力佑护,结果张煊论死,陈名夏无罪免议。时隔不久,谭泰以阿附多尔衮被顺治帝“著即正法”。顺治九年正月,清廷为张煊昭雪,并将陈名夏革职。不难看出,此次冯铨和陈名夏仕途起伏,主要因为裹挟于顺治帝对多尔衮及其党羽的清算中,事均不涉及满汉矛盾,但朝中汉官南人、北人之形势日趋显现。
顺治十年,陈名夏复补秘书院大学士,仍署吏部尚书。顺治帝到内院反复告谕汉官:“满汉一体,毋互结党。”特别诫谕陈名夏“益谆切焉”,面对陈名夏强辞以对的态度,顺治帝警告他:“尔勿怙过,自贻伊戚。”同年三月,顺治帝重新起用冯铨,认为“原任大学士冯铨素有才学,召入
内院办事”,并对曾令其致仕进而解释道:“数年以来,未见有所建明,且经物议,是以令其致仕回籍。朕思冯铨原无显过,且博洽典故,谙练政事,朕方求贤图治,特命起用,以观日新。”要求冯铨“谕到之日,即速赴京”。冯铨至京当晚,顺治帝便召集他与洪承畴、范文程、额色黑、陈名夏人宫,与他们讨论翰林官员的贤愚优劣问题,提出:“朕将亲考其文之优劣,可定其高下。”冯铨借机上奏日:“皇上简用贤才,亦不宜止论其文,或有优于文而不能办事行已弗臧者,或有短于文而优于办事操守清廉者。南人优于文而行不符,北人短于文而行可嘉。”冯铨此番言论暗指以陈名夏、陈之遴等江南籍汉官文行不符,无能无守,遂顺治帝称道:“铨之言是。”仍授弘文院大学士,以原官办事。
顺治十年春天,由几社余脉之慎交社和同声社共同主持,江南文人在苏州虎丘集会,推奉吴伟业为宗主,苏州、松江等地共有五百多人参加。清初,江南文人的结社立盟为明末士风高昂的延续。清军攻陷南京及其强行剃发后,江南文人志士多有慷慨悲歌之抗清壮举。故明举人周宝瑜、贡生朱集璜、诸生顾炎武等拒守昆山城,故明御史金声、诸生江天一于绩溪起兵抗清,以及黄宗羲、陈子龙、夏完淳等名士的抗清活动。这些活动虽然没有成功,但其所彰显出的江南缙绅气节为清初统治者所恐惧。顺治帝亲政后仍时刻提防江南文人的言行,在朝中对江南籍汉官加以警觉,并多有猜忌。
在审讯京师“元凶巨盗”李应试(黄膘李三)案时,陈之遴“默无一语”,在奉命审理此案的济尔哈朗诘责下,陈之遴说:“李三巨恶,诛之则已,倘不行正法,之遴必被陷害。”陈名夏也上奏说:“李三广通线索,言出祸随。”因为李应试在京城“事诸王贝勒等得其欢”,汉官并非害怕李三而是惧怕其依仗为恶的满洲贵族。转年正月,顺治帝至内院阅览会典,就此案不解之处,问大学士陈之遴、陈名夏。他说:“黄膘李三一小民耳,廷臣畏惮不敢举发,其何故也?”陈之遴等人回奏道:“如告发其事,倘宥其死,则告发之人必隐受其害。”顺治帝听后颇为不快,说:“身为大臣见此巨恶不以奏闻,乃瞻顾利害,岂忠臣耶?”陈之遴听罢无言以对,不久,便被免去大学士之职。顺治帝认为臣子应忠君以死,何以顾虑“必受其害,其为身谋而无事君之道”,认为陈名夏、陈之遴等人缺乏对清朝的效忠。后来发生的诸多迹象越来越表明,顺治帝对陈名夏、陈之遴为代表江南籍汉官的猜忌在不断加剧。
顺治十年二月,清廷处理任珍案。兴安总兵、阿达哈哈番任珍发现妻妾与属下人通奸,随即私行杀死多人,并激起所部变乱,致使伤亡二百九十余人,逃散多人。任珍惧罪,遂遣家人到京,行贿兵、刑二部官员。事发后,下法司堪问,朝中侍郎、尚书等多人被牵连获罪,任珍被革世职一半。而以陈名夏为首的二十七名汉官联名上疏,要求以杀人罪重治任珍。顺治帝对此十分恼火,斥责他们:承袭明代结党宿弊,党同伐异,明显是与满官二心。四月初九日,顺治帝下令内三院九卿科道等官员云集午门之外,公开对陈名夏等人“严行议罪”。结果陈名夏、陈之遴等二十六人分别受到降级、罚俸的处分。顺治帝在谈及陈名夏等人得罪之由时说:“初议错误,则亦已尔,及再三申饬,即当省改,岂可仍行混议?凡事会议,理应划一,何以满汉异议?虽事亦或有当异议者,何以满洲官议内无一汉官?汉官议内无一满官?此皆尔等心志未协之故也。本朝之兴,岂曾谋之尔汉官辈乎?故明之败,岂属误于满官之言乎?奈何不务和衷而恒见乖违也。自今以后,务改前非,同心图效,以副朕眷顾之意。不然,朕虽欲尔贷,而国法难容。”
任珍案后陈名夏、陈之遴等江南籍汉官的境遇更是每况愈下。十一年正月十一日,顺治帝至内院,诘问陈名夏日:“今观汉官图报主恩者,何竞无一人耶?”陈名夏慌忙回奏:“臣等岂无报效之心,即有此心,皇上或无由洞悉耳。”顺治帝话中带话地说:“数年来徒廑朕怀,曾不愉快。应升之人得升,不思图报犹可;不应升者越次简用,全不思报,反谓己才所致。”陈名夏回答:“皇上厚恩无不思报,但臣等才庸识浅,致有错失为难必耳。”顺治帝遂警告他:“错失何妨,与其才高而不思报国,不如才庸而思报国之为逾也。倘明知而不思报效,擅敢乱行,事发决不轻贷。彼时不得怨朕,自贻伊戚耳。”陈名夏为明朝翰林修撰,降清后扶摇直上,很快加太子太保,官至大学士,吏部尚书。上述这段君臣对话不难看出,冯铨的话开始深入顺治帝的头脑,“其才高而不思报国,不如才庸而思报国”,恰恰成为“南人优于文而行不符,北人短于文而行可嘉”的转译。顺治帝开始对先前言官指控陈名夏结党行私,铨选不公等罪行有所认可,认为陈名夏迎合固宠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徇私植党,滥用江南匪人。两个月后,陈名夏便遭到灭顶之灾。
顺治十年四月,顺治帝曾说:“冯铨与陈名夏等素相矛盾,朕所习知。”在对待“北党”、“南党”问题上坚持的原则是“凡天下邪正贪廉,大利大害,务要实心为国”。这个国当然就是指满洲人的清朝。顺治帝在谈及党争之弊时说:“明末群臣背公行私,党同伐异,恣意揣摩,议论纷杂。一事施行,辄谓出某人意见;一人见用,辄谓系某人汲引;一人被斥,辄谓系某人排挤。因而互相报复,扰乱国政,此等陋习,为害不小,朕甚恨之。”近来内外诸臣中“尚有仍踵前代陋习,妄生意度者,深为可恶”。今后,“若有挟私疑揣,以至角立门户,渐开报复之端者,必重罪不宥”。
三、清初对江南缙绅的打压政策及其变化
在处理满汉关系上的局限性决定了顺治帝对朝中的汉官任用的基本原则是满洲利益至上,满人优于汉人。在对待朝中汉官上,顺治帝对江南籍汉官更充满了猜忌,在处理江南籍汉官上明显体现打压的态度。
对于朝中以冯铨为首的“北党”和以陈名夏为首的“南党”之间的明争暗斗,顺治帝是清楚的。由于满洲贵族集团对朝中江南籍官员有着更多的猜忌,对他们的警觉与打击的程度也明显大于“北党”。顺治帝对陈名夏的彻底清算,达到了打压朝中江南籍汉官势力的顶峰。
陈名夏在任吏部尚书时,力图恢复某些明朝旧制,在铨选用人上又多偏爱江南籍汉官,且自恃才高,既与墨守关外旧规的满洲贵族相抵牾,又多与北方籍汉官不和。
满洲大学士宁完我,对恃才倨傲的陈名夏也非常忌恨。顺治十一年二月初十日,宁完我受命参予满洲议政大臣之列。三月初一日,他上了一道参劾陈名夏“党首怀奸,情事叵测”的密疏。他在疏中指控陈名夏:“性生奸回,习成矫诈,痛恨我朝剃发,鄙陋我国衣冠,蛊惑故绅,号召南党,布假局以行私,藏祸心而倡乱。何以明其然也?名夏曾谓臣曰:‘要天下太平,只依我一两事,立就太平。臣问何事。名夏推帽摩其首云:‘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臣笑曰:‘天下太平不太平,不专在剃头不剃头,崇祯年间并未剃头,因何至于亡国。为治之要惟在法度严明,
使官吏有廉耻,乡绅不害人,兵马众强,民心悦服,天下自至太平。名夏曰:‘此言虽然,只留头发、复衣冠是第一要紧事。”“臣思我国臣民之众,不敌明朝十分之一,而能得明朝天下者,以便服骑射,士马精强故也。今名夏欲宽衣博带,变清为明,是计弱我国也。”疏中又罗列了陈名夏“结党奸宄”事七条罪状。除徇私、党庇、婪脏等项外,还称:“陈名夏父子居乡暴恶,士民怨恨,全家避居江宁国公花园中,此园系无主产业,例应入官,价值十万金,江宁各上司公捐银三千两代为纳价,见今名夏妻子居住。又故明吏部吴昌时女奸逃执讯,名夏子陈掖臣嘱江宁各上司释放为尼,因而包占。又,掖臣横行江宁城中,鞭责满洲,破面流血,闹至总督公署,赔礼保放;又,掖臣坐大轿、列棍扇、说人情、纳贿赂、掣肘各官,俱敢怒而不敢言,无名冤揭贴遍城内,上写名夏‘不忠不孝,纵子肆虐。”
顺治帝接到奏疏后,即令内三院九卿科道詹事等官会同对陈名夏“逐款详问,从重议罪”。陈名夏在受审中,对宁完我所劾“罪状”逐条反驳,抗辩不屈,只承认说过“留发复衣冠”的话。议陈名夏论斩,妻子家产分散为奴。顺治帝“但念久任近密,不忍肆之于市”遂改为处绞,妻子家产免分散为奴。三月十一日,陈名夏被绞死。
陈名夏被处决后,朝中立即有人想趁机剪除异己。言官们纷纷上疏,“或称名夏亲戚,或日名夏党羽,交章纷纭,横加株连”。一时间人心惶惶,不知大祸几时临头。顺治帝担心挟私报复,使挟嫌者得以朋党。遂宣布:“以后论人论事,只许指实直言,不许再借陈名夏亲戚,党羽进奏。如有违犯者,定行重治,必不轻贷。”因为他并不想彻底摒弃朝中大批的江南籍汉官。
陈名夏被处决后,朝中另一位江南籍重要大臣陈之遴也未能幸免,而连遭厄运。顺治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顺治帝围猎于南苑,当众指责大学士陈之遴有朋党之行,嘱其要改过自新,并以此告谕诸臣说:“今人多结朋党,究其结党之意,不过互相攀援,以求富贵耳。”两天后,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魏裔介便上疏弹劾陈之遴,言其结党营私。随后,接二连三地有人奏疏指控陈之遴“徇私背公”。陈之遴有感“南北各亲其亲,各友其友”,回奏请求处分,顺治帝遂以原官发盛京居住。
陈名夏、陈之遴二位朝中江南籍大臣相继遭惩,充分体现了顺治帝对“南党”的态度和立场。为了避免造成江南汉族缙绅阶层的恐慌,顺治帝告诫各官:“朝廷立贤无方,不分南北。南人中有贤有不肖,北人中亦有贤有不肖。朕近日处分各官虽多南人,皆以事情论,非以地方论。”并要求各官:“尔等比肩事主,皆当仰体此意。凡有论列,须从国家起见。毋歧方隅,毋立门户,毋泄己私忿,毋代人诬陷,毋以风闻辄告,毋以小过苛求,务期公忠自矢,共还荡平之志。”皇帝所言虽然冠冕堂皇,但从此朝中南人势力大大衰落,实现了对江南籍汉官的打压和对江南士人的震慑。
顺治十四年,岁为丁酉,这年顺天科场案、江南科场案相继被揭发。
顺天乡试科场,主考官为翰林侍读曹本荣和侍讲宋之绳,大理寺左右评事李振邺、张我朴、国子监博士蔡元禧、行人司行人郭浚等十四人为房考官。由于当时营求者猬集,辇金载银,幅集都下。诸考官因嘱托答应过多,而额数有限,没有别的办法,只得闱中推敲,煞费苦心。结果爵高者必录,爵高而党羽少者次之,在京三品以上官员子弟无不选中;财丰者必录,财丰而名不素布者又次之。
榜发后,众考生一片哗然。刑科右给事中任克溥于十月十六日上疏参劾,他说:“北闱发榜后,途谣巷议,喷有烦言。臣闻中试举人陆其贤用银三千两,同科臣陆贻吉送考官李振邺、张我朴贿买得中。北闱之弊,不止一事。”顺治帝得知后,立即要求吏部、都察院对此事严加审讯,得实奏闻。十月二十五日,顺治帝下旨:“贪赃坏法,屡有严谕禁饬,科场为取士大典,关系最重。况辇毂近地,系各省观瞻,岂可恣意贪墨行私。所审受贿、用贿、过付种种情实,可谓目无三尺,若不重加惩治,何以惩戒将来。”遂命将李振邺、张我朴、蔡元禧、陆贻吉、项绍芳,以及行贿有据之举人田耜、邬作霖全部斩立决,家产籍没,父母兄弟妻子俱流徙尚阳堡,主考官曹本荣、宋之绳另行议处。
就在李振邺等人正法后第二天,吏部即传檄各省,逮捕案犯各家老幼,抄没资产,提拿要犯。一时,纵骑四出,辱骂鞭策,盈车累轴,一百零八名案犯男女家属出关流徙。
十一月十一日,顺治帝谕礼部:“将今年顺天乡试中试举人,速传来京,候朕亲行复试,不许迟延规避。”十九日又谕“如有托故规避,不赴试者,即革去举人”,并且永远不许应考,“仍提解来京,严究规避之由”。顺治十五年正月十七日,顺治帝亲自在太和门举行复试,并派满兵监视考场,一片森严。二月十三日,宣布取中一百八十二人,仍准会试。八名文理不通者,革去举人。
顺天科场案自顺治十五年十月案发,将李振邺等七人处决后,朝廷一直穷追不舍,迁延半载,株连甚广,以致“朝署半空,囹圄几满”。狱中病者、死者时有发生。至顺治十五年四月,刑部审拟议奏,斩立决者十九人,立绞者五人,绞监候者一人。顺治帝以人命至重,恐其中或有冤枉,命将人犯提来,亲行面讯。案犯俱供作弊情真,顺治帝考虑如此众多人犯一时处死,于心不忍。最后决定从宽发落,一律免死,各责四十板,流徙尚阳堡。主考官曹本荣、宋之绳因日夕陪皇上侍读,特恩姑免议。
与顺天科场案几乎是同时,江南科场案也遭到言官参劾。这年江南乡试,主考官方犹、钱开宗,因作弊过多,榜发后士子大哗。主考官离去时,士子随舟唾骂,投掷砖石。顺治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工科给事中阴应节向朝廷参奏:“江南主考官方犹等,弊窦多端。榜发后士子忿其不平,哭文庙、殴考官,物议沸腾。其彰著者,如取中之方章钺系少詹事方拱乾第五子,悬成、亨咸,膏茂之弟,与犹联宗有素,乃乘机滋弊,冒滥贤书。”奏上后,顺治帝下旨:“方犹、钱开宗,并同考试官,俱著革职。”命刑部差员速拿方章钺来京严行详审,命总督郎廷佐就闱中一切弊窦速行严察,将人犯解交刑部,命方拱乾明白回奏。
顺治十五年三月十三日,顺治帝亲行复试丁酉科江南举人。二十一日,取中吴珂鸣一人,准同今科会试中试者一体殿试;汪溥勋等七十四名仍准作举人;史继佚等二十四名亦准作举人,罚停会试二科;方域等十四名文理不通,革去举人。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再复试丁酉科江南举人。命下后,府县敦促就道,众举子仓皇束装,父母兄弟挥涕而别,诸家无不罄产捐资,以因缘上下。四月初九日,定叶方霭等七十名仍准作举人,其中十三人免罚科,准会试;第七十一至九十名亦准作举人,其中十八人罚停会试二科。
顺治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最终审结江南科场案犯。顺治帝下旨:将主考官方犹、钱开宗斩立决,同考官叶楚槐等十七人俱绞立决,妻子家产,一律籍没入官;卢铸鼎已死,其妻子家产亦籍
没入官;举人方章钺等八人,俱责四十板,家产籍没,与父母兄弟妻子流徙宁古塔;程度渊在逃,责令总督郎廷佐等速行严缉解获。
此案自十四年冬逮捕诸犯审讯,已历一年,有人甚至以为可因缘幸脱。刑部原奏拟将主考官斩绞,同考官流徙尚阳堡,方章钺等人革去举人。而顺治帝却严命重处,并责斥刑部对此案“徇庇迟至经年,且将此重情问拟甚轻”,还将刑部尚书图海、白允谦等人革去加衔加级,或降级留任。
不难看出,顺治帝在处理丁酉科场案中南闱、北闱的不同态度,北闱纳贿舞弊情节要比南闱厉害得多,但是顺治帝对江南闱案所涉官员和举子惩处程度明显重于顺天闱案,江南闱案部议轻而谕旨重,顺天闱案部议重而谕旨轻,顺治帝之所以重处江南科场案所涉人员,意在震慑江南文人士子,彰显满洲统治威严,压制江南文人高昂的民族气节。
明末江南文人士子结社立盟相沿成习,为了提防汉人门派相投,顺治帝多次严令“内外大小官员,各宜各守职掌,不许投拜门生。如有犯者即以悖旨论罪”。他认为投拜师生即为结党,并严禁私交、私宴,以“永绝朋党之根”。顺治十七年正月二十五日,礼科右给事中杨雍泰奏请朝廷,严禁民间文人士子结社订盟。“今之妄立社名,纠集盟誓者所在多有,而江南之苏松,浙江之杭嘉湖为尤甚”。顺治帝明确要求:士子不得妄立社名,纠众盟会,其名片往来亦不许用同社同盟字样,结社订盟,严行禁止。显然这道禁令主要是针对江南文人的活动,至此,自明中期以来的江南士人结社会盟,聚众演说,播讲学术,评论时政的活动便销声匿迹,不复有聚集讲论之事。
顺治帝亲政不过十年而已,在其执政期间对降清的汉官大胆任用,多有笼络。面对朝中降清汉官的党争,他从维护清朝统治和满洲贵族集团根本利益出发,对朝中江南籍汉官多有猜忌、不断打压,这种做法主要出于对江南文人抗清活动和民族气节的警觉与敌视,旨在重压摧毁江南文人的高昂士气。这种警觉、猜忌、打压的态度是清朝入关后政治斗争、军事形势和社会矛盾的必然体现。
顺治帝在其临终遗诏中将“渐习汉俗”、“委任汉官”作为自己的罪责,否定了他自己一生中最有光彩的政绩。尽管有学者推测这份遗诏未必出于顺治帝本意,可能出自皇太后及诸王之手。由此不难看出清初满洲贵族集团中顽固势力的基本立场。顺治帝死后,在江南地区相继发生的哭庙案、奏销案、抗粮案、明史案以及多起针对江南士绅文人的高压事件,既是满洲保守势力强硬政策的体现,更是清初复杂政治形势下满洲统治集团核心利益所致。
康熙帝执政后,尽管清朝对江南地区的排满情绪仍保持高度警觉和提防,且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地方。但是随着南明政权的结束、台湾的统一,科举铨选的制度化,清朝在全国统治日臻巩固,清统治者更多以调和满汉矛盾、强调满汉一体及尊崇汉文化,获取江南缙绅对清朝统治的认同为统治策略,逐步消弭江南文人的排满情绪和民族隔阂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