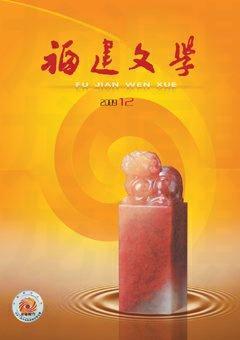返老还童记留级(外一篇)
魏 拔
魏拔,本名魏世英,福州人,从事文学编辑三十多年,曾任《福建文学》副主编、《当代文艺探索》主编,编审。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业余写作文艺评论和散文随笔。
一
1942年夏天,我小学毕业时,恰逢福州市中招办招初一新生一百多人,我考进后编在丁组,念了一个学期就留级。贪玩不肯读书是直接原因,深层一看,有几件事使我感到屈辱,精神上负担很重,上课毫无兴趣。
一开学我就病了几天,病好去上学时,只见全班已编好位,教室里坐得满满的了,就让我坐在最后一位,编最后一个座号。座位原是按照高矮编的,坐在后面的都是大同学,有的可能已有十五六岁了,而我十二岁,个子小,又很腼腆,插在大同学中非常孤独。到了集队上操场,别人按座号排好队,我的座号在最后人却矮小,就要塞到前面去插队,人家不高兴,自己也很不好意思,所以进教室精神上就很压抑,自觉是低人一等的“媳妇仔”。
在格致小学毕业时,不知为什么老师叫我在毕业典礼上致答词。上到初中,一次集队时,童子军教官吴昶澄问:“你们这个班有人会演讲吗?”一起从格致小学来的一个同学说我会演讲,这样一来,我就被教官指定去参加市三青团举办的演讲比赛。我心里喊着“糟了”,自己非常害羞怕场面,上到讲台演讲不是比绑上法场还难受么。可是又不敢声辩,不敢推辞,只好硬着头皮去做准备。参加演讲的几个男女同学,都风度翩翩,口齿伶俐,博得一片掌声,只有我一上台就看见教官瞪大眼睛盯着自己,心一慌,手脚都没地方放了,也不知讲了什么,当然比赛被刷了。后来,我眼前总出现教官瞪大眼睛的样子,我想他一定被我气得七窍生烟了,从此我到学校就提心吊胆,唯怕再遇见教官时他会训我一顿。
当时初中读的是抗战前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出的课本,这些课本抗战以后没有再版,大家都要到南后街旧书店买课本来读。上学不久我的一套课本不见了,别人告诉我是某同学“三只手”偷去了。我自己不敢去讨,让母亲去讨,结果讨不回来,旧书店里又再买不到,上课时只好请求同桌的同学将课本放当中一起看,自己当然很不好意思。没有了课本怎能念好书呢!
这个学期真是糟透了,我没有一个朋友,没有玩伴,当然也没法玩了,只有每天回家读章回小说。
当时市中校址在扬光中学,就是现在福州市公安局所在地。全校只一座红砖楼,后面有个操场,只能集队出操用,勉强能做球场。学校初创,没有什么设备,连乒乓桌也没有。记得大约有十位左右同学骑脚踏车,当时脚踏车大约还没有国产的,而福州在抗战期中海运中断,不会有车进口,所以有脚踏车骑着上学实在是很可以炫耀一番。市中这十部左右脚踏车大约是当时全福州城有数的吧,有时,从市中驶出三四辆脚踏车同时冲到街上,招摇过市,就可以构成街头一景。更有时,车技好的同学特意表演,将铜板扔在地上,而后骑车经过,到跟前时单腿跨下,俯身拾铜板,就会招来周围一阵掌声。不用说,这几位骑车同学被人认为是市中贵族,大家用羡慕的眼光看他们。其他同学要骑车,都是到车店租车。店里出租的脚踏车,全是脏黑不见电镀亮白的硬胎车。所谓硬胎,就是没有充气的内外胎,是利用废旧的汽车轮胎,剪下薄条,绕在车轮外圈,用铁线勾紧。当时的废旧轮胎是很有用处的,可以裁下做皮鞋底,做布鞋底,我穿过三四厘米厚车胎底做的鞋,笨重耐穿,在物资十分匮乏的当时,也算是令人看中的时装。脚踏车用的硬胎,是旧轮胎做其他用途以后剩下的边角料,可算是物尽其用。到店时租车手续方便,租金也不贵,中学生还拿得出。我都是在仙塔街车店租车,一推上街就骑,弯弯扭扭,横冲直撞,不慎会撞到菜摊粪担,学生哥脸红一下,就像箭射出般骑过去了。大约租过三四次就学会骑车了。于是敢于上街兜风去,学着放单手放双手。这是我读初一时,在屈辱憋闷的熬煎中唯一感到的乐趣。
二
留级生大约有十来人,新学期又招了新生,留级生同新生合在一起,再读初一上。女生没有留级的,大概她们都用功,年纪大、个子大的男生也没有留级的,他们不见得书都读得好,但他们有办法不留级。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咧,所有留级生都是不起眼的、上不到台面的小家伙,现在聚到一起,就形成一个小群体。小群体里当然也各有所好,又分为两三个小圈圈。我和几个圈子的人都交朋友,孤独感没有了,如鱼游在水中,舒展自如。
有个姓姚的同我最要好。姚是湖南人,据说他父亲是少将高参,当时在江西铅山第三战区任职,却把儿子放在福州读书,雇了保姆照顾,姚没有父母管束,生性又顽皮活泼,见闻也比我多,所以都是他怂恿我做这做那,拉我去玩。他的湖南风味的普通话很流畅,脸上表情丰富,又不怕场面,曾被学校挑去演话剧。他告诉我,他演儿子,一个女同学演母亲,儿子伏在母亲肩上,会闻到那个女同学身上的香味,太有意思了,我觉得他有点“歹”,爱谈女人。又觉得他心里想什么嘴上就说出来,别人放在心里不说的他敢说,爽直可爱。他不在上学时玩,总是放学后拉我在校外玩,他租住在天皇岭一家大宅院的花厅房,院里有假山鱼池,非常阴凉。有时,我们在他家里攀假山爬来爬去,说说笑笑,有时,去爬乌石山,钻丹霞洞,笑笑闹闹。那时的福州真是孤寂,既无戏剧电影可看,公园里也冷清荒凉,想玩也没地方玩。后来有个新生陈胖子也和我们玩到一起,这陈胖子扭扭捏捏好做女儿状,也喜欢演戏,我和姚爱逗他穷开心。听说三民里民教馆有排演话剧,姚就拉了我和陈胖子跑去看。到三民里一个空空荡荡的大宅院寻找,却没见有排演什么话剧的影子,几乎连人也没见到。后来姚和陈又说,有个在街上可以见到的大女孩,既会演戏又唱闽剧,于是这个女孩子在我们心目中就成为当时“福州一”的文艺明星。后来圈子扩大了些,拉来两三个小学高年级的朋友,几个人聚到一起商量着要演戏,又说要组织个什么社,发展社员,大家一起做什么事情,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组织社团。记得有个姓程的小学高年级学生去刻了一个什么社的大图章,给每个人印发了什么证,后来当然没有了下文。可以说,这是我最早的社交活动。
我参与的另一个留级生圈子沉迷于下棋,既下象棋,又下军棋。下象棋全凭技艺,要下一步想三步,挺费心思。下军棋的技艺虽然不如下象棋高,却可以用计谋,搞心理战,更有趣味性。计谋首先用在布阵上:“师长”身先士卒站在“前线”,后面跟着“炸弹”,“师长”一旦被敌方“总司令”吃了,“炸弹”就去和“总司令”“抱倒”;敌方“地雷”布在后方三行以内,我方先派“排长”去探“地雷”,一旦“排长”牺牲,再派“工兵”去挖“地雷”,排除了障碍之后,就可以出奇兵长驱直入敌营,抬走敌方“军旗”,取得全胜。以上,是最基本的谋略,会下棋的人人懂得。记得有一次和一个姓陈的同学下军棋,我趁敌方“炸弹”躲到“行营”,不注意保护“师长”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总司令”冲上前把敌方前线的“师长”吃了。不意这是“炸弹”伪装做“师长”,诱我上当,断送了“总司令”性命。我在懊悔莫及之后才发现对手用了阴谋诡计:原来,他在布阵时就把“炸弹”放在前线第一行。这是违反常规的,人家布阵都是“炸弹”跟“师长”,既保护“师长”也保护自己,哪有把“炸弹”放在最前面,不怕敌人用“工兵”抱“炸弹”么?后来陈和别人下棋,我来看他布阵,他竟然把军力全偏到一边,另一边唱空城计;“地雷”也不分布两边,集中在一块,而躲在“地雷”后面那个死角落里的竟是个“军长”(敌方要是不把这枚“地雷”挖掉,这个“军长”就老死山窟,永无出头之日了)。这使我大开眼界,知道了虚虚实实,出奇制胜,正是兵家制胜之道。吃一堑长一智,一次输棋的教训使我终生受用无穷。
下海陆空军战棋那才叫过瘾,可惜这种棋不容易买到。我是从下海陆空军战棋才学到一点点军事知识,知道海军有主力舰、巡洋舰、驱逐舰和潜水艇几种等级,知道空军有侦察机、轰炸机、战斗机、驱逐机的区别。坐下来下一回海陆空军战棋,做一次三军统帅,那种运筹帷幄的派头,那种立体战争的气势,那种既要出动飞机轰炸敌方大本营,又要派遣潜水艇偷袭敌人主力舰,手忙脚乱指挥一场你死我活、激烈异常的恶斗的强烈刺激,会叫站在一旁观战的人羡慕得要死。谁拥有一付海陆空军战棋,就像拥有亿万财富一样值得骄傲。这付军棋的主人肯让你坐下来对阵主战一回,那简直是一次恩典,给你极大的面子。
有一种六子棋比较简单。随便在地上画个正方形,四横四竖,就是棋盘,各捡小石子或碎瓦片做六个棋子对下,走成□□○一条线,□方就把○子吃掉,反之亦然。还有一种棋叫做“猪母猪仔”,也是在地上画棋盘,随手捡小石子做棋子,猪母一方只一个大的棋子,猪仔一方有若干个小棋子,具体走法我现在忘了,总之或是猪母把猪仔吃光,或是猪仔把猪母围死,以定胜负。这种棋可能来自民间,虽然简单,也有点窍门。随时随地蹲下就可玩,站起来把手上小石子一扔,脚下把棋盘一擦,两人就散走了。
还有一个圈子的几个人喜欢在校园里跑来跑去,推推搡搡,吵吵闹闹。有一次不知为什么吵架打起来了,一个姓王小同学被人踢了一脚,睾丸踢进肚子去,他手按腹部疼痛难当,人昏倒了。周围有年纪稍大的同学赶快抬着他“跳”,还好很快睾丸“跳”落原位,几个人就扶着他回仙塔街家里,好在他的父母不在家,年纪大的同学说“不要紧了”,去买了“本结”(不知这两个字是不是这样写)糖给他吃,这事就遮掩过去了。我当时恰好在场,事后见姓王的同学并未张扬,心里挺佩服他又老实又“臭硬”。
过东方新年
——新西兰札记
我和老伴到奥克兰探望女儿和外孙女,在香港会同两位亲家一起来。亲家是短期旅游,一月十七日到达,二十五日要回香港,所以一到达,全家就抓紧游览。逛三四天,歇一两天,转眼就到了二十四日。于是又抓紧过年,白天买海鲜买牛肉鸡肉,做几碗佳肴,晚上吃年夜饭。吃饭之前,将国内带来的大红倒“福”和对联贴在门上,有点像过年的样子了。开宴的第一道菜,是香港人重视的“好事发财”,蚝干煲发菜,取其谐音,讨个吉利。压轴大菜是福州人逢年过节、红白喜事都少不了的太平燕(鸡蛋加扁肉燕),这就有了吉祥如意的双保险,饭后给了孩子压岁钱,应有的程序好像都完备了,总算按照传统习俗在海外番邦提前欢度一回春节。
二十六日早上,我出门散步,独行一段路之后,远远望见二三十米开外对面人行道上有人向我招手,于是我也举手回应。一位老人走来了,是黄皮肤黑眼睛的同胞。陌生人在异国相逢,顷刻像老朋友似的畅谈起来。他自我介绍姓恽,来自天津,一子一女都在新西兰,老两口就跟来这里定居,已经一年多了。“今天是大年三十啦,”他说,“恰好亲家也来旅游,我们前天聚在一起吃一顿饭,就算过年啦。今天孩子们都上班了。”我说:“真巧,我也同样。”随后,他介绍说,奥克兰东部华人多,我们这里西部就少,还没有形成华人社会圈。不过,附近也有几家华人,老人们有时在社区聚会活动,下棋打牌的也有。因为我还没有投入此地华人社会活动的思想准备,听了他的介绍也不去细加查问,这天晚上,当然还要吃一顿好饭,饭后就没戏啦。要在国内,正是万民同乐收看春节晚会节目的黄金时刻,可是此地没有中文电视,装卫星接收装置要两三千元纽币,移民来的中国人多数没有装,我们也同样,因此无法收看CCTV的卫星转播,实在是件憾事。
新西兰人口三百万,华人占总人口百分之二左右,而百分之七十居住在奥克兰,按此推算,奥克兰华人大约有五万人。此地办有华文报纸四五家。几家报纸都很重视春节的宣传,都刊登国家总理、市长、部长、议员和中国外交使节庆贺春节的题词,报道华人社团举办春节活动的消息,有的副刊还撰文介绍贺岁时舞龙、舞狮、吃团年饭、给压岁钱等传统习俗。阅报得知,今年奥克兰华人社团有各种联欢会、舞会、聚餐会、园游会乃至佛教的法会、基督教的圣餐会等庆祝活动。正月初一下午七点,新西兰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假某广场放映CCTV春节晚会录像,我们全家认为最佳选择便是去看这个晚会录像。
提前吃过晚饭,六点开车去某广场,下车时见已有一批华人在等候。时间还早,大家都到儿童游乐场走动。人们陆续开车来,将近七点,在一个大活动室门口排了长队。排在前面的一位先生看见后面来了熟人,连忙招呼快到前面来插队。我不禁笑了:这不是在国内常见的情景么!想不到在国外,只要中国人在一起,这种情景又再出现。进场不久,两三百个座椅就坐满了。那位先生用报纸、衣物替熟人占了六七个椅子,神情紧张地看守着,直到熟人都进来就座,他方才松口气,笑了。我看在眼里,好笑在心里,觉得眼前的“插队”、“占位”恰是中国社会的一角缩影,具有典型意味。我想,中国人处在这样的典型情景中,会如鱼得水,活跃许多。而我自己,在国外的精神拘束好像一下子也放松了。
一位热心的主持人上台向大家解释:原先没有估计到,租的这个场所窗子没有布帘,白天无法暗场,只能等天黑了才好放映春节晚会录像。现在放映的是去年元宵节晚会节目,请大家将就先看。果然,台上布幕有模模糊糊的影像,看一会眼睛就很吃力。此刻窗外光线正强,看样子只好坐着等两个钟头了。
在场的以三四十岁的中年男女为主,估计都是从中国内地技术移民来的,有大学以上文化教养。大家表现出充分的耐心,有的看报,有的走动,更多的勉强看布幕上模模糊糊的影像,秩序很好,一会儿,热心的主持人又对大家说:八点半天黑以后,多数人要是说可以放映春节晚会录像了,我们就放映;节目很长,不少人明天还要上班,今晚就放一半,明晚继续。话声刚落,有人喊道:不要,不要,今晚放完。有人拍掌支持,这就算民主通过了,完全中国式。
天黑以后放映效果好多了。那么多精彩的歌舞、小品、相声、戏曲、杂技,汇集成五彩缤纷的艺术长卷,令人目不暇接。远距离的布幕影像毕竟不如近距离的电视荧屏光亮,正襟危坐在公众场合毕竟也不如躺在家中沙发上舒服,四个小时看下来够累的。除了少数带孩子的提早退场,全体都坚持到底。好比是饥饿的人吃了十全大补、满汉全席似的满足,散场时已是深夜。除夕看电视上的春节晚会,已成为中国人新的文化传统,有缘看到这个新的文化传统移植于新西兰华人社会,让我印象难忘。
一月三十一日,即农历正月初四下午,在奥克兰东部豪威克广场有一个盛大的“庆祝东方新年”园游会,女儿约了朋友和我们一起去参加。这个园游会是由亚洲协会(简称UAA)和新西兰华夏协会联合主办的,经过充分的筹备,组织了许多节目。主办者在报纸广告提请公众注意:“如果您要来观赏,请别忘了携带轻便的折椅,或用来铺在地上的毯子,下午阳光强烈,要准备遮阳帽,黄昏以后气温下降,则需要准备御寒外套,因为节目由下午三点开始直到晚上八点结束。”夏天阳光强烈,确实需要遮阳帽,而“准备御寒外套”未免有点夸大其词,不过主办者的好心提示还是令人感动的。
我们到达广场时将近四点,见草地搭了两个舞台(一个露天,一个雨盖),台前已坐了不少观众,中国人居多,小半是外国人。节目也已经开始。我们选好位置,支起遮阳凉伞,席地坐下欣赏节目。原来节目分两段进行:三点至六点,表演拉丁美洲音乐、歌唱、舞蹈。拉美艺术很有特点,我第一次观看就获得深刻的印象。演出服装一律黑色。乐器只两种:吉他和手鼓。男女演员应该都是本地拉美裔居民,属于业余表演,可是跳起踢踏舞非常之认真,非常之熟练,技巧上有很大的难度,不亚于专业水平的演出。一位女演员配合着吉他伴奏,一边敲打手鼓一边演唱,手鼓技巧变出各种花样,甚具魅力。我被吸引之时猛然想到,不少民族的艺术越是民间色彩浓厚就越突出鼓的作用,看来这种共同性自有它的道理。节目进行到后半段时,我注意到亚洲民族如中国、韩国的民间艺术也十分看重鼓,就益发相信,作为一种打击乐器,鼓,最简单,最原始,却也最富于情绪性、鼓动性、集体性,最能表达欢快的激情,在万民同乐的节日庆贺活动中,它总是不可缺少,不可代替,具有变化万千的魔幻般的生命力。
六点,庆祝东方新年正式开始。担任司仪的小姐特意说明,因为亚洲其他国家如韩国、菲律宾也过春节,所以我们称之为东方新年;今天的晚会,韩国、菲律宾的朋友也一起参加联欢。
草地广场的一边,另外搭了两个凉棚,排了几十张合椅,招待贵宾在里面就座。这时,有两个穿蓝色军服、背负无线电话筒、十八九岁左右的军人(不知是不是警察或保安人员)从凉棚引了国家总理谢普莉、曼奴考市长、各国使节等贵宾上了雨盖舞台。这时我才留意到,这个舞台是经过布置的,顶上挂四盏中国宫灯、十一盏红灯笼(不知为何是十一盏),后幕则挂一件戏装大红龙袍,算是传达出了中国传统的吉祥喜庆的气氛。开幕仪式上,女总理、市长先后致词。后来表演节目,韩国、菲律宾使节也致词,足见这个园游会规格高,也足见当地政要对于东方新年的重视。
谢普莉总理是去年在一次和平政变中上台的,政治上应该是有魄力的。在这次园游会上,她一个人坐在露天舞台侧边看表演,身旁既无前呼后拥的随从,也无戒备森严的保卫,只像个普通妇女观众。舞狮时,她被请上台发红包;菲律宾民族舞蹈演到一半,她又被引上台对舞;一直到舞台演出结束,广场上舞龙灯开始,她又到场接见。从始到终,不装腔作秀,保持着憨厚和朴素。我对这位女总理不免产生由衷的敬意。
韩国、菲律宾和中国的节目表演从服装到道具,从动作到音乐,都尽量显示民族的、民间的传统特色。演出当然只是业余的水平,甚至只达到最最业余的水平。然而有几个特点却很可贵。其一,参加表演的大多是年轻人,有的只有十几岁,看来是在新西兰长大的后代侨民。他们远离祖国故乡,难得能在一年一度过东方新年的机会学习故国的传统习俗,哪怕只是简单地模仿,也维系着高山流水斩不断的民族感情。其二,有一批外国青年和小孩学了韩国功夫、中国功夫,拿来作汇报表演。那些动作有的十分简单,不过是入门的一、二、三,但是表演者那股认真劲儿却不能不叫人感动。他们穿着功夫服装,腰缚色带,据说不同颜色分出等级,如黄带是初段,黑带是最高段。表演时都遵守一定之规,哪怕只是打出一拳就完事,也要严格照规矩来。后来看舞龙时,我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不但龙会摇头摆尾,还会摇尾摆头,头跟着尾走;而且,龙有时不抢珠,倒会珠去追龙,捧腹之余,觉得何妨就把这看作中国传统文化推陈出新一例哩!难道龙头跟着龙尾走不更富有革命意味么!无意中,我在这里上了中国文化国际化的一课。其三,主办者似乎有一个意图,就是尽量搜奇索异,向在场外国人展览中国传统文化。最后一个节目叫传统服装表演,让演员穿上古装戏衣上台走一圈。这时司仪小姐特别热心地介绍:这是中国皇帝的服装,这是皇帝妃子穿的,这是汉朝的将军,这是明朝的官吏,这是杨玉环,这是赵飞燕,——老实说,连现代中国人都弄不清楚的几百年乃至两千多年前古装,洋人当然更要看得目瞪口呆。真是应该感谢主办者对外宣传中国文化的这份热心。
庆祝东方新年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原来,在奥克兰东区有许多亚洲新移民,一位名叫萨伦(SHARON)的KIWI(意为本土)女士带领一批亚裔组织亚洲协会,默默地为亚洲新移民服务。一九九六年就举办了庆祝东方新年的园游会,既让离乡游子感到温暖,也向KIWI介绍东方文化。今年与华夏协会联合举办活动,得到亚洲各国许多厂商和媒体赞助。萨伦女士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从寻找赞助单位、协办单位,接洽政府安全单位,邀请表演人员、邀请贵宾,直至安排场地、租用临时厕所,都大费周折。可是晚会中她不出台露面,仍然默默无闻地在幕后操劳。这位女士实在很可敬,另外一位台湾来的中国小姐张俪龄,也就是晚会上主持全部节目的司仪,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她在场上先用英文介绍节目,再用中文介绍,都相当流利。有时说了英文,说中文反而忘了恰当的词语,自己叫道“哎哟,国语忘了”,可是到节目最后,她在介绍杨玉环和赵飞燕时,无意说了句“环肥燕瘦”,令我非常感动。我想,恐怕在中国内地土生土长的许多小姐是不知道什么“环肥燕瘦”的,哪比得上中国文化垫了底,再出来闯世界的张小姐。
(原载《中外论坛》1998年第6期)
责任编辑 贾秀莉 林 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