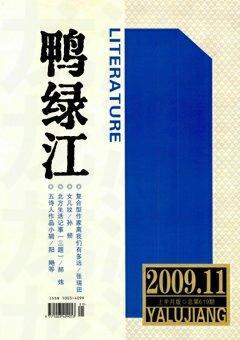北方生活记事(三题)
郝 炜
郝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吉林省文学创作中心聘任作家,吉林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为吉林市新闻工作者协会秘书长。中短篇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北京文学》《上海文学》《青年文学》《山花》《作家》《特区文学》《当代小说》等多家刊物,有多篇小说被《小说选刊》和《小说月报》转载,作品曾被收入《2000年中国年度最佳小说选》《中国短篇小说精选》等选本,出版小说集《感情危机》《老人和鱼》。先后获得吉林省首届文学奖、吉林省文学创作奖、吉林省政府长白山文学奖。
吃鹿肉
车进村不远,就见二叔背着手在房前迎接。下午三点多钟,还不是很暗,遍地雪光。二叔的身后是他家的苞米楼子,里面堆满了金灿灿的苞米,旁边散乱地堆着些苞米秆子,落满了雪。再远处,是山坡,有铺雪的小路通到山上,山上长满了柞木,挂着些灰暗的枯叶,间或有几棵松树,透露出点暗绿,在大片柞木的包围下,也是灰秃秃黯淡的样子,不见起色。
阿波边开车边说,二叔又喝了。我说你怎么能看出来。阿波说,二叔要是不喝,就笑嘻嘻地袖着手。你看他今天背着手,还不是喝了。我惊异于阿波的观察能力,我说你倒是适合写小说。阿波笑着说,我只是对二叔太了解了,别人我观察不明白,还是你写吧。
阿波把车停下,二叔走过来,阿波说,郝哥来了。二叔快速地伸过手来,说郝主任来啦?二叔的记忆力果然好,我只来过一次他便记住了。我握住二叔粗糙的手说二叔好,又来麻烦你了。二叔说,麻烦什么,进屋进屋。据二叔嘴里喷出的酒气和他说话走路的姿态,我认为阿波的判断是对的,二叔是喝了,而且喝了不少。
厨房里,二婶领着自己的两个姑娘忙碌,去年来吃猪肉的时候已经见过,打了招呼,她们还都记得我,说我拿的山竹特别好吃。我去年来时顺手买了水果,真是不好意思,今年走得急什么都没买,山里人还是重感情啊,她们记得你给她们的一丁点好处。我顺便在厨房看了一下,一大盆鲜艳的肉,知是鹿肉,已经用料喂好,旁边的小盆里有切好的圆葱丝,打好的鸡蛋,还有拌好的凉菜,可能就等我们了。二婶见二叔和阿波进来,就问开始吧?二叔把目光转向阿波,阿波说,开始开始。阿波的架势果然带着城里人的派头,看来阿波平时对二叔二婶家贡献不小,要不不会这么受欢迎。推开屋门,已经来了好多人,我事先不知道阿波找了这么多人,只见谭主任王主任杨主任李主任,已经在那里打上了麻将,韩记者金编辑还有两个不太熟悉的人打着扑克。炕上还有两个孩子在那里下象棋,煞有介事的,现在的孩子真是智商高,小小年纪都会下棋,想我们那时还是撒尿和泥的年龄,时代真的不同了啊。
阿波走进屋里说,别玩了,咱们开吃吧。大家纷纷打着招呼,都很热情,看来都是第一次吃鹿肉,都透着兴奋劲儿。我直接上炕,和几位主任坐在一起,中国人永远都要论资排辈,酒桌上尤其如此。阿波和韩记者金编辑还有那两个陌生人坐在地下那张桌,介绍了一下得知,那两个陌生人也不是外人,是王主任杨主任两位女主任的爱人,阿波办事就是周到,怕女主任不喝酒,先把人家老公给摽来了。
菜上来了,以鹿肉为主,还有几个菜:一盘豆芽凉菜、一个笨鸡炖蘑菇、一碗蒸扣肉(猪肉,是二叔从别人家买的,二叔今年没养猪)、一条大鲤鱼(是从水库买的),还有一盘鹿血糕和一盘鹿排骨,似乎还有鹿心肺什么的(不确定,没好意思问),够丰盛的。两个电锅里油吱吱啦啦地响,那盆鹿肉被端了上来,二婶的两个姑娘分别在两个桌子上忙碌,姐妹俩长得很相像,都是很红的脸蛋子,是那种常年在外劳动的肤色,她们都是笑笑的,让人看了觉得心里暖和。她们说话直率热情,喝起酒来不亚于男人,上次在二叔家吃猪肉时我是有领略的,这次看上去觉得她们反而有些腼腆了,可能是有几个生人,或许也因为桌上还没有那样的气氛。
去年吃猪肉的时候,好像也是这些人,只是没有两位女主任和她们的爱人。那次猪肉吃得我们终身难忘,好像就是因为两位女主任没来,她们总念叨,才有了这次鹿肉宴,因此要感激二位女主任,甚至要感谢她们的爱人。酒是从村子里的烧锅接的酒熘子,粮食酒,确切说是苞米酒。二叔家这里是山区,土地瘠薄,只能种苞米,别的东西不收。这酒度数挺高,据说是六十度。二叔又杂以山葡萄汁,看上去很好看,葡萄酒似的,我一向不喝白酒,但也向阿波要了一杯。阿波举着塑料桶对大家说,酒有的是啊,管够喝。阿波接着祝酒,说,别看二叔家就是养鹿的,可二叔从来舍不得杀鹿。今年二叔把鹿都卖了,特意留下了一头小鹿给咱们吃。我代表大家谢谢二叔二婶和两位姐姐。
我环顾四周,发现二叔没有在屋,这倒是反常的事情。去年吃猪肉时,二叔酒多话多,这次怎么躲了?问二婶,二婶说二叔中午陪客人喝多了,他要到山上转转,溜达溜达,醒醒酒。大冷的天,到山上转什么?我想二叔肯定是心里难受,阿波说二叔这是第一次杀鹿。他自己没动手,请别人帮的忙,中午他自己没动鹿肉一筷子,光喝酒了,就喝多了。
这里,我要介绍一下。二叔家这个地方叫歪头沟,房子都是顺着沟塘子建的。许多年以前这里是县里办的鹿场,二叔他们都是场里的职工。场里的工人是从四面八方抽来的,那时候场里养了上千头梅花鹿,满沟里走的都是梅花鹿,你如果是陌生人走到这里,会以为到了神仙呆的地方。那些鹿都是很温顺很漂亮的动物,它们在山上吃草,在沟里淘气,像一群自由的孩子。后来鹿场黄了,鹿场把房子卖给了大家,也把鹿分给了大家,大家就都成了养鹿专业户。头几年,养鹿还是很富裕的,鹿一般是五月份产仔,到了八月份就断奶了,一头仔鹿(母的)能卖个四千五千的,虽然成本高一些,但还是赚钱。近几年,市场变化快,仔鹿贱得几乎不如一头猪了,只卖四五百元,许多养鹿的人家都不养了。
我们兴高采烈地喝酒,大口大口地吃着鹿肉,说着一些俏皮话。我们管炕上的叫楼上,管地下的叫楼下,楼上楼下的就来回走动。楼下向楼上敬酒时,我建议还是应该叫炕上,上来敬酒就叫上炕。我进一步引申说,要不然就要起副作用了,因为那就得叫上床。王主任杨主任听我这么一说哧哧地笑,谭主任正襟危坐,一副目不斜视的样子,他只喝啤酒,有“啤酒潭”的美誉,轻易没有对手,现在他正把注意力集中在两位女士身上。戴着眼镜的李主任也是装傻充愣,不断地冲我眨眼睛,我比较了解他,就不去看他的眼神,他总是愿意冲别人眨眼睛,总想表明对别人的话有特殊领悟。王主任是美女,别看已经为别人生了孩子,模样依然不改,王美女不顾自己老公还在楼下的实情,把一条短信拿给我看,说你说的正好可以添加在我编的短信里。这个短信是这样的:男男女女一起喝酒,高了,有人上脸,有人上头,也有人上手,还有人上心。我看了一乐,是挺有意思,加一句“更有人上床”,呵呵,多么完整,真是不谋而合啊。谭主任说,你们俩搞什么名堂,有好的短信给我看看,我们部里正需要,我可以付费购买,一条五十元。大家这才想起,谭主任是手机报的主编,对内叫主任,对外叫总编。王美女把手机一藏说,不卖。谭主任说,为吗?王美女说,嫌便宜。再说,我也没有义务支持你的工作,你的工作干得太好,我们部里怎么办?谭主任说,你太小心眼儿了,没有大局意识嘛。王美女就说,那你喝了这杯酒,我就给你看。谭主任一听不含糊,说那我连干两杯。谭主任在美女面前是有牺牲精神的,他连续两杯一饮而尽,用手抹着嘴上的泡沫说,这回可以了吧。王美女说,可以是可以,但要每条一百。关键问题上谭主任还是不糊涂的,他说那可不行,财务上的事情我说了不算。王美女翻了谭主任一眼,把手机递过去,谭主任一看手机也乐了,是无声的一笑。李主任立刻不高兴了,说你们都看就不能给我看看吗,就也要过去看,看得李主任眼睛一眨一眨的,是不由自主的动作。
这边正高兴,两个孩子却在饭桌上争执起来。杨主任的孩子和二叔的二姑娘的孩子本来玩得很好,和杨主任的爱人在地下那桌吃饭,小家伙从开始就谨谨慎慎的,一口不吃和鹿相关的东西。二姑娘的孩子就问,你怎么不吃鹿肉呢?小杨就说,老师说要保护动物,鹿不能吃。二姑娘的孩子嘻嘻笑着说,这是我们家养的鹿,又不是山上的鹿。小杨还是坚定地说,那也不能吃。二姑娘的孩子说,那你怎么吃猪肉呢,小杨说猪肉就是用来吃的,鹿不是吃的,鹿是看的。二姑娘的孩子却说,我们这里都吃鹿肉的。小杨怒目圆睁,反复说明自己的理论,两个孩子的争论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吃了一会儿,我起身去上厕所,阿波也跟了出来。外面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雪,蓝色的天幕上往下飘着轻盈的雪花。我们走到鹿圈那儿尿尿,圈里空空荡荡,一头鹿也没有了。那些空荡荡的房子上挂着干豆角和干菜,还有几穗白苞米。我记得上次来,那些精灵的鹿还在这里探头探脑地逡巡,如今已物去屋空,不禁有些不舒服。雪花落在头上脸上凉津津的,我打了一个寒颤。我说,早点往回走吧,呆会儿不好走了。阿波说,忙啥,酒还没喝好呢。我说,不知为什么,一想起那些鹿就有些不舒服。阿波搂着我的肩膀说,你呀,怎么和我二叔他们似的。你知道吗,二叔的鹿是昨天卖出去的,卖给了南边的一个贩子,七头鹿总共没卖上多少钱,老俩口都哭了。其实二叔自己会杀鹿,可是咋也下不了手,雇人杀这头鹿,还给了人家二斤鹿肉。二婶说,那鹿挺可怜的,一看有人来就啥都明白了,圈里就它一头鹿,它呦呦地叫着,扑通一跪,刷刷掉眼泪,她后来切肉都切不下去了,总看见那双眼睛。
阿波先进屋去了,我没有动,我也看见了那双眼睛,在黑暗里闪动,我一直觉得鹿是很温顺很高贵的动物。那个孩子说得对,鹿不是吃的,鹿是看的。鹿有那么美丽的皮毛,那么美丽的角,生长着那么美丽的鹿茸,它走路轻盈而富有弹性,像跳着狐步舞。而且今天这是一头小鹿。想一想真的有些难受,文人的臭毛病啊,吃都吃了,还想什么想啊?
有人在暗处抽烟,我一看是二叔。我说二叔你怎么不进屋?二叔说我喝多了,怕搅了你们的兴。我说外面这么冷,进屋去吧。二叔说,我习惯了,每天这时候我都在鹿圈里转呢。我问二叔,把鹿卖了,还要干点啥?二叔说,咱就是养鹿的,这些年也没干过别的,过了年就给我二姑爷打工去。我一愣,他二姑爷去年我见过,也是一豪爽的汉子,据说也养了很多鹿,是这一片的养鹿大户。我说他就不赔吗?二叔说,人家比咱会侍弄啊,人家总出去学习,舍得投资啊,去年底他一头公鹿就花了十万,谁能比得了?呵呵,大老远的养鹿的都到这里来配种,光配种就挣钱。二叔与其说是在述说,不如说是在炫耀。二叔还说,我说我要把我那些鹿给他,算入股,这小子可倒是鬼,说你那鹿都是不值钱的品种,出(卖的意思)了吧,我给你开支,一个月给你千八的。其实钱不钱的不重要,我就是找个营生。你可说呢,这个鬼玩意,和我还算计呢。
我冷了,再一次让二叔进屋,二叔和我一起走进屋去。这时候正是高潮,二叔在厨房里犹豫了一下,说我还是不进去了,就蹲在地下抽烟。我也陪他在那里抽烟,反正酒喝到这种情况,有我没我都一样了。我看着二叔窝在那里低下了头,他好像睡着了。我也有些困倦。好像过了很长时间,听着屋里一片人声嘈杂,有人走了出来,结束了。谭主任里倒外斜地走出来,看见我一愣说,我还以为你先走了呢,原来猫在这里。我说我又不会开车,往哪儿走?他打着嗝说,你算躲了,我被两位女将和她们老公灌得够呛。我心想,你还是愿意啊。就进屋穿上大衣和大家往外走。二叔又站了起来,依旧袖着手站在院子里和大家打着招呼,看来是有些清醒了,人也有些蔫,不似我们来时那么兴奋。我想,他家猪也没了,鹿也没了,来年看来是没有什么吃的了。二婶和两个姑娘也走出来,她们只是站在那里,木桩子似的站在灯影里,满脸都是僵硬的笑。
阿波夹着包大气地一挥手,说,上车!我们就都和二叔他们挥了挥手,上了车。三辆车缓慢地开进了雪雾中。
谭主任肯定是喝高了,有强烈的说话欲望,他不断地在后面捅着我的后背说,哎,我答应王主任了,那条短信我同意给一百,不过可没你份啊。
我说,我无所谓,贡献了,不过谭总咋不怕财务了?
谭主任舌头有些硬,说,我自己拿五十啊,咱不犯规。还得让她请客。
我说,你小子挺鬼啊,借机会和美女吃饭,你赚了啊!
阿波也说,谭主任,看来还是你收获大啊。
谭主任也不说话,在暗中嘿嘿地笑。不一会,他就彻底不说话了,我回头一看,见他早已歪着头在后面睡着了,有涎水顺着嘴巴淌出来。
车拐上乡道,一片旷野,周围的山一下子辽阔起来。车灯前雪花飘舞,歪头沟很快就被甩到后头了。
古 迹
山呢,叫团山子。有名,是古迹。吉林老八景之一就有“团山对峙”一说,也就是说城东城西各有一个团山子,但我要说的是东团山。东团山位于城东,早些年,城东这地方比较偏僻。桥东不说了,桥东那时还没有开发,一片荒凉。桥西这面就够一说,叫东大滩,地势低洼,正处在松花江在个城市的拐弯处,一片破乱的民居,考证起来差不多都是自己盖的,住常了也就有了手续。住在这里的居民都是平头百姓,一下雨多数人家屋里就进水,苦不堪言。好在那时候领导很深入群众,只要下大雨,市领导一准去看东大滩。市领导进这家出那家的,后面跟着几个拿本子拿相机的记者(那时候还没有电视,电视是后来的事情),于是大家吐吐苦水,说说心里话,领导们都表示要尽快对那里进行改造。第二天报纸上和广播里就有了他们的声音,他们就高兴,说领导重视呢。领导重视是重视,估计也是没有资金,改造就没了下文,好在那里的人们已经习惯了,他们就期待着下一届领导,也期待着下一次下雨,那时就可以再见见领导,再吐吐苦水了。时间久了,那里的人习惯于领导的关心和慰问,有事愿意找领导。知道这个背景对这个故事之所以能成为故事很重要。
你要是问起团山子他们当然知道,他们只知道有东团山,就会向对岸一指,喏,就是那个小山包。山包真的不大,看上去和坟墓差不多。不过,你别小看这个小山包,它在一定程度上可是代表着吉林古代的历史和文化啊。
大约在西周和秦汉之交(久远吧?中国的历史一考证起来都那么久远),东北土著秽貊人的一支(大概叫槖离人吧)以一个叫东明的为首南下渡过松花江来到这个东团山麓,建立夫余国,臣服于汉玄菟郡(我对历史不太了解,都是抄的,这里可能有些混乱,汉代是后来的事情啊。其实东北史本身就有些混乱,好在我不是做考证的),是我国东北地区乃至东北亚地区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当时那里也叫南城子。近年来在其附近发现了数以千计的夫余贵族和平民的墓葬,出土了金、银、铜、铁、陶、玉、石、漆器八百多件。公元470年高句丽好太王亲征夫余,494年被勿吉所逐,此地又先后成为高句丽王国北境的军事要塞和勿吉王国的粟末部地。公元698年至926年,唐代地方政权渤海国涑州的州治就沿用了东团山山麓的“南城子”一称。而后,历经辽、金、元、明、清诸代,都有人在这里劳动生息。说了这么多,就是一句话,我们这个城市的历史都在这呢,无非是说它重要呗。
可是在那么多年里,这里一点也没显出重要来,不说别的,单说它山脚下的那条铁路,如果当初认为这地方重要,怎么也不会就在山脚下走啊。估计搞设计的这个人没学过历史,觉得这个地方挺荒凉的,也就没管历史不历史了(说到这里就要多说两句,不知道别的地方,反正我们这座城市的铁路好像最牛了,它想往哪儿走就往哪走,不是进公园就是占历史遗迹,咳)。还有的说,这条铁路是日伪时期修的南满铁路的一段,那就更不用追究了,日本人管你什么历史不历史的,怎么方便掠夺怎么来。
这铁路从那里越过一座江桥就进了城市,现在的城市那是相当地繁华,我前面说的东大滩已经今非昔比。这些年,市政府实施东部开发战略,以前所未有的优惠政策,吸引着全市包括外地的房地产开发商进军东大滩。东大滩成了金银滩了,一座座高楼平地而起,一个个高档住宅小区应运而生,昔日的东大滩立刻旧貌换新颜。富人们赶着进高档小区,穷人们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但这改善毕竟有限度,他们住的叫做动迁楼或者回迁楼,多数是在铁路边上。铁路边上就铁路边上,经历了多少年冬天寒冷雨天泥泞的东大滩人能住上新楼,乐都乐不过来呢,还有什么可说的?每天早晨,他们听着火车的鸣叫声起床,站在楼上边看着火车从楼下经过边刷牙洗脸,还高兴呢。那时候,他们习惯了火车为他们提供的时间。早晨有一列开往哈尔滨的火车,6点35分经过,他们就说,老哈来了,该起床了。7点左右有一趟开往白山的车,他们就说,老白来了,该上班了。他们每天都拿火车打哈哈凑趣。
可是人这东西,就是耐不住时间,许多人时间长了就觉出了这里的不好,说是噪音污染,说是在这楼里住短寿。怎么就短寿了,那些年住平房的时候也是在铁路边上,光顾了水患,没有人想什么噪音不噪音的。现在不行了,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讲究生活质量了,你富人知道住好地方,我们也知道,只要攒下了买房子钱,人们就开始纷纷逃离这里,去了更好的地方。现在好地方有的是啊,就看你有没有钱。跟前不考虑了,什么江畔明珠啊,什么江畔人家啊,什么鸿博花景啊,跟前的好房子都让富人占领了。听说江南那里空气质量好,又是新开发的,说那里的房子便宜,就都奔那里去。
但是,能搬走的毕竟是少数,多数人还得在这里居住下去。他们的说法就不一样了,他们说,一过火车,楼就像在浪里漂浮,这才有松花江上的味道嘛。他们说,以前晚上最怕火车,现在好了,到点不过火车,还睡不着觉呢,你说贱不贱?这人哪,就是环境的产物,他什么都能适应,又什么都不能适应。他们说,那么多人都大老远地赶来看吉林八景,我们站在楼上就看见了。确实,站在楼上望出去,一江秀水蜿蜒而过,那山倒映在水里煞是好看,铁桥也是英姿勃勃的。说起来现在是没有了,早些年这里还有守桥部队呢,这里的人总能看到他们出操和上岗下岗,那军人敬礼的姿势真带劲啊,别人谁能看到啊。
我前面说了,什么事情也耐不住时间。时间一久,这人的毛病就来了。有人觉得受不了了,说住在这里头疼,说住在这里时间长了耳聋(已经有几个人查出轻度耳聋,有懂的人说再长期这样下去就是中度和重度耳聋),也有人说住在这里休息不好,容易患抑郁症(抑郁症大概不是这么得的吧),反正这个那个的就都来了。凡事总有带头的吧,就有向市里写状子反映的,开始时是要求火车通过这里时不要鸣笛。实际上,自从这里的铁路局归到沈阳铁路局后,铁路已经不怎么牛逼了,特别是提速后,车次也减少了。市里大概经过与铁路方面协调,很快就答应了,火车经过这里不鸣笛。这里的人就有些得意,早晨刷牙的时候看着火车经过,还很有兴致地冲火车上的人挥一挥手,牙膏泡沫全粘在嘴上;小孩子更是要叫上一叫,有讨厌的孩子就站在阳台上,把着小鸡鸡冲着火车方向撒尿,博得大人们一笑。这里的人就有了胜利者的姿态。
过了一阵,这里的人们又不舒服了。他们看团山子看腻了,看大桥也不舒服了,原来是雄伟的,现在看着就有些别扭,挡视线啊,好好的一条江,让它一拦坏了景致不说,每天咣当咣当就这桥上最响,响得是真烦人啊。怎么办?要求铁路改道。这大概有些难度了,但是这里的人们提出这想法不是没有依据的,他们也是懂政治的。其实,这个城市一直想要把火车站挪到城外去,这几年,这个城市发展很快,原来是城市边缘的地方现在都成了中心区,如果把车站挪一挪,就更合理和科学了。但是铁路不归地方说了算啊,他们就去和铁路上的人研究。那时候,这里还有自己的铁路局,还能和中央(就是铁道部吧)说上话,可是等到的结果是在原地建了一个车站,看着还没有原来的气派。后来,铁路局被合并到沈阳了,连分局都不是了,估计放个屁都要到长春去请示,差不多成了一个三等站,市领导也就气馁了。这里的人不理解领导啊,还是用状子往上反映。他们给市人大写,给市政府写,天天去那些能反映的部门反映。那些部门的人也不急不恼,就那么听着,真是好脾气,他们让大家等消息,可是消息永远没有。你今天来他们让你等消息,你明天来他们还是让你等消息。告状的人慢慢的就懈怠了,那些部门之所以好脾气要的就是这样的结果。但是也有不一样的,那个政府信访办的主任就是一个很好的人,他说,要反映呢,我们这级不行,当然我们也有义务反映,但我们现在连铁路局都没有了,解决问题的难度太大啊。主任虽然没有说应该往哪里反映,但告状的人听明白了,要想解决必须往上反映,往上有长春,有沈阳,有北京,这里的人挠着头皮想了想,算了,太费劲了。
这年头,只要你想干事情,总是有人愿意给你出主意的。在商场上这可能就叫策划,在政治生活中叫出谋划策,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好处,想睡觉就有人给你递个枕头。有一高人就给这里的人们出主意了。这个城市不是历史文化名城么,他们最近要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团山是典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听说沈阳的一个高句丽时代的遗址就申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批下来就拨款啊保护啊什么的。东团山要是申请下来,这铁路桥能留住么?现在不比从前了,中央也是重视文化的,铁路和文化遗产比哪个重要?呵呵,这真是好主意啊,我们怎么就没想到,告状的人捶着脑袋,立刻觉出了自己的蠢笨。于是,立刻找人写状子,这状子可就和原来不一样了,得找专业人士写,得把那些新的旧的都写上,当然还是越旧的越好,得有考证啊。我没看见他们写的状子,但是我估计离不开我上面说的那些内容。
呵呵,往深了我就不说了,小说嘛,说多了就有人对号。结果还是可以说一下的,经过层层努力,上面已经开始着手研究这件事情了,这大概就是个好兆头。提出铁路迁移是附带的意见,因为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嘛,要是外国人过来一看有铁路,能批吗?等等等等。当然,这是铁路上的事情,不大好办,铁路也许不管你是不是文化遗产。
山还是那个山,圆圆的,像个馒头。每天有几列火车,绕过山脚,越过横跨在松花江上的大桥,向着城市驶来。当然也有向城市外驶出的。它们都必然要经过和惊动那些住在铁路边上的居民,居民们看见火车依然亲切,依然向火车挥着手,让人看上去很和谐的样子。
杀猪匠
早些年,杀猪匠在北方是很牛的职业。其他季节还看不出什么,也可以说其他季节杀猪匠和别的农民也差不多,看不出有什么区别,但进了腊月就不一样了。
腊月是杀猪的季节,也是杀猪匠大显身手和忙碌的季节。当然,那是对有本事的杀猪匠而言的。
一进腊月,猪就不怎么长膘了。就有人开始张罗杀猪。
一般说,先杀猪的大都是喂不起的和要办婚事的。但是再喂不起,杀猪的头半个月也得给猪吃点好的,比如喂些苞米或者榨油榨出的豆饼渣,这叫给猪上膘。
平常的日子,猪们也是很艰苦的,饥一顿饱一顿地吃糠咽菜。猪食菜一般都采自河边或者田间地头,多是那种叫杨铁叶的植物(我也不知道学名叫什么,很高,多叶,秋天结一串一串的籽),割回来,和苞米面、白菜叶子、酒糟什么的和在一起在锅里煮,煮好了就放在缸里沤着,有点像发酵。喂猪的时候,要把猪食从缸里捞出来再煮一下才喂,即使是这样的猪食也不能光吃干的,是干的稀的一起来,倒在猪食槽子里。猪们也不傻,只有渴了才会先喝点稀的,一般都先将嘴触到槽子底部捞干的,干的吃了了,有那懒散的猪就不吃了,这触一下那触一下。主人对付它们是有经验的,不是不吃吗?弄点谷糠往表面一撒,猪不知是计,以为美餐来了,紧忙争抢起来。谷糠浮在表面上,吃糠必然要连汤带水地吃,这就下去了半槽子,待一层没了再撒一层,这猪食就差不多见底了。想想猪们也是不容易啊,忍饥挨饿,还不是为了这挨宰的一天。
杀猪匠一般都要去请,有名的就那么几个。有的牛气但活计好,一刀见血;有的好说话但手艺一般。就看东家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了。有的屯子没有像样的杀猪人,就要走个十里八里的去请外屯子的,那多数都是牛人。杀猪的多数都拿着三件东西。杀猪刀,这是必须的。好的杀猪匠那几天的杀猪刀是要天天磨的,磨得飞快,能吹毛过刃,直到有人来请,才把刀用看不出颜色的布裹起来,夹着。第二样东西是一根长长的铁条,俗称通条。通条大概有一米左右,一头是个圆环,一头类似长长的扦子,用处我一会儿要说。第三样东西很平常,叫刮子。是铲子一样的东西,一头有刃一头卷曲为把,刮猪毛用的。杀猪匠们就掐着这三件家什走天下。
杀猪匠很少参与抓猪,不是干不了,是不屑于干。抓猪的都是邻近的半大小子,平常有劲没地方使,这时候都摇摇晃晃地上来了,再说捞忙也不是白捞,是有酒喝的。
抓猪一般都是早晨,这天就不喂了,喂也是白喂。猪们还没睡够就被捅醒,不知死期来临,还有些不高兴,还要哼哼一下。半大小子们早已按捺不住,发一声喊冲进去就把猪按住。有讲究的,觉得猪圈下不去脚,就设法把猪赶出来,在院子里行事。有的猪真是英勇啊,知道不好,拼命挣脱,常有猪穿墙而去,那是一两米高的墙啊,看来任何动物在关键时刻都是有潜力和创造力的。猪那惊人的一跳和逃跑常常使人们始料不及,都呆呆地望着逃去的猪。那猪受了惊吓好多天不回来,差不多成了野猪,人们也就暂时杀不成了。也有胆小驯服的,看见那么多人对它使劲,早就在那里筛糠了,人们一拥而上,它早已经吓得大小便失禁,猪屎尿弄得可哪儿都是,也有的弄到了人身上,就笑声一片。说,这瘟猪。看来猪和人是一样的,软弱的也是要被人瞧不起的。束蹄被擒的猪们被用绳子死死系上,用的那种系法有说法,叫作“猪蹄扣”。用猪蹄扣绑人,也是挣不脱的,那扣是越挣越紧。被系了猪蹄扣的猪们成了拱形,躺在那里哼哼不已,一声高一声低地嚎叫,实际是一种无奈的抗争。我们经常说的“杀猪一般的嚎叫”,其实是这时候,真正杀的时候,猪们连哼一声都来不及。
接下去还要过秤。人们也是太过残忍,你杀就杀呗,还要知道是多少斤,倒也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一个比较。早有那半大小子把一根杠子从猪腿中穿了过去,两个人一使劲抬起来,另有人用那大秤一称,报一声多少多少斤,就引来哗的一片笑声,都说好,说比谁谁家的个大,就高兴。主人更高兴,抱着拳说托大家的福。和大家有什么关系呢,不过是要那样说,图个喜兴罢了。
案子这时已经备好,该轮到杀猪匠上场了。此前他可能一直抽着烟,仿佛是在看热闹,杀猪杀得多了,就有些麻木。如果一切正常就无话可说,如果真的遇到了逃跑的猪,他心里也是释然的,仿佛今天的事情有了变故,他也无可奈何,夹起东西就走。主人还要很歉意地相送,说改天,杀猪匠却是走了就不再来了,要杀就得另请高明,这里面有规矩,有说道。对于那个杀猪匠来说,他就相当于杀过了,猪在他那里躲过了一劫。
但好运气的猪毕竟是少数,多数会被按在案子上,这惊心动魄的一刻终于来临了。猪有的还在嚎叫,有的已经无力嚎叫,只剩下哼哼了。只见杀猪匠挽起袖子,上前摸了摸嗓子窝那儿,摸准了,就用刀把那地方的毛剔净,露出白的皮。下面有人准备好了大盆,是用来接猪血的,盆里放点盐,还放着用来搅血的高粱秆,血出来后为了防止它凝固,要有人不断地搅动。猪血也是很好的东西,留着灌血肠呢,那是另一道工序了。
杀猪匠是不容分说的,上去就是一刀,这一刀才是真本事。有的刀柄已经插进去了,他要听见猪那轻微的哼的一声才把刀拔出来,这就是经验了,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一刀进到了什么位置,外人是看不出名堂的。刀一出来,血就喷出来了。杀猪的第一步已经完活,剩下就是接血了。接血的人手忙脚乱,拼命地搅着,那血不断地淌下来,淌过一段时间出血沫子了,才把盆撤到一边。
杀猪人这时已经站到一边抽烟去了,他的手上还带着血,抖都不抖,他看着手上的血,判断着自己这一刀如何,从血流出的情况他就能感到这刀到没到位,血出没出净。如果血出不净就容易捂血,就是没杀好,因为肉中带血是大忌,做出的肉不好吃不说,关键是丢了手艺。
看着血淌完了,他丢下烟头走到已经死掉的猪前,用刀在猪的后腿上挑开一个口子,猪已经流净了血,他伏在那里就吹起来,旁边的人眼瞅着他把那条腿吹鼓了。接着他把通条插进去,开始捅一捅,吹一吹,间或还用棒子敲一敲,很快那只猪整个被吹得圆圆的了。通条的作用我们便知道了。其实被吹完和通完的猪皮已经和猪肉离鼓了,揭开它就是一整张皮。我一直觉得杀猪其实不难,最难和最累的是干这个活,杀猪匠一般吹完之后都会累得呼哧呼哧的。后来这步骤改用气管子往里打气,这就没意思了,就不是手艺了。再后来,连气管子也不用了,我估计主要是猪皮的用处不大了。
水早已经烧好了,热气腾腾的,是那种开过之后有些凉下来的水,太热不行,太热容易秃噜皮,太凉又刮不下毛。众人帮着杀猪匠把猪抬到锅沿上,杀猪匠就用瓢舀着热水一边浇一边用那个刮子在猪身上刮,咔哧咔哧的,让人听了毛骨悚然。那毛就一片一片地掉下来,锅里外头都是,不一会儿一头干干净净的猪就脱出来了。接着是开膛破肚,一切就变得简单了,对于一个杀猪匠来说,肢解一头猪易如反掌。但是,开膛的一刹那大家是要看的。一是看手艺,好的手艺是刀尖正好戳在心尖上,那样就不免使人一阵惊呼和赞叹,杀猪匠也面露得意之色。另一个就是看膘肥,可以伸进巴掌去比量,说三指膘四指膘,那时候越肥越好啊,膘肥好(火靠)油。有那杀猪匠比较生猛,从热腾腾的大肠上割下一块大油放在嘴里生吃起来,让围观的人目瞪口呆。
在整个肢解过程中,要先把猪头割下来,大小要根据主人家的要求,割好了还要留一个孔,用绳子拴着吊在仓房里,再把四蹄和尾巴卸下来用麻绳捆好,和猪头放在一起,留着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吃呢。怪不得东北人都爱养猪,猪全身是宝啊,猪的内脏心肝肺被一起取了出来,那叫一副“灯笼挂”。猪的肠子被取出来了,粪便被倒掉后,用雪、盐和小灰反复搓洗,粗大的自然是留起来,较细的小肠就被切成几段拿去灌血肠了。
灌血肠也是有功夫的呢。接好的猪血已经把那血筋滤出去了,这时屋内烀肉的老汤已经沸腾,用老汤把猪血勾兑好,再加上点佐料,就可以灌血肠了。灌好的血肠一般都扔在雪里埋着,煮的时候一定要掌握火候,先用急火煮开,再用文火慢慢煮熟。这时候会有人拿着根银针不断地往血肠上扎,看看血肠还冒不冒血,一旦不冒血了立刻捞出来,生怕煮老了。出锅后,切成片,蘸点韭菜花和蒜酱,那个香啊。吉林市就有一家“老白肉血肠馆”,专营白肉血肠,上百年历史了还经久不衰,凡是外地客人来,都会被领到那里品尝一下,说明血肠是何等受欢迎。
内脏被掏空后,杀猪匠还要用斧子把猪从脊椎处一劈两半。猪肉被一分为二了,每一半又被分为血脖、前槽、腰窝、后鞧等,一一卸开,一切才算收拾完毕。
这时候就轮到女人们上阵了,她们切的切剁的剁,开始准备宴席了。眼看着那些肘子、排骨,还有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和着酸菜一起下锅,咕嘟咕嘟很是诱人,香味顿时飘起来了。孩子们就跑前跑后,热闹的情景真的不亚于过年啊。
杀猪对于那时的农村是件大事,主人家就借着机会请客了。吃杀猪宴叫“坐席”。请客分几拨,一拨是亲戚,直接的亲戚不管多远都要告诉一声的,我小的时候,就曾经跟着爷爷步行二十多里路去姥姥家坐席。一拨是屯子里的头面人物,比如队长会计等等。再有一拨就是邻居,邻居就是有选择地请了,都请谁也请不起。捞忙的不用说了,有些邻居是日常帮助过自己的,这些家不光大人要来坐席,走的时候还要给小孩子带点东西,比如几片血肠几片肉了,这是女主人要考虑到的。
吃就不说了,什么样的吃相都有,有的甚至喝多了打起来。杀猪匠这时候已经变得不重要了,或者说主人已经顾不得他们了。他们也没的挑,都是自己照顾自己。有爱吃肉的,就用笊篱在锅里捞几块肥肉放在碗里,淋点酱油,蹲在灶台边上闷着头呼噜呼噜吃下,状如吃粉。完了,用手一抹嘴,夹着自己的东西走人了,招呼都不打。等到主人发现,人家可能已到家了,有懂事的事后要补一下的,送点猪头肉什么的。也有的杀猪匠洗洗手,换了衣服,坐下和熟悉的人一起喝酒,喝到酣处也不忘那些家什,走的时候拎上主人赏的东西,一摇一晃地回去了。
到了阴历二十七八,就不杀猪了。杀猪请人都请不去了。眼瞅着快过年了,都在忙着蒸粘豆包、做饽饽呢,都顾着自己忙活,谁还有心思去吃请啊。
责任编辑 牛健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