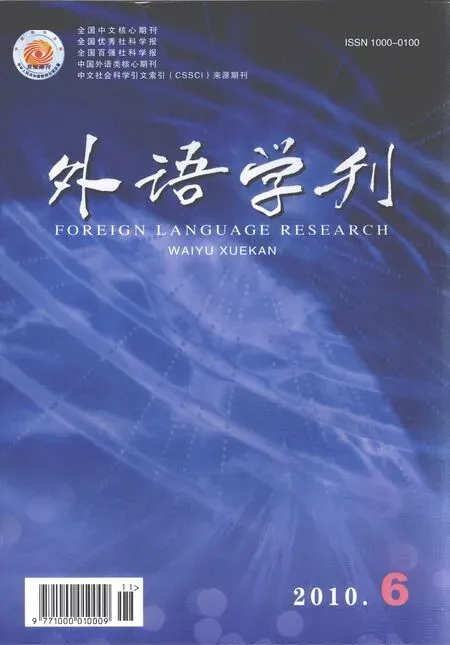西方符号学理论在中国
严志军 张 杰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210097)
在西方,符号学的思想早在20世纪初就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来了,符号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然而,西方符号学理论传入中国则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索绪尔、皮尔士、巴赫金、艾柯等符号学家的理论渐渐为中国学术界所熟悉,甚至在研究方法论上深刻影响着中国学术界。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中国学术界对西方符号学理论的接受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语言学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对西方符号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首先始于语言学界,以索绪尔的二分法的语言符号学理论为依据,努力从语言学的体系化方法去揭示各种西方符号学理论的特征。第二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是超语言学阶段,在此时期,中国学界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环境的变化,已经不再仅仅用语言学的方法去把握符号的体系性和确定性,而且还走出语言系统的羁绊,以皮尔士的三分法符号学研究方法和巴赫金的对话思想为指导,探讨符号的多义、符号的非体系性和未完成性。第三个阶段(21世纪)是中国学术界对西方符号学理论的中国化时期,即“化西”的时期。由于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语境,中国学者们对形形色色的西方符号学理论采取了“和而不同”的兼收并蓄的态度,注重研究各种理论的相通之处,竭力运用符号学解读的多元化方法,探索多元融合的研究途径,同时也在认真研讨符号的实际应用,走出一条自己的理论和实践之路。
本文旨在揭示西方形形色色的符号学理论对中国学界产生的方法论影响和研究思维的更新,以及这些符号学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应用,从而描述中国符号学界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符号学研究轨迹。
1 接受的语言学方式:体系性与确定性
中国学界对西方符号学理论的译介并非仅仅开始于外语学界,中国逻辑学会和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均展开了自己的研究并且成立了相关的符号学研究会。然而,早期对西方符号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还是通过语言符号的研究来推进的,特别是对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理论的译介和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较早出现的关于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研究的论文有岑麒祥的《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和他的名著〈普通语言学教程〉》(1980)、徐志民的《索绪尔的语言理论》(1980)、徐思益的《论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1980)、刘耀武的《论索绪尔的语言哲学》(1981)、徐盛桓的《组合和聚合》(1983)、许国璋的《关于索绪尔的两本书》(1983)等。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只是在向中国学界介绍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思想,更重要地是为中国学界用索绪尔体系化的语言研究方法来研究各种符号,例如文艺符号、文化符号等,开辟了研究的新途径。一般说来,西方符号学探讨语言学与符号学关系的观点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观点是认为语言学从属于符号学,语言学仅仅是符号学的一个分支,此类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早期的索绪尔、皮尔士和后来的雅各布森、韩礼德等以及人类学家拉康等。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曾经强调,语言可以是心理学、生理学、人类学、语法和语文学的研究对象,但是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语言是作为符号的系统。他指出,“语言无法包含各种由符号构成的系统,因此必须有一种符号的学科”,语言是“建立在听觉形象基础上的符号系统”(Komatsu 1993:71-72)。
第二种观点是以罗兰·巴尔特等为代表的符号学家把符号学视为是语言学的一个部分。巴尔特在《符号学原理》一书的导论中就明确写道:“符号学知识实际上只可能是对语言学知识的一种模仿”(巴尔特 2008:20)。他的符号学研究均是建立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础上的,他甚至认为,符号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按照一切结构主义活动的方案,建立一个来自语言学的,研究意指系统的适切性原则(巴尔特2008:73)。
第三种观点是以意大利学者翁贝尔托·艾柯为首的一批学者的折中观点,把语言学和符号学看成两个独立的学科。当然,艾柯在自己的《符号学与语言哲学》等符号学专著中也论述了符号学与语言学的内在联系,特别是符号学与语言哲学之间的关系(艾柯2006)。
然而,在我们看来,这三种观点其实并不矛盾,第一种观点主要是从研究范围的角度来认识的,就范围而言,语言学肯定是符号学的一个部分,因为语言也只是符号的一种,符号学研究的范围显然要比语言学宽广得多,自然包含语言学。第二种观点则是从研究方法的途径出发的,从方法论的视角来看,符号学的研究自然主要凭借的是语言学研究的方法,很多符号现象只有用言语行为才能得到深层解释,符号学的体系也多数是通过语言体系来建构的,甚至符号学与语言哲学有着无法隔断的联系,要通过语言哲学来得到理论提升。第三种观点,实际上是上述两种观点的结合,既强调语言学与符号学各自独立的学科特征和历史渊源,又说明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促动。
由于中国符号学界深受索绪尔语言学方法的影响,不少符号学家又首先是语言学家,再加上语言学研究更接近于自然科学,可以避免意识形态问题的干扰。因此中国学术界对西方符号学理论的接受在第一个阶段,主要是语言学方式的,也就是注重符号结构的体系性、符号意义的确定性。不少学者的研究直接是围绕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展开的,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第一,索绪尔语言学思想及其二元对立的结构原则探讨;第二,索绪尔与其他学者思想的对比研究。这种以语言学方式来阐释符号现象,把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引向深入,也促进了中国学界的逻辑学、哲学等领域的研究。
2 跨越语言学的门槛:非体系性与未完成性
中国学界在受到西方符号学界影响的同时,也保持了自己的学术个性,尤其是到了第二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特征在对西方符号学接受的过程中慢慢显露出来,这主要表现在中国学界对西方符号学理论的选择接受上,不再是笼统地接受,而是根据自身文化的传统来有选择的加以接受。
如果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做一个极其简单的比较,可以说,中华文化是一元的,而西方文化是多元的,前者注重整体性的考察,后者则是着重各个侧面的考察,也许这与中西方神话中的“万神之主”不同有关。中国的“万神之主”如来佛是可以控制一切的,孙悟空再有本事也逃脱不了如来佛的掌心,而西方的“万神之主”宙斯就不可能掌控所有的神。
中国古典文学批评注重“意境”、“风骨”、“神韵”,关注从整体上“感悟”研究对象,而西方的文学批评则是抓主要矛盾的,或以创作为中心,或以文本为中心,或以读者为中心等等,就如同中医与西医的不同。因此,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学界在继续用语言学的方法研究符号现象的同时,又开始尝试对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典籍中符号学思想的挖掘,符号学研究涉及到语言学之外的文学、翻译、艺术和文化、社会等领域。美国符号学家皮尔士的“三分法”(每节、对象和解释)、巴赫金的“多元”、“复调”、“未完成性”等符号学思想倍受关注。符号意义的不确定和多元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而且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这样,以索绪尔语言学为理论依据的符号的体系性、确定性、结构性便被打破了,符号学的研究超越了语言学的门槛,进入到大社会的语境之中。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了大量超越语言学界限的符号学研究论文,例如丁和根的《戏曲演出的符号化特征》(1990)、吴国华的《符号学与国情语言学的关系》(1994)、陈道德的《传播学与符号学散论》(1997)、向容宪的《符号学与语言学和逻辑学》(1998)、高乐田的《民俗学与符号学》(1998)、曾湘云的《名雪域符号学》(1999)等等。
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学界不仅是从范围上扩大了符号学的研究,走出了语言学的圈子,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了除语言学方法以外的其他研究方法,例如社会学、文化学、叙述学、心理学、人类学、广告学、行为学、神学等等。原苏联符号学家别列津和戈洛温的社会符号学思想被广泛接受,即符号是社会信息的物质载体。不少学者还从符号功能的角度,探讨了符号在宗教仪式、交通、传媒、音像艺术等方面的作用,例如王红旗的《生活中的神秘符号》(1992)、吴文虎的《广告的符号世界》(1997)、连甫的《你身边的符号》(1997)、荀志效的《意义与符号》(1999)等等。国际符号学副会长李幼蒸先生在《理论符号学导论》(1999)一书中就把符号学研究分为“语言符号学”、“一般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李幼蒸1999)。他努力把符号学研究推进到人文社会科学以外的学科,甚至进入到自然科学等领域。王铭玉与宋尧合著的论文《中国符号学研究二十年》也清晰地反映出这一发展轨迹(王铭玉宋尧合2006:385-402)。
3 接受与变形:方法论与多元化
进入21世纪之前,中国学界在对西方符号学理论译介和接受的同时,已开始以中国古代丰富的实物宝藏和文献资料依据,努力追溯中国历史上的符号学思想发展。例如李先焜的《公孙龙“名实论”中的符号学理论》(1993)、许艾琼的《荀子正名理论的符号学意义》(1993)、周文英的《〈易〉的符号学的性质》(1994)、苟志效的《论先秦哲学的符号学致思趋向》(1995)、李先焜的《〈墨经〉中的符号学思想》(1996)、高乐田的《〈说文解字〉中的符号思想初探》(1997)等等。非常遗憾的是由于语言文字的局限,这些成果还很少为西方学术界了解。
然而,中国文化的丰厚底蕴使得中国符号学界对西方符号学理论的阐释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性。尤其是进入21世纪前后,索绪尔、皮尔士、巴赫金、艾柯等符号学家已经为中国学术界熟悉,其理论也跨越语言符号等学说的界限,渗透进中国学界的各个层面,促进中国学界的思想解放。这时,中国学界对形形色色的西方符号学理论的接受已经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陈治安、刘家荣主编的《语言与符号学在中国的进展》(1999)描绘20世纪末西方语言符号学在中国接受和发展状况。可以说,中国符号学界对西方符号学理论的接受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变形阐释,也许正是这些变形的接受才反映出西方符号学的中国化接受。
在中国符号学者看来,符号学首先是一个方法论问题,符号学之所以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就是因为它具有独特的研究符号的方法。把符号作为研究对象,并非是符号学的专利,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都研究符号。只不过,符号学研究符号是尽可能多地发掘符号意义的多元,而其他学科则不会关注符号的可阐释空间,这才是符号学与其他学科的边界。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学者更多地关注西方符号学理论的方法论影响。中国南京师范大学国际符号学研究所所长张杰教授于2007年在《美国符号学学刊》上发表了题为《俄苏符号学在中国的接受》论文。该文在回顾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俄苏符号学理论对中国文艺学界的影响之后,从方法论的角度揭示了俄苏符号学理论对中国文艺学界由革命、审美话语向对话、复调转型中的积极作用以及俄苏符号学与中国文艺学在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影响和最终的殊途同归。
2009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的《俄罗斯文艺》在第3期上推出了一组论文,其中田星撰写的“雅各布森的‘诗性功能’理论与中国古典诗歌”就是通过罗曼·雅各布森的诗性符号功能理论,揭示中国古典诗歌的独特魅力。她认为,“雅各布森的‘诗性功能’理论,因其清晰、明确的外延和内涵,科学地阐明了诗歌语言的独特性质,弥补了中国传统诗学研究中的主观性和模糊性;不仅如此,该理论还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它以极其浓缩的语言精炼地揭示出语言这造物者怎样造就了诗的篇章。中国的诗学研究尚存在着‘失之简略’或‘失之繁复’的现象:‘简略’大凡出于主观印象或神秘主义,让人不得其所;‘繁复’则源于对诗歌文本从韵律、节奏、对仗、意境、理趣等各个方面做独立式的考察。而雅各布森的“诗性功能”理论是抽象出来的科学模式,‘对等原则’在语音、词汇、语法、语义所有语言层面的运作将诗歌结成一个层级统一体,保证了诗歌文本分析的整体性和概括性”(田星2009:94)。另一篇值得一提的是管月娥的论文“乌斯宾斯基的结构诗学理论及其意义”,论文不仅揭示了乌斯宾斯基诗学符号学理论的价值,而且探讨了中国古典文化对它的影响。论文指出,“乌斯宾斯基的结构诗学理论在研究的方法论上具有其独到性。他突破了西方传统的科学思维模式,融合了中国古典诗学研究的‘整体观’,通过对‘视点’问题的多维度审视和深入的剖析,指出不同视点之间的有机联系,强调文本形式与内容的二元融合,并将作者、读者共同置于文本结构的研究之中。他的研究既有局部的清晰性,也有整体性的把握,对中国当代诗学研究不无启发”(管月娥2009:84)。
由于中西方文化特点的不同,西方符号学理论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撞和交融下不断被融入,也不断被变形。在中国,符号学研究不仅使得人们的认识变得更加多元和丰富,而且在“和而不同”的话语语境中,促动着各种观点、理论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形成一种“和谐”的、“平等对话”的学术氛围。
管月娥.乌斯宾斯基的结构诗学理论及其意义[J].俄罗斯文艺,2009(3).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田 星.雅各布森的“诗性功能”理论与中国古典诗歌[J].俄罗斯文艺,2009(3).
王铭玉.语言符号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王铭玉宋尧.中国符号学研究二十年[A].符号与符号学新论[C].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翁贝尔托·艾柯.符号学与语言哲学[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Komatsu,Eisuke.Saussure’s Third Course of Lectures on General Linguistics(1910-1911)[M].Oxford:Pergamon Press,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