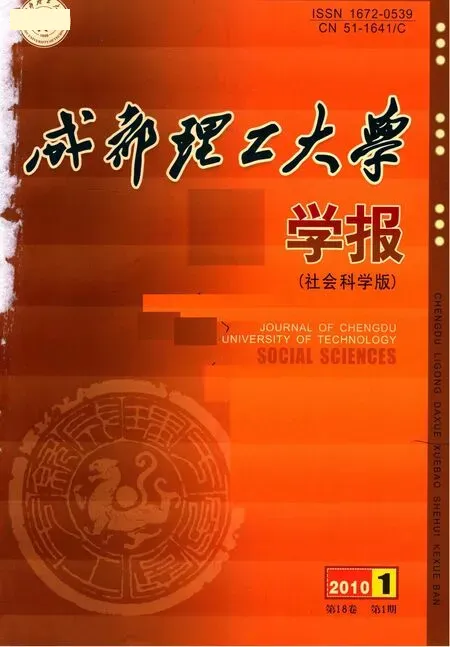女性主义肥皂剧研究方法评析
马薇薇
(中南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女性主义肥皂剧研究方法评析
马薇薇
(中南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女性主义肥皂剧在研究方法上强调性别概念,特别是女性体验,借鉴了美国主流传媒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研究方法,对传统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革新。当然无论是早期运用较多的量化研究,还是更受推崇的定性研究都有其阙如之处,这和女性主义研究者本身矛盾的立场有关。
女性主义;肥皂剧研究;量化分析;定性分析;民族志研究
一、研究方法概述
在最初的肥皂剧研究方法上,美国主流传媒学派所持的经验主义路线是主流,因为肥皂剧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和广告商的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美国不像欧洲,对新型媒体的分析没有受到诸如“其它老的文化形式在美学价值上更加优越”观点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主流传媒学派的肥皂剧研究方法要么采用社会学方法,讲求试验,经验观察,客观描述;要么采用统计学的方法分类,数字图表,量化分析。
作为一个必要起点,当女性主义理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把肥皂剧研究列入研究视野,女性主义肥皂剧研究方法很自然地借鉴了美国主流传媒学派的量化方法,当然经验主义传统显然无法穷尽肥皂剧研究的全部任务,只能从表面探讨肥皂剧现象,在分析肥皂剧对人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时就显得无能为力了。女性主义肥皂剧研究方法上的更进一步,就在于强调性别概念,特别是女性的体验,揭示肥皂剧深层或隐含的文化内涵以及所观察到现象的社会历史根源,借此探究肥皂剧中复杂的表意机制。诚如著名女性主义学家哈定(S·Harding)指出的,“女性主义研究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方法论和知识论,其中包括三个特征:其一,以女性的经验作为社会分析的来源;其二,研究的目的是为女性说话;其三,把研究者和研究主题放在同一个批判的平面上。”[1]
作为一种新兴的批评类型,女性主义既从性别权力结构出发,也不排斥将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现代主义、精神分析中的有效成分纳入自己的方法论中。女性主义肥皂剧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大类,一种是量化研究方法,如内容分析、调查研究等,这是女权主义肥皂剧研究中运用得最广泛、最基础的研究方法,特别在早期的肥皂剧研究中出现得比较多。通过对肥皂剧中出现的与女性有关的种种“因素”加以统计与分析,致力于最终得出一个的结论。荷兰学者莱恩·昂(Ien·Ang)就根据42封观众来信,看重研究了美国著名肥皂剧《达拉斯》观众快感机制产生和起作用的方式。戴安娜·米罕通过“计算女性角色或女主角的数量,在情境喜剧中以一个女性为代价而换来的笑话出现的次数,或者是戏剧性的暴力场景中有关女性犯罪或针对女性所犯罪的次数”,提出了“关于女性角色的力量与无力,脆弱与坚韧的问题”。[2]
女性主义肥皂剧的研究方法另一种是人文科学的定性分析方法。定性分析的研究方法更易于将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置于平等的地位来考察,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共同参与了整个过程,研究者将自己看成是被研究者中的一员,随时随地意识到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态度情感对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影响;而研究对象的主体意识和情感意愿也将通过这个过程体现出来,使研究者能够透过研究对象的眼光去理解这个世界,这样所得出的结果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互动的产物[3]。
定性分析包括很多具体研究方法,深度访谈是较早使用的一种。如赫塔·赫措格(Herta·Herzog)是广播肥皂剧的一位早期研究者,她通过对收听肥皂剧的观众进行访谈,发表了题为《我们对白天连续节目的听众究竟知道什么》的历史性论文,认为这些广播肥皂剧为什么如此深入观众的感情,是因为观众的大部分——妇女可以借此发泄感情、实现梦想、得到满足。还有实地观察的研究方法,女性主义研究者实地观察女性收看肥皂剧的行为,不参与其中,只是单纯记录女性在家庭环境中收看肥皂剧的有关信息。实地观察和深度访谈这两种研究方法常常会结合起来运用。如多萝西·霍布森(Dorothy·Hobson)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围绕着一部长期播放的英国肥皂剧《十字路口》(Crossroads)所做的研究。霍布森说自己的方法是晚上和某个家庭一起观看《十字路口》,看完后再进行访谈。一个家庭中男性很少观看这部电视剧,即使有男性观众观看,通常也只有女人愿意和霍布森走进厨房探讨当晚播出的那一集,女性们表示她们有时不得不在丈夫的敌意中看节目。[4]
其他研究方法还有个案研究、心理分析等,本文在这里主要以民族志研究方法为例进行分析。女性主义肥皂剧研究采用民族志的方法,受到了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影响。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不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转变了将大众传媒归结为异化、物化层面的做法。特别自霍尔(Hall)以后,西方以英国文化研究为核心的大众文化研究更加重视受众的力量,并把受众研究向时间、空间、性别等各个领域延伸,进行了许多富有价值的研究方法的探索。肥皂剧的民族志研究就是文化研究学派运用得颇具特色、也很广泛的一种。民族志是源于人类学的一种田野调查方法,它指研究者通过深入研究某一特定群体,长期观察研究以后,从这一群体的文化内部,来说明该文化的意义和行为。这种研究方式的好处在于研究者不会轻易“替人说话”,从而相对客观些。[5]。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民族志的研究将目光聚焦于电视受众,成为一种典型的受众研究。莫利是民族志研究方法的最早提倡者,他指出,电视的民族志研究的起点应当是家庭。“因为牵涉电视的活动都是在这里创造出来的,而说明或结合看电视之意义,大抵也在于此完成。家户与家庭都是外在更大社会与文化环境之产物,透过了它的日常互动类型,透过了它自身的内部关系体系,以及他自己的合法性与认同性构之文化,提供了探究自然情景下,意义之产生与消费的最佳实验室。”[6]民族志研究方法使用日常生活的叙事代替了宏大的政治理论,既是一种文本实践又是一种社会实践。纳汀格尔(N·Nightingale)指出,民族志研究的目的是描述而非批评或解释,它提供的是数据而非文化批评[7]。然而大众传媒研究发现它所采用的民族志方法虽然不是纯粹的人类学研究,但是它提供了有关媒介受众以及他们与媒介内容之间关系的新材料,以及对大众社会态度的更深刻理解。[8]因为这个原因,尽管在它的使用中有很多理论问题尚未解决,但仍繁荣并发展起来。
许多女性主义学者也纷纷采纳民族志的研究方法,非常典型的方法是,研究人员例如选定家庭,然后花上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和女性观众在一起看电视,讨论节目内容,探讨她们看电视的方式,以及电视在家庭生活中的作用等等。这些采访的记录副本是以后进行分析的原始数据,并且在公开的研究成果中会附带摘录。女性主义肥皂剧研究,采用民族志方法的主要著作有多萝西·霍布森的《十字路口》、玛丽·艾琳·布朗的《知识和权利:肥皂剧观众的民族志》、塔尼娅·莫德斯基的《从今日肥皂剧中探索明天》。
二、女性主义肥皂剧研究方法的启发价值
从发展的角度,女性主义肥皂剧研究所采用的这些研究方法有重大的启发价值,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和新的知识生长点。第一,尽管有人认为女性主义研究方法与传统的方法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是,在笔者看来,女性主义研究方法并不是对传统社会研究方法的简单修正,而是从一种范式向另外一种范式的转换,重新构建各种传统的认识论对社会生活的分析,从而找到理解女性的实际体验的方法论基础。在用女性主义方法对大量涉及到女性的社会现象重新进行分析和解释的过程中,经常出现“反常”,正是这些“反常”,带来了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从而带来对社会的新认识。[9]
第二,女性主义者把女性既作为研究对象,又作为知识的生产者,所以,女性主义肥皂剧研究转变了传统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使人们对诸如自然性别、社会性别、家庭暴力、同性恋、乱伦、性骚扰等开始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此同时,女性主义重视地方性知识的生产过程,重视各种不同女性“位置”的知识,这些探究丰富了对“她者”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二元论”立场,丰富了我们对社会的认识。另外,女性主义肥皂剧研究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课题,如对身体语言、日常谈话等的研究。女性主义肥皂剧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还适用于对其他弱势群体的分析。如,对老年人、残疾人、贫困人口等弱势群体的分析,因而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第三,女性主义肥皂剧研究也为社会科学方法的创新提供了一个绝好例证。许多女性主义者指出,如果把方法仅仅看成是一种能够做出“发现”的方法,那么,方法就会成为一种自我封闭的东西。现在,学者们已经认识到,方法不应该是自我封闭的,它只是一种工具、一种视角。方法本身不是一成不变的,就像科学的内容一样是不断增长和发展的,它也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变迁。这样,女性主义方法就向公认的传统方法提出挑战。另外,“女性主义方法是一种具有强烈价值导向的研究视角,将服务于那些关注社会正义的学者,因而具有强烈的实践意义。这种实践意义也为方法研究的创新提供了有益的思路。”[10]
三、女性主义肥皂剧研究方法的阙如
女性主义肥皂剧的研究方法中,量化分析方法存在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肥皂剧和观众之间的关系复杂而且是多方面的,怎么可能用什么科学规律来解释女性观众和内容虚构的肥皂剧之间的奇妙关系呢?女性观众清楚地知道肥皂剧的故事并不真实,但为什么她们仍每天心甘情愿、甘之若饴地收看呢?一份这方面的问卷调查到底能说清楚多少问题,这是让人怀疑的。这种把自然科学的方法生搬硬套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显然不妥的。“计算女性角色或女主角的数量,在情景喜剧中以一个女性为代价而换来的笑话出现的次数,或者是戏剧性的暴力场景中有关女性犯罪或针对女性所犯罪的次数。”[11]如此简单量化分析的直接结果,就使得肥皂剧中的女性形象总是被定位于被动的、顺从的、被情感支配的性别角色,活动范围限制在家庭里,有工作的女性也仍然是以家庭生活为主。由此,女性主义批评者得出结论,认为肥皂剧限制了父权制社会的意识形态,强化了一套由来已久的性别陈规。这样看来直接把自然科学的量化分析的方法套用在肥皂剧上并不是完全适用的。
这里以内容分析的缺陷为例展开分析。由于内容分析过多依赖于肥皂剧文本的分析,自然就存在着不足:第一,内容分析把研究的视野局限于肥皂剧文本,忽视了肥皂剧播放过程中能动的观众的作用。批评者在做内容分析得出结论时,往往要依赖于两个假设:一是假设在观众的心目中,肥皂剧播出的内容具有现实性和真实性,观众可以把那些虚拟世界中的生活、人物解读为现实生活中的生活、人物;[6]261二是肥皂剧的观众究被动接受肥皂剧演出的内容,自己无法独立思考。而在现实情况中,肥皂剧观众与肥皂剧文本之间的互动关系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生活、心理、地域、种族、宗教、性别等诸多因素参入其中,产生的影响很难分析清楚。
第二,内容分析采用单一量化分析方法,容易忽视经济、政治、文化等权力因素,而满足于唯一的性别权力结构的分析视角。如果内容分析习惯于停留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就不容易对肥皂剧研究做出深层的探究。批评者就有可能用量化分析的具体操作来满足自己预先设定的结论,这一点尤其可能在商业电视控制中被利用。
一部分女性主义学者也认为量化分析属于男性方法(M ale M ethods)的代名词,这样定性分析受到了大部分女性主义学者的推崇。但这种研究方法也并非完美无缺。在肥皂剧研究上,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无疑带来了一些有益的启发,但是也招来了很多质疑。第一,民族志肥皂剧研究是从一个小群体入手,有时甚至是小群体的抽样调查结果,这样的结论是否具有代表性?第二,研究者本身也是电视观众,他自己的经验很可能有意无意地进入到研究的结论中去,民族志应有的研究距离还可能存在于对电视观众的分析中吗?第三,民族志肥皂剧研究把获得的资料作为肥皂剧研究的分析证据,但这些证据就真的有资格成为研究文本吗?或者只仅仅是丰富了研究文本和扩大了文本范围?第四,因为研究人员预先构筑一个社会群体,那么如此仿真的群体是否可以和正常生活中的社区观众完全相同呢?这些质疑看来不是民族志方法本身解决得了的,但我们更不能否认民族志的肥皂剧研究成果的重要,它提供了研究肥皂剧的另一种独特的视野,作为肥皂剧研究的辅助,常常成为一种必要的修正和手段。
再如在实地观察中,最难以达到的是观察对象的代表性以及抽样的科学性。只能实地观察某一时段女性观看肥皂剧的信息,但女性在家中等不同环境(比如做饭、做家务、和朋友闲聊)下的收视情况就观察不到了,这种方法也易受主观干扰。由于实地观察依赖研究者的感觉和主观判断,同时也依赖与研究课题有关的假设,因此其研究结果将无可避免地受到研究者本人先入之见的影响,对事物另一面的观察很有可能被忽视或扭曲。有鉴于此,实地观察不要只使用一个观察者,其结论一般要由两三个甚至更多的观察者进一步证实。这种方法还影响研究对象行为的真实性。从理论上讲,所有研究方法都可能对研究对象行为的真实性构成影响,实地观察法在这方面的影响尤其明显。在对家庭收视行为的观察研究中发现,研究者在场对接受观察的家庭成员确实有影响。不少女性指出,他们所有的活动都受到研究者在场的影响。
在深度访谈中,讨论局面的维持及效果的保证有相当难度。研究者在研究中作为领导者控制研究群体,有可能引导他人的谈话中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被研究的妇女。因此,深度访谈调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主持人的技巧,她必须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探索更深入的问题,什么时候阻止讨论的话题,怎样使所有的参与者加入讨论。这些都必须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细心才能完成,对参与者一个嘲讽性或不恰当的评论,都可能会对群体的行为产生负面的影响。特别在小规模的深度访谈中,小规模深度访谈的调查样本由自愿者组成,她们并不必然代表周围人们的意见,记录仪器或调查场所的特性会使参与者感到拘束。如果参与者偏离讨论问题太远,所得到的资料可能无甚价值。结果是否可以推论或如何推论,是深入访谈最易引起的问题。[12]
其实,无论是定量分析方法还是定性分析方法,女性主义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肥皂剧研究中都有遇到两大难点:一是知识分享中的权力关系。依女性主义的立场逻辑,研究者要帮助参与研究的女性去“发现”她们自己,让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一起决定研究的目的、怎样研究并运用研究成果。然而,在实际研究中,研究者不可能真的把她的“发现”与专业知识分享出去——研究者的自身利益,来自研究委托者、赞助商等对研究结果的社会评价,面对学术界的“承认”、“接纳”问题等,均是研究者不得不考虑的因素。[13]二是研究者的知识优势的影响。一般而言,从事女性研究的研究者,比之被研究者的女性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特别在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的研究中,研究者在事实上具有知识精英的身份背景,具有一定的知识优势。这种研究者所具有的知识优势,难免不影响到她与被研究者的现场关系、调查过程及调查结果——从语言、谈吐、情感、气氛,到心理认同等等,极易出现研究者为“控制者”,而被研究者为“被控制者”的知识生产的不平等格局。即使一位研究者,能以平等的心态对待被研究者,而她在研究现场的“知识位置”——“倾听者”的身份,也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居高临下地把研究者置于“被动的知识位置”上。
四、女性主义研究者的矛盾立场
研究方法上出现的诸多问题,更多和研究者本人的矛盾立场有关。尽管女性主义学者在研究方法上已经采用了全新的性别视角,但她们对待肥皂剧的立场仍然是矜持而保持距离的。早期的女性主义肥皂剧研究是因为需要一些议题来佐证她们的观点,肥皂剧看着合适就拿来用了,而非肥皂剧本身引起了她们多大的研究兴趣。这使得早期的女性主义学者喜欢直接拿一种思想观点来分析肥皂剧文本,得出的结论明显有一种决定论的色彩。比如阿楚尔在肥皂剧研究中运用了激进女性主义的观点,从性别差异角度来反对男性象征秩序,认为女性气质优于男性气质。阿楚尔在论述中,解释说肥皂剧将这种压制性的父权制家庭理想化,隐含的意思就是,女性能够并且应当抵制肥皂剧中这种遭到贬低的形象,反对这种侮辱性的生活场景,从而寻找回自我,重获自主和独立。[2]241指出肥皂剧家庭复制出父权制社会中的理想家庭,这种解读无疑使阿楚尔用一种纯粹批评者的角度,坚持对肥皂剧所代表的父权制意识形态作彻底批评。这样直接拿一种思想观点来解析肥皂剧文本,得出的结论明显有一种决定论的色彩,父权制意识形态到底怎样令人信服的发生作用,阿楚尔并没有解释清楚。莫德斯基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她有时候是以一种很屈尊的姿态把肥皂剧当作艺术来看的,似乎是从美学的高峰俯视着它。她用一种权威的语言断言,“类似同性恋的问题却被轻易地忽略了,然而,这是个可以分解家庭结构而不是暂时分裂家庭的问题”。[14]有趣的是,在澳大利亚的肥皂剧《96号》和美国的肥皂剧《王朝》、《三十多》、《落杉矶法律》中,同性恋在剧中却是表现得如此地显著,如此地引人同情。
随着女性主义肥皂剧研究的发展,许多女性主义批评者不再坚持一种超然物外的研究立场,事实上,这一点也很难做到。一个重要的矛盾显现出来: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集观众与批评者的双重身份于一身,作为观众所获得的视觉愉悦和作为批评者所进行的意识形态批评之间必然会产生一定的矛盾,如何处理与协调这个矛盾已经引起了许多女性主义批评者的关注。
比如蒙福德既是一位喜爱肥皂剧的观众,又是一名持有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立场的批评者,如此双重身份造成的矛盾该如何调和?蒙德福一直在做自我挣扎:“我即从这一剧种得到了愉悦,又认识到这种形式的倾向就是要复制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压抑性的意识形态,这二者之间必须得到调和。”[15]5这番疑问在一开始便奠定了蒙福德肥皂剧研究的基调,指导着她的研究。身为一个女性主义学者,蒙福德做肥皂剧研究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便是她从1969年17岁开始观看肥皂剧,积累了多年的亲身感受。尽管如此,蒙福德也意识到自己既“不能从其它肥皂剧观众里把自己轻描淡写地择出来”,又不能坚持认为这些女性观众“对一种明摆着是商业化的、性歧视的劣等形式的享受令我沮丧”,也“不能自称像某些观众一样天真,和那些不是职业批评家的观众有着同样的接受习惯”。“若是身称自己的批评专长和理论专长根本不曾影响我观看肥皂剧的方式,或是断言自己从未激荡在剧中叙事所带来的愉悦之中,我想那也会是一派胡言。”[15]6蒙德福努力在观看中保持“一定程度的自觉意识”,希望自己是“一个肥皂剧迷,但不仅是个肥皂剧迷,是一个批评家,但从来不单单是个批评家。”[15]7但遗憾的事,蒙德福还是没有很好处理这种微妙关系。她的研究从一开始就试图通过保留一种“自觉意识”,使自己能够在观众与批评者这两个角色间轻松自如地转换。在她的论述中,不断在自身的收看体验和纯粹客观的他者收看体验之间跳来跳去,又没有阐明清楚二者之间的关系,使得这两种收看体验混淆在一起,最终使得整个文本在分析、讨论和下定义时,狭隘而缺乏深度。
可见,女性主义学者的观剧经验和她的研究身份,势必会对肥皂剧研究的客观性产生威胁。尽管女性主义学者们努力避开这个陷阱,但是,诸如“批评家/理论家并不是她口中的观众一分子”[15]5这类的话语仍然如梦魇般追逐着她们。
[1]吴小英.女性主义社会研究述评[J].国外社会科学,2000,(2).
[2]伊·安·卡普兰.女性主义批评与电视[C]//[美]罗伯特·C·艾伦.麦永雄,柏敬泽,等,译.重组话语频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53-254.
[3]Reinharz,1992;Oakley,1981 Reinharz,Shulam it,1992,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Oxford U-niversity Press.Oakley,Ann,1981, Interview ing Women:A Contradict ion in Term s,in Doing Feminist Research,ed.By H.Roberts,London:Rout ledge&Kegan Paul.
[4]Dorothy Hobson.Crossroads:The Drama of a Soap Opera.Methuen :London,1982 :108-110.
[5]潘知常,林玮.传媒批判理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267.
[6]大卫·莫利.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M].台湾:台湾远流图书出版公司,1995:280-281.
[7]N.Nightingale,“What’s Ethnographic about Audience Research”in Austral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39,1989:18-22.
[8]J.Fiske,Reading the Popular,Boston:Unw in Hyman,1989:104.
[9]Nielsen,J.M.,ed,Feminist Research Method,Westview Press,1990:22.
[10]刘军.女性主义方法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2002,(1):39.
[11]安娜·米罕:《夜晚的女性:黄金时间中的女性角色》[C]//.[美]罗伯特·C·艾伦编.麦永雄,柏敬泽,等,译.重组话语频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53.
[12]龙耘.注重宏观把握,审视整体过程——定性分析方法简介(上、下)[J].当代传播 ,2000,(5)、(6).
[13]Pamela Abbott and Claire Wallace,C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Feminist Perspectives.Routledge,1990:289.
[14]Tania Modleski.Loving With a Vengeance:Mass Produced Fantasies For Women.New Yo rk:Methuen,1982:205.
[15][美]劳拉·斯·蒙福德著.林鹤,译.午后的爱情和意识形态:肥皂剧、女性及电视剧种[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Analysis of Fem in ist Research Methods Soap Opera
MA Wei-Wei
(School of Liberal A rts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3,China)
Feminist soap opera in the research methodsemphasize the concep tof gender,especially women experience,learn f rom the U.S.mainstream media,schools and the British school of cultural studies research methods of traditional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of the innovation.Of course,w hether the early use of mo re quantitative research,o r a mo re qualitative study by the respected have their lacking of the Department,this and feminist researchers closely linked to their conflicting positions.
Feminism,soap opera research,quantitative analysis,qualitative analysis,ethnographic research
I106
A
1672-0539(2010)01-006-06
2010-01-20
国家社科项目《电影文化产业的文化传承与文化消费》(06BZX020)
马薇薇(1978-),女,湖南津市人,讲师,主要从事中西新闻比较、影视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