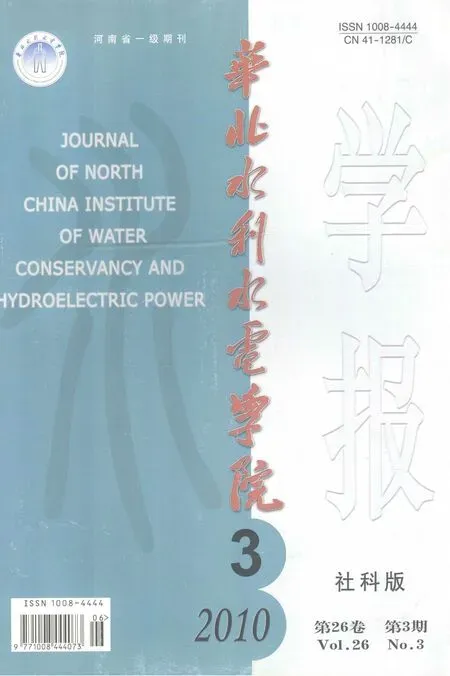忧郁而华美的歌唱
——简媜散文简论
刘涵华
(安阳师范学院,河南安阳455000)
忧郁而华美的歌唱
——简媜散文简论
刘涵华
(安阳师范学院,河南安阳455000)
简媜是台湾著名散文家,其“计划性写作”主要分为三个主题:个人断代史、女性命运、家族赴台数百年垦拓史。简媜散文带有某种悲观色彩,但作者顽强的抗争精神、鲜明的文体探索意识和典雅华丽的语言风格,使其作品成为台湾女性散文和整个女性汉语散文中的佼佼者。
“计划性写作”;悲观色彩;文体探索;语言风格
简媜是台湾著名的女性散文家,曾获台湾三大散文奖和时报文学奖等多个奖项,并出版有《水问》《只缘身在此山中》、《月娘照眠床》、《私房书》、《浮在空中的鱼群》、《下午茶》、《梦游书》、《空灵》、《胭脂盆地》、《女儿红》、《顽童小蕃茄》、《红婴仔》、《天涯海角》等十多部散文集。20世纪90年代,大陆的友谊出版公司出版了《水问》之后,其他出版社也竞相出版了简媜的《忧郁女猎人》、《玻璃夕阳》、《烟波蓝》等多部散文集。简媜散文不仅赢得了学者们的高度评价,而且也正在为大陆越来越多的读者所接受。
一、主题意向的完整呈现
散文创作最初对于简媜而言,是一种精神上的抚慰力量。从宜兰乡下进入都市读高中后,简媜一度陷入孤独和自卑中,作为一种抵抗方式,她开始了散文写作。正如她后来在接受采访时所言:“我在写作这条路上,开始的方式可能跟别人不太一样,是在心情最狼狈、最落魄、最孤独的时候,碰上这件事情。”而当写作给她带来了成功与荣誉之后,散文创作对于简媜而言,便不再是一种人生的应急举措,而是经过统一规划,具有明确计划性的创作活动了。
迄今为止,她的每一本散文集几乎都有着鲜明的主题意向:《水问》集中反映了自己的大学生活;《月娘照眠床》是作者对故乡人事的深情回顾;《私房书》是都市生活浮光掠影中的心情小札;《下午茶》以茶喻人生,抒发自己对人生与社会的看法与感触;《梦游书》描写身为都市边缘人的生活体会;《胭脂盆地》探索世界性的大都市台北置身于文明与传统间所形成的复杂关系;《女儿红》则抒写女性心理的幽微情感;《顽童小蕃茄》记载自己的小侄女——一个单亲家庭中小女孩儿的成长经历。这种一本散文集具有一个相对集中主题的写法,台湾研究者称之为“计划性写作”。这种写作方式的主要特点是,其思想和主要内容在创作过程开始之前就已经产生,经过一定时间的素材积累和情感酝酿而逐渐成熟。在下笔之前,其整体构架业已基本完成,而真正的写作过程,只不过是给已经呼之欲出的灵魂一个可以往来于尘世之间的血肉之躯而已。这就比那些由一篇篇相互孤立的散文组成的作品集,多出一种经过宏观构思的整体性力量。
简媜二十多年的散文创作,从主题性方面呈现出这样一个轨迹:先是以一种半自觉的方式构建出了个人的断代史,即系统地反映了自己的“原乡生活”、“大学时代”、“爱情世界”、“初为人母”等人生的不同侧面。需要指出的是,简媜散文中的个人断代史,并非那种“小女人”式的生活实录,而是经过了艺术再造、充满个体魅力的心灵史。
以个人的心灵史为切入点,简媜又逐渐扩大自己的视野,对广大女性的集体命运进行了具有形而上意义的深入思索。应该说,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是区分女性散文家品位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这一方面,不少优秀的女性散文作家都有所建树。如果加以横向比较,简媜的《女儿红》即使放在整个20世纪所有的汉语女性散文中,也毫不逊色。这个作品集引起了无数女性的强烈共鸣,一版再版,应该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对女性集体命运进行深入思索的基础上,简媜又难能可贵地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她以女性视角为原点,回溯历史,记叙并诠释了自己家族的先祖数百年前从福建过海垦拓的艰难业绩,并详细记述了自己所认识的抗日史和近代台湾社会的变迁史。这就使得简媜为自己的生命存在和自己的散文创作寻到了文化和血缘之根,其视野的开阔和历史的纵深感,都是其他的女性散文很难企及的。
简媜这种经过审慎的理性思索,构架出清晰的创作理念与计划,然后将作家内心的主题意向以集束的方式完整呈现出来的方式,一方面显示了简媜对散文写作的宏阔襟抱,自有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气;另一方面也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展示了她作为女性散文家不可多得的文学能量与才华。
二、带有悲观色彩的抒情基调
司方维在谈到简媜的散文集《女儿红》时曾认为:“伤痛是简媜散文集《女儿红》的一个文眼,写到了女性作为母者的疼痛,作为女人的伤痕,也写出了女性作为人的生命体验。这些痛苦的经验都已经超越了物质层面,来源于灵魂的无处安放,从而表达了对生命和人生的思考。”[1]其实,不仅仅《女儿红》是这样。纵观简媜散文创作,可以说都具有一种带有悲观色彩的抒情基调。
这种抒情基调的形成,首先和作者的成长经历大有关系。简媜幼年丧父。父亲在世的时候,她对这种父女情缘并没有太深刻的体会,而一旦父亲去世,便给她留下了永生永世的悲情与伤痛。简媜的名篇《渔父》,极为深刻地抒发了这种刻骨铭心的情感,特别是“捡骨”一节,可以说是字字饱蘸思亲之泪。
我们做了十三年的父女,至今缘尽情灭,却又在断灭处,拈花一笑,父亲,我深深地赏看你,心却疼惜起来,你躺卧的模样,如稚子的酣眠、如人夫的腼腆、如人父的庄严。或许女子看至亲的男人都含有这三种情愫罢!父亲,滔滔不尽的尘世且不管了,我们的三世已过。
《四月裂帛》是简媜另一流传甚广的名篇。其中结尾写到了自己男友的亡故,在貌似无情中流露出浓烈的悲观情绪,仿佛情人间撕心裂肺的死别,不仅无法回避,而且只能是以这样一种无情的方式包裹、埋葬。“纵观简媜散文,生命性一直是贯穿简媜散文的精魂之所在,然而简媜散文生命意识的凸显,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死亡意识为观照,死亡是促使简媜走上创作道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2]
对于自己散文的悲观抒情基调,简媜自己也是有所认识的。“我很早的时候,性格的基调是悲观的(作品中写到死亡很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几乎是觉得,我活到二十岁就好了,那种对生命、存在,非常的感到无奈,因为累积太多悲伤的故事,而自己的成长过程不太顺利。”或者可以说,简媜散文中的这种悲观的基调,除了与成长过程中的不幸经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和她自己的内在的秉赋有关。
郑明俐认为:“每个够格的创作者都有他先验的文学理论在,但他本身并不很清楚他的文学体系是怎么样,他有他的文学观、人生观及思想,这是作者创作的原点。”[3](P10)随着简媜散文创作活动的不断延续,这种不甚了了的创作原点也逐渐明晰起来,成为一种创作风格的理性追求。简媜认为:“我觉得悲伤会让人深刻,比较去思考存在的温馨与价值;喜悦和幸福可能会让人肤浅。”相比较之下,简媜早期散文的悲观抒情基调比较强烈,而后期理性色彩则更突出一些,更有节制一些。
这种带有悲观色彩的抒情基调,作为一种美学风格,自有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胡明伟在《悲剧意识与文化传统》中曾指出:“悲剧意识是指在人类发展过程和社会发展进程中,体现在某些人物身上的那种无为而为的心理倾向”“只有人们正确地认识和把握现实的悲剧性,并想改变自己的生存困境,悲剧意识才可能形成。”[3]对于一个13岁就失去父亲的乡下女孩而言,这种觉醒之后的悲剧意识正是促使她不断向命运抗争的主要动力。简媜是悲观的,然而她并不绝望。依靠数十年持之以恒的努力奋斗,作者从一个没有父亲的乡下女孩儿,最终成长为一个出色的作家,成功地拥有了极富光彩的人生。而简媜散文带有悲观色彩的抒情基调之所以具有积极意义,原因也正在于这伴随着悲情的顽强抗争。
三、在文体的边缘地带寻求创新
作为一切文章的母体,散文可能是所有文学样式中内部分类最多、争议也最大的文体。对于大多数作家来说,散文只是他们的“文余”,兴之所至的时候“客串”一下,所以他们对散文文体本身关注和思考得较少。但对于专事散文创作的简媜就不一样了,宏阔而高远的文学理想使之充满了探索精神和创建意识。简媜理性指导下的文体探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适度的虚构
真实地表现自我,以及自我所能感知到的客观世界,是散文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特征,也是散文区别于小说的最后疆界。因此,散文不允许虚构,否则,它就失去了自身的特质,同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这是多少年来人们业已形成的通识。但是,对于什么是真实,却一直有不尽相同的认识。近年来,刘锡庆、陈剑晖等学者的散文理论,也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不少论述。而在简媜看来,散文是写意的艺术,真情实感是它最重要的特征;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细节与情节的真实也许就不再是绝对重要的了,而只有心灵的真实才值得引起人们充分的关注。简媜认为:“我在作品中比较不会作现实人生的移植,是经过处理的,即使在作品中见到有些生活的影子与轨迹,也都是经过处理的。”这种处理,既包括裁剪与取舍,也包括细节与情节的适度虚构。在简媜散文中,特别是回忆早期家乡生活的那些篇什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或许有些像鲁迅创作《朝花夕拾》时的情形。鲁迅在《朝花夕拾·小引》中坦言:这10篇作品“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4]。应该说,“只记得是这样”更能表现作者对故乡的思念与眷恋,更符合作者的心理现实。
(二)注重人物的对话
对话是小说中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方法之一。简媜散文借鉴小说这一特点,在散文中嵌入精彩的对话,并使之兼有推动叙事、营造情境、塑造人物形象等多种功能。除此之外,简媜散文中精彩的对话还有效地控制着叙述角度的变换,也成功地缩短了叙述距离。《渔父》中写自己仓皇地向大伯公询问父亲遭遇车祸的情景:
“阿爸怎么样?”
“啊……啊……啊……”他有严重的口吃,说不出话。
“怎么样?”
“啊……啊……,伊……伊……”
就在我愤怒地想扑向他时,他说:
“死……死了……”
他蹒跚地走去,摇摇头,一路嗫嚅着:“没……没救了……”
这样充满艺术张力的对话不仅成功地再现了情景,而且也刻画出了当事人复杂的心理活动,只要读过便令人终生难忘。
(三)蒙太奇手法
简媜散文非常善于借鉴多种艺术种类的表现技巧,特别是电影中蒙太奇手法。蒙太奇在法语里是“剪接”的意思,后来被发展成一种电影中镜头组合的理论。当摄影师在描述一个主题时,可以将一连串相关或不相关的镜头放在一起,在组合中产生暗喻的作用,这就是蒙太奇。
在借来的时空,我们散坐于城市中最凌乱的蓬壁,抽莫名其妙的烟,喝冷言热语的酒,我将烟灰弹入你的鞋里,问:
“欸,你也不说清楚,嫁给你有什么好处?”你脱鞋,将灰烬敲出,说:“一日三顿饭吃,两件花衣裳嘛,一把零用钱让你使。”
我又把烟灰弹进去:“那我吃饱了做什么?”
你捏着我的颈子:“这样么,你写书我读——再弹一次看看!”
我又把烟灰弹进去。
这是简媜散文中回忆自己恋情的片断。她成功地将蒙太奇手法平移到散文创作中,不仅产生了画面感,而且产生了画面与画面之间切换的蒙太奇效果。其中男友虚张声势的“大男子主义”和简媜因被爱而“有恃无恐”的对比在巧妙的衔接中相得益彰,恋人之间的亲昵与谐趣也因之表现得淋漓尽致。
四、典雅华丽的语言风格
“诗人的语言是他自己的语言,诗人始终不可分地存在于这一语言之中;他利用这语言的每一个词形、每一个词、每一个语汇,都为了直接的目的,换言之,是纯然直接地表现自己的意图。”[5](P53)简媜的文学语言极富特色。从高中二年级的习作,到成名之后的名篇佳作,其思想内容一直在不停地发展变化,但其语言风格却相对稳定,一以贯之。简媜的散文语言风格,堪称典雅华丽。所谓典雅华丽,主要是指声音和谐悦耳、词语艳丽绚烂、句式变幻多姿、辞格华美奇巧。“把我当成你回不去的原乡,把我的挂念悬成九月九的茱萸,……先将梦泽填为壑,再伐桂为柱,滚石奠基,并且不许回头望我,这样,我才能听到来世的第一声鸡啼。”“你的眼睛里有海,烟波蓝,两颗黑瞳是害羞的,泅泳的小鲸。”从想象到音节和节奏,都充满一种难以言说的韵味,汉语言的美得到了几乎是淋漓尽致的发挥。简媜在评价自己的散文语言时曾说:“我的文字当中吸收了蛮多诗的成份,这是中文系本身的一个养分,一个重要的养分。”“我文章写完之后会从头念一遍,因为在念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哪些地方是拗口的,哪些地方是松散的,有时视觉和声音的感觉会不一样。也会去避免歧义或会生干扰的连结。”可见简媜的文学语言的成功并非所谓“妙手偶得”,而是几十年努力经营的结果。
良好的语言天赋和如琢如磨的反复推敲,固然是其散文语言成功的主要原因;但从另一方面看,在这些典雅华丽的语言后面起支撑作用的,还有作者对生活深刻的体验和细致入微的观察、感悟能力。简媜远远超越常人的艺术感受能力,依仗语言的外显才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两者互为表里,不可或缺。关于这一点,不再做过多的论述。
在当代女性散文的发展过程中,简媜的出现应该说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标志意义,许多研究者都基于此对其散文作出很高的评价。“台湾散文家简媜在《女儿红》中致力于摹写女性悲剧和生命情状;同时,在艺术表现上运用意象、意境以及精致典丽的语言达到散文美的效果。”[7]而高云认为:“简媜散文的出现,对于改变女性散文阴柔有余、阳刚不足、视野较狭的弱点,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8]总之,简媜的散文无论是作为台湾的“文学经典”,还是作为整个当代汉语女性散文的佼佼者都可谓当之无愧。
[1]司方维.触摸灵魂的疼痛——评简媜散文集《女儿红》[J].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06,(6).
[2]李琴.简媜散文中的死亡意识[J].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05,(2).
[3]郑明俐.現代散文纵横论[M].台北:大安出版社,1986.
[4]胡明伟.悲剧意识与文化传统[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6).
[5]鲁迅.鲁迅散文·诗全集[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6]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7]辛倩儿.美与悲剧的融合和抗衡——简媜散文对女性悲剧的摹写[J].2007,(1).
[8]高云.一株行走的草——简媜散文品评[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
Abstract:Jian Zhen is a famous contemporary essayist of Taiwan.Her“plan of writing”includes three themes:personal dating history,the fate of women,family history for hundreds of years in Taiwan.Jian Zhen’s prose is somewhat pessimistic outstanding,but her indomitable fighting spirit,clear consciousness of exploration and elegance style make her prose works both in Taiwan and the Chinese women’s prose in the crowd.
Key words:“Plan of writing”;Pessimistic color;Stylistic exploration;Language style
Songs of Melancholy and Beauty——A Brief Analysis of JianZhen’s Essays
LIU Han-hua
(Anyang Normal University,Anyang 455000,China)
I206
A
1008—4444(2010)03—0051—04
2010-04-19
刘涵华(1955—),女,河南安阳人,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