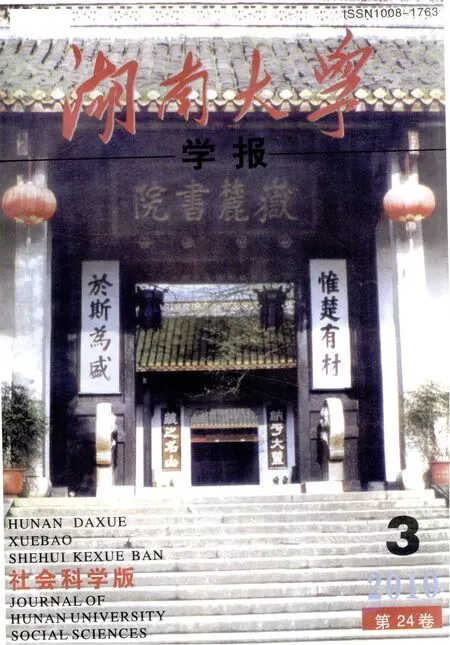《尚书考异》版本比较研究*
高原乐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102)
《尚书考异》版本比较研究*
高原乐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102)
《尚书考异》是第一部系统考辨《古文尚书》为伪作的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关于此书版本。较有价值的是台湾故宫藏旧抄本、《四库全书》文渊阁抄本、孙星衍平津馆刻本。台湾故宫藏旧抄本年代最早,有了它,可以大体推测《尚书考异》在传写过程中致误之由。文渊阁抄本最为常见,四库馆臣在将此书收入《四库全书》时,对书中许多讹误作了校正。平津馆刻本最为完整,它不仅比前两个抄本多出两万余字。而且更全面而系统地对《古文尚书》进行了辨伪搜证工作。但此本虽经顾广圻、孙星衍两位清代大学者“详加校正”,但书中仍沿袭了故宫旧抄本的许多错误。这也就是说,《尚书考异》迄今尚无一部理想的版本。本文通过《尚书考异》版本的比较研究,以见各版本的优缺点及其价值。
梅鷟 ;《尚书考异》;版本比较
《尚书考异》在明代及清初只有传抄本,并未刻板印行。台湾故宫藏《尚书考异》旧抄本两册,不著撰人姓名,不分卷。此书后附一册明韩邦奇《洪范图解》。韩邦奇《洪范图解序》末句题“正德乙亥六月中旬,苑洛子韩邦奇书”。傅兆宽先生《梅辨伪略说及尚书考异证补》以此序为韩邦奇《尚书考异题记》①傅兆宽《梅辨伪略说及尚书考异证补》第9页“:明韩邦奇书写尚书考异记云‘:正德乙亥六月中旬,苑洛子韩邦奇书。’”同书第12页注谓“:明韩邦奇《尚书考异题记》,故宫善本,页287,蓝格旧钞本,五卷二冊。”,认为至少在明正德十年(乙亥)前《尚书考异》已经成书。按:此说不确,韩邦奇此语与《尚书考异》一书并无关涉。台湾故宫藏《尚书考异》旧抄本(以下简称“故宫旧抄本”)年代不明,但可以断定它早于四库全书本的《尚书考异》,并且两者同属一系。
四库全书本《尚书考异》,得之于范懋柱家天一阁抄本,原抄本不分卷数,四库馆臣将之分为五卷,以《舜典》以下为卷二,《仲虺之诰》以下为卷三,《太誓》以下为卷四,考旧本异同为卷五。卷首有《四库全书提要》及《尚书考异·原序》。我们今天所见的是文渊阁抄本四库全书《尚书考异》(以下简称“文渊阁抄本”)。根据电脑录入字数统计,全书纯字数约为五万四千余字。以文渊阁抄本与故宫旧抄本相比较,前者更正了原抄本引文及引文出处等许多讹误,从文字的准确度的角度看,文渊阁抄本较故宫旧抄本为优,但此书在收入四库全书的传写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新的讹误。
清嘉庆(公元1796-1820年)中,孙星衍访得《尚书考异》善本,其书分为六卷。《大禹谟》以下为卷二,《仲虺之诰》以下为卷三,《太誓》以下为卷四,《周官》以下为卷五,考旧本异同为卷六。卷首有顾广圻《校定〈尚书考异〉序》(作于嘉庆壬申年,公元1812年)与孙星衍《〈尚书考异〉序》(作于嘉庆癸酉年,公元1813年)。此本为孙星衍校刊平津馆丛书之一,也是《尚书考异》的第一部刊刻本(以下简称“平津馆刻本”),其书扉页有“嘉庆甲戌孟秋兰陵孙氏校刊”字样,甲戌年为公元1814年。台湾艺文印书馆百部丛书集成据清嘉庆孙星衍校刊平津馆丛书本影印,卷末附《四库全书总目·〈尚书考异〉提要》和胡玉缙所撰《四库提要补正》。此本无《尚书考异·原序》,有可能在流传中失落。根据电脑录入字数统计,全书纯字数约为七万八千余字。字数增加近两万四千字。
三个本子相比较,以平津馆刻本最为完整,它不仅比故宫旧抄本与文渊阁抄本字数多出两万余字,而且更全面而系统地对《古文尚书》进行了辨伪搜证工作。说其“全面”,是说平津馆刻本几乎逐段逐句对《古文尚书》的篇章加以考核分析。说其“系统”,是说平津馆刻本完全依循《古文尚书》文本的篇章顺序列置条目,而绝无紊乱错置之处。相比之下,故宫旧抄本与文渊阁抄本所列之条目不仅是有选择性的,而且条目重出、前后错置的情况颇为严重。我们的总体印象是,故宫旧抄本与文渊阁抄本属于《尚书考异》的初稿本,而平津馆刻本《尚书考异》则是一部完成本。
平津馆刻本沿袭了故宫旧抄本的许多错误,特别是许多因年代数字相近而造成的舛误。此本虽经顾广圻、孙星衍两位清代大学者“详加校正”,但书中此类舛误依然如故。而这些舛误在文渊阁抄本中则已经得到更正。我们推测这个工作是四库馆臣在将此书收入四库全书时所做的,而不是作者本人做的。如果是作者本人做的,那在平津馆刻本中就不会沿袭原稿中的舛误。
台湾故宫藏旧抄本《尚书考异》在三个本子中年代最早,有了它,我们可以大体推测到《尚书考异》在传写过程中致误的原因。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尚书考异》较早抄本的独特之处。
此次点校整理《尚书考异》,以平津馆刻本为底本,以文渊阁抄本为对校本,以故宫旧抄本为参校本。经过点校整理后《尚书考异》文本约十万五千字,加上校记,总字数约十二万五千字。以下从几个方面对《尚书考异》不同版本的正误及其价值问题作一讨论。
一 以平津馆刻本校正文渊阁抄本之例
(一)字形相近所造成的舛误
1.《尚书考异》卷三《仲虺之诰》篇:“盍志而子美德乎?”盍,文渊阁抄本误为“盖”。平津馆刻本作“盍”为是。
2.同卷同篇:“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归道。”好,文渊阁抄本误为“如”。平津馆刻本作“好”为是。
3.同卷《太甲中》篇:“习与智长,故幼而不愧。”幼,文渊阁抄本误为“切”。平津馆刻本作“幼”为是。
4.同卷《说命上》篇:“又恐其荒失遗忘,故使朝夕规诲箴谏。”忘,文渊阁抄本误为“亡”。平津馆刻本作“忘”为是。
5.《尚书考异》卷四《泰誓下》篇:“《淮南子·道应训》”,应,文渊阁抄本误为“广”。平津馆刻本作“应”为是。
6.同卷《微子之命》篇:“武王亲释其缚,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榇礼而命之,使复其所。《史记·宋世家》云:‘……于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与平津馆刻本对校,文渊阁抄本于此段文字讹误多处:祓,误为“被”;榇,误为“概”;宋,误为“宗”;位,误为“伍”等。
7.同卷同篇:“往哉惟休,无替朕命。”休,文渊阁抄本误为“林”。平津馆刻本作“休”为是。
8.同卷《蔡仲之命》篇:“祝佗之言,可以见《周书》四篇逸者三篇:一、《伯禽》;二、《唐诰》、三《蔡仲》是也。”唐,文渊阁抄本误为“康”。平津馆刻本作“唐”为是。
9.同卷同篇:“其言又孰真孰伪,孰得孰失,亦昭然若数一二矣。”一,文渊阁抄本误为“上”。平津馆刻本作“一”为是。
10.《尚书考异》卷五《周官》篇:“杂遝众贤,罔不肃和。”遝,文渊阁抄本误为“还”。平津馆刻本作“遝”为是。
11.同卷《君牙》篇:“以物丰民人也”。丰,文渊阁抄本误为“农”。平津馆刻本作“丰”为是。
12.《尚书考异》卷六《尧典》篇:“司马贞以为太史公据之而作‘便在伏物’。晋《古文》作‘平在朔易’。”物,文渊阁抄本误为“生”。晋,文渊阁抄本误为“书”。“便在伏物,晋”因而误为“便在伏生《书》”。文渊阁抄本于此卷(在文渊阁抄本为卷五)中“晋”字误为“书”字者有多处。另,同卷《杍材》篇:“晋人于上篇‘成王’字,因马氏以为后加直刪去。”“晋人”,文渊阁抄本误为“者文”。以上引文中之“晋”字,在平津馆刻本中皆不误。
13.同卷同篇:“乖剌甚矣。”剌,文渊阁抄本误为“则”。平津馆刻本作“剌”为是。
14.同卷《盘庚小序》:“‘治’皆作‘乱’,其字与‘始’不类。”治,文渊阁作“始”,乃沿用《尚书注疏》本之误。平津馆刻本作“治”为是。始,文渊阁抄本作“治”,亦沿用《尚书注疏》本之误。平津馆刻本作“始”为是。
15.同卷《牧誓》篇:“百人为卒。”“百人”,文渊阁抄本误为“夏”字。平津馆刻本作“百人”为是。
16.同卷《金縢小序》:“晋人作‘新逆’。”逆,文渊阁抄本误为“迎”。平津馆刻本作“逆”为是。
17.同卷《顾命》篇:“诧,丁故反。奠爵。”丁,文渊阁抄本误为“下”。平津馆刻本作“丁”为是。
18.同卷《文侯之命小序》:“马云:‘能以义和诸侯。本作谊。’”作,文渊阁抄本误为“祚”。平津馆刻本作“作”为是。
(二)年代数字相近而造成的舛误
《尚书考异》卷五《周官》篇“:《襄三十年》君子曰‘:《诗》曰:淑慎尔止,无载尔伪。’信之谓也。”三,文渊阁抄本误为“二”。平津馆刻本作“三”为是。
(三)条目错置所造成的舛误
与平津馆刻本相较,文渊阁抄本编次先后未归条理,颇显凌乱,当为草创之本。今举数例如下:
1.平津馆刻本《尚书考异》卷三《说命上》列有一长条:“王宅忧,亮阴三祀,既免丧,其惟弗言。群臣咸谏于王曰:‘呜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实作则。天子惟君万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禀令。’……”文渊阁抄本于此条之外,重出“明哲实作则”一条,并将其错置于《说命下》。
2.平津馆刻本《尚书考异》卷三《说命中》列“说拜稽首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一条。而文渊阁抄本于此条只录“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之文,并将此条错置于《说命下》。
3.平津馆刻本《尚书考异》卷四《泰誓上》列“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文渊阁抄本将“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与“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分列两条。并将其错置于《泰誓中》。
4.平津馆刻本《尚书考异》卷四《泰誓上》列“同力度德,同德度义。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一条。文渊阁抄本于此条只录“同徳度义”一句。并将此条错置于《泰誓中》。
5.平津馆刻本《尚书考异》卷四《泰誓上》列“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尔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时哉弗可失”一条,文渊阁抄本于此条只录“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二句,并将此条错置于《泰誓中》。
6.平津馆刻本《尚书考异》卷四《泰誓中》列“惟受罪浮于桀,剥丧元良,贼虐谏辅,谓己有天命,谓敬不足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厥鉴惟不远,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文渊阁抄本于此条只录“厥鉴惟不远,在彼夏王”之文,并将此条错置于《泰誓下》。
二 以文渊阁抄本校正平津馆刻本之例
(一)字形相近所造成的舛误
1.《尚书考异》卷一“伏生今文《书》二十九篇”条:“伏生壁藏之时初不止二十九篇。”止,平津馆刻本误为“亡”。文渊阁抄本作“止”为是。
2.同卷“孔安国《尚书注》十三卷”条:“诸贤虽注先汉的传《古文》。”“诸贤”二字,平津馆刻本误为“者矣”。文渊阁抄本作“诸贤”为是。
3.同卷“孔安国《尚书序》”条:“非如后世之繁衍末术也。”衍,平津馆刻本误为“行”。文渊阁抄本作“衍”为是。
4.同卷同条:“不遗余力矣。”力,平津馆刻本误为“方”。文渊阁抄本作“力”为是。
5.同卷“《舜典》”条:“亦宵夫谖说者乎?”宵夫谖说,平津馆刻本误为“肖夫缓说”,文渊阁抄本作“宵夫谖说”为是,意谓宵小之徒所作欺诈之说。
6.《尚书考异》卷二《大禹谟》篇:“不及舜,必益以三言然后喻。”益,平津馆刻本误为“并”。文渊阁抄本作“益”为是。
7.《尚书考异》卷四《泰誓上》篇:“刑罚不怒罪,爵赏不逾德。”怒,平津馆刻本误为“恕”。文渊阁抄本作“怒”为是。
8.同卷《武成》篇:“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反,平津馆刻本误为“及”。文渊阁抄本作“反”为是。
9.《尚书考异》卷五《周官》篇:“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先王”二字,平津馆刻本误为“先生”,文渊阁抄本作“先王”为是。
10.同卷《毕命》篇:“君陈想齿、德俱尊于毕公者,故胤周而先毕。”胤,平津馆刻本误为“乱”。文渊阁抄本作“胤”为是。
11.同卷《君牙》篇:“乃惟由先正旧典。”正,平津馆刻本误为“王”。文渊阁抄本作“正”为是。
12.《尚书考异》卷六《西伯戡耆》篇:“耆,《古文》作‘黎’。”耆,平津馆刻本误为“晋”。文渊阁抄本作“耆”为是。
(二)字音相近所造成的舛误
1.《尚书考异》卷一“孔安国《尚书注》十三卷”条:“冲又受之何人哉?”受,平津馆刻本误为“授”。文渊阁抄本作“受”为是。
2.同卷“孔安国《尚书序》”条:“故其包罗略取。”罗,平津馆刻本误为“络”。文渊阁抄本作“罗”为是。
3.《尚书考异》卷二《大禹谟》篇:“然自授受之后,未闻其行事有大异于前日者。”“授受”二字,平津馆刻本误为“受授”。文渊阁抄本作“授受”,与所引王充耘《读书管见》原文相合。
4.《尚书考异》卷四《武成》篇:“而封黄帝之后于蓟。”黄,平津馆刻本误为“皇”。文渊阁抄本作“黄”为是。
5.《尚书考异》卷六《洛诰》篇:“戊辰,王在新邑。”“戊辰”二字,平津馆刻本误为“戊申”。文渊阁抄本作“戊辰”为是。
(三)年代数字相近而造成的舛误
1.《尚书考异》卷二《大禹谟》篇:“《襄二十三年》仲尼曰:‘《夏书》曰:念兹在兹。’”二十三年,平津馆刻本误为“二十四年”。文渊阁抄本作“二十三年”,与所引《左传》原文相合。
2.《尚书考异》卷三《仲虺之诰》篇:“又《襄三十年》子产曰:‘《郑书》有之:安定国家,必大焉先。’”《襄三十年》子产曰平津馆刻本误为“《襄二十九年》子太叔”。文渊阁抄本作“《襄三十年》子产”,与所引《左传》原文相合。
3.《尚书考异》卷四《泰誓下》篇:“《襄二十三年》闵马父曰:‘奸回不轨,祸倍下民可也。’”二十三年,平津馆刻本误为“三十三年”。文渊阁抄本作“二十三年”,与所引《左传》原文相合。
4.同卷同篇:“《宣二年》君子曰:‘戎昭果毅以听之之谓礼,杀敌为果,致果为毅。’”二年,平津馆刻本误为“元年”。文渊阁抄本作“二年”,与所引《左传》原文相合。
5.同卷《旅獒》篇:“《宣二年》:‘公嗾夫獒。’”二年,平津馆刻本误为“元年”。文渊阁抄本作“二年”,与所引《左传》原文相合。
(四)张冠李戴式的舛误
1.《尚书考异》卷一《舜典》篇:“岂孟子所传《尚书》顾脱‘舜典’二字?”“孟子”,平津馆刻本误为“孔子”。文渊阁抄本作“孟子”为是。
2.《尚书考异》卷二《大禹谟》:“晋人窃取庄周之寓言。”“庄周”,平津馆刻本误为“《淮南子》”。文渊阁抄本作“庄周”为是。
3.《尚书考异》卷三《说命中》篇:“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子夏”,平津馆刻本误为“子贡”。文渊阁抄本作“子夏”,与所引《论语》原文相合。
(五)篇页错置所造成的舛误
《尚书考异》卷二《大禹谟》篇有一段文字,平津馆刻本与文渊阁抄本有较大出入。平津馆刻本于此段文字中多处文义不通,今录其文如下:
考之《尧典》曰:“窜三苗于三危。”蔡沉曰:盖其负固不服,乍臣乍叛,舜摄位时而窜逐之。考之《皋陶谟》曰:“苗顽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时乃功惟叙。’”初未尝有命禹“徂征”之事。帝又曰:“皋陶方只厥叙,方施象刑惟明。”帝以付皋陶之象刑,若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者是也。又安得有禹“徂征”之事?蔡沉曰:“禹摄位之后,帝命徂征,而犹逆命”,其违叛圣经、党邪说,而助之攻正,一也。
考之《禹贡》曰:“三危既宅,三苗丕叙。”与《尧典》“窜三苗于三危”之文特相照应,与帝命皋陶为士,五流有宅之刑,特为互见,可见伏生圣经未尝失其本经,非独口以传授而为壁出之善本也明矣。今蔡沉言:禹治水之时,三危既宅,而旧都犹顽不即工,为乍臣乍叛之实,若果然者,则舜之窜为徒窜。而史臣下文“四罪咸服”之言当削矣。此其违叛圣经、党邪说,而助之攻正,二也。
“既宅”、“丕叙”之后,而旧都犹“顽不即工”,尚安得谓之“既宅”、谓之“丕叙”哉?且其负固全力之时,不假用兵,而可以宅之于三危之远,顾于旧都遗落之种,乃敢阻兵,安忍而逆命抗衡于誓师之久,又不通之说矣。此其违叛圣经、党邪说而助之攻正,三也。
相比之下,文渊阁抄本却文通义贯。细究其致误之因,乃将“禹治水之时”至“助之攻正二也”共六十五字误置于“今蔡沉言”之后。这可能是由原抄本篇页错置所造成的舛误。今参考文渊阁抄本调整复原。并将原文中的“二也”改为“一也”;“一也”改为“二也”。调整复原后,其文如下:
考之《尧典》曰:“窜三苗于三危。”蔡沉曰:“盖其负固不服,乍臣乍叛,舜摄位时而窜逐之。禹治水之时,三危既宅,而旧都犹顽不即工。”为乍臣乍叛之实,若果然者,则舜之窜为徒窜。而史臣下文“四罪咸服”之言当削矣。此其违叛圣经、党邪说,而助之攻正,一也。
考之《皋陶谟》曰:“苗顽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时乃功惟叙。’”初未尝有命禹“徂征”之事。帝又曰:“皋陶方只厥叙,方施象刑惟明。”帝以付皋陶之象刑,若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者是也。又安得有禹“徂征”之事?蔡沉曰:“禹摄位之后,帝命徂征,而犹逆命”,其违叛圣经、党邪说,而助之攻正,二也。
考之《禹贡》曰:“三危既宅,三苗丕叙。”与《尧典》“窜三苗于三危”之文特相照应,与帝命皋陶为士,五流有宅之刑,特为互见,可见伏生圣经未尝失其本经,非独口以传授而为壁出之善本也明矣。今蔡沉言:“既宅”、“丕叙”之后,而旧都犹“顽不即工”,尚安得谓之“既宅”、谓之“丕叙”哉?且其负固全力之时,不假用兵,而可以宅之于三危之远,顾于旧都遗落之种,乃敢阻兵,安忍而逆命抗衡于誓师之久,又不通之说矣。此其违叛圣经、党邪说而助之攻正,三也。
(六)不明情实所造成的舛误
《尚书考异》卷一《舜典》篇①文渊阁本《舜典》篇在卷二。有一段文字,平津馆刻本作:“《史记》亦以‘慎徽五典’接于‘尧典’之下,原未尝分,则伏生所传之本,正孟子所读之本。”其中第一句,文渊阁抄本作“今马迁《史记》亦以‘慎和五典’接于“‘尧善之’之下”。
《尚书考异》作者认为,孟子所读之真《古文尚书》,《舜典》合于《尧典》之中,原未尝分为《尧典》、《舜典》两篇。伏生所传亦是此本。伏生之后,儒者从《尧典》中又分出《舜典》一篇,以“尧善之”一句为《尧典》末句。以“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尚书考异》作者找到一个重要的证据,即司马迁《史记》所引之《尧典》,“慎和五典”接于“尧善之”之下,这足以证明当时《尧典》与《舜典》是合而为一的。司马迁当时所见《尚书》与今传《尚书》版本有所不同,今本《尚书·尧典》“慎徽五典”,在司马迁所见之《尚书》传本中作“慎和五典”。因此文渊阁抄本“今马迁《史记》亦以‘慎和五典’接于‘尧善之’之下”与《史记》文本相合,而平津馆刻本“《史记》亦以‘慎徽五典’接于‘尧典’之下”一句中,不仅“慎徽五典”之文与《史记》不合,其“接于‘尧典’之下”一语尤其不通。平津馆刻本之所以有如此舛误,乃在抄录者与整理者不明情实之故。
三 文渊阁抄本与平津馆刻本异文之例
文渊阁抄本与平津馆刻本有许多异文之例,所谓“异文”,是指两者皆可成立,无此是彼非的问题。在本文前面,我们曾假设文渊阁抄本《尚书考异》是作者考辨《古文尚书》的一个初稿本,而平津馆刻本《尚书考异》则是一部完成本的著作。如此假设不误的话,那平津馆刻本便是一部经过修订润色的本子。兹举数例如下:
1.《尚书考异》卷一“孔安国《尚书序》”条下,文渊阁抄本:“况‘八卦’之说,岂忍尽刊?”平津馆刻本改“刊”作“黜”。
2.同上条下,文渊阁抄本:“《史记》……未尝言五十九篇也。”平津馆刻本改“五十九”作“二十五”。
3.《尚书考异》卷一《舜典》篇,文渊阁抄本:“学者当知张霸、孔安国等增‘舜典’二字,赝也。”平津馆刻本改“张霸、孔安国”作“孔安国、皇甫谧”。
4.《尚书考异》卷二《大禹谟》篇,文渊阁抄本:“圣人禅授气象,似不若此。”平津馆刻本改“授”作“受”。
5.同上篇,文渊阁抄本:“礼家虽有‘三谏号泣’之说。”平津馆刻本改“说”作“义”。
6.《尚书考异》卷三《汤诰》篇,文渊阁抄本:“高祖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平津馆刻本改“高祖曰”为“《汉书》”。
7.《尚书考异》卷四《泰誓上》篇,文渊阁抄本:“收拾逸《书》。”平津馆刻本改“拾”作“葺”。
8.同卷《微子之命》篇,文渊阁抄本:“今节去‘勋应乃懿’四字。”平津馆刻本改“节”作“摘”。
9.同卷《蔡仲之命》篇,文渊阁抄本:“足以笼蔽数十百万之耳目。”平津馆刻本改“十百万”作“千百年”。
10.《尚书考异》卷六《尧典》篇,文渊阁抄本:“晋人因孟氏‘险阻既远’之‘阻’,而改‘祖’字。”平津馆刻本改“孟氏”作“《孟子》”。
以上十例清楚地表明,凡平津馆刻本后来所修订润色者,在文字表达方面皆较先前更为精准贴切而符合全书体例。
四 以故宫旧抄本作为参校本
如前所述,我们对于《尚书考异》的点校整理,是将平津馆刻本作为底本,用文渊阁抄本与之对校的。对校中发现的疑点与问题,再以故宫旧抄本作为参校本来作进一步的比勘分析。故宫藏旧抄本在三个本子中年代最早,有了它,我们可以大体推测到《尚书考异》在传写过程中致误的原因。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尚书考异》较早抄本的独误之处。
(一)文渊阁抄本《尚书考异》致误的原因
文渊阁抄本讹误的原因有两大类,一是四库馆臣所采集的原抄本之误为文渊阁抄本所沿袭。二是其原抄本不误,在收入四库全书转写过程中所带来的新的讹误。而判断这两类讹误的参照系则为故宫旧抄本。
第一类情况是这样的,故宫旧抄本、文渊阁抄本同误,平津馆刻本为正。故宫旧抄本与文渊阁抄本同属一系,即皆为《尚书考异》的初稿本,四库馆臣虽然曾对此书稿中的讹误做过核正,但仍然不免沿袭原书稿中的一些讹误。平津馆刻本为《尚书考异》的增修完成本,然而不为四库馆臣所见。此《尚书考异》完成本曾对其初稿中的讹误做过一些核正,也自然不为四库馆臣所知。如:
《尚书考异》卷六《盘庚小序》:“‘治’皆作‘乱’,其字与‘始’不类。”治,故宫抄本与文渊阁抄本皆作“始”,乃沿用《尚书注疏》本之误。平津馆刻本作“治”为是。始,故宫抄本与文渊阁抄本皆作“治”,亦沿用《尚书注疏》本之误。平津馆刻本作“始”为是。
第二类情况是这样的,故宫旧抄本、平津馆刻本皆不误,独文渊阁抄本讹误。这种情况只能有一种解释,即文渊阁抄本在转写过程中又带进了一些新的讹误。如:
1.《尚书考异》卷三《仲虺之诰》篇:“盍志而子美德乎?”盍,故宫旧抄本与平津馆刻本皆不误,文渊阁抄本误为“盖”。
2.同卷《说命上》篇:“又恐其荒失遗忘,故使朝夕规诲箴谏。”忘,故宫旧抄本与平津馆刻本皆不误,文渊阁抄本误为“亡”。
3.《尚书考异》卷四《微子之命》篇:“武王亲释其缚,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榇礼而命之,使复其所。《史记·宋世家》云:‘……于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此段文字,故宫旧抄本与平津馆刻本皆无误,而文渊阁抄本则有讹误多处:如:祓,误为“被”;榇,误为“概”;宋,误为“宗”;位,误为“伍”等。
4.同卷《蔡仲之命》篇:“其言又孰真孰伪,孰得孰失,亦昭然若数一二矣。”一,故宫旧抄本与平津馆刻本皆不误,文渊阁抄本误为“上”。
5.《尚书考异》卷五《周官》篇:“杂遝众贤,罔不肃和。”遝,故宫旧抄本与平津馆刻本皆不误,文渊阁抄本误为“还”。
6.《尚书考异》卷六《顾命》篇:“诧,丁故反。奠爵。”丁,故宫旧抄本与平津馆刻本皆不误,文渊阁抄本误为“下”。
7.同卷《文侯之命小序》:“马云:‘能以义和诸侯。本作谊。’”作,故宫旧抄本与平津馆刻本皆不误,文渊阁抄本误为“祚”。
(二)平津馆刻本《尚书考异》致误的原因
平津馆刻本讹误的原因也有两大类:一是它作为《尚书考异》的完成本沿袭了初稿本中的许多讹误。二是初稿本不误,其完成本在转写和整理过程中带进了一些新的讹误。而判断这两类讹误的参照系也是故宫旧抄本。
第一类情况是这样的,故宫旧抄本、平津馆刻本同误。后者是前者的增修完成本,仍沿袭了初稿本中的许多讹误。而与故宫旧抄本同属一系的文渊阁抄本却对这些讹误作了核正。推测四库馆臣在决定将此稿收入四库全书之时,对此稿中的引文与引文出处等讹误做了核正。例如:
1.《尚书考异》卷二《大禹谟》篇:“《襄二十三年》仲尼曰:‘《夏书》曰:念兹在兹。’”二十三年,故宫旧抄本误为“二十四年”。平津馆刻本同误。文渊阁抄本作“二十三年”,与所引《左传》原文相合。
2.《尚书考异》卷三《仲虺之诰》篇:又《襄三十年》子产曰:“《郑书》有之:‘安定国家,必大焉先。’”《襄三十年》子产曰故宫旧抄本误为“《襄二十九年》子太叔”。平津馆刻本同误。文渊阁抄本作“《襄三十年》子产”,与所引《左传》原文相合。
3.同卷《说命中》篇:“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子夏,故宫旧抄本误为“子贡”。平津馆刻本同误。文渊阁抄本作“子夏”,与所引《论语》原文相合。
4.《尚书考异》卷六《洛诰》篇:“戊辰,王在新邑。”戊辰二字,故宫旧抄本误为“戊申”。平津馆刻本同误。文渊阁抄本作“戊辰”为是。
第二类情况是这样的,平津馆刻本讹误,故宫旧抄本、文渊阁抄本皆不误。这种情况也只能有一种解释,即初稿本不误,其完成本在转写和整理过程中带进了一些新的讹误。例如:
1.《尚书考异》卷一“伏生今文《书》二十九篇”条:“伏生壁藏之时初不止二十九篇。”止,故宫旧抄本与文渊阁抄本皆不误,平津馆刻本误为“亡”。
2.同卷“孔安国《尚书注》十三卷”条:“冲又受之何人哉?”受,故宫旧抄本与文渊阁抄本皆不误,平津馆刻本误为“授”。
3.《尚书考异》卷二《大禹谟》:“晋人窃取庄周之寓言。”“庄周”,故宫旧抄本与文渊阁抄本皆不误,平津馆刻本误为“《淮南子》”。
(三)故宫旧抄本独误之例
故宫旧抄本有一些讹误,在文渊阁抄本与平津馆刻本皆不误。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产生于故宫旧抄本的抄写错误,它只是此一抄本的独特现象。二是原稿既有的讹误,一方面在收入四库全书时为四库馆臣所核正;一方面在作者增修为完成本时做了核正,或是在孙星衍校刊时做了核正。以下即是其例:
1.《尚书考异》卷二《大禹谟》篇:“《哀十七年》‘楚王与叶公枚卜,子良以为令尹。’”十七年,文渊阁抄本与平津馆刻本皆不误,故宫旧抄本误作“十六年”。
2.同卷同篇:“民兴胥渐,泯泯棼棼。”渐,文渊阁抄本与平津馆刻本皆不误,故宫旧抄本误作“占”。
3.《尚书考异》卷六《金縢小序》篇:“孔颖达曰:‘……取喻既同,不应重出。’”取,文渊阁抄本与平津馆刻本皆不误,而故宫旧抄本误作“则”。
五 故宫旧抄本、文渊阁抄本、平津馆刻本皆误之例
我们在对《尚书考异》的点校整理过程中,也发现故宫旧抄本、文渊阁抄本、平津馆刻本皆误的例子。这类例子又可分作两种情况,一是《尚书考异》引述他书,我们以所引原书本文校对之,发现三本皆误。如《尚书考异》卷四《泰誓上》篇引司马迁《史记》:“慢于鬼神,大晏乐戏于沙丘。”其中“晏乐戏”,文渊阁抄本作“晏乐戈虚”,误看“戏”字而分写作“戈虚”。故宫旧抄本与平津馆刻本皆作“最乐戏”,误看“晏”“字”而写作“最”。此为三本皆误的显例。
二是《尚书考异》中有个别之处,读之不通,而三本皆如此,疑有误字,而无证佐。对于此种情况,我们在校记中予以指出,并推测所误之字。此种校勘方法,可以视之为“理校”。例如,《尚书考异》卷六《大诰》篇列如下一条:
“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弗肯构?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后弗弃基’?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弗肯获?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后弗弃基’?”
郑、王本于“肯构”之下亦有“厥考翼”一经,晋人刪去。孔颖达曰:“治田、作室,为喻既同。故以此经结上二事。取喻既同,不应重出。……”孔颖达既逞其臆见如此,蔡沉略不置思而即从之,遂使圣人之经为晋人所涂抹者凡一十有四字。……其辞气不可断绝,与“厥考翼”一经相为唱和,故此一经决不可少,乃圣人之本经,颖达以为先儒之妄增,则非矣。晋人不知全章之大势,错认“乃”字与“矧”字若相唱和,其意以为“堂”、“播”之始者轻者尚不肯为,况构、获之终者重者其肯为之乎?如此则二句辞气雍容,可以暂歇,故直削去“厥考翼”一经而不顾也。
上面所标出之“一经”、“此经”、“此一经”等,其中的“经”字,按文意皆当作“段”字。但无论故宫旧抄本、文渊阁抄本和平津馆刻本皆作“经”字,并且所引孔颖达《尚书正义》原文也作“经”字。我们反复研寻,终不得其解。兹列于此,有待识者指教。
(Institute of History Stud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Beijing 100102,China)
A Comparative Study on Different Versions of Shang Shu Kao Yi
GAO Yuan-le
As the first systematic work on the falsification of Gu Wen Shang Shu,Shang Shu Kao Yi is of great academic values.The most valuable versions of this work include:The manuscript from National Palace Museum of Taiwan Province,the manuscript from Si Ku Quan Shu(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originally collected at Wen Yuan Pavilion of the Imperial Palace,the block-printed version collected at Pingjin Library, the private library of Sun Xingyan,a well-known textual critic of the Qing Dynasty.The manuscript from National Palace Museum of Taiwan Province is the earliest version,and it may generally suggest contributing factors of errors in Shang Shu Kao Yi.The manuscript from Si Ku Quan Shu originally collected at Wen Yuan Pavilion of the Imperial Palace is the most common version that has corrected many errors of the original.While the block-printed version from Pingjin Library is the most complete one that has not only over 20,000 words more than the other two versions, but also much more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evidences to prove the falsification of Gu Wen Shang Shu.Although Gu Guangqi and Sun Xingyan,two experts on textual emendations of the Qing Dynasty have made intense calibrations in this version,a multiplicity of corruptions that are common to Imperial Palace manuscripts could still be found in it. In other words,so far there is no perfect version of Shang Shu Kao Yiasyet.This present paper makes a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merits and faults as well as academic values of the aforementioned three versions of this work.
Mei Zhuo;Shang Shu Kao Yi;version comparison
K204
A
1008—1763(2010)03—0025—07
2009-04-14
高原乐(1976—),女,辽宁沈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中国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