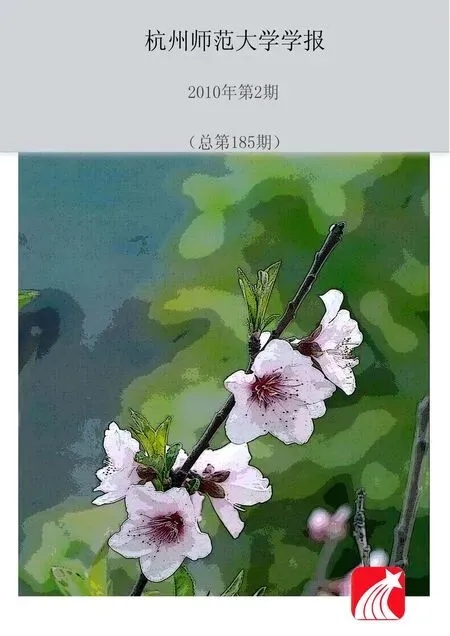梁启超与近代“国学”概念的提出
——兼论中国近代国学思想形成的几种分析路径
朱俊瑞
(杭州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浙江 杭州 310036)
21世纪儒学研究
梁启超与近代“国学”概念的提出
——兼论中国近代国学思想形成的几种分析路径
朱俊瑞
(杭州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浙江 杭州 310036)
“国学”概念的提出和争论发生在20世纪初,曾经与“国学”交替使用的“中学”“旧学”“国故”“国粹”等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让位于“国学”,与梁启超对国学的独特阐释有着一定的关联。梁启超把国学与“旧学”从区分到合并,确立了“国学”的学统;国学与“新学”的对立,树立了“国学”的中心位置;“新国学”与国故运动的交锋,标明了“国学”的完整内容。
梁启超;国学;汉学;新学;新国学
“国学”最早的确切含义是指国家一级的贵族学校,西周时期的学校分为“国学”和“乡学”两种,设在周王朝都城和诸侯国都城的学校为国学,是大贵族子弟的学校;各地所设的乡学则是一般贵族子弟的学校。后来“国学”泛指“京师官学”,主要是“太学和国子学”。[1](P.76)晚清以降,“国学”被赋予了新的涵义,近代所谓的“国学”,“其概念在清末与二三十年代曾几度引起争论,终因界定含糊,分歧太大,无法统一”,“但也大致有其特定的指称对象和范围”,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是把“国学”引申为“中国传统学术”。[2](P.2)张岱年也解释说,20世纪初,“国内一些研治经史的学者编印《国粹学报》,其后章太炎著《国故论衡》,又作了《国学概论》的讲演,于是国学的名称逐渐流行起来。称中国学术为国学,所谓国是本国之义,这已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了”。[3](P.1)至于曾经与“国学”交换使用的“中学”“旧学”“国故”“国粹”因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弃而不用,“国学”因何被约定俗成独领风骚,无关本文的宏旨。但就思想家个体而言,概念的使用和转换往往是思想变化的界标。梁启超正是在对“旧学”“西学”“新学”“国故”等问题的思考中,提出并选定了最能代表“中国学术”的概念,即国学。
一 “国学”与“旧学”(清代汉学)
近代“国学”概念的使用,梁启超可谓始作俑者。1902年夏秋间,梁启超致函黄遵宪,提出创办《国学报》。在黄遵宪的回信中,可以间接看出梁启超的办报宗旨和基本设想:“《国学报》纲目体大思精,诚非率尔遽能操觚,仆以为当以此作一《国学史》,公谓何如?”又说:“公谓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义,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至哉斯言,恃此足以立国矣”。看来,梁启超信中至少出现了“国粹主义”“旧学”两个概念。从黄遵宪的否定性意见中,还反映出梁启超关于“国学”“国粹”问题的思考受到日本的影响:“持中国与日本较,规模稍有不同。日本无日本学,中古之慕隋、唐,举国趋而东,近世之拜欧、美,举国又趋而西。当其东奔西逐,神影并驰,如醉如梦,及立足稍稳,乃自觉己身在亡何有之乡,于是乎国粹之说起。若中国旧习,病在尊大,病在固蔽,非病在不能保守也。”除了国性差异不宜在中国彰显“国粹主义”外,黄遵宪反对筹办《国学报》的另一个理由是时机不成熟,认为中国此时需要“大开门户,容纳新学”,倡言“国学”、发扬“国粹”应该是充分“新学化”或“西学化”后的事情。他谢绝梁启超的邀请,并称“公之所志,略迟数年再为之,未为不可,此大事后再往复”。[4](PP.292-293)
1902年《国学报》议而未成,但学术界还是认为这是“近代国学概念的重要肇始”[5](P.278)。但仍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追问:
其一,梁启超是否因黄遵宪的反对而放弃了“国学”的主张?本文认为,在《国学报》未面世的情况下,把《国学报》与同时期的《新民丛报》对照分析,也不失为判断梁启超是否放弃“国学”思想的可行方法。梁启超筹办《国学报》的宗旨是“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义,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这种塑造国民的思想,与他创办的《新民丛报》不仅时间上相近,在宗旨上亦无大的区别。更准确地说,《国学报》是把《新民丛报》“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的主题集中展现。所以,《国学报》虽然未果,但梁启超拟办《国学报》的缘由及国学思想基本内涵可以从《新民丛报》中得到间接证明。尤其是在1904年的《新民丛报》上,梁启超开始明确使用“国学”一词,其代表作《新民说》也彰显“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的宗旨。据此有理由相信,《国学报》中未能展示的思想胚胎在《新民丛报》中得以正常发育。
其二,梁启超倡导的“国学”具体内涵是什么?尤其是《国学报》“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中的“旧学”应作何解?朱维铮对此有专门的分析。他认为:“‘国粹’一词,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学人造作的。首先将它引进中国的是谁?或以为是梁启超,则尚待考证。1902年秋天,梁启超有创办《国学报》的计划,他的理由是‘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这论调同梁启超以往憎恶‘旧学’即清代汉学的说法完全相反,而酷肖章太炎的口吻。这个计划,受到黄遵宪的反对而胎死腹中,但仍由章太炎力倡,而在1905年‘国学保存会’创办的《国粹学报》刊行,才得以实现。十八年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将清代汉学表征的‘复古’思潮,比作欧洲的‘文艺复兴’,其实也是由章太炎在清末首倡,并由《国粹学报》的主将刘师培等多方发挥过的意见”。[6](P.43注释)
朱维铮的研究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即梁启超“国学”概念的提出与他对“旧学”即清代汉学(下文中带引号“旧学”专指清代汉学)的态度转变有关。这又导出了新的问题:梁启超此时提出的“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中的“旧学”是否特指清代汉学?梁启超是否因放弃对清代汉学即“旧学”的“憎恶”而提倡“国学”?
1902年,梁启超自信进入了学术选择的成熟时期。他在这年发表的《三十自述》,虽然仍有“所以报国民之恩”的焦虑,但对中国学术派别的取舍态度鲜明。他以激动的心情回忆说:“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辞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仍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7](P.2223)
由此看来,1902年前后,梁启超仍带有激情地要将自己满脑子清代“旧学”“摧陷廓清”,丝毫看不出用“酷肖章太炎的口吻”倡导“汉学”之意。因此在1902年拟办《国学报》时,梁启超不会对“汉学”抱有好感。事实上,甚至到1904年前后发表的《新民说》“论私德”(1903年10、11月、1904年2月,载《新民》第38-39、第40-41、第46-48号)中,还集中表述了对“汉学”的“恶感”*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学术的不满,在此之前主要是批判科举制度时间接评论其“无用”等等,详见1896年《变法通议·论科举》。另外,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还回顾了《时务报》时期对中国学术的态度:“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而集中表述他对汉学的不满,《新民论》中当属第一次。:
乾、嘉以降,阎、王、段、戴之流,乃标所谓汉学者以相夸尚,排斥宋、明,不遗余力。……若汉学者,则立于人间社会以外,而与二千年前地下之僵石为伍,虽著述累百卷,而决无一伤时之语;虽辩论千万言,而皆非出本心之谈。藏身之固,莫此为妙。……故宋学之敝,犹有伪善者流;汉学之敝,则并其伪者而亦无之。何也?彼见夫盛名鼎鼎之先辈,明目张胆以为乡党自好者所不为之事,而其受社会之崇拜、享学界之尸祝自若也,则更何必自苦以强为禹行舜趋之容也。……汉学家者,率天下而心死者也。此等谬种,与八股同毒,盘踞于二百余年学界之中心,直至甲午、乙未以后,而其气焰始衰。而此不痛不痒之世界既已造成,而今正食其报……哀哉
按照梁启超《新民说》的构想,改造新民的主要途径是“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又要“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8](P.550),中国传统的学术又是“淬厉”的重要方面,但这种造就“不痛不痒之世界”的“汉学”,理应排除在“国学”之外;这种“几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也当在“廓清而辞辟之”之列。[8](P.587)因此,梁启超最初拟办“国学报”中的“国学”与章太炎的“国学”在内涵上有明显的不同。
这种不同,到了1904年发生了变化。《新民说》“论私德”发表后不到一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的“论近世之学术”部分(1904年9、10、12月,载《新民》第53-55、58号),对汉学的评价的确有了变化,只是这时与梁启超拟办《国学报》已隔两年。如果说1904年下半年梁启超开始放弃对旧学即“汉学”的“憎恶”,似乎更有说服力。*这种推论如果正确,首先当感谢朱维铮先生的启发。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到1904年发表“近世之学术”部分时,开始明确用“国学”代替“中国学术”,并以比较客观的态度评析此前厌弃的“汉学”。他说:“夫本朝考据学之支离破碎,汩殁性灵,此吾侪十年来所排斥不遗余力者也。虽然,平心论之,其研究之方法,实有不能不指为学界进化之一征兆者。至其方法,何以不用诸开而用诸闭,不用诸实而用诸虚,不用诸新而用诸陈,则有别有种种原因焉。”[9](P.273)
梁启超对汉学的开脱,主要是自来于其对汉学产生背景的“同情之理解”。他分析说:“吾论近世学派,谓其由演绎的进于归纳的,饶有科学之精神,且行分业之组织,而惜其仅用诸琐琐之考据。然则此学派之所以不尽其用者,原因何在乎?曰:是不一端,而时主之操纵,其最也。自康、雍间屡兴文字狱,乾隆承之,周纳愈酷。论井田封建稍近经世先王之志者,往往获意外谴;乃至述怀感事,偶著之声歌,遂罹文网者趾相属;又严结社讲学之禁,晚明流风余韵,销匿不敢复出现。学者举手投足,动遇荆棘,怀抱其才力智慧,无所复可用,乃骈辏于说经。……销其脑力及其日力于故纸之丛,苟以逭死而已。”[9](P.276)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清代“汉学”问题上,梁启超与章太炎之间的学术渊源,笔者更赞同王俊义和夏晓虹的见解。王俊义认为章太炎“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1900年出版并于1904年修订再版的《訄书》中。特别是修订后的《訄书》曾在中国思想界、知识界引起极大震动”。而在“同一时期研治清代学术思想史的学者中成就更为突出、影响更大的当推梁启超。他几乎与章太炎撰写《訄书》的同时,也于1904年发表了自己研治清代学术思想的处女作——《近世之学术》”。[10]夏晓虹也认为:“虽然梁启超曾为1900年刊行的章太炎名著《訄书》初刻本题写过书签,在1904年续撰的第八章论述清学的《近世之学术》部分(实含有原先所拟《衰落时代》与《复兴时代》之内容),也曾参考同年面世的《訄书》重订本中《清儒》诸篇,或引录或驳诘,而若比较二人的著作体式,章书更近于唐代刘知几的《史通》与清人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已说明梁作还该另有取法。”[11]
因此,梁启超1902年筹办《国学报》中的“国学”与《新民丛报》中的“旧学”,基本上是排除了清代“汉学”后的中国学术,而1904年展示的国学,则代表了中国学术的全部。本文认为,梁启超在1904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重提“国学”一语,有特殊的意义:
1.梁启超找到了表达贯通几千年中国学术的最佳词汇,即“国学”。
梁启超1902年开始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时,把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界为七时代:一、胚胎时代,春秋以前;二、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三、儒学统一时代,两汉;四、老学时代,魏、晋;五、佛学时代,南北朝、唐;六、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七、衰落时代,近250年;八、复兴时代。到1904年发表六、七部分时,开始明确用“国学”代替“中国学术”,除了思想方面的变化外,首先有表达方式方面的刻意追求。
对于一种学派的界定方式,梁启超表现出极高的天赋和悟性。黄梨洲说:“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即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明儒学案·发凡》)梁启超对其中的“一二字”别有新解:“标举一两个字或一两句话头,包举其学术精神之全部,旗帜鲜明,令人一望而知为某派学术的特色。”
“凡讲学大师标出一个宗旨,他自己必几经实验,痛下苦功,见得真切,终能拈出来,所以说是‘其人得力处’;这位大师既已循着这条路成就他的学问,他把自己阅历甘苦指示我们,我们跟着他的路走去,当然可以事半功倍而得和他相等的结果,所以说是‘即学者入门处’。”[12](P.4896)
以“国学”替代“中国学术”,既有梁启超“其人得力处”,更含有使“国学”导入“学者入门处”的用意。
2.“国学”取代“旧学”,表面上看是梁启超对清代学术的包容,实际上梁启超开始思考整个“中国学术”的“治学精神”,即中华“学统”。清代汉学家既然列为“学统之正派”,自然应在“国学”史上添加重墨浓彩的一笔。
梁启超对“旧学”(清代汉学)态度的变化,除了同情清代汉学家在政治高压下的“趋利避害”外,在研究的结果上,他开始确立汉学在国学中的地位:“乾、嘉间学统之正派”,“惠、戴之学,固无益于人国,然为群经忠仆,使后此治国学者,省无量精力,其功固不可诬也!二百年来诸大师,往往注毕生之力于一经,其疏注之宏博精确,诚有足与国学俱不朽者。”[9](PP.277-278)针对清代“桐城派”对汉学的非议,梁启超则反驳说:“汉学固可议,顾桐城一派,非能议汉学之人,其学亦非惠、戴敌,故往而辄败也”,“桐城派巨子……自谓尸程、朱之传,其实所自得者至浅薄!姬传与东原论学数抵牾,故经学家与文学家始交恶云。自宋欧阳庐陵有‘因文见道’之说,厥后文士,往往自托于道学。平心论之,惠、戴之学与方、姚之文,等无用也!而百年以往,国学史上之位置,方、姚视惠、戴何如哉?”[9](P.278)
相对于半年前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对汉学家“与二千年前地下之僵石为伍”“藏身之固,莫此为妙”的嘲讽,现在的梁启超则只是惋惜汉学“不尽其用”,并从对汉学家的指责移向了对专制政治压制的批判。在后来的《清代学术概论》等著作中,除了集中梳理清代汉学的科学精神外,更张扬了清代汉学家的学术人格,把清代汉学的地位更推进一步。
3.“国学”的提出主要是区别于近代的“西学”或“新学”。
如果联系同时期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系列论文以及他“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的设想,不难看出,1902年梁启超拟办的“国学报”中的“国学”主要是指清代以前的中华“国粹”。到1904年底,梁启超在“国学”问题上的态度基本确立,即已经告别了昔日对“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的豪情,代之以对中国几千年学术思想的眷恋和对青年“邃于国学”的期盼。国学不再是与“旧学”相对举,而是与西学构成了对应关系。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的最后,梁启超特别指出:“吾更欲有一言,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以严氏与其他留学欧美之学僮相比较,其明效大验矣!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国学为我青年劝也。”[9](P.284)不言而喻,接受西学必须“邃于国学”。这种结论来自对中西学术关系的经验分析,也明确表达了他对“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的不满。
另外,梁启超在1902年《国学报》和《新民丛报》中提出的“淬厉旧学”含有整理“国粹”之意,但“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并没有使用更富有民族情感的“国粹”,反而采用相对中性的“国学”来表述“中国学术”或“中华学术”。“国学”概念相约成俗并得以流行,而感情分明的“国粹”“国故”“旧学”等语汇则逐步淡出中国现当代学术界的视线,这至少是可以接受的一种解释。
二 “国学”与“新学”
梁启超、黄遵宪在酝酿“国学”时,连带论及的另外一个概念是“新学”。“国学”与“新学”是否构成直接的对立关系呢?事情也并非如此简单。
梁启超提出“国学”概念的时间正是近代新学风行之时。[13](P.210)梁启超又是康有为新学体系中的“一员最有力之大将也”*素痴:《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转引自夏晓虹《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页。。丁伟志认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既是一个以维新变法推行‘新政’为宗旨的新的政治派别,又是一个创制出一套‘新学’体系为‘新政’做立论根据的新的学术派别。把‘新政’奠基于‘新学’的基础之上,以‘新学’——新的知识、新的学理、新的价值标准、新的文化观念——来阐明和论证变成法,行‘新政’之必要,这正是维新派思想家高出于当时其他各种有识爱国之士的地方,也正是他们区别于和高出于洋务大员的地方。”[14](P.176)这是从近代政治变革和学术发展的意义上予以肯定。陈其泰认为:“在晚清新学创造的实践中,梁启超、夏曾佑所走的道路是成功的。他们接受了由龚自珍和魏源奠定、康有为所发扬的进步公羊学说的传统,站在哲学思考的高度,信奉万事万物处在变易之中和人类历史朴素进化的观点,强烈要求革新政治、以救亡图存为己任,同时,他们热心学习和传播西方进化论和其他进步学说,决不以公羊学家自限,不墨守清代经师附会经义的旧规,并且摒弃主观武断的方法,努力运用近代进化论这一新鲜哲学观探求新知。”[15](P.342)这是从近代学术文化转型意义上对“新学”的肯定性评价。
梁启超何以在“新学”方兴未艾之际另树“国学”的旗帜?王先明认为主要是近代“新学”中的学术缺陷所导致。他认为:“国学无疑是相对于新学而起的一种学术文化思潮”,“至少,国学的兴起与新学发展的偏向不无关系”,主要表现是:“第一,以大量输入西学和搬用西方词语为手段的新学,难免形成学术文化发展方向上的‘欧化’倾向,从而疏离了民族学术文化的根性,这在民族危亡时代必然引起学术救亡和文化复兴的民族情感的涌动。”“第二,在新学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外来之新思想’尚未能真正扎根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土壤之中从而完成中学与西学的整合”。由于近代新学在“无选择的”输入外国学说的情况下,也形成了新学与生俱来的缺陷:其一,对于西学汲取的“稗贩、笼统、肤浅、错误诸弊”。其二,新学的创建具有强烈的“功利性”,“缺少一种求真求是,以学术为目的的精神,使学术本身变成了手段”。其三,“新学未能形成一个相对稳定和成熟的体系,并以此成为规范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模式”。[13](PP.238-248)这又是一种对“新学”的否定性判决。
从梁启超的文稿中,可以发现他讲的“新学”可以分为二种:一是指洋务以来的所有“西学”;二是指康、梁“新学”。对于这两类不同的“新学”,他的评价也完全不同。
对于近代尤其是洋务以来的所有西学或“新学”,梁启超从学术的本源上予以全面的否定:
一切所谓“新学家”者,其所以失败,更有一种根原,曰: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时主方以利禄饵诱天下,学校一变名之科举,而新学亦一变质之八股。学子之求学者,其什中八九,动机已不纯洁,用为“敲门砖”,过时则抛之而已。……殊不知凡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真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质言之,则有“书呆子”,然后有学问也。晚清之新学家,俗求其如盛清先辈具有“为经学而治经学”之精神者,渺不可得,其不能有所成就,亦何足怪?[16](P.3105)
但对于“光绪间所谓‘新学家’”之新学,亦即康梁“新学”,梁启超用“不中不西即中即西”自表其短,但自始至终凝结着自我辩解、先抑后扬的情结。他分别从“西学”的传播和“中学”的改造两个方面对康梁“新学”予以辩解。
西学传播中的“无制限的尽量输入”或“梁启超式输入”,难免有一定的盲目性,梁启超主要是从正面予以肯定:
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众。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盖如久处灾区之民,草根木皮,冻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颐大嚼,其能消化与否不问,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而亦实无卫生良品足以为代。[16](PP.3104-3105)
西学传入的过程,也是康梁改造旧学的过程。梁启超也曾指出康梁“新学”存有“摭古书片词单语以傅会今义”“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等等弊端[16](PP.3100-3101),但更从社会进化的角度评价了康梁“新学”在“旧学”改造中的历史地位:
戊戌学问和思想的方面,我们不能不认为已经有多少进步,而且确已替将来开出一条大进步的路径。这里头最大关键,就是科举制度之扑灭。……到“戊戌维新”前后,当时所谓新党如康有为、梁启超一派,可以说是用全副精力,对于科举制度施行总攻击。前后约十年间,经了好几次波折,到底算把这件文化障碍物打破了。如今,过去的陈迹很像平常,但是用历史家眼光看来,不能不算是五十年间一件大事。[17](P.3249)
1924年在《亡友夏惠卿》一文中,梁启超又对康梁“新学”进行概括性的总结:
我们当时认为:中国自汉以后的学问全要不得的;外来的学问都是好的。既然汉以后要不得,所以专读各经的正文和周秦诸子。既然外国学问都好,却是不懂外国话,不能读外国书,只好拿几部教会的译书当宝贝。再加上些我们主观的理想——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我们所标榜的“新学”,就是这三种原素混合构成。我们的“新学”要得要不得,另一问题。但当时确用“宗教式的宣传”去宣传他。[18](PP.5207-5208)
依据上述的论证,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如果把“新学”界定为光绪间所谓“新学家”(即康梁“新学”)倡导的那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学问,这种“新学”的优点可以概括为“宗教式”的热情、“激进式”的破旧、“朵颐大嚼”般的享受等等,并不含有用“国学”取而代之之意。丁伟志、王学泰也多从这种意义上正面肯定康梁新学。
2.近代以来的新学(包括康梁“新学”),在学术的本源上远离了学术所以为学术的宗旨,或者说,也背离了“为学术而学术”的“国学”学统。挽救这种“失败”新学的办法,只能是努力使之回归“为学术而学术”之路。在这种意义上,“国学”与“新学”的确是一种对立关系。康梁“新学”除了上述问题外,在西学汲取中存在“稗贩、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王先明据此认为梁启超倡导国学意在解决新学的偏向,也是合理的。
3.解答上述两种矛盾观点的关键是要紧扣梁启超上述言论发表的“时间”。梁启超对康梁“新学”的反省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后。以此推断梁启超的“国学”是替代康梁“新学”,说服力未免不足。
4.梁启超在近代新学风行之时提出“国学”概念,但不能笼统地讲“国学”与“新学”是一种对立关系。真正对立的“新学”有特定的对象性,是那种以崇拜西学为特征的新学。换言之,梁启超在1903年前后倡导国学不是试图克服康梁“新学”自身的“杂乱”或“肤浅”,而是力图校正一种畸形发展的“新学”,即已经偏离了梁启超设定的“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新学之学。对脱离“中体西用”的新学的不满*梁启超所倡导的近代新学的基本内核不只是“不中不西即中即西”,而是一种以中学为主体的中西学术的并立,即“中体西用”。这种“中体西用”当然不同于张之洞那种以捍卫专制体制为目的的“中体西用”,而只是一种中西不同学术关系的考量,学者们多有分析,兹不赘述。,是他倡导“国学”的关键。
三 国故运动与梁启超的“新国学”*“新国学”的提法取自蒋广学所著《梁启超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终结》(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梁启超的‘新国学’并非一家、一派之学说”,“新的国学必须在处好先秦各家学说、佛教哲学以及各种新兴学科的关系后才能建立起来,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五四后梁启超在国学问题上有一句话:“在学术界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笔者赞同用“新国学”来概括梁启超后期的国学思想,至于“新国学”的内涵则应有具体的分析。
对一战后世界潮流的反省使中国不少思想家走向了东方文化,梁启超也因此被学者们归类到东方文化派中。*五四时期的文化派别一般分为马克思主义者、西化派、东方文化派。东方文化派又被细分为梁启超、张君劢为代表的的玄学派;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张士钊为代表的甲寅派;吴宓、胡先骕、梅光迪为代表的学衡派。郑师渠认为,东方文化派内部虽然派别林立,个人的情况也多不同,但他们对于战后世界潮流的变动的感悟“理路相类”,“欧战是西方文化过于趋重物质文明而忽略精神文明的必然结果”,世界的文明之路应该从东方文化中吸取诗情。总之,“调和中西,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是东方文化派共同的文化取向。这种调和中西的思路,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表述为:“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郑师渠据此认为梁启超是东方文化派中表达中西文化调和思想“最具体”的人物之一。[19](P.17)学术界也大多认同梁启超晚年趋向保守的观点。但这种观点也值得商榷。
用“中西调和”或趋向保守可以说明梁启超后期思想的某些方面,持此说者首先在判断标准上有明显的纰漏:
1.仅以梁启超的“西学”为准线评述其后期“中西调和”的保守性,方法未必妥当。在这种单一的视域下评述梁启超的思想,等于用梁启超的“左手拉右手”,无法说明梁启超在西学和“中学”方面的真正变化。比如,以“中学”为背景,容易发现其在“国学”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和五四后的新发展;以“西学”为基点,看到的往往是梁启超在“西学”认识上的变化。不同的视域所得结论可能会截然不同。如果研究他的“国学”思想,应当以“中学”为主要线索,把握其在“国学”问题上连续性、继承性的一面。“中西调和”是事实,但走向“保守”则未必。*关于五四后思想家“调和”的智慧,学术界围绕着“杜亚泉现象”已多有肯定,兹不引述。但在同类问题上对于带有“政治性”问题的梁启超,还没有平等对待。
2.五四后对学术派别的分类和性质的判定基本上是以“西学”为准绳,实际上是预设了“西化”的无上权威性和绝对性并以此作为评判一切的价值标准;或以“政治正确”作为学术分类裁定其历史地位的天然尺度。这种简单认定新胜旧、今胜昔的朴素进化论,形成于晚清,在“五四”时期达到高潮。流风余韵,至今不绝。
梁启超“新国学”思想的形成带有鲜明的文化思潮背景,它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回应。更准确地说,五四后梁启超“新国学”概念的提出与五四时期的“整理国故”运动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关于梁启超的古书辨伪与整理国故的关系,已有论述。详见吴铭能《梁任公的古文献思想研究》,台湾学生书局2001年2月版,第114-118、275页。该书对本文分析梁启超后期国学概念的形成极有帮助。但不能将之视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补充,更不能把“新国学”视为对新文化运动的反动。
仅从表面上看,梁启超在“在同盟会成立后,尤其是章太炎主持《民报》后,他就很少言及国粹了”[20](P.94)。在民国初年国内围绕着整理国故而展开的有关“国学”“国故学”的争论中,梁启超的确没有参与热闹的“正名”活动*民国初年有关“国故”“国学”“中学”“国粹”“国粹学”“国故学”“中国学”“新国学”的正名,是民国初年“整理国故”的一大景观。有关问题的争论罗志田做了详尽的论述,详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这种置身于学术思潮之外的做法似乎不太符合梁启超的风格,但“冷淡”表象的背后却含有梁启超对“国学”不证自明的理解,让他牵挂的是整理国故运动的方向问题。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科学”和“人权”为最初的宗旨,新文化运动的走向却在不断地自我调整和分化。按照胡适的解释,五四时期的新思潮的流向至少应该包括“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21]。胡适一路的“许多过去新的先锋,都转而向着整理国故去深厚自己”。[2](P.46)在整理国故方面的影响,桑兵总结说:“20世纪20至30年代前半,是国学研究的鼎盛期。由于在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的胡适等人提倡整理国故,使得国学研究成为时尚。国学教育和研究机构竞相设立,不仅青年后学踊跃投考,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专门杂志和出版社纷纷出台,一些报刊则特辟国学专栏,以论文、专著、教科书和丛书的形式发表了大量国学论著;既有的国学倡导者仍继续鼓吹,一批少壮新进之士又加入行列;标明国学的学术性结社明显增多;响应者除集中于京沪外,还扩展到西北、东北、闽粤及香港等地。”[2](P.10)这里所说的“既有的国学倡导者”,应该包括梁启超在内。
遗憾的是,学术界只是关注了新派的“国故”,却忽视了梁启超已经从正面“杀出”,迅速以自己得心应手的“国学”与之过招接应。从思想史的脉络上,“整理国故”表达在先,梁启超表述“新国学”在后,似乎梁启超被动地参与了“国故运动”的合奏。但梁启超的参与重在保持特定的“音调”。他说:“近来国人对于知识方面,很是注意,整理国故的名词,我们也听得纯熟,诚然,整理国故我们是认为急务,不过若是谓除整理国故外,遂别无学问,那却不然。”那么,区别于国故运动的“学问”是什么?就是那种当时让欧洲学者惊叹、梁启超自欧游回来正在兴致盎然地展示的中国“人生哲学”。[22](P3343)无论是内容还是方法上,“新国学”都是对整理国故运动的矫正而非简单的补充或否定。笔者将另文专门分析。
总之,国学与“旧学”从区分到合并,梁启超确立的是“国学”的学统;国学与“新学”的对立,树立的是“国学”的中心位置;“新国学”与国故运动的交锋,标明的是“国学”的完整内容。梁启超的国学教育思想随着“国学”概念的“能量转移”不断注入新的内容。
[1]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缩印本)[K].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
[2]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张岱年.《国学丛书》序[C]//国学今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4]黄公度.致饮冰室主人书[M]//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5]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6]朱维铮.《清代学术概论》导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7]梁启超.三十自述[M]//饮冰室文集点校:第四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8]梁启超.新民说[M]//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一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9]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一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10]王俊义.二十世纪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之回顾[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3).
[11]夏晓虹.中国学术史上的垂范之作——读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J].天津社会科学,2001,(5).
[12]梁启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M]//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13]王先明.近代新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M].北京:商务出版社,2000.
[14]丁伟志,陈崧.中西体用之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15]陈其泰.清代公羊学[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7.
[1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17]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M]//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五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18]梁启超.亡友夏惠卿[M]//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19]郑师渠.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0]喻大华.晚清文化保守思潮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1]胡适.新思潮的意义[J].新青年,1919,7(1).
[22]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M]//饮冰室文集点校:第六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沈松华)
LiangQichaoandtheProposalof“GuoXue”ConceptinModernChina——OntheApproachestoAnalysingtheDevelopmentof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inModernChina
ZHU Jun-ru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icience,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36, China)
The proposal of and debate on the concept of “Guo Xue” occurred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concepts, such as “Zhong Xue”, “Jiu Xue”, “Guo Gu” and “Guo Cui” had been used alternatively, but were finally replaced by “Guo Xue”. And this was related to Liang Qichao’s original explana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from distinguishing “Guo Xue”and “Jiu Xue” to combining the two conceptions. He defined the scientific tradition of “Guo Xue”. In contrasting “Guo Xue” with “Xin Xue”, he set up the central position of “Guo Xue”.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Xin Guo Xue”and the “Guo Gu” movement identified the integrated contents of “Guo Xue”.
Liang Qichao; Guo Xue; Han Xue; Xin Xue; Xin Guo Xue
2010-02-25
朱俊瑞(1965-),男,山东昌邑人,历史学博士,教育学博士后,杭州师范大学政法经济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
B259.1
A
1674-2338(2010)02-0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