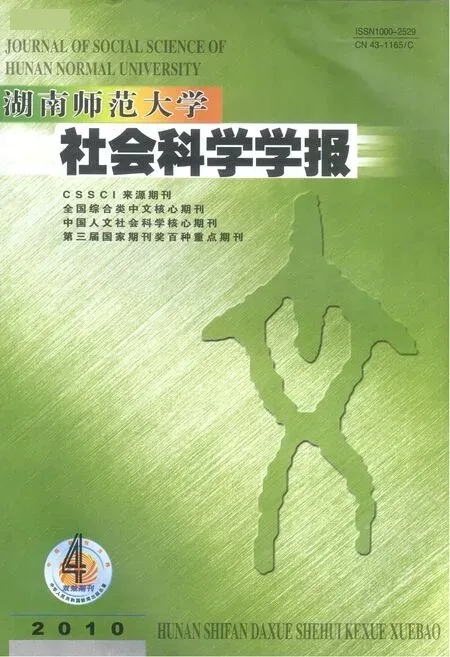“两极化刑事政策”之理性辨思
田兴洪,马长生
(长沙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
“两极化刑事政策”之理性辨思
田兴洪,马长生
(长沙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
黄华生博士的文章对两极化刑事政策进行了全面批判和否定,实际上是对该政策的基本含义、历史背景、理论依据等方面所进行的严重误读。迄今为止,两极化刑事政策仍然是当今诸多国家行之有效的主要刑事政策,是刑事政策发展的世界性趋势,也与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很大的相通性。
刑事政策;两极化;宽严相济;理论依据
两极化刑事政策,即在处罚上对轻罪的处罚较以往更轻、对重罪的处罚较以往更重(简称“轻轻重重”),从而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之政策,被我国学界普遍视作当今西方国家的主要刑事政策,是刑事政策发展的世界性趋势,与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很大的相通性。但是,黄华生博士在其《两极化刑事政策之批判》(载《法律科学》2008年第6期,以下简称“黄文”)一文中,对两极化刑事政策进行了全面批判和否定。本文谨就两极化刑事政策作一些分析和思考,以就教于黄华生博士和各位读者。
一、对“两极化刑事政策”不能作极端化解读
1.“黄文”对两极化刑事政策基本含义的误读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刑事政策出现了两极化的发展趋势。所谓刑事政策的两极化,即刑事政策朝着宽松(轻罪)和严厉(重罪)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黄文”认为,两极化刑事政策逻辑上存在严重缺陷:第一,从字面上讲,两极化意味着刑罚分别向最重和最轻两个极端发展,彻底的两极化就是同时实行极端的重刑化和极端的轻刑化。第二,两极化刑事政策只提出对于轻微犯罪的轻缓政策和严重犯罪的严厉政策,对于中等严重程度的犯罪没有涉及,采取了回避的态度。[1]其实,这是“黄文”对两极化刑事政策的含义作极端化解读后得出的错误结论。首先,不论是“两极化”还是“轻轻重重”,都只是学者们对于当今西方国家对轻罪轻处、重罪重处之刑事政策的形象概括,而西方国家本身并没有对其刑事政策冠之于“两极化”或者“轻轻重重”之名称。既然西方国家之刑事政策本来就不存在相对应的名称,又如何能够对这些中国化了的形象语汇作片面的字面考究呢?其次,美国等西方国家目前刑事政策的特点是突出和强调重罪和轻罪这两极,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些国家对于两极以外的中间犯罪放任不管或者没有针对这些犯罪的刑事政策。除了“轻轻重重”以外,对于犯罪中的“不轻不重”者采取通常的不严不宽的适中治理对策,这本是两极化刑事政策的应有之意。
2.“黄文”对两极化刑事政策历史背景的误读
“黄文”认为,“两极化刑事政策的深层次原因是,美国当时轰轰烈烈的矫正刑运动出现了严重危机”。“黄文”在这里未免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第一,以严格刑事政策产生背景之“偏”概括两极化刑事政策产生背景之“全”。众所周知,两极化刑事政策是由严格刑事政策和宽松刑事政策组成的,这两方面刑事政策的旨趣不同,产生背景也各不相同。一般认为,严格刑事政策的产生背景主要是犯罪形势严峻、教育刑理论受到怀疑、报应刑主义一定程度的复归等,而宽松刑事政策的产生背景则主要是社会对于刑罚功能和刑罚资源有限性的理性认识。而“黄文”却将美国两极化刑事政策的诞生仅仅归结于“矫正刑运动出现了严重危机”,而忽略了两极化刑事政策中宽松刑事政策之产生背景,显然是片面的。即使就严格刑事政策来说,“矫正刑运动出现了严重危机”也不是其产生的全部背景。第二,以美国之“偏”概括世界其他国家之“全”。美国虽然是实行两极化刑事政策的典型国家,但是美国的情况也不能代表所有国家的情况。在实行两极化刑事政策的西方国家中,两极化刑事政策的侧重是不同的。西欧诸国以及日本等都是实行两极化刑事政策颇有特色的国家,忽略这些国家两极化刑事政策的具体产生背景,是不能对两极化刑事政策的产生背景得出总体性的科学结论的。本文认为,两极化刑事政策最深刻的背景是各国犯罪态势严峻和刑罚资源不足,而不是矫正刑的危机。原因很简单,存在矫正刑危机的国家只是美国等少数国家,而实行两极化刑事政策则是世界性趋势,犯罪态势严峻和刑罚资源不足则是国际社会的共同特征。
3.“黄文”对两极化刑事政策理论依据的误读
“黄文”认为,两极化刑事政策将报应刑论和矫正刑论两种对立的刑罚理论切割使用,理论上前后矛盾。[1]其实,“黄文”的这种批评是软弱无力的。首先,两极化刑事政策是一种综合性刑事政策,其理论依据也必然是综合性的。经过历史上报应刑论和矫正刑论的长期交锋和借鉴融合,当今刑罚理论的主流理论和发展趋势是折衷刑论。所以,同时用报应刑论和矫正刑论来解释两极化刑事政策的合理性并没有什么不妥,而且,将这种既讲求报应又讲求矫正的折衷论作为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两种刑事政策(实际上是一种刑事政策的两个方面)的理论基础,是最合适不过的,也是完全符合同一事物矛盾着的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法原理的。其次,两极化刑事政策是有深厚的理论基础的,不仅有严格刑事政策和宽松刑事政策各自的理论基础,更有宽松刑事政策和严格刑事政策相辅相成、矛盾统一、共同应对复杂犯罪的共同理论基础。可见,将这种理论不当“切割”的恰恰是“黄文”。
二、“两极化”仍然是世界各主要国家刑事政策发展的主流趋势
“两极化”是刑事政策发展的世界性趋势。但是,“黄文”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并不像美国那样经历了矫正刑的滥用,不具备美国那样实行两极化刑事政策的背景和成因,所以它们并没有奉行两极化刑事政策。”[1]“黄文”的这一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其错误的根源在于“黄文”把“经历了矫正刑的滥用”作为了奉行两极化刑事政策的必要条件,并进而把“矫正刑运动出现了严重危机”作为两极化刑事政策的唯一产生背景。“黄文”提出了“两极化刑事政策的非普遍性”的论点后,分别从德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并未实行两极化刑事政策的角度论证其论点的合理性。然而,“黄文”的论据却是不存在的,因而也是不科学的。
1.“黄文”认为,德国没有奉行两极化刑事政策
其理由是:在德国,罪责原则、法治国家原则和人道主义原则仍然是德国刑事政策的基本原则[2](P9)。笔者认为,这些论据欠缺说服力。因为罪责原则、法治国家原则和人道主义原则是现代刑事政策的普遍原则,两极化刑事政策实际上也是以上述原则为圭臬的。事实上,德国也是奉行两极化刑事政策的典型国家。在德国,尽管终身自由刑受到强烈批评,但德国刑法典仍将其保留了下来。针对明显增加的对法秩序和公共安全构成威胁的最为严重的犯罪形式如暴力犯罪,强调刑法的严肃性和严厉性必须明确地予以保留[3](P141)。1992年的有组织犯罪法加大了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力度,1994年的犯罪防治法进一步加大了打击力度,并将之扩大至暴力犯罪[3](P31)。与此同时,德国对轻罪实行轻刑化的趋势也十分明显,《德国刑法典》的刑罚体系几乎是以罚金这一主要适用于轻微犯罪的刑种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尽可能少地课处刑罚,尽可能多地给予社会帮助”成为德国现行法律的一般发展趋势[3]。另外,德国刑事政策“轻轻”的策略还贯穿于整个刑事程序之中。[4](P146)
2.“黄文”认为,法国没有奉行两极化刑事政策
其理由是:第一,在法国,目前的主流刑法学认为,现代刑罚围绕着三项主要功能:威慑功能、报应功能与社会再适应功能,追求一种“复合性目标”。第二,法国刑法已经废除了死刑,实际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个人的“社会再适应”也仍然在进行[5](P422)。本文认为,这些论据欠缺说服力。首先,刑罚功能“复合性目标”何尝不是两极化刑事政策所竭力追求的呢?因为折衷刑论正是两极化刑事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其次,法国废除了死刑的事实也不能说明法国就没有了严格刑事政策。事实上,两极化刑事政策同废除死刑并不是不相容的,何况,只要保证最重的罪被判处最重的法定刑,那么该国的罪刑阶梯就是合理的。法国取消了死刑,那么无期徒刑就是适用于重罪的最高刑,对重罪是判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还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抑还是判处无期徒刑,仍然具有选择的空间。“从重”“从轻”从来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绝不能因为法国没有了死刑,就认定法国不能实行严格刑事政策了。实际上,法国也是奉行两极化刑事政策的典型国家。在法国,当代在犯罪化方面的刑事政策的思路之一就是要打击危害性严重的暴力性犯罪[6](P474-480)。同时,在《法国新刑法典》中,与轻罪刑罚制度的灵活多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重罪刑罚制度极为统一和严格。并且在《法国新刑法典》通过以后,立法者又采取了行动,建立了一个“不可缩减的刑期”[7](P6)。同时,在法国,宽松刑事政策同样引人注目。刑事政策思想在刑罚上的变化就是刑罚重点逐渐从威慑功能转向犯罪人的社会再适应功能,与之相适应,在刑罚的结构和适用上形成了宽缓局面。
3.“黄文”认为,俄罗斯没有奉行两极化刑事政策
其理由是:在俄罗斯,1997年生效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坚决贯彻民主化和人道主义原则”[8](P4);另外,俄罗斯联邦已经成为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1]。本文认为,这些论据欠缺说服力。因为两极化刑事政策并不是专制和野蛮的代名词,也要“坚决贯彻民主化和人道主义原则”,而且,俄罗斯事实上的废除死刑,与该国能否实行两极化刑事政策并无必然联系。实际上,俄罗斯也是奉行两极化刑事政策的典型国家。正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释义》序言的作者斯库拉托夫(时任联邦总检察长)、列别捷夫(时任联邦最高法院院长)、波别盖洛(时任联邦总检察长顾问)指出的,俄罗斯联邦1996年刑法典“一方面保留对严重犯罪和特别严重的犯罪、对累犯、职业犯罪和有组织的犯罪的严厉制裁,而另一方面对不需要如此严峻对待的犯罪人适用更宽缓的感化措施。”[8](P4)这不正是对两极化刑事政策的高度概括吗?
4.“黄文”认为,日本没有奉行两极化刑事政策
其理由是:日本的刑事立法具有活性化,刑法保护的早期化和宽泛化,犯罪化和重刑化等特征[9](P6)。笔者认为,仅凭这些论据还远远不能说明日本没有奉行两极化刑事政策。事实上,二战以后,日本的刑事政策也表现出明显的轻轻重重的两极化趋势。从“重重”一极来看,最明显的就是日本国家一级的刑事政策,在近一段时期正在进行着以“扩大刑法统制”为方向的积极的立法活动[10]。比如,日本加大了对严重犯罪如有组织犯罪等的打击力度,就是适例[11]。但是,日本除了上述犯罪化和重刑化等刑事立法特征外,刑事立法的轻缓化趋势也是十分明显的。比如,主要适用于轻罪的罚金刑在日本刑法中占有突出的地位[12]。在日本,观念上自由刑是刑罚体系的中心,但在实践层面上罚金刑却是刑罚体系的中心[13](P392)。又比如,日本是采用起诉便宜主义的典型国家,警察阶段的“微罪处分”和检察阶段的“暂缓起诉处分”使得日本有相当数量的轻罪案件被从轻处理掉[10]。
5.“黄文”认为,美国的两极化刑事政策也似乎到了强弩之末,显露出趋于消停的迹象
其理由是:第一,美国国内对于体现两极化刑事政策的典型立法“三振出局法”的质疑变得强烈起来。第二,美国对于死刑的适用呈下降趋势。笔者认为,这些论据欠缺说服力。“三振出局法”只是美国严格刑事政策中的一项具体政策,并不能代表美国严格刑事政策的全部。何况“三振出局法”目前只是受到质疑而并没有被取消,即使被取消了也并不说明美国对两极化刑事政策就要“堰旗息鼓”了,一个国家对国内的某些刑事政策作局部调整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并不能说明什么实质性的问题。美国对严重犯罪,尤其是严重暴力犯罪和有组织犯罪,一直都是采取从重打击政策的。尤其是美国9·11事件以来,在反击恐怖主义方面采取的政策措施不断增强[14]。至于“美国对于死刑的适用呈下降趋势”就更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了。因为美国已有多个州早已废除死刑,难道能够据此说美国的这些州自从废除死刑后就放弃了两极化的刑事政策吗?
三、“两极化刑事政策”与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相通性
关于两极化刑事政策与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关系,学界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是“等同论”,即认为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其实就是西方国家两极化刑事政策的中国表述,二者并没有什么实质区别[15](P616)。二是“对立论”。比如,“黄文”认为:“两极化刑事政策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存在明显冲突,在一定意义上是根本对立的。”[1](P70-77)笔者认为,“等同论”和“对立论”都走向了极端,都是错误的。两极化刑事政策与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区别不是本质上的,更不能以这些区别抹杀二者在根本上的相通性:第一,二者在基本内容上具有很大的相通性。从内容来看,二者都是由严格刑事政策和宽松刑事政策两部分组成。至于从字面表述来看,我国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似乎更强调“内缩”,即“宽”、“严”互补,而两极化刑事政策更强调“外张”,即“轻罪更轻”、“重罪更重”,但这只是表面上的差异,不能掩盖二者内在的一致性:其一,两极化刑事政策其实也是强调互补的,严格刑事政策和宽松刑事政策共存于一体中,都服务于国家和社会治理犯罪的共同目标,这本身就是相互依存的;其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其实也是外张的,因为强调“宽”、“严”,就是强调差异性,强调对某些犯罪突出“宽”而对某些犯罪突出“严”,实际上也是两极化的表现。第二,二者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那就是轻(宽)重(严)有别,区别对待。由于两极化刑事政策形成时间早、影响范围广泛,可以说,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在反思“严打”刑事政策的弊端并科学地借鉴了西方国家两极化刑事政策的合理内核基础上形成的,是对我国曾长期实行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同时,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形成又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两极化刑事政策理论。二者可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因此,我们将二者的关系定位为“相通论”。
四、我国刑事政策之“两极化”
“两极化”刑事政策在我国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在《左传》中就有“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的治国策略之记载。在我国革命根据地时期,“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两极化趋势则更加明显。比如,1940年12月,毛泽东在《论政策》一文中明确指出:“应该坚决地镇压那些坚决的汉奸分子和坚决的反共分子,非此不足以保卫抗日的革命势力”,“对于反动派中的动摇分子和胁从分子,应有宽大的处理。”“对敌军、伪军、反共军的俘虏,除为群众所痛恶、非杀不可而又经上级批准的人以外,应一律采取释放的政策。”解放战争时期,刑事政策的两极化趋向得到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在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一文中指出:“本军对于蒋方人员,并不一概排斥。而是采取分别对待的方针。这就是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在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刑事政策又发展成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1956年9月19日,罗瑞卿同志在中共八大第一次会议上作了《我国肃反斗争的主要情况和若干经验》的报告,指出:“党在肃反斗争中的严肃与谨慎相结合的方针,体现在对待反革命分子的政策上,就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惩办与宽大,两者是密切结合不可偏废的。”我国1979年刑法还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确定为基本刑事政策。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为应对犯罪率居高不下的严峻形势而开展的“严打”,在执行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扭曲现象,特别是在集中打击行动中往往重视打击与惩办,忽视从宽,使得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难以得到有效执行。因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在纠正“严打”政策的一味从严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的基础上,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继承和发展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而产生的,因而,在能够宽和时尽量宽和成为这一政策的主要价值蕴涵。但是,这也并非矫枉过正而忽视对重罪的严厉惩处。2007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指出,在刑事政策上,我们一方面应“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依法严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依法严惩爆炸、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的犯罪,抢夺、盗窃等多发性侵犯财产犯罪……”,另一方面则应“当宽则宽,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重视依法适用非监禁刑罚,对轻微犯罪等,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不大,有悔改表现,被告人认罪悔罪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尽可能地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依法从轻、减轻处罚,对具备条件的依法适用缓刑、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罚,并配合做好社区矫正工作;重视运用非刑罚处罚方式,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予以训诫或者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建议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这难道不是对“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两极化思想的最好阐释吗?可见,对于重罪的“严”和对于轻罪的“宽”从来就没有脱离我国刑事政策的发展轨道,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时代背景下,治理犯罪的重点有所不同,“轻”、“重”两极有所侧重而已。实际上,没有区别对待就没有政策,“两极化”刑事政策的精神实质就是对轻重犯罪实行区别对待。因而,“两极化”刑事政策也可以说就是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两极化”实际上只是对“区别对待”这一刑事政策精髓的形象概括而已。而且,对重罪和轻罪区别处理并非不管一般犯罪,“抓两头带中间”并不失为一种科学的工作方法。
但是,“黄文”认为,两极化刑事政策包括的“轻轻”和“重重”两个方面,无论是“轻轻”还是“重重”,都不符合我国目前刑事法治的发展需要[1]。我们对此不能苟同。在上文对我国实行“两极化”刑事政策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再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论证。
1.“轻轻”是我国轻罪刑事政策的总体发展趋向
“黄文”认为:我国不宜实行“轻轻”的刑事政策。其理由是:在我国,“轻轻”只能是局部的、次要的,不应当成为趋势和主流。相反,我国今后需要适当扩大刑法的调整范围,增设新的犯罪行为。[1](P70-77)我们认为,增设新的犯罪并不是否定对轻罪从轻处罚的“轻轻”刑事政策。我国刑法第5条明确规定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第37条则明确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这是对“轻轻”刑事政策的实质性规定。此外,我国不仅在依据实际情况适当扩大刑法的调整范围,也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于已失去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作了非犯罪化处理[16](P23)。还需要指出,“黄文”对于“轻轻”的理解只限于非犯罪化,未免过于狭隘。从西方国家的两极化刑事政策实践来看,不论是“轻轻”还是“重重”都是贯穿于刑事立法、司法、刑罚执行等整个刑事法治过程的。所以,对于“轻轻”也要全面理解。如果我国刑法中的某些轻罪暂时还不能从立法上予以非犯罪化,那么,对其进行非刑罚化、轻刑化和非监禁化总是可以的。另外,对于轻罪实行的不起诉及简易审判程序等都属于“轻轻”的范畴。
2.“重重”是我国重罪刑事政策的总体发展趋向
“黄文”认为:我国不宜实行“重重”刑事政策。其理由是:如果再往两极化方向发展,那么在重刑这一极就意味着继续增设死刑[1]。对于“黄文”的这一观点,我们也不敢苟同。首先,“重重”并非是无限制的重,并非是无止境的重,更不是不讲科学、不讲分寸的“越重越好”,恰恰相反,“重重”是讲科学、讲分寸、讲规则的重,是实事求是的重。所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严打’是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体现,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其次,“重重”绝对不等同于死刑,“两极化”更不等于走极端,提倡严格刑事政策与主张死刑的限制直至废除是不矛盾的。
[1]黄华生.两极化刑事政策之批判[J].法律科学,2008,(6):70-77.
[2][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3][德]汉斯·海茵里希·耶赛克.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刑法典序.德国刑法典(2002年修订)(徐久生,庄敬华译)[A].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
[4]马登民,张长红.德国刑事政策的任务、原则及司法实践[J].政法论坛,2001,(6):146.
[5][法]卡斯东·斯特法尼.法国刑法总论精义(罗结珍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6]何秉松.刑事政策学[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2.
[7][法]皮埃尔·特律什,米海依尔·戴尔玛斯-马蒂.序——为《刑法典》在中国出版而作[A].法国新刑法典(罗结珍译)[C].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
[8][俄]斯库拉托夫,列别捷夫.俄罗斯联邦刑法典释义(黄道秀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9]日本刑法典(第2版)(张明楷译)[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10][日]武内谦治.日本犯罪状况及刑事政策(胡晗译)[EB/OL].http://www.fsou.com/html/text/art/3355672/33 5567280_1.html/2009-02-04.
[11]莫洪宪.日本惩治有组织犯罪的最新法律对策[J].国外社会科学,2001,(3):51-55.
[12]朱志峰.日本现行罚金刑制度及发展趋向考察[J].当代法学,2007,(5):154-158.
[13]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14]储槐植.英美法系国家刑法变革对中国的启示[J].当代法学,2006,(2):124-128.
[15]王海涛.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我国刑罚结构完善的潜在影响[A].赵秉志.和谐社会的刑事法治(上卷)[C].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
[16]韩芝康.论我国重婚行为的非犯罪化[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06.
(责任编校:文 泉)
On“Bipolar Criminal Policy”
TIAN Xing-hong,MA Chang-sheng
(College of Arts and Law,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Changsha,Hunan 410004,China)
Today,bipolari criminal policy is also the main criminal policy in many countries and it is the developing trend of world criminal policy.There are similarities between criminal policy combining leniency with severity of our country and bipolar criminal policy.
criminal policy;bipolarization;combining leniency with severity;theoretical basis
DF613
A
1000-2529(2010)04-0071-04
2010-04-05
湖南省刑法学研究会2008年重点科研课题“中外轻罪政策比较研究”[08ZD003]
田兴洪(1969-),男,湖南保靖人,长沙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博士;马长生(1944-),男,山东莘县人,长沙理工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省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