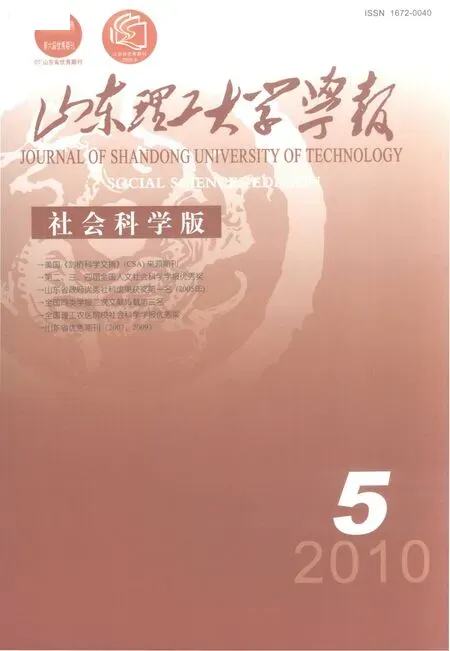“模仿”中的当代文学生存——再论“文学想象力缺失”
张小青
(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北京100081)
在当今这个由科学技术引领、物质欲望充斥、经济利益至上的时代,人类也许正面临着自诞生以来最严峻的危机,我们的心灵不断失落,精神遭遇前所未有的空虚,曾经有过的幸福感随着社会的发展却越来越淡漠。有人把现在的人类贴切地比喻为狂奔在物欲世界中的文明野兽,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世界里,有几个人肯停下脚步回头看看曾经走过的路,我们究竟是不断地靠近文明,还是离文明越来越远?我们究竟是在创造着文化,还是将文化带向毁灭?
文学,被称为人类思维的奇葩,被看做人类心灵的精华。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冲击,随着国家人文精神的不断沦丧,中国的当代文学也没有能够“出淤泥而不染”,还是被卷入了市场的交易当中。当文学走上一条不归之路,我们的心灵寄托还有没有未来?
难道,现在的文学就只能是一种娱乐大众的手段,让人们在茶余饭后或者是上下班途中,瞥两眼煞有介事的于丹讲论语和易中天讲三国?难道,现在的文学就只能是网络上写手无限光彩的世界?难道,现在的文学刊物就只有《故事会》才能留住大众的视线,其余的只能当做圈内人士自娱自乐的安慰与消遣?
中国当代文学的萎靡不振,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德国学者顾彬更是断言“中国当代无文学”。诺贝尔文学奖从没眷顾过中国人,很多人对其评奖原则颇有微词,可是难道瑞典文学院的评委们仅仅只跟中国过不去?无论是出于民族自尊心,还是出于对文学这项事业的热爱与坚持,抑或者是出自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有一批学者开始对当代的中国文学进行反思。在反思中,文学“想象力”的问题浮出了水面,并一度成为学者们讨论争辩的焦点。想象力的缺失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一蹶不振的主要原因。有学者指出,之所以我们当代文学到不了一个较高的精神层面,是因为占据了我们创作主流的,依然是那些满足于对现实表象进行简单复制或者对历史材料进行重构的作品,而真正充满生命想象的作品,却越来越单薄。
在多元文化的时代,随着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也有很多人在比较文学领域里探讨过中西文学想象力的问题,试图以西方文学的想象力为镜子,映照出我们文学想象力的缺失。我们认为,这种讨论在开始的时候就有了很大的偏颇,很多学者并没有真正地以比较文学“平等”的眼光去看待和审视两种异质文化背景下“想象力”,很多人要么就持着所谓“文化大国”的架子认为我们包括当代文学在内的一切文学作品都充满想象力,要么就一味地否定中国文学的想象力,认为中国文学的想象力一直低下。这其中的一点原因在于中国古代文学的辉煌已经不是我们垫垫脚就能够到的境界了,“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见庄子《逍遥游》)。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联系已经基本断裂,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古代文学传承的文脉已基本断裂。因此,因为古代文学想象力的发达而不承认当代文学想象力的缺失,或者因为强调当代文学想象力的缺失而把中国古代文学一起全盘否定掉,都是十分不客观的。如果与西方文学想象力相比较,也应该按照时间轴,具体阶段的文学具体分析,而不应该笼统地一言以蔽之。
此外,在比较文学的视域下,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不同的文学现象是适应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因此有一些讨论就变得没有意义。随着比较文学的观点不断发展,关于中西文学想象力比较的讨论便逐渐停止了。但是,学者们却依然没有停止对中国当代文学萎靡不振,对中国当代文学想象力萎靡不振的思考。
其实,与其把想象力不发达看成是中国当代文学没落的原因,倒不如看成是没落的表现。这样可以使我们不仅仅停留在表面,而可以进行更深入一点的探寻。有一些学者们相继提出了像政治倾向、文化政策、社会现实、生存困境、读者兴趣、作家素质,以及传媒多元化等一系列原因,这些都是导致中国当代文学想象力不发达的因素。而笔者倾向于“作家”,也就是时代的“文人”们更应该对此负责。本文试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进一步分析。
一、“模仿”中的文学生存
(一)文人的惰性——从西方“模仿”
单正平在《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中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国近代文学史是一部模仿文学史。”[1]234一句话粉碎了多少人盲目自信的童话。而中国当代文学又何尝不是在“模仿”中的一种存在呢?甚至与近代的中国文学比起来,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在近代的政治上一度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然而,事到如今,在这样一个没有战争的年代,中国却自觉自愿地沦为了文化殖民地。
中国走向这样一条模仿西方的道路是有一定历史原因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遭遇列强的侵略,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时,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当中国暴露在西方屡屡的侵犯下,曾经的泱泱大国,唯我独尊的美梦破灭了。中国第一次真正地开始承认西方比自己优越,比自己强大。从“师夷长技以自强”到“师夷长技以制夷”,总之都是越来越依靠西方的文明来拯救自己。在文学界,知识分子活跃起来,像胡适、陈独秀、鲁迅、等等一批文人开始大量翻译国外的文学作品引入中国。并且文人们还倡导了“白话运动”,创立简体字,为的就是用最快的效率启发民智,从而使下层民众也参与到救国救民的运动中来。可是,我们却从需要走向了一味的模仿,并且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创造性。从文学理论来看,中国的文学理论界呈现出大部分的荒芜。如今到了21世纪,我们的文学评论,还在依靠着来自西方的文学概念和观念进行着分析。“悲剧主义”、“审美理想”、“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理论”,如果把这些概念全部拿走,中国当代的文学评论还存在吗?我们就这么心安理得地用着这些模仿来的概念,永远跟在西方文学批评建树的后面,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状态,懒惰变成了一种理所应当的事情。我们是对自己没有信心吗?不是,只是吃别人消化过的东西,总比自己咀嚼要容易的多。
至于作家的创作,也是在一片模仿中进行着。他们模仿着西方作家的叙事方式、创作手法和用词,但是致命的缺点就在于他们仅仅只模仿了表面,而把实质的东西扔掉了。文学的核心是“人”,人性的关注,人类自由意志的实现,我们当代的作家只去模仿西方的一种形式,却不从自己内在的素质进行提升,不去主动地思考问题,注定写出来的作品会缺少灵魂。
比如,米兰·昆德拉在中国流行起来以后,“肉欲”的描写成了“时尚”的“主流”。现在在中国作家的创作中,不管有多牵强,这种性描写是必不可少的。读他们的作品时,如果把大段的性描写删掉,会发现根本对这部作品没有什么影响,性与情是分离的,读到这样的描写时,更多的是一种恶心和无聊。而米兰·昆德拉不同,比如他的《玩笑》、《生活在别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昆德拉对他笔下的主人公都会有性的描写,可是他要说明的却不是这么简单,比如他笔下写到一个叫萨比娜的女性,对她和她的情人弗兰茨之间的爱情与性的描写,昆德拉是要告诉人们,标榜了太多流行观念的爱情,并没有那么纯净,弗兰茨说他爱萨比娜,可是那明明是一种恋母情结,他自己却不愿意承认,口是心非的媚俗,即使在两人赤裸裸地相对时,弗兰茨也一直在做别人眼中的弗兰茨,从没有脱下外面那层媚俗的外衣,萨比娜在得到弗兰茨的求婚后,毅然离开,因为她看不得这样的虚伪。在昆德拉笔下的性,是在为他的思想呈现寻找一条释放的道路,或许当代作家要学的不是这条道路,而是这种思想吧。文学作品的想象并不是说一定要创造一个如同《哈利波特》中的魔法学校或者是《指环王》中的中世纪中土大陆才算的有想象力,很多时候,想象力也是一种理性思考后的体现,没有深刻的人生认识,又怎么能写出深刻的作品呢。中国当代作家在描写“性”的时候,也是很生动的,可那又如何呢?只是没有灵魂的躯壳而已。
(二)创造性的丧失——从现实“模仿”
小说本就是虚构性的艺术,即使再努力地强调是写实的小说,也不可能是完全的写实,否则那就成了新闻报道而不是文学作品了。虚构就是想象的介入。康德曾经把人的想象分为再现性的想象和创造性的想象。前者是指以前发生过的事情或者景象在脑海里停留,在另一个时间内重新回忆起来的时候,当时的情景会在脑海中重新浮现,但是这样的浮现也已经是经过思维加工后再现出来的。而后者是指不是事实的再加工和再现,而是根据自己的认知水平或者感情构造出的一个全新的情景。
中国当代作家记录或者纪录片式的作品,就是大量地停留在再现性的想象阶段,很少有创造性的体现。因为很多作家在创作时忘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那就是现实与文学不同,文学并不是对现实的完全反映和模仿,而是利用现有的素材再创造一个与现实不同的世界。一味依靠对现实的模仿进行文学创作,会使得作家的创作意识越来越淡薄。现在很多作家标榜着“原生态写作”,在这样的作品里,其实也是为直接描写现实,放弃文学想象力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文学的创作可以写发生过的事情、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或者永远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不管是哪一种,都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事件本身。作家应该有一种自觉的意识,穿过世俗的浮表,进到更深的一层去挖掘和理解人性的意义。这种理解其实就是一种想象的过程,而想象也就是每个人对于同一个世界的不同理解。无论是题材还是叙述方式都没有那么重要,更不可能成为评判一部作品好坏的标准。可以这么说,把一部作品中反映的精神和人性抽象出来放在另外一个背景下,这个意义还是应该成立的。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卡夫卡、昆德拉、曹雪芹这些大师们的作品,都是这样的。而这也正是中国当代文学欠缺的地方,作家的想象力死了,而读者在读到他们的作品时,离开了这部作品所设定的环境,很多意义都不再成立了。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读很多当代作品时,当时感觉强烈,而一旦合上书,就不会在沉浸和纠结在里面的原因。
作家,绝不会仅仅是一个写手,它还应该是一个感情的领悟大师。仅仅凭借身体和快感完成的创作,难以打动读者的心灵。中国当代作家自觉的意识、领悟的意识、反思的意识都太薄弱了,把一些通过记忆搜集的零零碎碎的资料拼凑在一起的事儿,小学生就完全可以胜任了。那么这些受过多年教育的文人,又有何价值。也许这个时代太过艰难,我们的当代作家在生存和诱惑面前,放弃了文人应有的表达,不断向世俗和低级趣味靠拢,却不自知。中国当代文学想象力想要燃烧,中国当代文学想要摆脱这样萎靡不振的困境,只能依靠这些文人们创造性的自觉。永远活在模仿的世界里,无异于自取灭亡。
虽然我们也能听到一些反叛的声音。“今天是一个印刷的垃圾时代,是一个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时代,是一个文化侏儒多如牛毛而真知灼见无法求得共鸣的现代”。[2]159“在西方文明推进中的第三世界国家知识分子的狂歌热舞只能是一种新时期的‘投降主义’……庞大的中国知识分子阵营,为什么如此软弱,软弱到只剩下向西方献媚的一个声音?”然而,毕竟个别有自觉意识的学者和作家的力量是太弱小的,如果不能唤得更多人的觉醒,最终将会孤掌难鸣,沉寂在一片没有希望的荒漠中。我们当代的作家不应该再当西方和现实的追随者,对于生活、历史、生命、人性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深刻认识。
二、信仰沦丧的必然结果
为什么中国当代作家就会一直跟在西方的尾巴后面,为什么当代作家们就无法摆脱现实的束缚?中国当代文学想象力不发达的更深层的原因在哪里。
其实想象力作为人的一种心理能力,是不可能单独存在并且发挥作用的。感觉、认知、情感、思维、信仰、意志这些都帮助想象力能够在人们需要启动创造性的思维时,顺利地发挥作用。与西方优秀作家相比,与我国古代优秀作家相比,是说我们当代人的感觉迟钝了吗?还是我们的认知退化了?还是我们的情感不丰富?或者是我们的思维变粗糙了?还是说我们意志变脆弱了?即使有些方面的确有了退步,但其实也相差无几。可是信仰呢,我们的时代里,还有多少人拥有坚定不移的信仰。
我们总是一刻不停地忙碌着,可却又总是无所适从,人类的理想和民族的命运在这个时代突然变得遥远和可笑。人们都在为自己的生存活着,又能有谁会在崇高的理想与金钱之间的选择中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拜金主义横行于世,所有精神消失殆尽,一种没有“根”的感觉蔓延在我们中间。芸芸众生开始了浮躁的生活,没有了依靠的精神支柱,很多东西都面临着死亡。文学便是其中一个,在劫难逃。
古代文人的修身养性与气节风度在当代人包括当代文人身上都已经荡然无存。我们是政治上如此独立的国家,却为什么在文化的领域内自甘堕落,当这个国家的文人,作家的心中也已经被铜臭污染,恐怕除了文学的想象力,除了文学本身以外,其他的也会遭遇同样的噩运。看看世界上其他国家,宗教、民主、武士道、科学,都是他们不同的信仰。即使是非洲或者拉丁美洲依然存在的原始食人部落,也有自己的信仰,比如一头熊,一块石头,或者一种仪式。而我们又在信仰什么?我们的作家又在信仰什么?信仰,作为辅助想象力发挥创造性的一个必要条件,它的完全丧失,给想象力带来的毁灭是十分巨大的。或许,如果我们当代的文学想要崛起,想要得到灿烂的果实,重新树立民族的信仰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吧。
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也应该对自己有所反思。当代文学的想象力萎缩只是整个文学萎靡不振的一个表现,而不是它的全部原因。信仰的丧失加速了这样的必然。文化本无高低之分,当代中国人创作不出好作品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落后的,只是因为一些被我们忽视了的问题,文学作品呈现荒芜。或许,当我们正视这个问题以后,会打破现在这个尴尬的局面。
[1] 单正平.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 张承志.清洁的精神[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