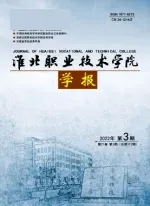苏辙《诗集传》训诂特点
魏明明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文学院,安徽淮北 235000)
苏辙《诗集传》训诂特点
魏明明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文学院,安徽淮北 235000)
苏辙的《诗集传》是北宋传注《诗经》的一部重要著作。其名物训诂条例完备,词语释义大部分承袭旧注,也有自作新解的部分。整部传注的名物训诂简洁明了。训释体例上采用分章阐释和整章阐释的方式,对前人有所超越。
苏辙;《诗集传》;训诂特点
宋代《诗经》研究著作有一百多家,其中北宋最重要的解诗著作为欧阳修《诗本义》和苏辙《诗集传》[1]。现今研究苏辙《诗集传》的专书,如陈明义《苏辙〈诗集传〉研究》[2]、李冬梅《苏辙〈诗集传〉新探》[3],探讨其版本流传、经学成就与思想等,很少涉及其训诂内容。总体来说对苏辙《诗集传》的研究不多,我们在这里主要探讨其在训诂上的特点。
一、词语训诂
北宋前期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人在研究《诗经》时主要把注意力放在《小序》和诗篇内容上,很少涉及其名物训诂[4]。苏辙的《诗集传》不但在《小序》的研究上颇有成就,对后人产生影响,在词语解释方面也下足了功夫,使《诗集传》成为一部完备的传注专书。在《宋史》曾记载苏辙反对王安石改科举而上书说:“乞来年科场,一切如旧,惟经义兼取注疏及诸家论议,或出己见,不专用王氏学。”[5]10824这正好概括了苏辙《诗集传》在词语训释上的特点。《诗集传》的名物训诂大部分袭用旧注,创新部分仅占百分之一。苏辙采用古注时,无门户之见,择善而从。
(一)条例完备
苏辙《诗集传》名物训诂方式多样,主要有以下几种:
1.同义词为训。如:颀,长也。(《齐风·猗嗟》)2.类名为训。如:榛,栗属。(《邶风·简兮》)3.指出比喻意。如:膏,言光泽也。(《郑风·羔裘》)4.义界为训。斩而复生曰肄。(《周南·汉广》)5.形容为训。蒙戎,乱貌也。(《邶风·旄丘》)6.描写为训。球,玉也。小球镇圭,长尺二寸;大球珽,长三尺,天子之所服也。(《商颂·长发》)7.指称为训。卫侯,许穆夫人兄戴公也。(《鄘风·载驰》)8.分解字义为训。掊克,掊敛克深,少恩之人也。(《大雅·荡》)9.一语多释。龟、蒙、凫、绎,鲁之四山也。(《鲁颂·闵宫》)10.探求义源。南箕非箕也,因之有是形而命之耳。(《小雅·巷伯》)11.以本字释通假字。匪斐通。有文之貌也。(《卫风·淇奥》)12.声训。究,久也。(《郑风·羔裘》)
(二)博采众说
正如向熹先生所言:“《毛传》在《诗经》研究史上有极大的权威性。”[6]352《诗集传》中采用《毛传》的占绝大部分。苏辙在采用《毛传》的说法上有多种形式。有的完全照录,如:“山脊曰冈。玄马病则黄。”[1]317(《周南·卷耳》)有的在《毛传》基础上增减文字或改字,如:“瑟:《毛传》‘矜庄貌’;《诗集传》‘矜庄也’。[1]345”(《卫风·淇奥》)有的解释语略有不同,如:“倩:《毛传》‘好口辅’[7]224;《诗集传》‘口辅好也’[1]346。”(《卫风·硕人》)有的《诗集传》对《毛传》的解释有所补充,如:“翿:《毛传》‘翿,纛也,翳也’[7]258;《诗集传》‘翿也,舞者之所翳也’[1]351。”(《王风·君子阳阳》)苏辙根据诗文内容补出“翳”的主语“舞者”,在注释时注意与诗文本身结合。有的《诗集传》只取《毛传》解释文字的一部分或其意义的一部分,如:“弁:《毛传》‘弁,皮弁,所以会发’[7]218;《诗集传》‘弁,皮弁也’[1]345。”(《卫风·淇奥》)只取其“皮弁”意,省略了其作用“所以会发”。有的《诗集传》的解释文字与《毛传》不同,但意义相同,如:“蘀:《毛传》‘蘀,槁下’[7]303;《诗集传》‘蘀,落也’[1]359。”(《郑风·蘀兮》)
《郑笺》是《诗经》研究史上仅次于《毛传》的重要著作,《诗集传》的训诂一部分也采用了《郑笺》的说法。有完全录用的,如:“茇,草舍也。”[1]322(《召南·甘棠》)有的在《郑笺》训诂的基础上增减文字,但意义相同,如:“拜:《诗集传》‘拔也’[1]322;《郑笺》‘拜之言拔也’。[7]78”(《召南·甘棠》)有时《郑笺》训释语较多,《诗集传》只采用其中的一部分,如:“正:《诗集传》‘所射于侯中者也’[1]369;《郑笺》‘正,所射于侯中者,天子五正,诸侯三正,大夫二正,士一正’[7]356。”(《齐风·猗嗟》)《郑笺》解释较详细,还涉及到了礼制,苏辙只取其意义的前半段,说明词语的意义即可。
唐孔颖达《毛诗正义》[7]在疏不破注的原则上传疏《毛传》和《郑笺》,事实上也有很多新的见解,当《正义》与《毛传》《郑笺》不一致时,苏辙也会采取《正义》的说法。如对“荡荡”的解释,《郑笺》:“法度废坏之貌”;《正义》:“荡荡是广平之名,非善恶之称”;《诗集传》:“广大貌”。(《大雅·荡》)这里苏辙认为“荡荡上帝”是形容“天之广大”,而非郑所作的政教之说。因此,他直取本意,与《正义》意同。
苏辙《诗集传》在训诂上还兼采汉唐其他作品和诸家学说。如:有用《说文》的。“湜湜:《郑笺》‘持正貌’;《说文》云‘水清见底’;《诗集传》‘水见底也’。”(《邶风·谷风》)有用贾逵说的。“清庙:贾逵《左传注》云:‘肃然清净,谓之清庙’;《诗集传》‘肃然清净曰清庙’。”(《周颂·清庙》)有用《韩诗》的。“敦:《毛传》‘敦,厚’;《郑笺》‘敦犹投掷也’;《韩诗》云:‘敦,迫’;《诗集传》‘敦,敦迫也’。”(《邶风·北门》)除了以上诸家,苏辙还采用了《草木疏》《经典释文》《广雅》等著作和郭璞、孔安国的说法。
(三)自创新解
《诗集传》中名物训诂自创新解的部分不到全书的百分之一。一共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无旧注,《诗集传》作补注。这种例子很少,只有10例,例如:《邶风·柏舟》:“薄言往诉,逢彼之怒。”《诗集传》:“逢,迎也。”[1]327这里“逢”字毛、郑均无注,孔颖达在作疏时也用的“逢”本字。苏辙在这里将其补注为“迎也”。另一种情况是不同意旧注,自作新解,这类例子比较多,如:《郑风·羔裘》:“彼其之子,舍命不渝。”《郑笺》:“舍,犹处也。”《诗集传》:“舍,施也。”郑玄认为“是子处命不变,谓守死善道,见危授命之等”,苏辙则认为“舍命不渝”是“出令而不变”的意思。因二人对“命”的理解不同,故导致他们对“舍”的理解不同。
(四)训诂重简明
苏辙在传注《诗经》上以简略为主,每字只用一字或几字来解释,只求达义,完全摈弃汉唐注疏的繁琐之气。如“陪:陪贰也。”[1]490(《大雅·荡》)“祁祁:众也。”[1]394(《豳风·七月》)这不仅受当时疑经风气的影响,也是因为苏辙认为“注释经书不需如此详尽,否则将窄化读者的视野”[8]282。他说:“孔子之叙《书》也,举其所为作《书》之故;其赞《易》也,发其可以推《易》之端,未尝详言之也。非不能详,以为详之则隘,是以常举其略,以待学者自推之,故其言曰:‘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夫唯不详,故学者有以推而自得之也”[1]315指出孔子叙《书》赞《易》均未尝详言,是为了让后来的学者自己推理而自得其义,以免妨碍了他们的思考空间。所以他作《诗集传》注解简明,“以为此孔氏之旧。”[1]315苏辙认为“读书百遍,经义自见”,他在《上两制诸公书》中说:“昔者辙之始学也,得一书伏而读之,不求其传,而惟其书之知。求之而莫得,则反复而思之。至于终日而莫见,而后退而求其传,何者?惧其入于心之易,而守之不坚也。”[9]15说明自己读书的方法是先读元典,反复琢磨,“至于终日而莫见”时才参考传注。所以苏辙是以自己深思而得的最精要的词语来注释《诗经》。苏辙“年二十作《诗传》”[10]19,期间经历了近40年,谪雷前完成此书。在他的得意之作《诗》《春秋传》《老子解》《古史》中只有《诗》有名物训诂,完成时间最长,其用心之深可以想见。
二、训释体例
分章阐释和整篇阐释是苏辙在传统章句体例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传统的章句体例在解释词义之外再串讲大意。这种体式在《毛传》中已经使用,而且简洁明了。但《毛传》以句为单位,重视字词的训诂,所以不利于对诗意作整体把握。苏辙改造了这一体式,他根据《毛传》对诗篇作的章句的划分,以诗章为单位作解,有的还以整篇诗为单位,在序下或首章下揭示全诗主旨,这样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诗篇大意,克服了传、笺体和传统章句体对诗意的支离。
(一)分章阐释
分章阐释是苏辙《诗集传》的主要训释结构。也就是说根据每篇诗章数和句数的说明列出各章诗句,再分别对各章进行词语的解说,章句的串讲或章旨的说明。如《齐风·猗嗟》。
这首诗分为三章。苏辙在首章下先逐词训释,然后说明了全诗的诗旨。第二章只有词语训释。第三章不但解释词语,还对本章最后两句“四矢反兮,以御乱兮”的诗意进行串讲。《诗集传》中任何一首诗都会分别列出各章诗句,让读者一目了然。词语解释或在串讲前,或在串讲后,或在串讲中,位置不固定。而且苏辙重在首章说明诗意,后几章往往只列出诗句和词语解释而无串讲。
(二)整篇阐释
《诗集传》中有时还对一首诗进行整体阐释。既有字词解释又有诗意说明。如《召南·采蘋》。苏辙解释这首诗时,就是先列出整首诗然后做整体说明。因为诗中涉及到了妇礼,而且整首诗都只在说明这一礼法,各章也只是点出其中的一点,如果再按分章阐释的方法来解释很容易就肢解了这一礼节,所以采用整体说明的方式,并且引用了《礼记》来具体解释这一礼法及其全过程。这样就把整章诗的内容串起,浑然一体,使诗意得到跟准确、连贯的表达,避免了因分章造成的文意的支离破碎。《毛传》和《郑笺》虽也有对句意的说明,但主要是字词的训释。这种训释方式虽在细节上做足了功夫,却忽视了诗歌的整体性,也就破坏了诗意的连贯性。分章阐释和整篇阐释有利于对诗歌内容作整体理解。我们可以看出,苏辙对前人成果择善而从并合理利用,使自己的阐释更趋于完善。不得不说苏辙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更有创见。
[1] 苏辙.诗集传[M].四库全书·经部70.
[2] 陈明义.苏辙《诗集传》研究[D].台湾:东吴大学中文所,1993.
[3] 李冬梅.苏辙《诗集传》新探[M].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
[4] 杨新勋.宋代疑经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
[5] 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 向熹.《诗经》语文论集[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7] 李学勤.毛诗正义[M]//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8] 吴叔桦.苏辙与朱熹《诗经》诠释之比较[M]//诗经研究丛刊:第十七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
[9] 苏辙.栾城集[M]//曾枣庄,舒大刚.三苏全书:第18册.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
[10] 孔凡礼.苏辙年谱[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张彩云
I206.2
A
1671-8275(2010)02-0098-02
2009-10-27
魏明明(1985-),女,安徽淮北人,淮北煤炭师范学院文学院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诗经》训诂学。
——评杜朝晖《敦煌文献名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