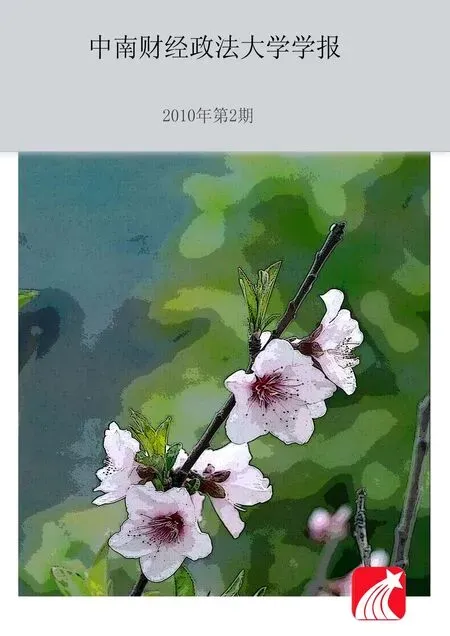美国的政府间转移支付改革及启示
徐小平 张启春
(1.华中师范大学 政治学研究院,湖北武汉 430079;2.武汉理工大学 期刊社,湖北武汉 430070;3.华中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是各级政府之间财政关系制度的重要内容,是西方各国联邦财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平衡区域间财政能力差异、均衡各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发挥着核心作用。不同于世界上多数国家以无条件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的模式,美国在分类拨款改革前一直实施以有条件拨款为主导的转移支付模式,联邦政府转移支付超过98%采取的是有条件拨款方式,而且主要采取专项拨款方式。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开始了将庞大、烦琐的专项转移支付制度逐步调整为分类拨款的大规模的合并浪潮。目前,美国政府最大的转移支付项目,包括公共医疗补助制度、AFDC(1996年后被TANF取代)以及教育转移支付等的实施均由零碎繁多的专项拨款合并成了大宗的分类拨款。分类拨款已成为美国联邦政府对州和地方政府转移支付的一种主要形式。因此,了解分类拨款产生的背景和原因,总结其演变的过程和特点,分析其几十年来实施的效果和特征,从中可以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这构成本文的宗旨。
对美国分类拨款产生后转移支付所采取的三种形式,国内学者有不同译法①,本文采用钟晓敏的译法,称categorical grants为专项拨款,block grants为分类拨款。两者的区别和联系很明确,分类拨款是同一类别的众多繁杂的专门项目拨款的综合、归并。区别于专项拨款的窄范围、过于繁杂、零碎、重复的特征,分类拨款是宽口径、分大类的拨款方式。尽管现存分类拨款在某些方面存在不同,但大多数同时具备以下特征[1]:(1)联邦拨款资助被赋予在一个功能区域界定广泛的宽范围的援助活动之中;(2)接受拨款区域的政府——州政府在联邦分类拨款相关问题识别、设计规划、联邦拨款分配方面有实质性的决断力;(3)区别于专项拨款形式复杂繁琐的要求(包括行政的、财政报告的、计划的和其他联邦政府强加的要求),分类拨款对上述联邦赋予的要求仅仅被限制在保证国家目标的完成所必须的范围之内;(4)联邦拨款资助建立在法定公式化的分配基础之上,很少有配套要求。
一、改革背景与原因
美国联邦政府的转移支付改革,以分类拨款在美国的正式诞生为标志,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在90年代中后期达到顶峰,至今已有40余年的历史。
追溯其改革背景,与1929~1933年的大危机和20世纪60年代联邦政府实施的“大社会计划”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相关。大危机促使美国联邦政府开始运用转移支付手段来对州和地方政府进行干预,直接导致了联邦转移支付的迅速增长,联邦政府的拨款已成为战后州和地方政府的重要收人来源,特别是在各类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领域。但美国联邦政府对州和地方政府的拨款绝大多数以专项拨款形式为主,一般性拨款比例极小。特别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大社会计划”的实施,联邦政府创办了数百个旨在支持或帮助以一些被严格定义的接受者或活动为受援对象的计划,这些计划从为乡村污水处理系统提供拨款到为残疾儿童的教育提供资助,覆盖广泛的公共服务领域。至1970年,联邦政府每年支付的专项拨款项目达530个。正是这些庞杂的专项拨款计划实施所带来的问题直接催生了分类拨款形式的诞生。具体而言,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
一是与专项拨款形式相比较,分类拨款方式更符合联邦财政的原则,能带来更高的管理效率。分类拨款计划将同类型的社会服务按大类合并成一揽子拨款,直接解决援助项目庞杂、设置重复问题,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分类拨款和其他合并的建议分享一个共同的原理,即通过赋予州政府更多的管理机动性能改善转移支付的效率,特别是在联邦政府拨款措施被认为失效、缺乏效率的地方,分类拨款被誉为联邦政府支配州政府改革和进行国家目标追求实验的一个工具。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1974年,城市重建改造专项拨款计划的失败为制定社区发展分类拨款(CDBG)提供了基本原则和思路。在CDBG下,联邦政府试图通过地方多种社区发展策略的试验来适应各个地方发展的需要。联邦政府在拨款分配中注意到地方政府更了解其辖区范围内的需求和存在的问题,需要的是一个城市社区综合发展计划而不是单一项目的城市改造拨款。国会的政策制定者们希望从州层面基于当地情况的福利工作试验中建立更广范围的国家目标拨款。此外,也有学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分类拨款这种转移支付形式之所以日益受到重视,重要性不断提高,还与里根政府的保守主义经济思想相关。“新联邦主义”主张更多地发挥州和地方政府的作用,在拨款形式选择上的体现就是增加没有附加条件的分类拨款的比重,相应地减少有严格附加条件的专项拨款的比重[2](P92)。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来自联邦政府的财政危机。联邦政府在实施政府干预的同时,也面临财政赤字压力。可以说,联邦政府的财政危机大大地强化了对转移支付形式改革和分类拨款方式产生的支持。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联邦财政赤字较过去增长了3倍,在此背景下,联邦政府对州和地方政府的拨款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联邦政府削减赤字的最有意义的项目。分类拨款也正是作为联邦政府减少国内开支的一个重大策略而出现的。比如在1981年的综合预算调节法案(OBRA)分类拨款计划下,赋予州政府在拨款上的权威和灵活性带来的结果是减少了约12%的联邦政府转移支付支出。依靠这些专项拨款的合并,联邦分类拨款计划实现了10%~30%不等的削减额度。总体而言,在联邦“赤字削减努力”的第一个十年里,联邦拨款由1978年的890亿元下降到1988年的510亿元。从预算角度来看,分类拨款作为紧缩管理的工具有着明显的优势。而从联邦政府的角度来看,将削减预算和拨款合并、调整救济结合起来,能够帮助联邦政府获得来自州政府对减少联邦支出所必要的支持,特别是在州一级政府相信这种削减是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联邦政府通过把这种痛苦决策的负担转移给州政府能减少其政治依赖性,而对州政府来说,以拨款的减少为代价换取的是其对分类拨款的支配决策权。
二、演变过程与最新进展
根据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分析,本文以分类拨款这种转移支付形式在美国的产生与发展为线索,将此次政府间转移支付改革大体划分为以下阶段[3]:
从1949年开始,经过整个50年代直至1966年前,可以称作改革的酝酿准备阶段。1949年,当时的胡佛委员会(The Hoover Comm ission)曾推荐以一种宽功能的、合并的转移支付制度替代当时实施的已觉察到的低效率的专项拨款(在此之前,分类拨款的可行性已获得了公共管理部门专家的认可)。1955年凯斯顿鲍姆委员会(The Kestnbaum Commission)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而20世纪60年代专项拨款计划的持续扩张促使美国当时国内行政管理部门的经济学家们如沃尔特◦海勒(Walte r Heller)和查尔斯◦舒尔茨(Charles Shu ltze)强烈要求对专项拨款进行合并。
1966年的《公共法案》(89~749)——一部综合的健康计划和公共卫生服务修正案的颁布,标志着改革的正式启动和分类拨款的诞生。《公共法案》第314(d)是第一个分类拨款计划,它将原来的9个专项拨款合并成一个健康分类拨款,因此受到了财政联邦制度专家们的高度重视,常常以首个分类拨款计划而被提及。尼克松执政期间,受“新联邦主义”思想的影响,曾雄心勃勃地提出了一个庞大的分类改革计划,声称要将当时所有专项拨款的1/3合并压缩归并为6个分类拨款[4]。议会通过了两项,即综合就业和培训法案(CETA)和社区分类拨款体系(CBGS)。此后,直到整个20世纪70年代,陆续出台了有关公共犯罪控制、高等教育、住房和城市发展、垃圾处理设施、人口控制等各分类拨款立法。但从分类来讲,有些拨款还不属于完全意义上的分类拨款,因为仍存在专项拨款的痕迹,常被称之为准分类拨款。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期,迫于联邦财政赤字的压力,分类拨款发展更为迅速。这一时期是以分类拨款为导向的政府间转移支付改革的高潮。1981年,大约有75个几乎集中于教育范围的项目被合并压缩为9个分类拨款计划。1981年后合并也曾一度搁浅,但在随后的福特、里根和克林顿政府执政期间,分类拨款改革得以继续。到1995财政年度,联邦政府的分类拨款支出达15类,几乎覆盖公共服务的大部分领域,总额约为362亿美元。随着1996年国会和克林顿总统办公室提交议会的第104会议议案的通过,又增加了10类分类拨款,它由原来共349项专项拨款合并而成。至此,分类拨款已达25项,由此形成了美国以州和地方政府作为联邦代理、以部门为分类依据的新型拨款方式。考察美国联邦政府历年预算可见,这一形式沿袭至今。小布什政府也提出了分类拨款或准分类拨款方案,用于一系列服务于低收入家庭的人类服务计划,包括公共医疗补助、住房供给、职业培训、儿童保护、道路运输等。联邦政府的拨款规模也逐年增长,2006年25类共843.4亿美元、2007年为871亿美元,而同期专项拨款分别是843.4和872.8亿美元,资金规模与专项拨款形式所占规模旗鼓相当,占到联邦政府对州和地方政府拨款总规模的近50%。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对美国政府间关系以及社会福利制度产生深远影响的是1996年《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平衡法案》(PRWORA)的颁布。作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最大的分类拨款改革,PRWORA受到了美国学术界、管理部门和政策制定者的广泛关注。法案的重点是改革社会救助项目,尤其是对“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项目(Aid to Fam 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AFDC)进行了改革[5]。它终结了联邦政府对年满60岁公民的补助和对有未成年子女家庭的补助计划,改为贫困家庭临时补助(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 ilies,TANF)。这一议案被认为是自罗斯福新政以来福利政策的最重大变化。它结束了自1935年以来,联邦政府对贫困人口的没有限制的福利补助,增加了工作要求,同时限制了受益时间[6]。比如规定,多数贫困家庭享受福利救济补助的时间不得超过5年;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人在接受福利补助的两年内必须参加工作;取消对合法移民食品券的联邦补助,等等。联邦政府还建立了奖惩制度:一方面,强化激励机制,对未超过总拨款配给的5%而圆满完成目标的州给予奖励;另一方面,加强处罚措施,对使用不当的救助金严加追究。法案的精神实质在于它只为暂时面临财政困难的家庭提供救助,加强对工作的激励并且减少受益者对政府转移支付计划的长期依赖。被克林顿称为旨在恢复福利制度本质,提供第二次就业机会,而不是把社会福利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这显然与从克林顿政府到布什政府期间,美国联邦政府仍然面临巨额赤字压力相关,旨在控制费用增长。据推算,这样6年内可削减联邦经费近600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布什政府也提出了削减赤字计划,要在2009年他的第二任期结束之前将财政赤字削减一半,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左右,到2012年将实现平衡的五年预算计划。但分类拨款计划规模尤其是资格型福利支出计划(entitlement program)分类拨款规模并未遭到布什政府预算的压缩,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占目前2.3万亿美元联邦预算的2/3。这标志着作为一种政府间转移支付形式,分类拨款已走向稳定成熟。
三、转移支付形式改革的主要特征
笔者认为,此次以分类拨款为核心内容的转移支付形式改革呈现出如下特征:
第一,从美国联邦政府转移支付形式演变来看,分类拨款形式的出现和稳步发展,改变了美国原有的以专项拨款为主要特色的转移支付模式,由此形成了美国由专项拨款和分类拨款构成、有条件拨款为主导的、两者规模相当的分配格局。作为美国联邦政府转移支付制度的一种新形式,分类拨款在提供国家目标意义上的公共服务方面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受到了联邦政府和州与地方政府的广泛欢迎。从政府间职能角度看,分类拨款可以被看作是联邦补助制度演变的一个逻辑阶段。
从联邦政府角度看,分类拨款的实施最直接的功用在于联邦政府得以成功释放财政赤字的压力,同时更为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在于政府间职能的调整。联邦政府通过公共医疗补助、对贫困家庭的临时补助以及教育、住房与城市发展等诸多领域的分类拨款改革,逐步地实现了这种压缩和调整。在较好贯彻联邦政府要达到的国家目标前提下,下放了部分公共服务职责,使其从具体繁琐的事务性工作中摆脱出来。分类拨款的分散效应和管理简单化效应节省了成本,改善了管理效率。
从州和地方政府角度看,州政府虽然在这一削减赤字过程中所得到的拨款总额较专项拨款方式下减少了,但由此换取的是它对本州范围内福利计划设计和执行的自由决策。相对于专项拨款方式下州和地方政府特别是州政府的被动接受角色,地方政府获得了空前的发言权和自由度,有助于发挥州和地方政府使用联邦资金的积极主动性。
专项拨款合并调整为分类拨款,也对相关社会福利、公共服务以及受援对象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公共医疗补助[7]、从AFDC到TANF的转变以及教育补助等较大分类拨款的实施及改革,对相关受援对象的状况诸如贫困家庭、单亲母亲抚养子女家庭及外来移民生活等影响广泛。尤其是1996年联邦福利改革法案的通过给贫困家庭可获得的援助带来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与AFDC的无限期现金补助相比,TANF只提供有限期间的援助,鼓励贫困人口通过就业自救,因此在执行过程中,许多州政府缩减了受援对象范围,把工作的重点放到了为贫困家庭提供就业培训与创造就业机会方面。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较大的社会争议。有人甚至评价说克林顿政府成功改变了美国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福利制度。
第二,分类拨款的类别数目和资金规模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就类别数目来看,从最初20世纪60年代的2个发展到现在已达20多个分类拨款计划。最早的两个分类拨款分别产生于1966年的健康计划和1968年的道路安全计划[3],而从近年联邦预算科目来看,分类拨款目前已达25类。就拨款总体规模来看(见图1),其绝对规模总体上呈不断上升趋势,从1966年的128.9亿美元增加至2007年的443.8亿。从分类拨款占联邦预算总支出的比重来看(见图2),总体上也呈上升趋势,由1966年的9.7%上升为2007年的16.3%。但同时也明显呈现出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从20世纪 60年代中期至1980年除个别年份外基本呈上升趋势,而1980~1990年则经历了一个不断下降的过程,比重由约14%逐年降至10.9%。1990年后又迅速回升,2003年最高接近18%,近年来基本维持在16%~17%。从分类拨款占GDP的比重来看(见图2),基本趋势与分类拨款占联邦预算总支出的比重基本相同。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1966年为1.6%,2007年为3.2%。1966年至20世纪80年代初不断上升,但在整个80年代同样有所下降,1990年后又有所回升,2003年达到最高值3.5%。

图1 美国分类拨款历年规模(1966~2007)

图2 分类拨款占联邦政府预算总支出的比重(1966~2007)
第三,从分类拨款的使用方向和各自变化趋势来看,则呈现出动态变化的格局。使用方向上,一方面强调联邦政府职能的传统角色,拨款主要集中于全国范围内社会公共服务特别是社会福利领域,在近年的分类拨款中排前两位的是卫生医疗补助和教育两大类。受援地区确定的其他项目还包括食物和营养、社会服务和儿童福利在内的社会安全支出项目。但另一方面在上述分类拨款项目的使用中,也发现资本性项目增长迅速,比如住房和城市发展已经位居第三,而具体到不同分类拨款项目,其变化幅度则差异较大。
四、结论与启示
综观美国政府间转移支付改革,其重要成果是催生了新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形式——分类拨款。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转移支付类型的新形式,其诞生与发展引起了各国政府与学术界的关注。笔者认为从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和启示:
(1)分类拨款作为此次改革的产物,是对美国原有转移支付形式和各国传统的转移支付形式的创新,它成功实现了传统有条件拨款和无条件拨款的有机融合。分类拨款诞生后,美国转移支付方式由以有条件专项拨款为主、一般性转移支付为辅的模式转变为由有条件专项拨款、分类拨款和一般性拨款三种方式组成的转移支付体系。分类拨款的出现和渐受欢迎,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基于财政联邦理论框架的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创新。
(2)通过分类拨款形式所拨款项全部用于贯彻联邦政府均等全国各地区公共服务的理念。从财力规模来看,联邦政府在提供国家目标意义上的公共服务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从分类拨款计划类别来看,与美国联邦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履行形成很好的对应性,集中反映了联邦政府公共服务的范围及其变化。通过分类拨款,受援地区可以将联邦补助直接用于本辖区相应社会公共服务领域,从而改善本辖区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缩小各地之间的差异。例如在每年4 000亿美元的社会福利开支中超过70%的开支是由联邦政府承担的,目前大部分都采取了分类拨款的形式,形成了联邦出钱,州和地方政府用钱、管事的格局。以分类拨款的方式来保障公共服务各区域的均等化,对中国当前解决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地区间和谐颇具借鉴价值。
(3)联邦政府发动的此次转移支付改革,调动了地方政府参与联邦全国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了州和地方政府对本辖区范围内公共服务的决策权利、对本地区来自联邦政府的补助拨款的分配权。州政府是作为联邦政府拨款的代理人和合作伙伴而出现,从而改善了联邦转移支付的使用管理效率。
分类拨款的各类拨款特别是最大的分类拨款项目,如公共卫生医疗补助和对贫困家庭的临时补助均由联邦政府统一立法,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此外,TANF取代AFDC,所体现的对就业和家庭的鼓励理念,也都值得我国重视。
中国目前的专项拨款规模在整个转移支付体系中已位居第二,仅次于税收返还,某些年份甚至超过了税收返还。但其使用方向、是否用于公共服务领域、各区域所占比重以及监督评估机制等问题均值得进一步研究。从专项拨款的使用来看,同样是项目种类繁多,分配缺乏科学的依据和标准。因此,有必要根据政府在新时期的职能、公共财政的框架要求重新梳理、调整、规范专项拨款,明确专项拨款在整个转移支付中所占比例、界定其使用的范围和方向,协调专项拨款与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职责分工。在教育、公共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也可适当借鉴美国分类拨款的经验,以分类拨款替代过于繁琐复杂的专项拨款项目。
注释:
①钟晓敏把categorical grants译为专项拨款,block grants译为分类拨款;吴培俊等人把b lock grants译为整块补助;马海涛等人认为有条件拨款(conditional grants)有时也叫专项拨款(categoricalg rants);杜放把categorical grants称为分类补助,把b lock grants称为切块补助。
[1]H ow ard Chernick.Block Grants for the Needy:The Case of AFDC[J].Journal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1982,1(2):209—222.
[2]钟晓敏.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论[M].北京:立信会计出版社,1998.
[3]Kenneth Finegold,LauraWherry,Stephanie Schardin.Block Grants Historical Overview and Lessons Learned[EB/OL].(2004-04-21)[2009-10-20].http://www.urban.org/url.cfm?ID=310991.
[4]Timothy J.Conlan.The Po litics of Federal Block Grants:From Nixon to Reagan[J].Po 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1984,99(2):247—270.
[5]Diana Romero,Wendy Chavkin,Pau l H.Wise.The Impact of Welfare Reform Po licies on Child Protective Services:A National Study[J].Journal of Social Issues,2000,56(4):799—810.
[6]LaDonna A.Pavettl.Creating a New Welfare Reality:Early Implementation of the 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 Program[J].Journal of Social Issues,2000,56(4):601—616.
[7]Jeanne M.Lambrew.Making Medicaid a Block Grant Program:An Analysis of the Implication of Past Proposals[J].The Milbank Quarterly,2005,83(1):4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