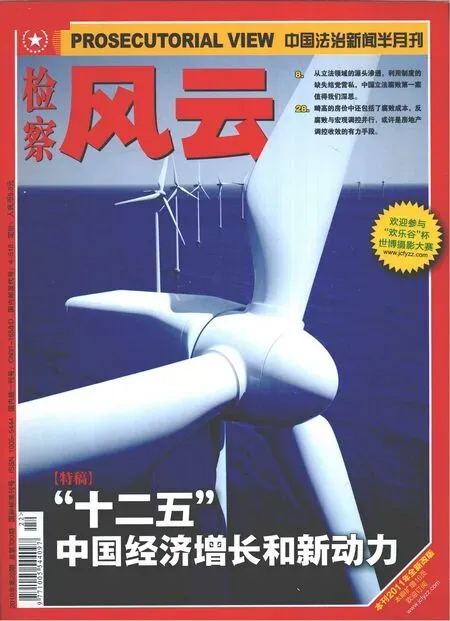透视立法腐败的“新型经典标本”
文/杨兴培(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透视立法腐败的“新型经典标本”
文/杨兴培(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郭京毅一案非同小可,从中略见管斑,着实让人惊呼——我国高端精英的立法腐败时代可谓山雨欲来。
郭京毅,何许人也?乃国家商务部条法司原副司长、正局级巡视员也。郭京毅于1986年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进入外经贸部条约法律司工作,曾在投资法律处工作多年,历任副处长、处长、副司长。2003年外经贸部并入商务部之后,郭京毅仍担任条法司副司长,并于2007年3月提升为正司级巡视员。副司长的职务、正局级巡视员的职级,在“官本位”的中国以十三亿人为分母,从相对角度而言必然得出物以稀为贵的结论,这种级别的官儿应称得起是高官,属于人中精品。特别是在商务部甚至在整个国家机关的司级干部中,44岁就如此高位当然可说年轻得志。但从绝对角度而言,在皇城根脚下类似的官儿车载斗量,不可胜数,也可说是如白日间满眼可见之彩云,夜晚时楼堂馆所内随时可遇之宾客。
只是郭京毅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利用从法律角度审核外资项目的职务便利大肆收受贿赂,开创了中国高端精英腐败的新形式、新类型、新标本——立法腐败,从这一点而言,郭京毅案无疑具有了一定的标本意义。
由郭京毅案引发的连锁反应——商务部外资司原副司长邓湛、国家工商总局外商投资企业注册局副局长刘伟、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检查司司长许满刚,以及在商务部对面办公的北京思峰律师事务所原主任张玉栋、注册律师刘阳,也相继被司法机关立案处理;在郭京毅案的行贿者名单中,有商界首富黄光裕向郭京毅行贿110万元,苏泊尔公司董事长苏显泽向郭京毅行贿30万元。由此看来郭京毅一案非同小可,从中略见管斑,着实让人惊呼——我国高端精英的立法腐败时代可谓山雨欲来。
大害无形:郭京毅案的社会危害
破坏人们对国家、公器及未来的期望
公元2010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政权建政六十一周年华诞纪念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在首都北京率领各级党政要员聚集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缅怀人民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立志要将先烈们未竟的事业进行下去,这一场景不免使人将思绪瞬间延伸到一百多来的历史风云中去。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镌刻的熠熠生辉的金粉大字向历史、向现实、甚至向未来诉说着一段中华民族的苦难、奋斗和崛起的历史。近代中国多灾多难,先是八国豺狼入室,后遭东洋铁蹄践踏,经过不屈的抗争,河山终于重光。虽又接续同室操戈,好在也是为了胜败去杀,新中国政权破蛹而出,如日东升,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世界为之一震。为了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开始踏上的道路能够延伸下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宣告:我们是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由此让整个中国人民感到自豪,国家终于属于人民的了。
然而,历史和现实却是吊诡的,由于体制设计的欠周而导致的制度性缺陷,也由于苦难的历史容易被人遗忘,更由于人性的丑恶得不到有力的制止和惩罚。一些成可为英雄,败可为乱贼的高端公仆、社会精英结党营私,干起败国害民之事。他们将原先曾信奉过的信念——“国家是我们人民大家的”,逐渐退化为“国家是我们的”,甚至蜕化为“国家是我的”。
本来,我们是人民共和国,国家是我们人民大家的,那么法律的制定就应当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应当体现着全体人民的应有意志。因此,法律是公器,是神器。公器乃当公论,神器焉能私用?然而郭京毅们以他们“巧妙”“智慧”的行为演绎着“国家即使还不能成为我的”,也要让“国家成为我们的”邪思恶念。
高端公仆、社会精英是社会的稀有之物,理当成为人间智慧的载体者,时代发展的规划者,模范行为的实践者,社会进步的贡献者,国家利益的捍卫者。但郭京毅们却成为了国家肌体的腐败者,社会利益的破坏者,人民权益的掠夺者。从1986年北大法律系毕业进入对外经贸部(后并入商务部)条法司,到2008年在商务部条法司巡视员职位上落马,郭京毅几乎参与和主管了20年来全部外资法律法规的起草和修订,他利用法律政策中的模糊地带,把制定法规和解释法律的职责转化为权力寻租的来源,一方面在司职外资审批的国家部委中编织关系网,一方面又扶持“潜规则”律师、暗通特殊利益集团获取其输送的额外利益。由此可以看出郭京毅案的最大社会危害体现在他们使国家及整个执法机制遭受颠覆性的破坏,使善良的人们开始丧失信心,败坏了人们对国家、对公器、对未来的期望,直接动摇了人们仅存一点信念的根基。
将政府部门利益化、将以权谋私行为合法化
郭京毅们身居高位,手握行政法规的制定大权,享受着解释法律法规的权威荣光和社会荣誉。但郭京毅们却并没有享禄奉公不负重望,而是滥用职权、涉足贪墨。无疑,郭京毅们这些高端官员是聪明人,是社会的精英,他们熟谙政治,精通经济,专研法律。然而他们仰仗着聪明,公权私用,干着他人想不到的勾当。据报道郭京毅几乎参与和主管了中国此前20多年来的外资法律法规的起草和修订,张玉栋领导的思峰律师事务所也曾经参与多部法律的起草,其中包括2006年对外资并购发生决定性影响的法律——《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俗称“10号文”)。而刘阳也参与起草了自1995年以后中国重大的利用外资方面的法律、法规。
按照近年来惯例,有关部门起草法律法规时,会邀请一些律师参加或者提供咨询。据行内人士介绍,“10号文”是中国近年来关于外资并购最重要的法律之一,于2006年8月8日由商务部、国资委、税务总局、工商总局、证监会和外汇管理局6部委联合公布,2006年9月8日正式实施。当时商务部表示,此法规是在2003年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的基础上修订完成的。2003年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后来被认为对“假外资”、红筹上市模式以及热钱进入我国未能提供有效的监管,从而使外资尤其是国外热钱轻松进入我国,或者变相进入敏感部门,威胁到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故后有对此进行专门修改的“10号文”的出台。知情人士称,郭京毅受贿,并非如此前传言所涉及的某个特定的外资并购项目,而是涉及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制定和司法解释,由此将可能波及中国所有外资并购项目,这也成为了中国有可能第一起在法律制定过程中官员通过受贿操控“立法”的案件,从而形成一种新型的腐败形式——立法腐败。
在这种大害无形的行为实施过程中,国家利益的受损已非言语可述。这种腐败与危害并不是体现在一时一地,而是体现在对国家整体利益的败坏之中。它是无形的,却又是巨大的;郭京毅们受贿是一时的,但它留下的祸害却是长久的;他们的犯罪行为可能是表面的,但他们的危害却是深刻的。这一行为已经表明,在今天的中国正悄悄演绎着一种“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私人化,私人违法利益合法化”的严重现象。而这一现象的延伸,将直接伤害到国家的神经系统,导致国家将不再是人民的共和国,法律也已不再是人民意志真实体现的可怕结局。
抱团结伙危害至深至巨,具有共同犯罪的表现形式和内在利益的私团化
从已披露的案情来看,郭京毅案中涉案人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郭京毅与张玉栋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大学同窗,情同手足;邓湛和郭京毅是关系密切的同事,亲密无间;郭京毅与刘伟不但关系密切,而且比邻而居;刘阳本来是郭京毅的属下,后来又到张玉栋的律所任职;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检查司原司长许满刚与郭京毅共同受贿,关系也不可小视。靠着这些十分“紧密”的关系,他们组成了一个封闭的“小圈子”。这种由高端精英组成“小圈子”人数不多,能量巨大。他们可以在多个层面主导制定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几乎“垄断”了十多年来中国大部分利用外资方面的立法“业务”。
正是这种高端精英抱团结伙式的犯罪,依靠着他们的聪明才智,从事的疯狂敛财行为且其手段极为隐蔽,既不与外人言,也不为外人见,以致很难在风起于青萍之末之时被及时发现、及时侦破。一旦东窗事发,事实上已经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也正因为这些人间精英、高端白领抱团结伙,自会暗中传递消息,相互传经送宝,在社会中将会形成一种以犯罪的高级手段表现为荣的价值观念。
也许他们对一些蝇营狗苟、偷鸡摸狗式的江湖盗贼不屑一顾;对那种愚笨式的贪污贿赂也暗暗窃笑。然而正是这种高智商、高技术、高手段的特殊性犯罪,使其犯罪的结果具有一定延后性,其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一时难于被人识破。同时这类犯罪证据极难获取,性质极难认定。按照现有法律,此类案件除了行贿受贿部分以外,其他行为还很难直接引律定罪,难于受到及时的法律惩处。欲罚无律,这在另一种意义上损害了法律的尊严。
制度设计:乏力的制约
郭京毅案的出现,尤让整个社会为之惊讶。一个精心设计的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为己任的外资审批制度,十余年间竟然垄断在少数几个人手里,在他们这个并不大的熟人圈里成了漏洞百出的玩物。在贪婪面前,外资并购的审批制度成为一个虚幻的、不可靠的空中楼阁。当然,在我们惊讶于立法领域腐败的时候,更应当要看到立法腐败的本质上还是由权力的滥用和缺乏应有的约束所导致的。

据熟悉国家外资外贸管理的人士介绍,以前面提到的“10号文”为例,在诸如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等审批的诸多环节规定了诸多模糊的条款。在法律规定模棱两可的情况下,无论是具体的操作程序,还是企业需要提交什么样的审核文件,是否符合规定,都完全取决于郭京毅们的“自由心定”和“自由裁量”。特别是“10号文”在如何与原有法律衔接、商务部与其他部门之间审批衔接等问题上,人为地留下了模糊地带,这就给郭京毅们很大的机会解释权和自由裁量权,大大拓展了他们在行政审批过程中的权力“寻租空间”,为他们精心设计利益寻租链条做好了铺垫。
在我国,《立法法》规定了以法律为主导,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行政规章等法的渊源为辅的立法格局。《立法法》虽然直接、当然地规定了各种立法权力的划分,但从中我们难以看到各个立法权正当性论述的痕迹,片面地讨论以人大立法为主导,而没有充分刚性地规定立法权被分解之后的诸多可能出现的问题。《立法法》几乎没有规定法律责任,对不尽立法职守或违反《立法法》的行为,没有设置必要的追究责任的制度。
法律一旦落实在司法过程中,如何理解法律的规定就成了司法者的意志体现。如果说司法者的“自由心证”和“自由裁量”有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在司法者之上和立法者之下具有行政色彩的法律解释一旦缺乏相应的规约和监管,人民的意志和法律的内涵往往因为个别人或个别小利益团体的暗箱操作而被蒸发、被添加。如此形成的法律解释,上不能直接受到人民(代表)的监督和制约,下不能受到司法程序的监督和制约,成了这一“准法律”制定过程中的一块“飞地”,这里撇开其正当性、合法性和合理性来自何处不谈,由谁来进行监督已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大问题,然恰恰这一不可忽视的大问题却被忽视了。郭京毅们正利用这一无人监督、容易逃脱人民目光所及的“飞地”的有利时空条件大肆作案就变得顺理成章。
加强监督,让阳光照耀立法领域
郭京毅案的出现,给我们的制度完善敲响了警钟。任何对权力的纵容和放任都将带来腐败,进而对国家、社会和普通民众造成祸害。而郭京毅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权力运行缺乏可供控制和监管的机制。因此,有学者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对立法权力的规制,引进立法辩论,规范立法游说以及公开立法程序,引导利益团体更广泛深入地参与到立法活动中来,从而实现对立法者进行多角度的规制,此举已变得迫在眉睫。此外,扩大立法民主还需强化公民参与,包括邀请专业人士参与起草法律法规或提供专业咨询,以及采取直接委托、公开招标等方式,将法规规章草案交由专业人士或专业组织起草。精英设计,民众选择应当是一种既集中体现人间智慧又真正体现还权于民的一种立法形式,大众参与有利于立法过程听取大多数人的意见,精英参与则有利于保证立法的专业水平。通过大众与大众、精英与精英、大众与精英进行充分的交融与博弈,这对于杜绝部门腐败和官员腐败这两种立法腐败能起到堤坝防洪的作用。
让权力在阳光底下运行,是一剂极为有效的防腐药。作壁上观、书中想,除了乱世和强盗做主的山寨明火执仗为所欲为外,自古以来凡是腐败都是在黑暗中进行的,腐败最怕阳光的照耀。所以遏制类似郭京毅式的立法腐败,加强监督,让立法活动和行使立法的权力在阳光底下运行,就变得刻不容缓。对权力进行监督,已经是一个说的嘴上起泡,听得耳朵长茧的老问题。但在中国只要这一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它就是一个常说常新的问题。2004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曾发表过一段十分精彩的讲话:“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人民)讲话”。对统治者的驯服,实际上就是对权力的驯服。把权力关进笼子,实际上就是把当官的关进笼子里。你看得到他、监督他的一举一动,却无需担心他能冲出笼子来“撕咬”你。所以对立法和立法权的监督,一方面必须让它在法律规定的渠道中运行,另一方面又必须在社会众目睽睽的监督之下活动。
如此看来,在立法过程中,我们不但应考虑将“郭京毅们”关在“笼子”里,还应把“笼子”放在阳光下,这对于我们预防“郭京毅们”的立法腐败是大有成效的。除此之外,加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实行金融实名制、防止贪官外逃机制等制度建设,对于克服腐败现象同样重要。忠言逆耳,良药苦口,但愿郭京毅案能够警醒社会精英、高端公仆,做到自觉地接受监督,防微杜渐。社会精英,高端公仆也应当知道,一生平安才是一种真福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