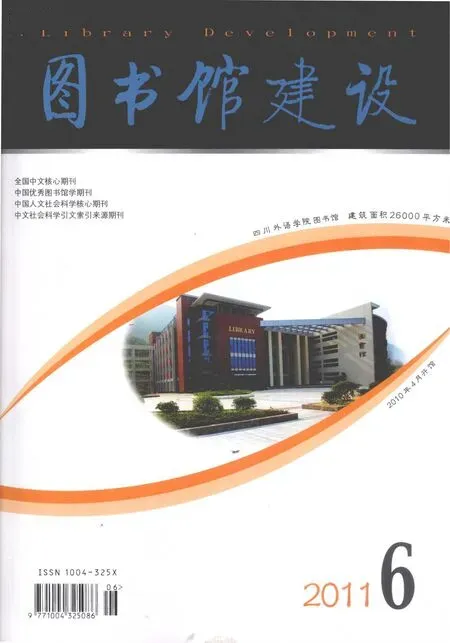中国古代藏书楼是中国近代图书馆的母体──兼议中国古代藏书楼的封闭性与开放性
黄幼菲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陕西 西安 710014)
中国近代图书馆是多元文化融合的产物。西方传教士是西方图书馆观念的“传播者”和中国近代图书馆发展的“促进者”;清末民初知识分子是西方图书馆观念的“践行者”、中国古代藏书楼的“扬弃者”和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奠基者”。除此而外,有一点必须充分肯定,中国近代图书馆是中国古代藏书楼的发展和继续,它的母体是中国古代藏书楼,它的根在中国,绝不“是西方思想文化传入中国的产物”[1]。中国古代藏书楼虽然具有很大的封闭性,“书藏”思想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它并非绝对封闭,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不能因为它的封闭性,就否定它的开放性。笔者试就上述问题谈一些想法,以求教同仁。
1 国内图书馆界关于中国古代藏书楼的争议
中国有无图书馆的历史?中国古代藏书楼是图书馆吗?答案都是肯定的。中国古代藏书楼就是图书馆,只不过它是近代图书馆的初级形式,近代图书馆则是它的高级阶段,“二者是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或历史时期的同一事物”[2]。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原因在于这个极其重要而严肃的问题至今仍未彻底解决。如果中国古代藏书楼不是图书馆,中国古代就没有图书馆;没有图书馆的历史,中国近代图书馆就必然“是西方思想文化传入中国的产物”[1]。在研究主体缺失正确指谓的情况下,所有关于研究中国古代藏书楼是中国近代图书馆母体的努力也就成了无本之末的徒劳之举。
从古代藏书楼到近代图书馆的演变,是中国图书馆史上一次重大变革。但由于此问题成因复杂,导致众说纷纭,争议颇大。目前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近代图书馆与古代藏书楼是两种不同的事物,近代图书馆是西方思想文化、图书馆观念和技术传入中国后的新生产物,是“舶来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近代图书馆与古代藏书楼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近代图书馆是古代藏书楼发展的历史必然。
1.1 “中国图书馆西来说”
第一种观点认为,“在研究中国图书馆的历史时,把古代的藏书和藏书楼当作中国图书馆的源头或前身,是极不妥当的”[1],因为它们“不仅仅是名称上的差异,而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事物”[1]。中国藏书楼的历史在近代之后就中断了,藏书楼也消亡了。“中国的图书馆实质上是‘舶来品’”[3],“采取的是‘拿来主义’,摒弃了自己的车,搭乘上西方的车”[3];它“是西方思想文化传入中国的产物”[1],“我们姑且将之称为‘中国图书馆西来说’”[1],因为“中国的藏书楼中缺乏演变成为近代图书馆的基本机制,不可能成为新式图书馆产生的母体”[1]。事实上,默认此观点的人还很多,如“杜定友‘(图书馆)是现代新进事业之一’的表述”[4],在事实上“否认了中国古代有图书馆的存在。流风所及,一直影响到今人对中国古代图书馆的理解。例如,谢灼华主编的全国高校核心教材《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在述及中国古代图书馆时均采用‘藏书楼’术语,而拒绝使用‘图书馆’一词;台湾严文郁《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一书以‘自清末至抗战胜利’为副标题,事实上也默认中国在‘清末’之前没有图书馆”[4]。
1.2 中国古代藏书楼是中国近代图书馆的母体
第二种观点认为,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我国图书馆(藏书楼)同世界各国图书馆一样伴随着文献的出现而产生,又随着科学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地自我完善、自我更新。“图书馆”一词是从西方引进的,但因此就认为中国近代图书馆是西方思想文化传入中国的产物则违背了历史。事实上,当与农业文明相适应的“第一代图书馆”(藏书楼)因其存在形式和活动内容而不能完成社会交给它的任务时,它就改变了自己的存在形式和活动内容,质变为“第二代图书馆”(近代图书馆)了。这就是说,“作为第一代图书馆的藏书楼阶段是图书馆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2],“是中国现代图书馆的母体”[2];同时,近代“图书馆又是藏书楼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必由之路”[2]。
《现代汉语词典》对“图书馆”一词的解释为:“搜集、整理、收藏图书资料供人阅览参考的机构”[5]。此处图书资料应作广义理解,不能仅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装订成册的纸质图书资料,还应包括各种形式、材质的文献资料。中国3 000年前的甲骨文就其本身性质而言就是一种广义上的图书资料。因为古代巴比伦的沉重的记事泥板都属于英国图书馆史研究的对象,那么就不应把“我国古代具有同样性质且相对泥板轻小易取的占卜记事的甲骨文献排除在我国图书馆史的研究范围之外”[6]。甲骨文献不仅刻有文字,而且可以供人占卜参考之用。因此,我国最早的图书馆,可追溯至夏代(约公元前的巴比伦时代)。据《史记》所载,《道德经》的作者老子曾任周朝藏室史,即藏书之史,故其可称为我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汉高祖刘邦率军入关,秦亡汉兴,宰相萧何遍收图籍,并建石渠、天禄二阁藏之,从此我国便有了专用的国家图书馆[7]。
事实上,中国古代藏书楼萌于殷商,形于两汉,发于隋唐,盛于宋清。我国古代藏书机构的名称颇多,称为“府”、“宫”、“阁”、“观”、“殿”、“院”、“堂”、“斋”、“楼”等,如西周的“故府”、秦朝的“阿房宫”、汉朝的“天禄阁”、东汉的“东观”、隋朝的“观文殿”、宋朝的“崇文院”、明朝的“澹生堂”、清朝的“知不足斋”及“铁琴铜剑楼”。人们之所以把古代藏书机构统称为“藏书楼”,“主要是由于古代的藏书机构‘重藏轻用’”[2],但它们已具备图书馆的最基本特征:收藏图书和利用图书。用历史的观点看问题,这一切都是正常的、必然的,是与当时社会需要相适应的。“今天的图书馆人用当代的标准苛求古人,就像成年的父母嘲笑幼儿的无知一样”[2]。我们完全可以说,“藏书楼是图书馆的初级形式,图书馆则是藏书楼的高级阶段。二者是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或历史时期的同一事物,既有联系(共性——收藏图书和利用图书)又有区别(个性——藏书楼是‘重藏轻用’,图书馆是‘藏用并重’和‘藏以致用’)”[2]。
2 中国古代藏书楼封闭性的成因
从先秦到清末,“虽然官府藏书与书院藏书在一定范围内是开放的,但总体而言,中国古代藏书楼是以封建保守、秘不示人为特色的,尤其私家藏书与寺观藏书更是如此”[8],其丰富的藏书虽然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影响很大,但“书藏”思想一直在古代藏书楼中占据主导地位。藏书楼最主要的功能是修史以治乱、尊经校书以施教化,同时提供国事咨询和传承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藏书楼不论是官府藏书或私家藏书,都是封建统治阶级为收集各种珍本秘籍而设立的“私人书库”,它的建楼宗旨在“藏”字上,封闭是其主流。那么,中国古代藏书楼的封闭性是如何形成的呢?
2.1 狭隘、自私的小农意识是其思想基础
古代的中国是农业大国,以低水平的家庭为单位的小农业生产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自给自足的个体农业经济限制了商业的发展,进而又限制了个体农业经济形态的转变。封建社会长期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使广大民众滋生了狭隘、自私的小农意识,藏书家也不例外。小农意识的主要特征是自私、自利。民众终身过着与世隔绝的田园生活,自产自销,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俗语道:“扇子有风,拿在手中;有人来借,等到秋冬”,即这种意识形态的真实写照。这些特征决定、影响着中国各项事业的命运,古代藏书楼作为社会和时代的产物,自然无法脱离其特定的社会环境而呈现出强健的开放形态。
藏书人的“自私”主要表现在:秘惜所藏,家业世守。这是中国古代私家藏书的重要特征。清末的王韬曾经指出:清代嗜古力学之士虽然“雅喜藏书”,但是“皆私藏而非公储”[9],“若其一邑一里之中,群好学者输资购书,藏庋公库,俾远方异旅皆得入而搜讨,此惟欧洲诸国为然,中土向来未之有也”[9]。藏书吾之私有,不借他人乃天经地义。明代范钦就明确表示,“书不借人,书不出阁”[10]364;唐杜暹在藏书题记中也说,“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11];清代王昶更是认为借书于他人“是非人,犬家类。屏出族,加鞭”[12]。
藏书人的“自利”主要表现在借书不还、损毁污染、据为己有。应该承认,在古代读书人中确有一些优秀读者,如宋代杜鼎升“凡借本校勘,有缝拆蠹损之处,必粘背而归之;或彼此有错误之处,则书札改正而归之”[10]378;明代宋濂借书必“计日以还”,“走送之,不敢稍逾约”[13]。但在古代读书人、藏书人中也有不少读者和藏书人思想素质不高,借他人图书或据为己有、或损毁污染。正如北齐颜之推在《家训》中所说:“或有狼藉几案,分散部帙,多为童稚婢妾之所点污,风雨虫鼠之所毁伤,实为累德。”[14]宋代“颖川一士子,九经各有数十部,皆有题记,是为借人书不还者。每炫本多”[15]。这种自私自利的小农意识严重限制了藏书的流通和利用,阻碍了藏书楼的开放和发展。
2.2 宗法制度导致的公共意识缺乏是其伦理基础
所谓宗法制度,是指封建社会王室贵族按血缘关系分配国家权力以便建立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它由周公创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家庭中的“父子”关系为核心,在宗族内部区分尊卑长幼,其实质就是把家族中的亲情血缘关系变为等级权力关系。宗法制度将权力叠加在血缘关系上,即权力的伦理化,使个体的服从不仅出于强制,而且要出于主动认可。孔子以仁释礼,“对礼加以改造,使礼、仪由外在的规范转为人心内在的要求,把强制性规定提升为自觉的理念,使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融为一体”[16],“将其‘自律型慎独伦理’异化而成为‘他律型的顺服伦理’”[17],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夫妻关系等)都被君臣化。显然,在这种普遍的人身隶属和依附关系的社会,人类把任何东西都看作是私有的,不是自己的,就是别人的,缺少公共认同。梁启超在分析中国为什么不能“合群”时,就曾认为首先在于“公共观念之缺乏”[18]。
公共观念就是公共意识。所谓公共意识,是指独立自由的个体所具有的一种整体意识或整体观念。它意味着独立自由的个体并不把自己作为孤立的个人,而是把自己认同于一个与他者联系在一起的共同整体,并以共同整体的共同价值规范自己的行为。公共意识意味着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只有具备了公共意识,一个人才有可能把属于私人的东西拿出来与他人共享,也才能对待他人的东西像对待自己的东西一样倍加爱护,否则只能是自私自利。费孝通在《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一书中曾说:苏州在“文人笔墨里是中国的威尼斯,可是我想天下没有比苏州城里的水道更脏的了。什么东西都可以向这种出路本来不太畅通的小河沟里一倒,有不少人家根本就不必有厕所。明知人家在这河里洗衣洗菜,却毫不觉得有什么需要自制的地方。为什么呢?这种小河是公家的。”[19]这就是公共意识缺乏的典型表现,因为人们的意识中只有纵的宰制型的关系,没有横的权利平等的关系。郑观应曾说:“我朝稽古右文,尊贤礼士,车书一统,文轨大同,海内藏书家指不胜屈。然子孙未必能读,戚友无由借观,或鼠啮蠹蚀,厄于水火,则私而不公也。”[20]
试想,在宗法制度导致的公共意识缺乏的伦理基础上,一个人怎么可能把自己的藏书与他人共享,或干脆把自己的藏书变为公共的藏书呢?
2.3 古代科技落后、图书数量少是其现实基础
图书数量是藏书楼开放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据统计,汉代刘向编目时,国家藏书才1万多卷。自此以后,可考万卷藏书家南北朝12位、唐代22位、宋代50位、明清超过百位。1万卷是什么概念?“1套《二十四史》3 249卷,1万卷约等于3套《二十四史》;《太平御览》1千卷,1万卷等于10套《太平御览》 ;1套《四库全书》79 337卷,1万卷约等于1套《四库全书》的八分之一”[12]。可见“1万卷”并没有多少图书。
为什么藏书数量不多呢?原因如下:①文字载体笨重。秦汉时期文字载体以简牍为主,秦始皇每天要读120斤重的简牍资料;汉代东方朔给汉武帝写的一封信,两个人才抬得动;司马迁《史记》130卷,用简策制作,堆积如山。②图书制作工艺落后,成书之困难令人匪夷所思。秦汉时期,简策的制作过程非常繁杂,除了杀青、编简之外,抄写时还得一手拿笔,一手拿刀,写错了用刀削去。即使在纸张普及之后,抄写图书也不容易。“清代蒋衡抄写80万字的《十三经》,整整耗费了12个春秋。清修《四库全书》,先后聘用书工3 826人,用了五六年时间才算抄写完毕”[12];“宋代成都雕印《太平御览》,刻工多至150人。清代泾县翟金生用泥活字印书,制成10万个泥活字,动员亲友36人参与,费时30年,最后弄得倾家荡产,一贫如洗”[12]。③藏书复本不足,影响传播。在封建社会,所有典籍、图书都是靠手刻或抄写来完成的,不仅费时费力、失误难免,而且一次只能抄写1部,生产量极为有限,很难保证每种书都有复本,这在客观上限制了藏书的传播范围。④缺乏鼓励发展科技的机制。早在宋代中国就发明了活字印刷,但这种图书制作的先进技术却迟迟得不到推广,雕版印刷技术长期徘徊不前,直到清末西方的机械印刷术传入中国并最终取而代之。尽管我国古代有“四大发明”等伟大创举,涌现出了众多杰出的科学技术巨匠,然而科学中心并没有在我国形成,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它当饭吃。”[21]
2.4 没有足够的读者群是其需求基础
中国封建专制的统治是建立在对广大劳动者残酷侵犯和掠夺的基础之上的。首先,残酷的经济掠夺使广大劳动者只能为维持基本的生理需求而奋斗,失去了阅读的基础和条件。其次,原始的生产手段使劳动者不可能有剩余的经济积累用于文化、教育这些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广大布衣阶层多为文盲,对劳动生产知识的需求不迫切,“知识、经验的传播基本限于传、帮、带的形式来完成,书籍对劳动阶层来说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有的甚至是废纸一堆”[22]。再次,在中国古代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受教育者绝大多数都是膏粱子弟,图书成为富人的奢侈品,读书上学成为富人的专利,但他们读的也无非是四书五经,阅读面极窄,图书的需求量不大。因此,难以形成源源不断的读者群。没有读者,也就没有开放;没有开放,就必然封闭。用现代经济术语来表述就是:图书没有市场,社会需求疲软。
3 中国古代藏书楼“开放书藏”理念的形成与践行
我们承认,中国古代藏书楼具有很大的封闭性,“书藏”思想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不论官府藏书、私家藏书抑或书院藏书,皆十分重视收藏和保护,而其对民众进行开放服务和教育的功能往往被忽略。应该看到,“封闭”与“开放”是相对而言的,那种认为古代藏书楼绝对封闭的观点是错误的。虽然中国古代藏书楼服务范围狭窄、流通方式落后,但它并非绝对的封闭,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同时对保存文化典籍、维持传统文化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事实上,建于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时期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和建立于公元4世纪末的罗马教皇档案馆等西方宫廷图书馆,当时也不向社会公众开放,仅供达官贵人使用,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开始从教堂中解放出来,向社会公众开放。
3.1 “开放书藏”理念的孕育及形成过程
虽然受到古代社会历史条件的种种制约,藏书的流通与利用受到了很大影响,但仍然有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文献传播和利用的重要性,主张开放书藏,并在这方面进行力所能及的尝试与践行。东汉末年蔡邕奏请灵帝后,将六经文字“书册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23],“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23],“此即著名的‘熹平石经’,这可算是官府藏书在文献的传播利用方面的一个早期范例”[23]。宋代馆阁藏书已可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借阅流通,“读者有皇帝及近臣、政府要员,还有一些经过许可的读书人、科举考生等”[24]。到了明清两代,随着私家藏书的兴盛,许多藏书家都主张开放书藏。明代藏书家李如一认为:“天下好书,当与天下读书人共读之”[25],并把自己的藏书楼命名为“共读楼”。明代的姚士曾提出“以传布为藏,真能藏书者矣”[23]的卓见。他们采取了各种当时可行的方式,或供人借阅传抄;或刊刻印行,广为传布;或延请学者,共同研讨;或捐献私藏,补充国藏,等等。这些理念和举措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古代文化的传播,虽然在今日看来未免有鄙陋之嫌,但对当时的古人而言已是难能可贵的了。
封建社会末期,一些藏书家逐步认识到旧有书藏模式的种种局限性,为弥补其缺陷出现了创立公藏之说。明末清初的曹溶在其著《流通古书约》中第一次阐述了开放藏书的思想,对那种“以独得为可矜,以公诸世为失策”[22]的狭隘传统进行了抨击,为流通古书创一良法 ;清代乾隆年间的周永年在其撰写的《儒藏说》中提出了“天下万世共读之”[22]的鲜明主张,在其《儒藏条约三则》的第三则就表达了“儒藏对四方读书之人开放,尤其要面对无力购书的贫寒之士”[22]的先进思想,称得上是公开利用藏书的首倡。这些都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前,标志着在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出现了建立公共图书馆的思想,他们的共同宗旨就是打破封闭分隔的私有藏书模式,让图书与更多的读者见面。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所带来的外来因素只不过刺激了中国内在积极因素的增长,大大加快了这一转化的速度。
3.2 “借阅”是“开放书藏”的重要形式
相互借阅是“开放书藏”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我国最早的借书记载始于汉代刘向,他在整理国家藏书时,曾向中大夫卜圭、臣富参等私人藏书家借书。“晋代范蔚藏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蔚为办衣食’。南齐崔慰祖藏书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帙,慰祖亲自取与,未常为辞’”[12]。唐代徐修矩藏书甚丰,著名诗人皮日休“假其书数千卷”[26]。宋代藏书家宋敏求藏书颇富,欧阳修、王安石、刘恕等都在他家借过书。“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时,就曾在崇文院设馆,借阅龙图阁、天章阁和三馆(即昭文馆、集贤馆、国史馆)、秘阁书籍。沈括、欧阳修等从事科学、史学研究,也曾充分地利用过馆阁藏书”[24]。在宋代,女真族建立的金国的平阳已经“出现了一种众人出资创办的公共藏书楼——‘赎书楼’。这些借阅方式虽与免费借阅不相同,但它毕竟属于开放型的”[25]藏书楼。明代藏书家徐火勃建红雨楼藏书,提出了“传布为藏”的观点,极力主张借书,“贤哲著述,以俟知者。其人以借书来,是与书相知也。与书相知者,则亦与吾相知也,何可不借”[27],并为前来红雨楼观书者免费供应茶水,热情接待。到清代,孙衣言的玉海楼、周永年的藉书园、国英的共读楼、陆心源的守先阁等都陆续向公众免费开放,徐树兰创办的古越藏书楼更是将这一借阅方式推向新的高度。
3.3 开放式藏书楼是“开放书藏”理念的重要践行阶段
在论证中国古代藏书楼是中国近代图书馆母体这个命题时,决不能忽视维新派倡导的开放式藏书楼。严格地说,开放式藏书楼是中国古代藏书楼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连接中国古代藏书楼和中国近代图书馆的“桥梁”,又是中国古代藏书楼“开放书藏”理念的产物和重要的践行阶段,它在我国古代藏书楼“孕育”近代图书馆的过程中承担着“阵痛”、“临盆”的关键作用。开放式藏书楼承上启下,不可替代。
开放式藏书楼的产生源于两个条件:①受古代藏书楼“开放书藏”理念的影响。“开放书藏”的思想是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精华所在。“明清以来,江浙一带为中国私家藏书中心,在中国历代藏书家4 715人中,浙江藏书家1 062人,江苏藏书家967人”[28]。在江浙常熟派和虞山派藏书家眼中,藏书绝不仅仅是个人和私家行为,“开放者之藏书”是其主要特点之一,“藏书致用、流通古籍的思想占主导地位,他们通过编印家藏书目来传播藏书信息,或以刻书为己任来广传秘籍,或提供借用以共享私藏”[28]。②维新派的积极倡导。戊戌变法前后,维新派知识分子为了解决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对未来前途进行了新的探索,掀起了群众性思想解放运动,有力地促进了当时封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变革,也使古代藏书楼这个母体吸允到了丰富的营养,“宫体”得到了优化改造,为开放式藏书楼的发展、近代图书馆的诞生营造了“产床”。
在古代藏书楼“开放书藏”理念的影响和维新派的倡导下,1895年后全国各地陆续设立的众多学会、学堂、报馆、译书局大都附设了开放式藏书楼。1897年湖南长沙设立的湘学会藏书楼、江苏设立的苏学会藏书楼,1898年湖南设立的南学会藏书楼,1900年创立的浙江藏书楼及1905年设立的上海国学保存会藏书楼,这几所藏书楼都具有一些近代图书馆的特性[29]。“徐树兰于1900年集议创办开放式古越藏书楼,无疑是华夏第一家开放式藏书楼”[28]。在《古越藏书楼章程》中,徐树兰阐明了他设藏书楼的宗旨:“一曰存古、一曰开今。”[30]他认为:“不谈古籍,无从考政治学术之沿革;不得今籍,无以启借鉴变通之途径。”[30]根据这一宗旨,他在所藏历代经史古籍的基础上,对“凡已译、未译东西书籍一律收藏。各书之外,兼收各种图画”[30]。同时,古越藏书楼有专门用来供读者读书的阅览室,设座位60个,有3个专职人员负责为读者借还图书,“欲看日报,在架上自由取阅;欲看月报,按借书方法借”[31]。“古越藏书楼在性质上已区别于旧式‘封闭式’的藏书楼,它以其公开阅览、公共使用为标志,孕育着近代图书馆的因素”[30]。
4 结 语
中国古代藏书楼是华夏文明的一枝奇葩,它虽然具有很大的封闭性,但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具备近现代图书馆“收藏图书与提供使用,或称知识信息的收集与传递”[32]的基本功能和本质属性,它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孕育、产生和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应该看到,不管是古代的藏书楼、近现代的图书馆,还是以后的数字图书馆,都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发展阶段,它们都要受当时特定社会条件的制约,“没有抽象的超然于社会机制之上的图书馆”[33],“阶段是个时间概念,不涉及‘有无’问题,‘图书馆’和‘藏书楼’是个名称概念,这是由中西文化差异性决定的”[22]。因此,中国近代图书馆是中国古代藏书楼的发展和继续;中国古代藏书楼是中国近代图书馆的母体和源头,是中国近代图书馆的根。
[2]于无声“.中国图书馆西来说”质疑[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93(2):27-30.
[4]傅荣贤,李满花,刘 伟,等.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为什么没有被建构为一门成熟的现代学科: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学科建设研究之一[J].山东图书馆学刊,2009(1):13-16.
[5]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3版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96:1275.
[6]陈海东.中国图书馆历史探源[J].情报科学,2002(8):875-877.
[7]刘勇华.中国图书馆变迁述略[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09(9):167-168,182.
[8]杨桂婵.清末新政与近代藏书楼[J].河南图书馆学刊,2003(6):84-85,92.
[9]付璇琮,谢灼华.中国古代藏书通史:下册[M].浙江:宁波出版社,2001:1080.
[10]黄建国,高跃新.中国古代藏书楼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99.
[11]谢灼华.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M].修订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104.
[12]曹 之.古代藏书楼封闭之原因刍议[J].图书馆论坛,2003(6):256-257.
[13]钱仲联.古文经典[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571.
[14]来新夏.漫话古籍的保护与研究[J].文史知识,2009(3):133-137.
[15]周少川.藏书与文化: 古代私家藏书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79.
[16]樊树志.国史[M].3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60.
[17]林安梧.儒学与中国传统社会之哲学省察:以“血缘性纵贯轴”为核心的理解与诠释[M].北京:学林出版社,1988:118.
[18]梁启超.新民说·论合群[G]//梁启超全集: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693-694.
[19]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差序格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4.
[20]程焕文. 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153.
[21]鲁 迅. 鲁迅杂文书信选续编:电的利弊[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2:126.
[22]叶柏松. 再议藏书楼与图书馆[J].图书馆,2003(1):92-94.
[23]赵彦龙. 试论中国古代藏书业的历史地位[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93(2):31-34.
[24]朱丽萍,乔高社.我国古代图书馆藏书的利用发展过程[J].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9(1):92-93.
[25]马艳霞.我国古代私人藏书的致用与开放[J].图书馆建设,2007(3):109-112.
[26]陈 忻.唐宋文化与诗词论稿[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131.
[27]郑伟章, 李万健.中国著名藏书家传略[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68.
[28]曹培根.藏书开放思想与实践:古越藏书楼与常熟藏书楼简论[J].常熟高专学报,2003(3):113-115.
[29]彭一中.我国近代图书馆的产生[J].广东图书馆学刊,1983(2):25-29.
[30]张树华“.戊戌变法”与我国开放式藏书楼的产生[J].北京图书馆馆刊, 1999(1):112-114,61.
[31]丁宏宣. 徐树兰创办“古越藏书楼”的进步性[J].图书与情报,1995(4):67-68.
[32]黄宗忠. 图书馆学导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230.
[33]汤树俭. 图书馆是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扁桃体”[J].新世纪图书馆,2009(5):2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