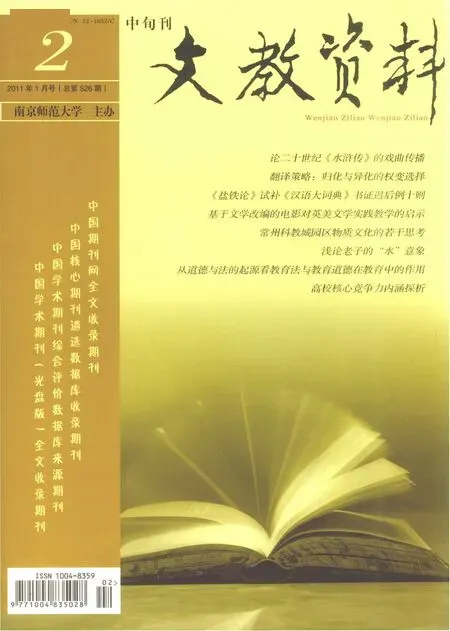左翼戏剧实践“文艺大众化”的再思考
朱晓莹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英国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认为:“大众”(the masses)一词本身就具有正反两面的意涵:“在许多保守思想里,它是一个轻蔑语,用来表达 ‘多头群众’(many heads)或是‘乌合之众’(mob),指的是低下的、无知的与不稳定的。而在许多社会主义的思想里,它却是一个具有正面意涵的语汇,被当成一个正面的或可能是正面的社会动力。 ”[1]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是二十世纪“文艺大众化”思潮的高潮。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时期明确提出“大众”不是“全民”,是新兴阶级的大众。1931年11月“文学的大众化”在“左联”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被明确提出。大众文艺的形式体裁问题成了当时讨论中涉及最多的一个方面,有两种主要的观点:一是用新的内容注入旧的形式或者用新的描写方法改造旧形式;二是根据大众的文化水平运用其所爱好的体裁创造出一些新的形式,主张新的文艺应该有新的形式。
这种思潮也强烈地冲击到文艺的一个重要门类——戏剧,不仅表现在戏剧理论的探讨和演剧的大众化实践,对剧本创作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29年中国第一个左翼剧团“艺术剧社”在上海成立,倡导“普罗列塔利亚演剧”并开展了实际的演出活动。随后,以田汉为代表的上海戏剧界人士纷纷转向,投入到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戏剧阵线。1930年上半年,艺术剧社先后组织了两次公演,将《爱与死的角逐》、《梁上君子》等西方左翼戏剧介绍到中国。由于左翼戏剧运动强调演剧是一种政治的辅助工作,是武器的艺术、斗争的艺术,因此这一时期左翼剧作家创作的作品大都以工人、农民为主人公,着重表现他们的革命斗争,及时、直接地反映现实生活中重大政治事件。如冯乃超、袭冰庐写的反映工人与资本家斗争的独幕剧《阿珍》,适夷创作的表现人民抗日反帝斗争的《S.O.S》,等等。左翼戏剧的演出体制同样体现了它的“群众性”和“集体性”:“深入都市无产阶级的群众当中,取本联盟独立表演,辅助工友表演,或本联盟与工友联合表演三种方式以领导无产阶级的演剧运动。”[2]
三十年代前期的左翼戏剧大众化运动主要在戏剧题材、结构的与时俱进,以及对于国外戏剧和传统戏剧戏曲的借鉴传承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同样也遭遇了挫折。“大众化”要求从剧本内容、演出形式上尽可能地贴近大众,因此为了获得更多更广泛的受众,很多戏剧都必须在流动的舞台上演出,这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它的演出形式与剧本创作,大多数演出的剧目都是独幕剧,富有戏剧性的剧本的缺乏,演出艺术的乏善可陈,使得戏剧演出屡屡沦为在舞台上喊口号然后带动观众一同喊起口号的表演,这些看似成功的“政治宣传”效果实际上与娱乐并无太大的区别,只不过是换一种形式的街头游行罢了。过度看重戏剧的宣传效果而忽视了艺术技巧,一方面确是出于政治宣传的要求,但其实也是“大众化”的先天缺陷所致:当“民众”逐渐转化为“大众”,戏剧创作者和观众的阶级划分也悄然生成,创作者被要求成为一个集体,个性被共性所淹没,人物成为群像的展示,成为符号。而作为观众的“大众”则由于“无产阶级”的政治称谓而获得了文化上的主导地位,“大众化”的创作也就要围绕着“大众”来展开,但实际情况是“大众”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拥有最强大的原始资源,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将资源转化为实际的艺术或者文学形式。而只有知识分子才拥有转化和改造的力量,在资源的转移和改造过程中,不仅存在着流失、变形,而且掺杂着改造者的许多一厢情愿的逻辑。戏剧创作者们绞尽脑汁进行创作,既要反映自己所不熟悉的工农生活与斗争,又要以之为武器引导和鼓动被认为是最先进但却是在经济文化上极端落后,政治觉悟也并不高的“大众”,功利性与审美性显然难以达到统一,个体让位于集体、审美让位于功利,创作上的艺术性的流失也就成为了尚可理解的共性。对戏剧“大众化”所作出的诸多努力却没有能完全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戏剧创作者们从预设的情境出发,试图以言传身教来感化和改造“大众”却并未能完全获得“大众”的认可,集体理念的充斥和个人情感趣味的缺乏成为这一时期戏剧的“致命伤”。
所以,在反思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时,我们理应看到,在以政治为考量标准的戏剧“大众化”过程中,为了尽最大可能争取群众的关注和支持,创作者只能“委曲求全”,在创作中抛弃“自我”,尽可能地关照最广大的“大众”,对工农大众无条件地认同,做“大众”的代言人。文学的大众化渐渐变为文学的无产阶级化、普罗化,“不能使大众理解、不能使大众爱好的,绝不是大众的文学,绝不是普罗塔利亚自身的文学”。[3]但“大众”作为一个落后的群体,又无力向戏剧创作者们表达具体的诉求,于是创作者们被灌输进政治理念和他们想象中的“大众”的呼声和诉求,创作者们将“大众”作为外壳覆于充斥着政治意识形态的作品上,期待获得最大限度的认同,最后却沦为知识分子自我的“狂欢”。尽管在阶级地位上“屈尊下位”,但是知识分子巨大的心理优势依然存在,作为启蒙者试图唤起、争取和改造“大众”的“启蒙”又在多大程度上能被启蒙者所接受?戏剧家们为了更好地灌输意识,实现对“大众”的启蒙和改造,不得不在形式上降低要求,学习“大众”的语言,借鉴“旧”形式、“旧”题材,在实际创作过程中,大众被抽象成一个概念,属于个体的存在意义逐渐被忽视,真正的大众艺术的价值也不复存在,大众抽离成了想象的主体,在文本中变为或正面或反面的脸谱化人物,结果导致了创作者和接受者的集体失语。
文学形态的最终生成包含着各种合力的作用,在这其中,客观因素往往比主观因素更为强大。我们无法否认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戏剧“大众化”运动中,文学作为一种政治宣传的工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恰又是作为 “工具”,文学被政治所挟持和利用,因政治的强势而失去了自我,政治思维取代了艺术思维,从美学的立场上来看,无疑是政治摧毁了文学,功利摧毁了艺术。但吊诡之处又在于,当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去考量那些在“大众化”口号下产生的作品时,去除掉作品中的政治理念、集体意识和口号话语,消解其外部的结构,实在的内容也全然失去意义,逃避了政治理念,去除了脸谱化、口号化,“大众化”也就成了一个空泛的口号。左翼戏剧大众化促使劳苦大众“认识自己的阶级立场,而兴奋地勇敢地做一个革命的战斗员,也是将来最健全的产业工人”的目的也就成了空中楼阁。
当然,我们丝毫不应怀疑这场“大众化”运动的参与者的真诚态度和牺牲精神,他们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进行文学创作,留下了不少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堪称经典的作品。尽管存在着政治取代艺术、脸谱化、口号化的种种缺陷,但是左翼戏剧的“大众化”运动存在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却无法泯灭。
[1]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北京:三联书店,2005:286.
[2]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宣言草案.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史料集[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17.
[3]沈端先.所谓大众化的问题.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