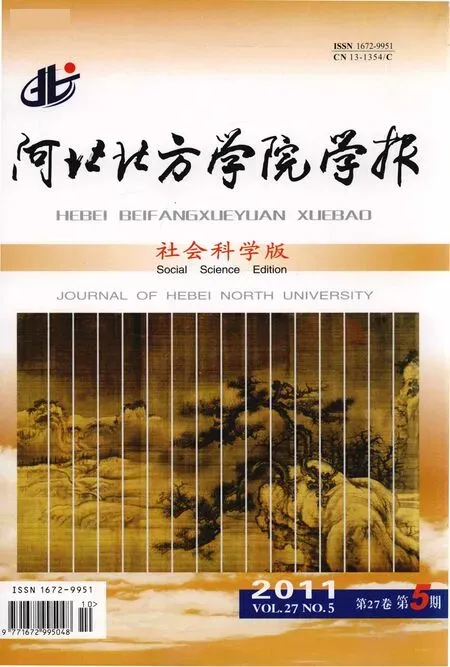论《春秋穀梁传》的文学剪裁
杨德春
(邯郸学院 中文系,河北 邯郸056050)
《春秋穀梁传》(以下简称《穀梁》)作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要作用,在中国经学史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是,自近代以来,对《穀梁》的研究却一直相对比较薄弱。
由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生活在广阔大陆上的农耕民族,生存条件的艰苦促使中华民族形成了勤劳朴素的民族性格,也促成了中华民族对文化艺术的功利态度。农耕生产的周期性促使中华民族注意总结生产和生活经验,这就使中华民族逐步成为重视历史的民族。但当时文史不分,往往以艺术方式从事历史和政治著述。六经皆史,所谓的经世大法不过是历史经验的总结。《穀梁》是作为一部经学文本流传于世的,其本质还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其中也存在着文学因素。其文学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挖掘。本文所采用的主要方法是写作元素分析法。经过与其它方法比较,笔者认为,用写作元素分析法比较适合于《穀梁》的文学研究。
《穀梁》是对《春秋》的解说,包括对《春秋》所记载的史实的补充和评论。因此,其文字内容可分为叙述的文字内容和论说的文字内容两部分,其中后者所占比例较大,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书中叙述的文字内容虽然所占比例较小,但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穀梁》在大多数情况下更大程度上关注于历史进程中的主体——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关注于人的本性之善恶、意念之正邪、人品之优劣、心志之高卑等心性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这就决定了此书叙述内容的特殊性。现以“晋杀其大夫里克”一章加以分析。
《春秋》僖 公 十 年:“晋 杀 其 大 夫 里 克。”[1](P361)《春秋左氏传》云:“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党会齐隰朋立晋侯。晋侯杀里克以说。将杀里克,公使谓之曰:‘微子,则不及此。虽然,子杀二君与一大夫,为子君者,不亦难乎?’对曰:‘不有废也,君何以兴?欲加之罪,其无辞乎?臣闻命矣。’伏剑而死。于是丕郑聘于秦,且谢缓赂,故不及。”[1](P362)
《春秋左氏传》的叙述内容旨在强调晋侯杀里克的背景以及晋侯与里克之间的利害关系。
《春秋》僖 公 十 年:“晋 杀 其 大 夫 里 克。”[2](P226)《春秋公羊传》云:“里克弑二君,则曷为不以讨贼之辞言之?惠公之大夫也。然则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弑奚齐、卓子,逆惠公而入,里克立惠公,则惠公曷为杀之?惠公曰:‘尔既杀夫二孺子矣,又将图寡人,为尔君者不亦病乎?’于是杀之。然则曷为不言惠公之入?晋之不言出入者,踊为文公讳也。齐小白入于齐,则曷为不为桓公讳?桓公之享国也长,美见乎天下,故不为之讳本恶也。文公之享国也短,美未见乎天下,故为之讳本恶也。”[2](P226-227)
《春秋公羊传》的叙述内容也旨在强调晋侯杀里克的背景以及晋侯与里克之间的利害关系。
《春秋》僖公十年:“晋杀其大夫里克。”[3](126)《穀梁》云:
称国以杀,罪累上也。里克弑二君与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辞言之,何也?其杀之不以其罪也。其杀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为杀者,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将杀我乎!”故杀之不以其罪也。其为重耳弑奈何?晋献公伐虢,得丽姬,献公私之。有二子,长曰奚齐,稚曰卓子。丽姬欲为乱,故谓君曰:“吾夜者梦夫人趋而来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将卫士而卫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于世子,则世子可。”故君谓世子曰:“丽姬梦夫人趋而来曰:‘吾苦畏!’女其将卫士而往卫冢乎!”世子曰:“敬诺!”筑宫,宫成。丽姬又曰:“吾夜者梦夫人趋而来曰:‘吾苦饥!’世子之宫已成,则何为不使祠也?”故献公谓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于君。君田而不在。丽姬以酖为酒,药脯以毒。献公田来,丽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于君。”君将食,丽姬跪曰:“食自外来者,不可不试也。”覆酒于地而地贲,以脯与犬,犬死。丽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国,子之国也。子何迟于为君?”君喟然叹曰:“吾与女未有过切,是何与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尔其图之!”世子之傅里克谓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则可以生,不入自明则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明则丽姬必死,丽姬死,则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宁自杀以安吾君,以重耳为寄矣。”刎脰而死。故里克所为弑者,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将杀我也。”[3](P126-127)
《穀梁》的叙述内容旨在强调里克弑二君与一大夫是为重耳,然后引出申生也以重耳为寄,从而显出申生之善;又以丽姬之恶反衬申生之善。这样一来,《穀梁》的叙述内容就与《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的叙述内容完全不同。君已老,且已昏,申生入自明,其难如登天,但并不是不存在使君明之的可能,且还有宗族和上层贵族的道德评判和人心向背。一旦真相大白,就算献公想使丽姬不死,也难以服众,即宗族和上层贵族这一关是过不去的。故一旦真相大白,则丽姬必死,丽姬死,则君不安。申生宁肯自杀,以安献公。可见《穀梁》特别强调申生的孝。以重耳为寄之言,表明申生认定丽姬以邪恶不能使其子获得政权,其实自古以来以邪恶获得政权者不可胜数。这就更加显现出申生心灵之纯洁善良,这就与丽姬的私心和邪恶狠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内容是《春秋左氏传》和《春秋公羊传》不可能叙述的,因为它们均以利害关系和政治实力冷静地记述和分析历史事件。
又如:《春秋》僖公二年:“虞师、晋师灭下阳。”[1](323)《春秋左氏传》云:“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宝也。’对曰:‘若得道于虞,犹外府也。’公曰:‘宫之奇存焉。’对曰:‘宫之奇之为人也,懦而不能强谏。且少长于君,君暱之。虽谏,将不听。’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冀为不道,入自颠軨,伐鄍三门,冀之既病,则亦唯君故。今虢为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请假道,以请罪于虢。’虞公许之,且请先伐虢。宫之奇谏,不听,遂起师。夏,晋里克、荀息帅师会虞师,伐虢,灭下阳。先书虞,贿故也。”[1](P323-325)
《春秋左氏传》先言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晋献公舍不得。荀息认为若最终灭虞,不过是将宝藏于外府而已。晋献公又担忧宫之奇,荀息分析宫之奇懦而不能强谏,又少长于君而君必昵之。晋献公既然知道虞有宫之奇,则说明献公是有意于伐虞久矣。荀息假道于虞之说辞先夸大其功以投其所好,其所好就是喜欢被奉承。
《春秋》僖公二年:“虞师、晋师灭夏阳。”[2](P206)《春秋公羊传》云:
虞,微国也。曷为序乎大国之上?使虞首恶也。曷为使虞首恶?虞受赂,假灭国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赂奈何?献公朝诸大夫而问焉,曰:“寡人夜者寝而不寐,其意也何?”诸大夫有进对者曰:“寝不安与?其诸侍御有不在侧者与?”献公不应。荀息进曰:“虞郭见与?”献公揖而进之,遂与之入而谋曰:“吾欲攻郭,则虞救之;攻虞,则郭救之,如之何?愿与子虑之。”荀息对曰:“君若用臣之谋,则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尔,君何忧焉?”献公曰:“然则奈何?”荀息曰:“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则宝出之内藏,藏之外府;马出之内厩,系之外厩尔,君何丧焉?”献公曰:“诺。虽然,宫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宫之奇,知则知矣。虽然,虞公贪而好宝,见宝,必不从其言。请终以往。”于是终以往。虞公见宝,许诺。宫之奇果谏:“记曰:‘唇亡则齿寒。’虞郭之相救,非相为赐。则晋今日取郭,而明日虞从而亡尔,君请勿许也。”虞公不从其言,终假之道以取郭。还,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宝牵马而至,荀息见曰:“臣之谋何如?”献公曰:“子之谋则已行矣,宝则吾宝也,虽然,吾马之齿亦已长矣。”盖戏之也。夏阳者何?郭之邑也。曷为不系于郭?国之也。曷为国之?君存焉尔。[2](P206-208)
《春秋公羊传》直接写献公寝而不寐,则其有意于伐虞久矣。接写荀息献计,以实利诱虞公假道,与《春秋左氏传》一样都是从物质上的利害关系入手。
《春秋》僖公二年:“虞师、晋师灭夏阳。”[3](P109)《穀梁》云:
非国而曰灭,重夏阳也。虞无师,其曰师,何也?以其先晋,不可以不言师也。其先晋,何也?为主乎灭夏阳也。夏阳者,虞、虢之塞邑也,灭夏阳,而虞、虢举矣。虞之为主乎灭夏阳,何也?晋献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产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晋国之宝也,如受吾币而不借吾道,则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国之所以事大国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币。如受吾币而借吾道,则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厩而置之外厩也。”公曰:“宫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宫之奇之为人也,达心而懦,又少长于君。达心则其言略,懦则不能强谏,少长于君,则君轻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国之后,此中知以上乃能虑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宫之奇谏曰:“晋国之使者,其辞卑而币重,必不便于虞。”虞公弗听,遂受其币而借之道。宫之奇谏曰:“语曰:‘唇亡则齿寒。’其斯之谓与!”挈其妻子以奔曹。献公亡虢,五年而后举虞。荀息牵马操璧而前曰:“璧则犹是也,而马齿加长矣!”[3](P109-110)
《穀梁》先言重夏阳也,以夏阳系虞、虢之安危。接写晋献公欲伐虢,荀息献计,也是从物质上的利害关系入手,但旋即归于人之心性。并不是人人都好利,中知以上能虑之,即理性能够超越利欲之心。人分中知以上和中知以下两种,中知以上是历史上的胜利者,中知以下是历史上的失败者。心智的高下成为影响历史的决定因素。
刘知几《史通》卷六《内篇·叙事》云:“然则才行、事迹、言语、讃论,凡此四者,皆不相须,若兼而毕书,则其费尤广。”原注:“近史纪传欲言人居哀毁损,则先云至性纯孝;欲言人尽夜观书,则先云笃志好学;欲言人赴敌不顾,则先云武艺绝伦;欲言人下笔成篇,则先云文章敏速。此则既述才行,又彰事迹也。如《穀梁》云骊姬以酖为酒,药脯以毒,献公田来,骊姬曰:‘世子已祀,故致福于君。’君将食,骊姬跪曰:‘食自外来者,不可不试也。’覆酒于地而地坟,以脯与犬,犬毙。骊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国,子之国也。子何迟乎为君。’”[4]《穀梁》写了覆酒于地而地坟、以脯与犬而犬毙这两个生动的细节,以见骊姬所下毒药之毒性极其强烈,从而反映出骊姬人心之狠毒。这两个生动的细节不可省略。刘知几从纯粹的历史学角度出发,主张“才行、事迹、言语、讃论,凡此四者,皆不相须,若兼而毕书,则其费尤广”。刘知几该论完全不顾这样的事实:在古代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还不知道艺术与科学的区别,而用艺术方法从事历史和科学的著述工作。
《穀梁》的叙述偏重于文学性的叙述,不是一一罗列历史事实,而是选取某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片断,这实际上是进行了文学性的剪裁。《穀梁》的叙述特别重视细节的真实性,不像一般历史著作只重视历史发展的线索和关节点,细节可以从略。由于细节能够反映生活的真实,而文学所要反映的正是生活的真实,可见,《穀梁》的叙述更偏重于文学性的叙述。《穀梁》的叙述有较多的合理的夸张和想象,吸收了某些民间传说的因素。
刘熙载《艺概》云:“《公羊》堂庑较大,《穀梁》指归较正,《左氏》堂庑更大于《公羊》,而指归往往不及《穀梁》。”[4](P18)袁津琥《艺概注稿》解释“堂庑”云:“本指正堂及四周的廊屋,这里是指作品的意境和规模。”[4](P19)刘熙载《艺概》将《左氏》、《公羊》的文学意境和规模归纳为一类,只是程度不同,而将《穀梁》、《左氏》之义理指归归纳为一类,只是程度上《穀梁》远胜《左氏》。《左传》之文学成就并不是由其文学意境和规模所决定,而是由其义理指归所决定,《左传》之名篇《曹刿论战》可以为证。《穀梁》之义理指归远胜《左氏》,这就为《穀梁》之某些篇章之文学性超过或远胜《左氏》提供了理论条件,之所以说《穀梁》之某些篇章超过或远胜《左氏》,乃是由于《穀梁》非为叙事性作品,文学性非其所追求。
在实际的文学鉴赏中也证明了上述分析,在中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古文选本《古文观止》第一篇即选《左传》之《郑伯克段于鄢》[6](P1),可见其文学性之高,但《古文观止》同时又选了《穀梁》之《郑伯克段于鄢》[6](P115),这是《古文观止》中唯一两篇同题入选的文章,可证《穀梁》之《郑伯克段于鄢》在文学性上不说胜过《左传》之《郑伯克段于鄢》,也可谓不相上下。《左传》惜字如金,《穀梁》之《郑伯克段于鄢》远少于《左传》而巨细毕现,在回答提问的过程中,娓娓而谈,以简练清晰的白描笔法描述以人物为中心的历史事件发展的全过程。由此应当可以窥见《穀梁》之文学剪裁之巨大成就。
[1] 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 春秋公羊传注疏[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 春秋穀梁传注疏[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 刘知几.史通[M].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十五.史评类.
[5] 袁津琥.艺概注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9.
[6] 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M].北京:中华书局,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