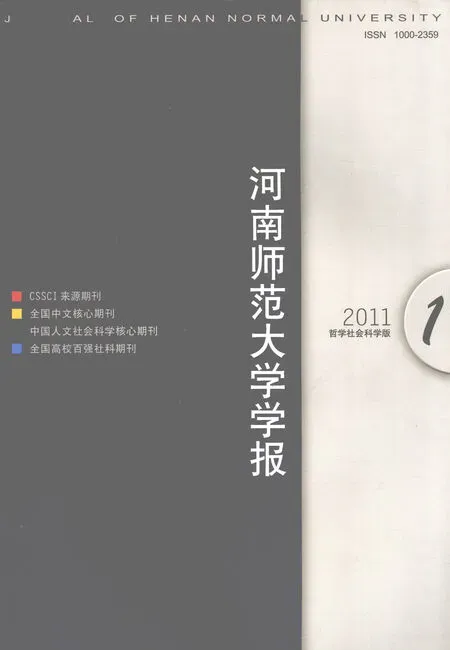辩证哲学视角下的本质主义学说
刘 叶 涛
(燕山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辩证哲学视角下的本质主义学说
刘 叶 涛
(燕山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本质主义是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哲学理论,但亚氏本质主义只适于刻画类事物的本质,对个体本质无能为力。分析哲学家克里普克借助其可能世界理论提出的新本质主义弥补了亚氏本质主义的不足。从辩证哲学角度把握两种本质主义及其关系,有助于准确把握相关理论的成就与问题,形成严整的分析型本质主义纲领,也可以体现辩证哲学和分析哲学相互为用的关系。
本质主义;可能世界;现实必然性;逻辑必然性;逻辑点
作为一种哲学理论的本质主义最早是由亚里士多德创立的,而当代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克里普克以其关于模态逻辑的可能世界理论为分析工具,提出了一种新型本质主义。从辩证哲学角度把握两种本质主义及其关系,有助于准确把握相关理论的成就与问题,形成严整的分析型本质主义纲领,也可以体现辩证哲学和分析哲学相互为用的关系。
一、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本质主义
亚里士多德的本质主义集中在他的四谓词理论和范畴学说中。
亚氏区分了特性、定义、属和偶性四种谓词:“所有命题和所有问题所表示的或是某个属,或是一特性,或是一偶性;因为种差具有类的属性,应与属处于相同序列。但是,既然在事物的特性中,有的表现本质,有的不表现本质,那么,就可以把特性区分为上述的两个部分,把表现本质的那个部分称为定义,把剩下的部分按通常的术语叫做特性。”[1]356如果命题的谓词描述主词所示事物的本质,这样的谓词就是定义,下定义的方法是属加种差。按照亚氏的说法:“本质特性被设定为与其他所有事物相关且又使一事物区别于其他所有事物的东西;例如,能够获得知识的那种有死的动物就是人的本质特性。”[1]440依马库斯的理解,“本质属性就是满足下列条件的一类性质:(1)一些对象具有而另一些对象不具有;(2)具有它们的对象就必然具有它们”[2]。这样,“能够获得知识的有死的动物”就是人的本质。若谓词揭示的是主词所示事物的非本质属性,这种谓词就是特性。尽管没有揭示本质,但它只属于主词表示的事物,如“能学习语法的动物”就是人的一种特性。在这两种情形下,主词和谓词的位置可以互换,我们既可以说“能够获得知识的有死的动物是人”,也可以说“能学习语法的动物是人”。就语言形式看,本质与特性没有差别,亚氏正是由此出发构建三段论体系的;但从哲学角度看,本质和特性却有重要分别,其关键在于对“种差”的把握。如果谓词表达了主词所示事物的一个要素,即与主词相应的种所属的较大的类,则称这样的谓词为主词的属。此时主词和谓词也有本质性联系:谓词揭示了主词所示事物的本质。如命题“人是动物”,谓词“动物”是人所属的更大的类,因而它是人的属。谓词还可表示主词所示事物的偶性,即为主词相应的种中的个别成员所有,但不一定为所有成员都有的属性,如“人是白的动物”。在这两种情形下,主词和谓词的位置不能变换,我们既不能说“动物是人”,也不能说“白的动物是人”。如果说前两种谓词说明的是“规律”,后两种谓词说明的就是“事实”。
从亚氏例子可以看出,其本质主义是关于类事物的,属加种差的方法只是针对类事物才适用。尽管他同时也指出,类事物的本质可以用来表述该类事物的具体成员,如他以人为例指出,“人的定义可以用来表述某个具体的人,因为某个具体的人既是人又是动物,而属的名称和定义都能够表述一个主体”[1]6,但四谓词理论终究没有正面探究个体本质。
亚里士多德关于个体本质的思想体现在其范畴学说中。他区分了十种范畴,其中以实体范畴为中心,其他九个范畴均用来规定和说明该范畴。亚氏把实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个别事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个体;第二类是所有个别事物的种;第三类是包含种的属。他把第一类实体称为第一性实体,把后两类称为第二性实体,认为第一性实体是所有其他事物的基础和主体,“除第一性实体外,任何其他的东西或者是被用来述说第一性实体,或者存在于第一性实体当中。因而如果没有第一性实体存在,就不可能有其他东西存在”[1]7。在第二性实体中,种比属更具实体性,因为种与第一性实体更接近,在对某个别事物加以述说时,说出它的种比说出它的属更贴切,而且属可以述说种,但反之不然。《形而上学》进一步提出,形式或本质是第一性实体。关于表达个体的概念“这一个”和表达事物本质的概念“是其所是”,亚氏认为两者“完全同一,并非出于偶然”[3]162。既然个体和它的“是其所是”也即它的本质是等同的,那么,表达个体本质的“是其所是”便是第一性实体,“是其所是”在单纯的意义上指实体和“这一个”[3]158,因而,个体的本质是事物的最终定义,只能由种和属来定义,而且个体的本质是个体的基础,决定了个体为何是这一个而不是另一个;但这种本质是抽象的,可以从认识当中分离出来,因而在本质的意义上讲,第一性实体就不再是感性的,而是理性的了。可见,亚氏认为个体有本质,且一个个体的本质决定了该个体的此性。
但亚里士多德关于个体本质的看法始终摇摆不定:因为将“这一个”与“是其所是”等同极为困难,因而个体本质根本无法定义。既然“是其所是”与“定义”等同,与“这一个”相等同的“是其所是”就应该是个体的定义,但在亚氏那里,属加种差的方法只是针对类事物的,对于个体来说,“都无定义,而是通凭思想、凭感觉来认识它们。脱离了现实,很难断定它们是存在还是不存在,但永远可以被说,可通过普遍原理被认识”[3]173。如此,个体的本质就不具有现实性,而成了一种潜在的可能性,成了某种不可言说、不可定义的神秘之物。正由于在个体本质问题上的摇摆,使得亚氏本质主义主要是以第二性实体为研究对象。譬如他说:“一种特性的被设定或者是由于本质,或者是永恒的,或者是相关于他物的,或者是暂时的。例如,‘人在本性上是一种文明的动物’就是本质特性;灵魂对肉体的关系就是关系特性,即一个指挥,另一个服从;永恒的特性如‘神是不朽的生命’;暂时的特性如‘某人在运动场周围漫步’。”[1]439亚氏只是在讨论暂时的特性即偶性时才讨论了个体(况且还是不确定个体),在其他情况下,他所讨论的都是第二性实体。
二、基于可能世界理论的新本质主义
克里普克是现当代哲学中打出本质主义旗帜的代表人物。我们知道,以罗素和逻辑实证主义学派为代表的前期分析哲学家拒斥一切形而上学,所有导致本质主义的学说都被他们宣布为虚妄,但到了20世纪后半期特别是70年代之后,为解决现代模态逻辑难题而创建的可能世界语义学,却为本质主义在分析哲学中的复活提供了可能;克里普克利用新的理论工具提出的新本质主义,为分析的形而上学开辟了一条崭新路径。
克氏本质主义包含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本质属性的界定。他认为,事物的本质属性就是其“必然”具有的属性,它历经一切可能世界而保持不变,使事物保持自身同一;偶然属性则是事物可有可无的属性,即在某些可能世界具有,但在其他可能世界完全可以不具有。依此标准,柏拉图最著名的学生、《形而上学》的作者等亚里士多德现实具有的属性,就只是他的偶然属性,因为可以设想这样的可能世界,在其中亚氏既没做柏拉图的学生,又没有写《形而上学》。那么,什么是事物的本质属性呢?克氏提出两种理论,一是个体事物起源的必然性原理,另一个是自然种类事物的内在结构原理。他认为,个体的本质只能诉诸其起源,起源决定它的本质,决定它的自身同一性。比如亚里士多德是由其父母的精子和卵子合成的受精卵发育生成的,因而他由之起源的那个受精卵就构成他的本质。自然种类事物的本质,就是该类事物全体成员共有的内在结构,如果水的分子结构是H2O,那么H2O就是水的本质。
第二个要点涉及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的关系。克氏认为,事物只要有其本质属性,即使它们失掉其他属性,也仍然是该事物;反之,事物如果失去其本质属性,即使它们在其他属性上仍与原事物相同,也不再是该事物。试想:亚里士多德幼年时期,其家庭发生重大变故,未能上学识字,当然更谈不上当哲学家,做现在归于其名下的那些事情,而另一个人如斯潘诺里斯,他不是来自亚里士多德父母的受精卵,但后来却做了现在归于亚氏名下的所有事情。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应把前一人识别为亚里士多德,把后一人叫做斯潘诺里斯。再设想这样一种非真实情形:有一种动物,它具有现实世界中老虎的一切外部特征——胎生、四肢着地、食肉等,但它有现实的鸟的内部结构。此时我们就应称之为鸟,而不能称之为虎:“不能完全根据虎的外表来给虎下定义,可能会有这样一个不同的物种,它具有虎的全部外显特征,但却有不同的内部结构。因此这个物种不是虎这个种而是其他物种。”[4]156
克氏本质主义与亚氏本质主义的根本差异,是前者利用新工具去分析事物的本质,特别是去分析个体本质,这种工具就是与模态逻辑可能世界语义学密切相关的可能世界理论。
从逻辑技术角度看,可能世界语义学通过“可能世界”来刻画“必然”、“可能”等模态词,以确定含这些算子的命题的真值,比如我们说“一个命题在现实世界必然为真,当且仅当该命题不仅在现实世界真,而且在所有可能世界真”。但从哲学角度看,可能世界的意义绝不像其逻辑意义那样简单。按照克里普克,可能世界并不是类似于现实世界的真实的物理实体,而只是现实世界的“反事实情形”,“可能世界是被规定的,而不是通过高倍望远镜发现的”[4]44;关于可能世界的关键思想是:它们不是有其自身独立存在方式的东西,不能脱离同现实世界的关系被发现,我们是从现实对象出发构造可能世界的:“我们可以指着一个对象,并问在它身上可能会发生什么。因此我们不是以世界为起点,然后再提出跨界同一性的标准问题;相反,我们以对象为起点,我们在现实世界不仅拥有这些对象,而且还能识别它们。于是我们就可以问,是否有某些事情对于这些对象而言是真的。”[4]53意思是,我们应从现实对象出发来思考可能世界,而不是相反。换言之,现实对象的属性的增减导致可能世界的产生,可能世界是认知主体对现实个体的现实属性进行“想象”的结果。
虽有上述差异,但两种本质主义有相同的出发点:它们都将本质属性理解为事物“必然”具有的属性。而对“必然性”做细致的层次辨析,正是可能世界理论发挥作用的地方。我认为,准确把握两种本质主义的关系需严格区分现实必然性和逻辑必然性,而把握该区分的关键在于获得下述认识:从逻辑的观点看,所有“想象”中无逻辑矛盾的世界都是可能世界;所有可能世界在逻辑上都是平权的,现实世界在可能世界系统中没有任何特殊地位,它只是可能世界之一,是其中一个实现了的世界。有两种情况需分别加以考虑。
首先,在某一可能世界,比如现实世界,无论个体还是类事物,“事物必然具有的属性”中的“必然”,是指现实世界中现实的必然,它是由事物的现实可能性决定的。按照辩证哲学对立统一规律,由内部存在的对立统一结构所决定,任一个体都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人们的认识相应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不断挖掘出的各种属性中,哪一个或哪一些是事物“必然”具有的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诉诸认知主体的社会实践,相对于客观事物的各种现实可能性,根据认知主体的社会实践目标来确定。例如对于一个医生来说,亚里士多德有多种现实可能性,逻辑学之父并不是他必然具有的,因为这个医生完全可以不关心除病理之外的其他属性。类事物本质的确定相对容易,但也要诉诸社会实践。内在结构固然可以构成类事物的共有属性,从而统摄该类事物,但认知主体在各自社会实践中未必都了解或关心内在结构,换言之,内在结构并非一类事物的仅有属性。类事物也包含多种发展的可能性,认知主体不一定非要通过内在结构才能认识该类事物。比如,普通人在识别水时就不需要像化学家那样,用原子结构作为水的区别性特征;即便同是化学家,他们也可能关心水的不同层次的结构。
其次,当在逻辑必然性层次跨可能世界考察事物本质时,所谓“必然”不再是现实的必然,而是逻辑的必然了。克氏所说本质是在所有一对象存在的可能世界中为该对象具有的属性。任一个体总要有一个起源,正从这个起源开始,个体进入不同的发展链条,其中每一个链条都构成一个可能世界。比如在现实世界,亚里士多德起源于其父母的精子和卵子合成的受精卵,其后成长为哲学家,创立了三段论,写了《形而上学》。但我们完全可以设想,这个受精卵经历了另一发展链条,也就是说,在另一个可能世界里,他没有创立过什么三段论,也没写过《形而上学》。可无论如何,亚氏没有起源都是不能设想的。于是,这个起源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就是必然的。显然,对于个体逻辑必然性的这种刻画,古典本质主义是无能为力的。不过,类事物本质是否可如克氏内在结构原理那般刻画,是需要另行研讨的课题。
基于上述,两种本质主义所谓的刻画必然属性,乃是本质所应涵摄的两个方面:亚氏本质主义立足现实世界,刻画现实世界类事物的现实必然性;克氏本质主义所刻画的“必然”则应被理解为跨可能世界的逻辑必然性。两者相辅相成,它们的结合可构成严整的分析型本质主义纲领。
三、个体本质主义的辩证解读
当前哲学界对于本质的研讨集中于个体本质。由于有可能世界为分析工具,使得克里普克能够超越古典本质主义,至少提供了一种刻画个体本质的方式。在我看来,克里普克关于个体的“起源的必然性原理”表明:对于个体来说,起源是决定个体的存在和保证个体自身同一性的条件。
首先,个体的起源是决定个体的存在。克氏所说的个体本质是跨可能世界的本质。从个体存在角度理解,它只是规定了个体的“有”,所谓起源只是规定了个体的存在,而并非在规定个体的具体属性。正是在决定个体存在这一点上,起源才成为个体的本质;除起源外,个体没有逻辑必然的属性。从这个角度讲,克氏本质主义刻画的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绝对本质。其次,个体的起源是保证个体的自身同一性的条件。除起源外,个体的自身同一性与任何属性无关,它独一无二、不可替代。从起源开始,个体包含无穷多发展可能性,无论哪一种可能性成为现实,都不会改变其自身同一性。仍以亚氏为例,不论他是否逻辑学之父,他都是亚里士多德。否则会得出荒谬结论。倘若有另一个体与该个体特征完全相同,也不能说明它们是同一个体,它们仍是不可相互替代的。设想另一世界有一个体具备现实的亚里士多德的所有属性,但只要有不同的起源,他们就是有各自自身同一性的不同个体。就个体而言,只有起源能够经受跨可能世界的逻辑必然性的检验:具有同一起源的个体是同一的,这个世界的亚里士多德和那个世界的亚里士多德在起源上同一,在现实世界他们是同一个东西。
然而,我们在具体实践中所关心的,并非个体上述本体论意义上的绝对本质,而是个体的现实必然性。而要刻画个体的现实必然性,则需诉诸“相对本质”概念。就理解这一概念而言,辩证哲学提供了独特视角。
辩证哲学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各种对立环节的统一,是事物自身内在的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的统一,这是事物运动、自我否定的内在源泉。它决定了我们所面对的任何对象都处于生生不息的变化之中。这是客观事物发展的“连续性”方面。我们能否在生生不息的演变中把握个体的现实必然性呢?列宁下述观点极富启发:“如果不把不间断的东西割断,不使活生生的东西简单化、粗糙化。不加以割裂,不使之僵化,那么我们就不能想象、表达、测量、描述运动。思维对运动的描述,总是粗糙化、僵化。”[5]事实上,也只有通过这种“僵化”的途径,我们才能探究运动变化的规律,把握变中之不变。正如黑格尔所言:“造成困难的永远是思维,因为思维把一个对象在实际里紧密联系的诸环节彼此区分开来。思维引起了由于吃了善恶之树的果子而来的堕落罪恶,但它又能医治这不幸。”[6]
有学者指出,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的这种“僵化”在现代逻辑中有着本质体现:一阶逻辑典型地表明了人类思维的一种割离本性。因为一阶逻辑将量词加诸对象域(个体域),而对象域由“原子个体”构成,我们将某种属性加于原子个体,就形成了原子命题,具体表现为个体具有某种性质以及个体之间具有某种关系。一阶逻辑只处理原子个体属性的有和无,不处理个体的内部关系与结构(当然包括内部对立统一的结构)[7]。因此,从一阶逻辑观点看,“由于人的思维的固有的割离性,我们就将变化着的个体看成是不动的‘点’。即不考虑个体的内部结构及其相互间的过渡,仅视之为一种离散的对象”[8]204。这种类似于几何学上的“几何点”和物理学上的“质点”的抽象形式的“个体”对象,被称为“逻辑点”。人类思想之所以需要这种离散性的逻辑点,其根源正在于辩证法所揭示的人类思维无法摆脱的“割离”性;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表明,这种割离本性植根于作为一种宏观生物的人类的社会实践:“演绎逻辑的这种特征(个体域由‘逻辑点’构成),体现了人类思维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基础在于人类实践的特性。人的思维是在实践中产生,并用于指导实践的。而人们的每一项实践活动,都有着确定的目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人们就必须把握事物的相对独立的确定的性质,必须由对世界的笼统的直觉,进展到对本来联结在一起的各个环节分别加以认识的抽象思维。这自然要求人们在认识事物时,首先要把面对的对象与其他对象分离开来,从逻辑上视之为‘原子对象’,这样才会进一步深刻地把握事物。……在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经典逻辑的过程中,将什么视为对象即‘逻辑点’是相对的。”[8]205-207
前已表明,我们实际面对的任何个体都处在“变化”之中,每一个体从其起源开始便进入此过程,其属性不断增减变易,并引起人的认识发生变化。但是,由于思维在认知实践中固有的割离性,作为实践主体的我们,会将变化着的个体看成是不动的逻辑点。这意味着个体的纵向发展被思维横向割断,连续的个体被“离散化”。个体自身虽变动不居,但思维的割离性使我们直接把握到的,是关于个体不动不变的“事实”,即在“同一时间、同一方面”上对“同一对象”的断定,这是亚里士多德关于(不)矛盾律的规定,它刻画出个体属性的有和无,即断定个体具有还是不具有某一属性。在社会实践中,我们正是借助这样的“事实”来相对地把握个体本质的。我们称这样把握的本质为“相对本质”。如前所示,所谓“相对”指的是相对于认知主体的观察视角,根据其社会实践目标来确定。因为思维对逻辑点的把握就是在实践当中进行的,而认知主体的观察视角取决于其实践目标。如前例,在医生视角下,逻辑学之父并非亚氏本质(现实必然具有的)属性,因为医生完全可能不关心除病理之外的其他属性,但对于稍有哲学基础的认知主体来说,它都是亚里士多德必然具有的。
实际上,克里普克本人对此也并非全无认识:“一个特定的事物是必然地具有某种性质还是偶然地具有这种性质,这取决于它被描述的方式。这一点可能与下述观点密切相关:我们是通过摹状词来指称各种特定事物的。”[4]40依其因果历史命名理论,专名是没有含义的严格指示词,在所有可能世界都指称同一个体;与专名相关的限定摹状词是非严格指示词,它们只能作为确定专名指称的手段,不能作为专名的同义词。摹状词的这种作用对于把握个体本质十分重要,而且在认知实践中也非常普遍。例如,我们在现实世界可借助“逻辑学之父”这个摹状词来识别亚里士多德,在另一可能世界则可借助“古希腊最残忍的杀手”来识别他。既然在思维过程中将什么视为对象是相对的,认知主体社会实践目标的不同也就决定了他借以识别指称的摹状词是不同的。而从可能世界观点看,只要遵循因果历史链条,在某一可能世界找到亚里士多德,就可确定其在该可能世界的存在,而不必在意是借助哪一个摹状词来确定的,因为亚里士多德既不必然是现实世界中逻辑学的创始人,也不必然是另一可能世界最残忍的杀手。有学者认为,克里普克因果历史理论的“一个重大历史贡献在于:它第一次明确揭示了语言和社会的关联,使社会因素在决定所指中起了重要作用”[9],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实践要素对于把握克里普克新本质主义学说的重要意义。
[1]亚里士多德全集:第1卷[M].苗力田,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2]R Marcus.Modal Logic,Modal Semantics and Their Application.Contemporary Philosophy:A new survey,V.1[C].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81:285.
[3]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M].苗力田,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4]S Kripke.Naming and Necessity[M].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 1980.
[5]列宁. 列宁全集:第3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285.
[6]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290.
[7]张建军. 逻辑悖论研究引论[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75.
[8]张建军. 科学的难题——悖论[M]. 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9]陈波. 逻辑哲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21.
[责任编辑张家鹿]
B505
A
1000-2359(2011)01-0001-05
刘叶涛(1977-),男,河北沧州人,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大学现代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辩证哲学、分析哲学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可能世界视域下的意义与真理理论研究”(08JC720014)
2010-10-16
——对《物理学》8.6(259b1- 20)的一种解读
——“自由落体”教学中的物理学史辨
——《古希腊文化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一课的教学思考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