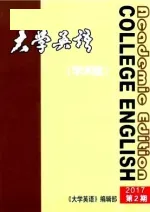生命之花可否独自静静绽放:比较父权社会下苔丝狄蒙娜与尤三姐的悲剧
张海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100191)
引 言
《奥赛罗》是莎翁笔下经典的四大悲剧之一,悲剧点众多。女主人公苔丝狄蒙娜虽洁身自好,却因爱人猜忌含冤而死的命运为其中的悲剧点之一。对于造成这场悲剧的原因可谓众说纷纭。总结国内学者主要研究成果,大致可归结为奥赛罗嫉妒的性格悲剧、奥赛罗摩尔人的种族悲剧以及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三种。《红楼梦》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其中所涉及人物数不胜数,个中人物多以悲剧收场,具体原因亦迥然。尤三姐作为其中金陵十二钗副册中的“情豪”,在决心嫁与其愿生死相许的柳湘莲之前,可谓风流至极。对于其自杀而亡的悲剧原因,国内学者研究多集结于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之缘故上。本文作者通过女权主义者的视角,在文本细读之后,创新性地提出二者之所以悲剧而亡的三点原因:父权社会通过两种对妇女物化的方式对女性进行歧视、压迫;女性本身虽经叛逆阶段,但终究向父权社会屈服;两位男性主人公(奥赛罗与柳湘莲)受父权社会传统性别角色观念——本文主要探讨中西贞操观念——之毒害,使其自身成为父权的代言人,直接毁灭其与女主人公的人生幸福。在这样两场悲剧中,其实女人和男人都是父权社会的牺牲品,因社会上根深蒂固的贞操观念,而丧失了她们及他们本最为珍视的恋人及幸福。
1.“钱袋”与“粉头”——女人是什么?
易普生在其《玩偶之家》中借诺拉的口,指出了女人的身份,婚前的女人是父亲的“玩偶女儿”,出嫁的女人是丈夫的“玩偶老婆”(易普生201)。而在中国的传统中,亦有女性要“三从”即:“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说法。在传统的父权社会里,女性是他者(De Beauvoir 273),是“客体”(330)。女性的这种形象在苔丝狄蒙娜及尤三姐身上可谓具有惊人的一致性。首先本文探究的是二者在经济上为何沦为附庸。
二者在物质上都可谓一贫如洗,苔丝狄蒙娜婚前住在“她父亲的家”(莎士比亚450)里,婚后跟随奥赛罗住在军营里,苔丝狄蒙娜的生存依靠父亲及丈夫,而不是自力更生。毋庸置疑,一个一无所有、连自己都无法供养的女人如何奢谈主体?而尤三姐似乎更为不幸,她待字闺中之时,便已无父,而母亲又“年高喜睡”(57),她及母亲、姐姐“素日全靠贾珍周济”(75),在尤二姐嫁与贾琏之后,她及母亲则住进了姐姐的新房。由此可见,她亦一直以来是由父权社会里的男人们周济度日的。自然,此种“窘境”何谈自我呢?而正因为两个女人物质上一无所有、全靠男人们,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她们沦为男人们的财产,使自己沦为了物。普兰斯A.莫罗在《社会疾病与婚姻》一书中,将女人分为了两类:一种受父权要求,需保持“贞洁”;第二种需要为男人提供“性满足”(转引自王泉 56)。这正如苔丝狄蒙娜及尤三姐的窘境。一方面,男人视女人为玩偶,男人们可以自己“享用”,如尤三姐的身份,贾珍、贾琏将姊妹二人当成“粉头来取乐”(83)(“粉头”即妓女),即男人利用女人的“性”满足自己的性欲;而另一方面,女人则成为了男人们的“钱袋”,男人们亦可将其“交换”出去,如苔丝狄蒙娜,通过守住苔丝狄蒙娜的贞洁,而保证物的高价值,从而将其嫁与“国里有才有势的俊秀子弟”(457)而获得更多的财产及声望。本文将用以下两段分别具体指出苔丝狄蒙娜及尤三姐是如何被物化的。
在《女性主义解读<奥赛罗>中伊阿古的男权话语》中,朱肖一精辟地指出男性伊阿古将“女人身体视为财产”(45),这主要体现为两类:伊阿古将“女性物化为父亲的财产”;“物化为丈夫的财产”。本文认为,不仅仅是伊阿古将苔丝狄蒙娜物化,文中出现的另一主要男性人物——苔丝狄蒙娜之父勃拉班修亦与之不谋而合。当勃拉班修受到罗德利哥挑唆、找到奥赛罗时,他说“杀死他,这贼(thief)!”(457);当奥赛罗问其为何动武时,他亦以“啊,你这恶贼”起句;当公爵询问勃拉班修为何忧虑时,他回答,他女儿被人“拐走”(461),而“拐走”在莎翁的原文中为stol’n(stolen);当奥赛罗出征在即,关于苔丝狄蒙娜住在何处的问题,勃拉班修的回答为“我不愿意收留她”(467),莎翁原文为“I’ll not have it so.”很显然,他像伊阿古一样,将自己的女儿视为其私有财产,如“钱袋”(450)之类,“thief”,“stol’n” ,“have”及无生命物体代词“it”非常明显地表明了勃拉班修通过言语表达在他意识之中是如何将其女儿物化的。他要把他的女儿嫁给“国里有财有势的俊秀子弟”(457)。玛格丽特·金说,“父亲通过女儿可以横向地与有用的朋友以及纵向地与后代子孙联系在一起”(41)。也就是说通过将女儿嫁到有钱有势的家族,他可以光耀自己的门楣。金说,“妇女是确立或保持娘家在婆家中社会影响力的重要途径”(68)。总之,在父亲勃拉班修那里,女儿只是他的钱袋,是他进一步攀龙附凤的招数而已。另外,另一主要男性人物凯西奥在对待比恩卡的态度上亦可说明《奥赛罗》中女人被物化的观念。凯西奥——奥赛罗的副将,当伊阿古说起比恩卡认为他会跟她结婚时,他如是说,“一个卖淫妇?”(538),此处译者将凯西奥将自己的身份定位“A customer”转译成了凯西奥认为比恩卡的角色,不管何种翻译,在凯西奥心中,他和比恩卡只是妓与客这种赤裸裸的买卖关系,做的是买卖“性”的交易。
而在《红楼梦》中,因贾敬去世,尤老娘携两个未嫁小女来至宁府看家。当贾蓉“听见两个姨娘来了,便和贾珍一笑”(55),读过后事,我们知道此笑隐含那种“聚麀之诮”(70)(即父子共妇的窘况)的低俗。后来贾蓉常“乘空寻小姨厮混”(60),为了能同两个姨娘厮混,避开其父贾珍,竟撺掇贾琏娶尤二姐,他想将来可趁贾琏不在家之时,趁机去胡作非为。而贾珍虽然有孝在身,却趁贾琏不在家,假借“探望”之名,与“三姐挨肩擦脸,百般轻薄起来”(81)。而贾琏假借为尤三姐向贾珍说亲之事,到尤三姐屋内,让尤三姐陪他喝酒。此三人行径全是妓院嫖妓的路数,可谓占尽了受其庇护的女人的便宜。
总之,尽管苔丝狄蒙娜及尤三姐被物化的方式不同,前者在于以其贞洁的人格被男权社会的人们用来交换到更为高价的商品,后者以其身体供男人享乐,但究其本质我们不难看出,父权社会里女人是如何受到男人的歧视与压迫的。可现在的人们之所以还津津乐道于苔丝狄蒙娜及尤三姐二人,远非是其物化性为其带来的殊荣,而在于其对父权社会的反抗上。这一点本文将在紧接着的下一部分予以阐述。
2.“我的夫主”与“素日可心如意的人”——女人一生为什么?
波伏娃认为,当一个女孩进入青春期,她将以“等待”的方式度过;尽管多多少少有些“掩饰”,但是事实上“她在等待一个男人的出现”(327)。为了从“父母的家里逃脱,脱离母亲的掌控获得自由”,她将以“消极、顺从”的方式,把自己交至“一个新主手中”(328)。然而,虽然结婚是父权社会中女人的必然归宿,可是年轻女孩在由从主体变为“客体”(object)、自我转向“他者”(other)、主要者(the essential)过渡到次要者(the inessential)的过程中,她内心会滋生一种矛盾,这种矛盾存在于“其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所处的状态”及“其作为一个女性这种职业”之间(334)。在“年轻女孩”这一部分,波伏娃鞭辟入里地描述了年轻女孩在实现这种痛苦转变时的种种心情表征。本文将结合苔丝狄蒙娜及尤三姐的不同情况,分析二者颇为复杂的内心挣扎,以及在此阶段她们所做出的对父权社会颇为大快人心的反抗。
在父亲的印象里,苔丝狄蒙娜是“一个素来胆小的女孩”,她生性“幽娴贞静”,哪怕是心里略起涟漪,她都会“满脸羞愧”(462-3)。如果见到奥赛罗这样一个又黑又丑的摩尔人,她“瞧着都感到害怕”,如何能与之相恋呢?而伊阿古亦说,“当她[苔丝狄蒙娜]好像对您[奥赛罗]的容貌战栗畏惧的时候,她的心里却在热烈地爱着它”(513)。而苔丝狄蒙娜本人说,她“先认识他[奥赛罗]那颗心,然后认识他那奇伟的仪表;我已经把我的灵魂和命运一起呈献给他了”(468)。由此可以得出,不管是对苔丝狄蒙娜本人还是其身边的人来说,苔丝狄蒙娜确实最先爱上的是摩尔人的心灵,而后才将其世俗化,爱他的外表,愿意在隐瞒其父亲的情况下与之进行肉体的结合。而当她刚与他相识,奥赛罗这样一个勇猛的男人是很可能吓到她的。从这正如波伏娃所说,男人使她“着迷”,亦使她“惧怕”(345)。“考虑到自己对他所抱有的矛盾态度,她会将他与她所惧怕的男性角色抽离,而虔诚地崇拜他的神圣性。”通常她爱慕的是一个享有“社交或博学盛誉”的男人,而这男人通常外表并不那么“令人着迷”(345)。据奥赛罗本人称,他“生得黑丑,缺少绅士们温柔风雅的谈吐”(515),他“年纪老了点儿”。这样一个奥赛罗是如何让一个“素来胆小的女孩”不惜与其父相对抗而与之相爱的呢?在叙述两人的恋爱经过时,奥赛罗说“她为了我所经历的种种患难而爱我”(465),换言之,奥赛罗丰富的人生阅历使其得到苔丝狄蒙娜的垂青。可以说少女的苔丝狄蒙娜在选择奥赛罗作为爱慕对象的时候,自己内心少不了挣扎。莎翁的戏剧没有告诉我们看客,苔丝狄蒙娜到底用了多长时间去克服内心对男人的恐惧,而毅然选择与初恋相结合,从而完成由爱到性的完美过渡。而波伏娃则告诉我们“两年后我们发现那个曾经古怪、叛逆的孩子已经沉静下来,充分地准备着接受一个女人应有的一生”(361)。
而尤三姐内心挣扎的情形则另有隐情,其表征与苔丝狄蒙娜的隐忍克制则明显不同,她在性上放荡不羁,不拘小节。这主要表现在三点:第一,其与众不同的不羁之笑,其粗俗、露骨的性挑逗语言;第二,嘲讽男人;第三,其喝酒的方式。经过文本细读,我们可看出尤三姐的性放纵并非与生俱来,而是有个过程的。开始对于贾蓉的骚扰,她“上来撕嘴”(57)而尤二姐此时却红了脸;后来面对贾琏的“百般撩拨,眉目传情”,她亦“淡淡相对”,尤二姐却“十分有意”(70)。可见此时的尤三姐在性方面并未理会,当然她并非不懂,此时的她可能情形如苔丝狄蒙娜,心里惦记着遥远的柳湘莲,对于远离性且有爱慕对象是高兴的。可后来当贾珍心怀歹意到贾琏新房,她姐姐委婉要求母亲回避,将自己置于尴尬境地时,不得不面对性的尤三姐“大方”接受了,和贾珍“挨肩擦脸,百般轻薄起来”(81)。而最后当贾琏到屋内将其与贾珍吃喝玩乐的情景抓个正着时,她不像满口仁义道德的贾珍“羞的无话”(82),而是“指贾琏笑道”(82),赤裸裸地指出贾珍和贾琏的企图,对自己用“粉头”(83)的字眼,而咒骂贾珍、贾琏为怀着“牛黄狗宝”(“牛黄狗宝”即坏心肠)(83)之人。接着她自斟自酌起来,举动竟泼辣至“搂着贾琏的脖子来就灌”,并挑逗“咱们来亲香亲香”(83)。最令人大快人心地是,她叫人叫尤二姐来,甚至说出“‘便宜不过当家’,他们是弟兄。咱们是姊妹,又不是外人”(83-84)的大胆之语。末了,她“拿他兄弟二人嘲笑取乐,竟真是他嫖了男人,并非男人淫了他”(84)。在性事上她一个小女子反倒“转败为胜”。可我们通过细读文本可发现她对贾珍、贾琏及贾蓉“泼声厉言大骂”(84),将新做的衣裳“用剪刀剪碎,撕一条,骂一句”(85)等行为,她并非享受于这种生活。而她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正如自己所说,“金玉一般的人,白交这两个现实宝玷污了去,也算无能[……]趁如今我不拿他们取乐作践准折,那到时,白落个臭名,后悔不及”(85)。由此可见,尤三姐并未生性淫荡,心里状态被种种外因激化了而已。波伏娃认为,年轻女孩扮演“反常性格”实属其抵触男人的一种举动(348),尤三姐饮酒便是说明。而“嘲讽之笑”及“激烈言辞”乃是其抵制性意象的举动(349-50)。另外通过“戏耍自己的身体,嘲笑男人,嘲弄爱情共同构成了一种否认性的方式”(349)。总之,尤三姐的种种似乎显得极为极端的举动都向读者透漏出了一个处于青春期的女子内心对性的鄙薄与仇视。结果,尤三姐的叛逆期一过,亦开始考虑婚姻,“终身大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儿戏”(88)。
反观上述叙述,不管年轻女孩曾如何叛逆,大多数情况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向婚姻寻求庇护,从而完成从女孩到女性这一职业的过渡。经历了这样一种内心挣扎的女孩,可以说更懂得真爱了,只是既然她们将全部筹码都压在男人身上,她们能否快乐幸福就只能取决于其看重的男性是否与其有满意的回应了。这两场悲剧的原因即在于此,两位男主人公奥赛罗及柳湘莲因其自身受父权思想毒害之深,已无力回应此种深爱,终错失幸福。本文将利用以下一部分仔细阐述其悲剧性。
3.“娼妇”与“剩忘八”——对于她们倾心的男人,她们什么最重要?
如果我们说两幕悲剧的悲剧性在于女主人公的惨死,这并不难理解,也勿需多做解释。但事实上,两幕悲剧的悲剧亮点还在于两位男主人公为爱而殉情或是了尘缘。由于妻子的贞洁,奥赛罗在自责中自杀而死。见证尤三姐刚烈而死的柳湘莲亦因敬佩与懊悔而削发为僧。本文的第三部分着重在于论述懂爱的男主人公们何以跟他们的女人一样成为爱情的牺牲品。
在论述原因之前,有一点需要澄清。在本文的讨论中,我们批判的是将女性置于他者地位的传统父权社会。按照常理来讲,两位男主人公应该为父权社会的代表而绝不应该是悲剧的集结点。然而本文认为,两位男主人公其实是传统父权社会里的他者。首先我们来看奥赛罗的身份。从伊阿古及罗德利哥的口中,一个词反复出现,那就是摩尔人(Moor)奥赛罗。在伊阿古的词汇里,这个摩尔人奥赛罗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他的黑,“黑将军”(Moorship)(448)、(black Othello)(488)、老黑羊(old black ram)(450)、“黑马”(Barbary horse)等词都是他的御用词汇。勃拉班修曾将奥赛罗描述成 “丑恶的黑鬼”(sooty)(458)。而奥赛罗自己也说过自己的 “黑丑”(black)。故事中其他人亦不同频次地提到过奥赛罗的黑。无疑,奥赛罗的“黑”是其与欧洲同辈人的“白”“最突出的一点区别”(“Othello”)。而透过黑白之争,反映出来的却是当时的人们对于摩尔人奥赛罗的种族歧视。伊阿古甚至当面对奥赛罗说,如果苔丝狄蒙娜与“跟她同国族、同肤色、同阶级的人”结婚,那会是“天作之合”(514)。换言之,身为摩尔人的奥赛罗与苔丝狄蒙娜不同国族、不同肤色、不同阶级。所以在欧洲以白人为主的社会中,奥赛罗因为自己的肤色和种族成为了边缘人。而《红楼梦》里的柳湘莲比起战功卓著的奥赛罗来说,似乎更逊一筹。《红楼梦》中关于柳湘莲故事的并不多,而主要是以柳湘莲戏弄薛蟠为主。刚一出场,柳湘莲的形象便是“最会串戏,且转的都是生旦风月戏文”(卷五106-07)。容貌方面,“因他年纪又轻,生得又美,不知他身份的人,却误认作优伶一类”(108)。社会地位方面,虽为“世家子弟”,却“父母早丧”(107),孤苦无依。总而言之,两幕悲剧中的男主人公并非传统男权社会的代言人,而是社会里的又一他者。
陈述完这一点,我们不禁生疑:同是社会的他者,为什么女人钟情的男人没有给她们要的幸福,而是以不同的方式亲手把幸福毁了呢?本文认为,男主人公虽是社会的他者,但他们都认同了传统父权社会中对女性贞操的苛求。
洛伊丝·泰森总结道,女性传统的性别角色定义为“贞洁”的天使,而坏女孩有多种,其中一种即为“荡妇”(88)。西方对于贞洁的叙述可追溯至圣经。首先圣母玛利亚以处女之身,孕育了耶稣,人们对于圣母玛利亚的崇拜不得不说是对其贞洁的崇拜。玛格丽特·金说,“圣母玛利亚的崇拜随着欧洲的成长而发展”,“对慈爱的母亲和无忧无虑的孩子这一和谐画面频繁和近乎痴迷的描绘,与生机勃勃的文艺复兴文化的诞生正相温和”(2)。可是文艺复兴的女性并不是圣母玛利亚的角色,金继续论述道,“每个女人都是夏娃的女儿,她原始的痛苦甚至压倒恩典的童贞”(3)。对于父亲的家族来说,女儿的贞洁是“父亲的荣誉”(38)。对于丈夫的家族来说,吉多·鲁格埃罗指出,“它[一个女人的性荣誉]与一种更为复杂的荣誉计算紧密相连,其中既涉及家族的荣誉,也涉及支配该家族的男人的荣誉”(转引自金 38)。所以,金直截了当地宣称,“守护贞洁是文艺复兴时期女儿们的头等大事”(38)。
在文艺复兴时期,女人一旦失去贞洁,惩罚便随之而来。首先,在身份上,女人由妇女变为“娼妇”。在金的著作中,她列举了几种划分女性的方式,正如她精辟地指出,不管是哪一种,“与依据妇女对男人的经济和性依赖来划分妇女的方法并无二致”(30-31)。其次,失去贞洁的女性下场通常都比较悲惨。在圣经旧约《申命记》一书第22章中说到,如果女人没有贞洁,“本城的人要用石头将她打死”,刑罚可谓极重。
文本细读后,翻译版本的《奥赛罗》涉及到贞洁及其反义词等类似的词汇竟多达30多处,出自奥赛罗口中的竟有十多次,他害怕自己带“绿头巾”(516)(536),痛恨当一个“王八”(541)。 他害怕就像伊阿古说的,“谁偷去了我的荣誉”(511)。当他对苔丝狄蒙娜妻子这个只为他提供“性服务”的称呼产生质疑时,他脑子里盘旋的就是“淫妇”(519)。在这里,妻子的真情是可以忽略的,重要的是男人不应因为女人受辱。由于奥赛罗认同了文艺复兴时期女性的童贞是男人荣誉象征的观念,他最终亲手掐死了自己的妻子。简言之,贞操是女人的荣誉,女人的贞操是男人的荣誉,而女人的人和心却什么也不是。
在中国,贞操的观念亦早已有之,最早可追溯到春秋中后期。“从一而终”的贞节观念最早出现于儒家经典中(许莹莹186)。到清朝时,“沿袭明代的旌表制度”(188)。而且,清朝对旌表的节妇烈女作了更加全面和具体的规定。“《大清会典》规定:自三十岁以前守寡,至五十岁不改节者或未及五十岁身故,其守节已满十五年的,称为节妇;殉家室之难或拒奸致死者,称为烈妇、烈女;许嫁未婚,夫死闻讯自尽或哭往夫家守节者,称贞女”(189)。
在导致尤三姐自杀的原因正是由于柳湘莲嫌弃其“不干净”。聪慧的尤三姐因忍不得柳湘莲对其的嫌弃,选择刚烈地自尽而死。柳湘莲虽是男权社会中、父权团体中的他者,但他却认同了男权社会中对女性的压迫,竟逼死了可能和自己相伴一生的爱人,而他终究又是这个男权社会中的异类,不忍爱人离去的他只能一剑斩青丝。
综上所述,正是“贞操”二字在男女主人公共同奔向幸福的道路上让彼此隔膜,最终竟造成阴阳两隔,而无缘今生相守。
结束语
田俊武、李硕两位老师曾在其论文《浅论莎士比亚奥赛罗的婚姻制度与妇女地位问题》中指出之所以造成悲剧的原因在于苔丝狄蒙娜对于奥赛罗 “过分绝对的无条件的顺从和忠诚最终酿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性灾难”(77)。于此,我赞同的理由是,似乎直到最后苔丝狄蒙娜依然对奥赛罗一片爱意,毫无悔意;可问题是,如果婚后她不顺从丈夫,本文作者并不看好《奥赛罗》会有别样的结局,因为伊阿古利用苔丝狄蒙娜引起奥赛罗怀疑的手段,正是她婚前对自由婚姻的大胆追求,如果婚后她依然如此,难保无需伊阿古挑唆,奥赛罗自己已亦疑心的结局。本文认为勇敢去爱的苔丝狄蒙娜既有年轻女孩处于叛逆期时的勇敢,亦有父权社会所无法理解的对爱的坚守。对于尤三姐亦然。当社会还是那样一个社会,当不管是男人和女人都还是那样的观念时,女人无论对爱如何坚守都是难以成就其一片爱意的。笔者认为,当务之急,社会人们应该转变观念,给女人一个自由,让其生命之花静静开放;给爱一个自由,让其自由地呼吸;给爱人们一个自由,让其可以勇敢地去爱。
De Beauvoir,S.(1953-1972).The Second Sex[M].Trans.and ed.H.M.Parshley.London:Jonathan Cape.
Tyson,L.(1999).Critical Theory Today:A User-friendly Guide[M].New York and London:Garland Publishing,Inc.
Wang,Q.(2006).A Lacanian Reading of Toni Morrison’s Three Novels[D].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
“Othello.” 13 January,2010
曹雪芹,高鹗(2006).图注红楼梦 [M].胡天复、于天池主编.第七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胡天复,于天池主编.图注红楼梦 [M].第五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金,玛格丽特(2008).文艺复兴时期的妇女 [M].刘耀春,杨美艳译.北京:东方文化出版社。
莎士比亚(2001).莎士比亚八大名剧<上>[M].英语学习大书虫研究室译.奎屯:伊犁人民出版社。
田俊武,李硕(2006).浅论莎士比亚奥赛罗的婚姻制度与妇女地位问 [J].戏剧文学。
许莹莹(2010).谈中国古代妇女贞节观的形成与变迁 [J].学理论。
易普生(1995).易普生文集 [M].潘家洵译.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朱肖一(2009).女性主义解读《奥赛罗》中伊阿古的男权话语[J].国外戏剧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