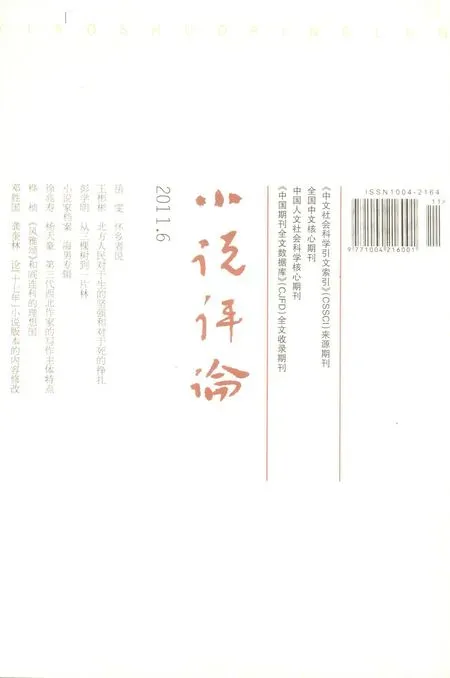女性的妖娆与华丽蜕变——海男长篇小说中的女性成长叙事
作为当代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海男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以其极具先锋性的诗歌为女性正名,90年代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更是以细腻的笔触抒写了女性这一群体的生存境遇。对女性成长的关注,对女性命运的思考是海男长篇小说一以贯之的主题。作为“一位为着女性而写作的作家”①,海男以敏锐的视角发掘出女性生存的真实处境,用诗性的语言为女性的成长做传,记录了女性在漫长的历史暗夜中所遭遇的灵与肉的困顿与冲突,并用喑哑的声音为在男权社会中进行痛苦挣扎与突围的女性呼号。海男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女性千娇百媚的妖娆图,在经历了肉身与灵魂的炼狱后,女性会实现一场华美的蜕变,要么完成自我的主体建构最终走向自由之途,要么在沉重的肉身中以死亡的方式体验灵魂的升华。
一
莫迪凯·马科斯(Mordecai Marcus)在《什么是成长小说?》中给成长小说下了一个定义:成长小说展示的是成长主人公经历了一次重大改变,要么是在对世界或他自身的认知上,要么是在性格上,或者兼而有之,这种转变会对主人公产生永久性的影响,使他摆脱童真,并最终不得不面对一个真实而复杂的成人世界。②从这一定义来看,海男的大部分长篇小说都涉及女性的成长,而且在女性的成长中往往又伴随许多偶然性事件,这些偶然性事件对主人公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虽然成长小说的“主人公主要是在13-20多岁之间的青少年,但这不是绝对的标准”③,普桑子出场时已是三十岁,但从小说文本来看,《蝴蝶是怎样变成标本的》以隐喻的方式展现了普桑子作为一个女性痛苦的成长历程。十年前偶然经历的一场鼠疫给普桑子带来了无法磨灭的记忆和对死亡的恐惧,以致十年来普桑子惶惶不可终日,成为一个典型的精神病患者:外表羸弱、面无表情、眼神空洞、身体颤栗、彻夜失眠……当普桑子意识到“我已经三十岁,我的青春被房间里那些蝴蝶标本耗尽”后,为走出人生的困境,普桑子先后向三个男人求助——郝仁、王品、陶章。郝仁医生让普桑子体验到了性,为逃避性同时也为了证明对初恋爱人耿木秋的忠实,她选择出走。出走后普桑子在战乱中邂逅酷似耿木秋的王品并在其身上寄托初恋的情感,但和郝仁一夜情后的怀孕事实让她放弃了王品。普桑子的生活不断地被偶然事件所篡改。就在普桑子决定给腹中孩子一个完整的家而充满希冀奔向郝仁医生时,他却已经结婚了。普桑子在母亲角色中体验到了成长的蜕变,女儿的出生让她感悟到生活的责任与重担,挂满蝴蝶标本的房间从此被锁了起来。长驻旅馆的王品怀着一颗爱情的心追逐普桑子,却又拒绝不了妓女的诱惑,让燃起爱情热望的普桑子再次选择出走,奔向断腿的陶章。普桑子同情战争给陶章带来的苦难,以悲悯的心态与他同居,却发现他已有其他女人。夏天的那场暴雨导致陶章意外身亡,同时结束了普桑子对现实的逃避。普桑子别无选择,再次归家。耿木秋的虚妄与飘渺,郝仁的善良与被奴役,王品的动荡与不贞,陶章的软弱与无奈,让普桑子深刻意识到,自己曾寄予厚望的男人都不能拯救她,女人只有靠自我才能获得拯救。目睹了一次次死亡后,普桑子由对死亡的恐惧转而发展到淡然面对,并在蝴蝶标本中实现了灵魂的自我拯救与涅槃。普桑子的成长进程很缓慢,每一步都离不开男性,男性是她一次次出走与回归的最终动因。男性让她体验到了性,体验到肉身的诱惑,同时也将她引向心智的成熟。普桑子的成长与“诱惑—出走—迷惘—顿悟—失去天真—认识人生和自我”这一成长小说的典型情节模式相吻合。也是在对男性的一次次失望与洞悉后,普桑子才成长为一个有着悲悯情怀、能够坦然面对死亡的女人,在飞翔的蝴蝶中走向心灵的自由。
普桑子的成长笼罩在1930年代战争的枪声中,但战争只是作为一种远景存在着,小说更注重的是其精神的蜕变。与普桑子成长背景截然不同,苏修(《亲爱的身体蒙难记》)的成长跨越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期三十多年的中国社会现实。15岁少女苏修带着对铁轨的好奇,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奔赴铁轨,却偶然见证了一场人世间最肮脏、最恶心的罪恶: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最原始的肉体侵犯——强奸。在强奸事件发生的那一刹那,苏修失去了言说的力量,失去面对人性恶的勇气,选择以晕厥来逃避强奸事件的在场。苏修也因此与受害者繁小桃的人生纠缠不休。这一事件给苏修日后的成长埋下深重的心理隐患,以致苏修在往后很长一段人生中都无法走出这一事件带来的阴影。
女人的成长始终离不开婚姻。苏修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一家汽修厂当副厂长赵师容的秘书。在还没来得及细细体味爱情时,为摆脱副厂长的纠缠,苏修与大学同学冯明闪电结婚。表姐姚梅在苏修内心里一直是引导她成长并走向自由的力量,表姐果断地结束婚姻促使苏修也对自己的无爱婚姻加以反省并选择离婚。这场短暂的婚姻并未促使苏修完成灵魂的蜕变,苏修的心智仍像懵懂无知的少女一样,对于男人的诱惑还缺乏正确的判断,与郑旷远恋爱的同时,浑浑噩噩中做了赵师容的情人并在八十年代末期与赵缔结了婚姻。婚后的苏修仍然像活在虚幻之中的天使,灵魂仍未扎根到坚实的大地。在发觉丈夫迷恋女色的本性未改,背着她与年轻女秘书偷情后,苏修毅然选择离婚。苏修就是在目睹人世间种种罪恶与人性的龌龊中亲历自己的成长。离婚后苏修在写作中找到了灵魂的寄托之所,在时间的游走间顿悟人生的真谛,时间是可以改变一切的,也是可以抚慰一切创伤与疼痛的。经历了父亲、前夫、樊晓萍、肖等人的死亡之后,苏修一次次梦回铁轨旁,在时间的流逝中终于迎来了成长,并以宁静的心态感悟死亡。这是一次延宕了多年的成长蜕变。
多年以后,受害者繁小桃以灵魂拷问者的姿态质问苏修当时为什么没有喊出来制止那场困扰繁小桃一生的历史噩梦,并四处奔波寻找那个男人以致身心疲惫。也是时间治愈了繁,让她再次躺在事发地点时顿悟到过去的耻辱已随风而逝,终于放下了灵魂的重负。苏修作为繁小桃的同性姐妹,一直为其恪守那个秘密,并不自觉地扮演了繁小桃灵魂疗伤者的角色。男性给女性带来的肉体灾难和身体耻辱,最终是在时间流逝中得以遗忘。
18岁,一般被视作青少年步入成人的年龄分水岭。但从心智发育来看,18岁还远未达到社会对成人心理承受能力的要求标准,还很难抵御与承担社会现实带来的冲击。在美国成长小说中一个常见的观念是罪恶与生俱来或曰“原罪”,成长主人公在走向成人的途中总有一天会发现世界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美好,而是到处充满了令人恶心的罪恶。发现罪恶并不是成长的目的,成长主人公必须学会如何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并保持自我的独立,才能够算是真正成人。海男在小说塑造了一系列十七八岁的少女形象,并向读者展示了女性成长与蜕变的艰难。
18岁的罗修(《县城》)在20世纪80年代的小县城里引领时尚,第三个穿上橘红色的喇叭裤,喜欢听邓丽君的歌曲,与货车司机李路恋爱后发生肉欲关系并怀了孕。为摆脱怀孕带来的不自由,罗修悄然来到一个小镇堕了胎。为拒绝沦为肉欲的奴隶,同时也是为了与世俗抗争,罗修放弃与李路结婚。罗修与咖啡商人、吹口琴的男人的交往使她意识到“男人可以制造快乐之谜,他们在旅途中不断地培植快乐,也可以不断地遗忘身后之事,所以,男人在前进,女人却在后退”,“女人是在不断后退中前进的”④。罗修在世人异样的眼光中坚持单身生活,并找到写作作为确证自己存在的方式。弟弟罗敏吸毒坠楼身亡后,罗修顿悟到人生充满了欲望,正是人对欲望的无止境追求给人带来了生存的困扰。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期,罗修为保持个人那点微小的自由,在成长的过程中一次次地从男人身边逃离,当她意识到自己和李路之间的真爱后,二人准备结婚却因李路的意外死亡而告终。从18岁到30多岁,罗修在生理上虽早已成为成人,但心智却是在困惑与彷徨中一步步迈向成熟。罗修的成长有得有失,父亲的死亡、李路的车祸、弟弟罗敏的坠楼让罗修更为坚韧,选择以坚强的方式应对生活中的苦难。
出走是成长小说最基本的结构要素之一,出走意味着选择,人只有选择并付诸行动才会在路上有所发现,有所感悟。普桑子、苏修、罗修等女性在面临人生困境时,都会不约而同地选择出走。出走即行动,意味着在路上,意味着出发。
几乎所有的女人在否定生活时所选择的就是拎着箱子走。走,似乎也是唯一的,在那一瞬间里。否定已经是另一条道路和箱子中被她的右手或左手轮流拎起来的、在边缘地带展开的、交织在她幻觉中的、另一种更有诱惑力的并将她现有生活否定的热情之火。出发,是她在否定之后唯一选择的操纵、塔楼和墙壁发出的,不是在梦中召唤她,而是在被施了魔法的嘴唇上的一个词汇。她总是因为找到了词汇而找到了一种方式,所以,她出发了。⑤
出走或曰出发,将成长主人公带入到一个新的、陌生的人生环境,在空间的置换中,女性摆脱了旧有的世界,与过去的存在状态决裂,在与新环境、新世界的冲突、碰撞中,女性不断审视自我,在对自我的批判与提升中实现人生的顿悟。出走的结果,可能是踏上新的人生征程,开辟新的人生境界,也有可能是再次回归,如普桑子在逃离男性时一次次离开自己居住的城市,但最后又一次次地回来。“城”在普桑子的生活中,已然成为一种人生的隐喻,普桑子在“出城-入城”的人生胶着中,完成了对自由的追求。
与出发相对,死亡也是促成主人公成长的又一有力途径。“在经典的成长教育小说中,死亡永远都是一个情节事件,它所带来的往往是一个情节的戏剧性冲突或高潮。”⑥在海男笔下,女性的成长都伴随着对死亡的见证。普桑子在对鼠疫的回忆中一直伴有河面漂浮而过的肚子鼓胀的尸体,雯璐男友、刘水、父亲、陶章的死亡改变了普桑子对待生命的态度,在见证死亡的过程中普桑子悟到此在的意义。罗修在父亲的死亡中刹那间悲哀地明白:“所有猛然间向我们的肉身袭来的幸福的证据、悲哀的颤栗,灾难的震撼,都是贯穿在我们生命中难以逃离的时间之镜,它像一面镜子在照着我们的卑微和我们佯装在脸上的自尊。”⑦落红在和父亲一起搀扶着奄奄一息的母亲奔赴父母亲年轻时约会的小山岗时,感受着母亲生命气息一丝丝的流逝,在母亲对爱情的坚守与缅怀中,落红看透了父亲的懦弱与虚伪。母亲死后,落红经过一番灵魂的挣扎后,决定拎着箱子离开父亲奔赴新的人生旅程。死亡意味着生命的结束,但对于成长主人公来说,死亡却意味着新生。
二
特里·伊格尔顿曾经深刻意识到:“我们作为‘文化’生物的程度并不高于作为‘自然’生物的程度,而文化的存在必须借助于我们的自然,这就是说必须借助于我们所具有的身体的种类和它们所属的世界的种类。”⑧身体是自我的边界,是自我在把握自身与外在世界关系时无法回避的首要问题。女性的成长,往往离不开对肉身的体悟,对肉身的感悟与超越是女性实现自我主体建构的必经过程。从肉身这一角度来讲,海男深谙女性写作的奥秘,即“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只有到那时,潜意识的巨大源泉才会喷涌。我们的气息(naphtha)将布满全世界,不用美元(黑色的或金色的),无法估量的价值将改变老一套的规矩”。⑨藉对女性身体的抒写,海男准确捕捉了女性的成长,找到了穿越女性肉体与灵魂的通道。
被誉为“女性身体的成长史”的《花纹》,描绘的是萧雨、夏冰冰、吴豆豆三个大学女生由女孩成长为女人的蜕变过程。对于少女和女人的区别,海男是这样理解的:“少女正在开始准备自己的身体,她们将为身体准备好承受一切负担的容器,比如:用花瓶来承担肉体的秘密,用镜子来承担自己的真实,用男人的影子来承担自己正在幻想中的那微妙而饱满的亲密关系;女人们呢,她们身心饱满地呈现出来,她们巧妙地掩饰着身体上的‘花纹’”⑩。萧雨在19岁进入大学后回家拿相机偶然窥视到母亲和一个男人的性场面,看到了母亲身上呈现的花纹后开始对性产生美好幻想。当萧雨准备将自己的肉身献给男友凯时,却发现凯已背叛了自己纯真的爱情;当萧雨准备与牙医好好谈一场恋爱时,却发现牙医已与诊所护士发生性关系;当萧雨抱着对流言的抗拒投入吴叔的怀抱时,吴叔的政治前途却使他无法离婚。萧雨每与一个男人交往时,都会在身体上、在心灵中留下深刻的“花纹”与烙印。夏冰冰怀着感恩之心自愿向赖哥献身,却为躲避赖哥妻子而被赤身裸体塞在衣柜里倍感屈辱,从此她看清了两人关系的实质,并毅然选择离开。进入广告公司后,夏冰冰在为老板的订单和事业付出时,恪守身体的尊严,最后在皮鞋商人那里寻觅到了超脱物欲的精神沟通。吴豆豆徘徊于简与刘季之间,终因一场车祸改变了命运,在脸上、身上留下了玫瑰花瓣般的“花纹”,围绕在身边的两个男人都弃她而去。吴豆豆在模特职业中寻找到了自我的梦想,冷静地拒绝了身边的男人,奔赴巴黎追寻自己的事业梦想。三个女生的成长,就是她们肉身觉醒的过程,这个过程离不开男性的启蒙,但也充斥着男性给她们带来的肉体与灵魂的伤害。
肉身是海男小说抒写女性成长的关键词之一,沉重的肉身与灵魂间无止境的纠葛是海男透过形而下的身体叩问形而上的灵魂的方式。在海男笔下,人必须正视赤裸裸的身体,在对身体的抚摸中真切地认识身体:
她怀着深深的好奇,自己开始对自己的肉体作一次真正的引领,双手就像她柔软的肉体中的符号,上帝让人拥有双手就是为了帮助人寻找到物和光圈,但上帝让人最早寻找的却是他们自己。……每一种生物都必须在最早时候了解自己的身体,这有助于它们的身体在赤裸之后穿上彩色的衣服,变成神秘的生命。⑪
肉身作为一种物质性存在的实体,可以藉自身获得完满自足性,从而摆脱意识形态的重负。“整个一部西方‘现代化’的历史,简单说在文化意义上就是以身体欲望为武器进行‘去魅’和世俗化的历史,身体是意识形态矛盾最尖锐最集中的策源地。”⑫从这一层面来讲,海男对女性肉身的书写与张扬,已具有为肉身正名的意义。肉身或曰身体,都有自己的尺度,都会给身体带来记忆。无论是虚幻还是现实,身体的记忆都会铭刻在心灵上。在海男笔下,女性肉身的展示不是为了猎奇,也不是为了媚俗,而是指向灵魂的向度,在灵与肉的冲突中叩问生存的价值:“灵魂如何可以变得自由起来,从我们的灵魂在身体中会感受恐惧、罪恶、道德、爱情、喜悦、审判、回忆、味道、沉重……的那一刻开始,我们的灵魂就与肉体在相互低语着,如何透过自己的灵魂来寻找自由——成为我们生命中最为沉重的现象。”⑬
作为一部“身体的祭书”,《身体祭》为我们展现的是战争状态下女人的肉身与灵魂间的尖锐碰撞。年仅二十岁的“我”在二战爆发后,带着对中国恋人李炽燃的思恋独自奔赴缅北,却不幸卷入日军军营,从此失去人身自由。在军营里,“我”亲眼目睹在非常态的情形下慰安妇的生活以及两性之间肉体的奴役与战争。贞子怀着对祖国和恋人的热爱被鼓动到军营来充当慰安妇,并自觉自愿为帝国的男性献身,哪怕是在堕胎三天后,仍又躺在帝国军人的身下。贞子对帝国的忠贞在军营里以一种肉体献祭的方式呈现,最终以死报国。东北女子李秀贞怀孕后却遭惨无人道的身体撕裂,在毫无麻醉的情况下,胎儿被活生生地从子宫中剥离,肉体在罪恶中被剥夺了存在的价值。军营中上至菊野子、野百合,下至贞子、贞玲,都被一种性别权力所驾驭、统治着,心甘情愿为帝国献身。在军营中,女性的身体成了男性主体唯一控制和支配的象征物。在军营这样一个远离社会伦理的空间中,“肉体是驯服的,可以被驾驭、使用、改造和改善。但是,这种著名的自动机器不仅仅是对一种有机体的比喻,他们也是政治玩偶,是权力所能摆布的微缩模型”⑭。权力对身体外在的、表面的规训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会存在,权力对身体的专制压服是规训的初级阶段,深入骨髓的心悦诚服才是规训后的最佳效果。军营中慰安妇们在身体的敞开中,灵魂也被驯服,在性的尖叫声中默默承受身体的凌辱。“我”在这一幕幕惨无人道的悲剧中,恪守人道主义精神,尽己所能帮助同性走出身体的深渊。“我”也不幸卷入慰安妇的行列,与日军军官岛野发生肉体关系,一步步地沦为战争的玩偶,已无法维护和捍卫身体的尺度,丧失了身体的底线和灵魂的城池。日军的溃败让“我”重获自由,战争却让“我”永远失去了恋人李炽燃。许多年过去,“我”在油画中终于摆脱了二战带来的那些奴役着“我”的沉重故事,在恋人的墓前获得了灵魂的自由。由二十岁的妙龄少女到垂垂老者,二战军营的慰安妇经历是“我”人生成长道路上一道永远无法回避与忘却的痛苦旅程,在伦敦-缅北-滇西-伦敦的空间转换中,“我”的人性得以保持与提升,在对自由与人道主义精神的坚守中,实现了成长的蜕变,尽管这种灵魂蜕变刻满了屈辱的伤痕与烙印。
对肉身的体验,是女性成长之途的必修课,也是女性感知自我与他人关系、建构“我”与他者关系的起点。“一个人不能基于他自身而是自我,只有在与某些对话者的关系中,我才是自我。”⑮而一旦女性在认识肉身时,将自己置身于物的地位,那么,女性的成长就会误入歧途。乌珍(《桃花劫》)就是这样一个女子。18岁的乌珍被卖进妓院,昔日的女学生在命运的捉弄下摇身一变为驿馆的“第一枝花”。从一开始,乌珍抗拒着姚妈的“身体规训学”——搔首弄姿、毫无廉耻地出卖肉体赚取男人的钱袋,时刻保持着逃离的警醒。在短暂的抗争之后,乌珍将逃离驿馆的希望寄托在嫖客身上,开始了肉体的献媚与颓废。马帮商人吴爷的宠幸让乌珍暂时摆脱其他妓女的命运,却让她的肉体彻底沉沦,灵魂已不再与肉体进行旷日持久的抗争。在妓院这一空间中,妓女只能被动地展示肉体的价值,“由于男性是视觉空间的主动者,男人的‘看’(looking)决定了视觉空间中的女性身体表象,并对这个表象加以控制和占有。男人——看,女人——被看构成视觉空间的二元对位,隐含深重的等级关系”⑯。在男人主宰的狭小天地里,妓女之间上演着同性间的竞争与倾轧。为保有驿馆第一枝花的地位,乌珍也会在黄昏出现在驿馆门口招徕嫖客。乌珍富裕人家大小姐的命运被一座驿馆彻底改写,“在她的命运中,他人的干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说,如果这种行动采取另外一种方向,就会造成完全不同的结果。决定女人的并不是她的荷尔蒙或神秘本能,而是她的身体以及她同世界的关系,通过他人而不是她自己的行动得以缓和的方式”⑰。在吴爷、白爷、二爷、黄家文等男性的纠葛中,在见证鸽子被强行堕胎致疯以及活埋的遭遇后,乌珍不再为任何男人保留肉身的位置,不再把希望寄托在任何人身上,一种复仇的野心渐渐在暗夜里滋生。乌珍藉白爷的宠幸,习得一手好枪法,并通过身体骗取二爷的信任。乌珍杀害白爷后取而代之成为土匪王,并将复仇指向姚妈。在精心设计下,乌珍剥夺了姚妈驿馆的经营权,并将姚妈的女儿桃花带到驿馆成为妓女,这一系列的报复强烈刺激着姚妈,终于在一个夜晚姚妈将驿馆付之一炬。厌倦复仇生涯后乌珍与吴爷远走他乡,18年后在小镇与儿子不期而遇,乌珍顿悟到自己此前对命运的抗争充满着无耻与罪恶,以跳崖自杀的方式完成对肉身的忏悔。在乌珍的成长中,肉体的沦陷并不意味灵魂的屈服,乌珍的灵魂时刻都蛰伏在看似驯服的肉体之下伺机而动。乌珍对姚妈的复仇,看似一场女性之间的战争,实际是以一种极端方式呈现出来的女性对男权决绝的反抗。乌珍运用心计一次次试图扭转自己在两性之间“被看”的位置,改变自己作为男性欲望与权威的对象地位,借以颠覆长久以来存在着的强大的男权秩序。这种颠覆是在不自觉的复仇过程中一步步成为现实的。在乌珍的成长过程中,姚妈充当了反面引路人的角色,姚妈追逐爱情而后被弃的境遇让乌珍最初感受到男性的不可靠,姚妈对金钱的不倦追求让乌珍洞彻到人性的贪婪与无耻。白爷则将乌珍引上另一条道路,即对权力的追逐与掌控,在枪声中乌珍感受到人性的泯灭与荒芜。乌珍的成长向我们展示了女性在肉身的抗拒与沉沦中,是如何以一种极端的姿态抗争男权社会的。
实际上,在海男笔下父亲这一角色往往在女性的成长中是以缺席的方式出场。普桑子的父亲在她出世之前就离家参战,三十多年后才以一座坟墓的方式来呈现父亲的形象;落红的生父在她17岁以前,是一张每月定期从省城邮寄来的汇款单;萧雨的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抛弃家庭,投入另一个女人的怀抱。父亲哪怕在成长中在场,也是被虚置为一种无力引导女性成长的背景。罗修的父亲大部分时候驻扎在省城而远离家庭,夏冰冰的父亲嗜酒如命,乌珍的父亲让童年的她过早背负肉欲的重负。父亲在女儿的成长中,一改传统文化菲勒斯中心的形象,而是一个无力的、软弱的父权文化的象征体。海男以自己的方式塑造了一系列猥琐的父亲形象,在父与女生命力的对比中,悄然瓦解父系的权威。从这一意义出发,海男是在用女性自我的肉身与体悟来颠覆男权传统。这种颠覆不同于陈染、林白笔下女性对自我的迷恋与偏执,也不是以一种无法调和的两性冲突来呈现,而是以一种缓慢的渗透浸濡了女性成长的历史与现实的天空,以男权的坍塌来映衬女性的成长。
“对那些不隐讳自己的女性身份的作家而言,写作与其说是‘创造’,毋宁说是‘拯救’,是对那个还不就是‘无’但行将成为‘无’的‘自我’的拯救,是对淹没在‘他人话语’之下的女性之真的拯救。”⑱毫无疑问,海男正是这样一位女性作家,她笔下的女性成长叙事也因此超越了性别的界限,直指向人类的生存之思,在历史的行进中叩问人类的灵魂。
注释:
①丁克南:《蝴蝶的意味(代序)》,《蝴蝶是怎样变成标本的》,海南出版公司1998年,第5页。
② MordecaiMarcus,“WhatIsanInitiationStory?”,JournalofAestheticsandArtCriticism,Vol。XIX,winter,1960。
③芮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版,第7页。
④海男:《县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页。
⑤⑦⑪海男:《女人传》,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页、第88页、第48页。
⑥王炎:《小说的时间性与现代性》,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版,第133页。
⑧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华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85页。
⑨埃莱来·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页。
⑩王千马:《海男:我对自己身体了如指掌》,http://blog.sina.com。cn/s/blog_588c684e0100023c。html。
⑫樊国宾:《主体的生成》,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版,第188页。
⑬海男:《身体传》,安徽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89-190页。
⑭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54页。
⑮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页。
⑯王宇:《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05页。
⑰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Ⅱ),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20页。
⑱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