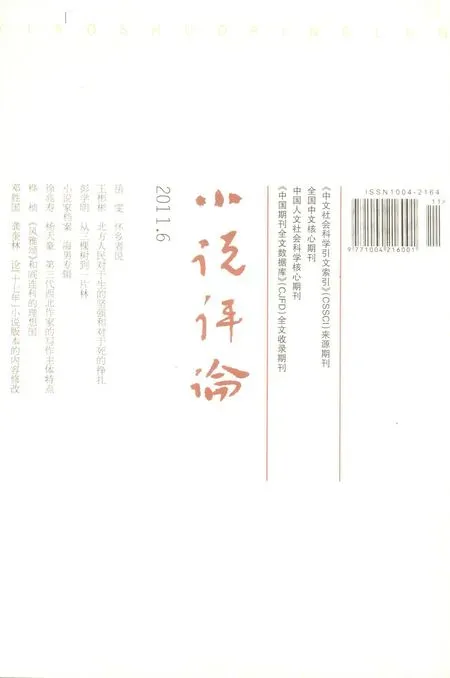怀乡者说
岳雯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
——鲁迅
文学和故乡,从某种意义上说,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在对方身上发现彼此,认识彼此,抵达彼此。我们常常在文学的身上发现故乡的影子,进入文学的世界,就像返回到精神的故乡,一切事物都以最美好的姿态呈现,那么适意、安稳,仿佛这个世界曾经许诺给我们的都会实现。当然,文学中也常常描写故乡。故乡寄托了我们所有的甜蜜与忧伤、梦想与牵挂,蕴藏了我们心灵的信息和关于生活世界的全部秘密。我们一次次在文学中返回故乡,无非是为了重温记忆中温暖的过去,重新积蓄力量,重新发现未能全部敞开的自我。说到故乡,其实还隐含着一个长期漂泊在外,时时回望故乡的人的形象。倘若不离开,故乡永远只是拘役你的小小笼子,昏黄的黯淡的天空,乏善可陈的人与事,以及缓慢的时间滴答之声;只有在回望中,一切才被赋予了生机,充溢了感情和力量。因此,写作者大多是怀乡者,他们在纸上涂抹只言片语,有可能都是在勾勒故乡的样子。今天,现代性横冲直撞,最大限度地改变这个世界,并切断我们和过去的联系之时,故乡在文学中呈现出什么样子?怀乡者又在呢喃什么?本文将选择几位作家,他们也许不算典型,然而他们发出的怀乡的声音却透露出在这个时代地表之下潜行的想象与渴望。
一
一个怀乡者和故乡之间,隔着渺远的时空距离:他(她)一般置身于车水马龙的城市间,默默怀想着乡村,城市与乡村,是地理的距离,浸透着思想和情感的汁液。这距离也是时间的距离,他(她)怀想的不是现在,而是遥远的过去,是完整的童年时光,是逝去的好日子。此时的乡村,静默不语,是记忆里模糊而真切的面影。因为过去太过美好,只存在于修改过的记忆和想象中,于是,无法返乡的怀乡者在纸上重建了故乡的模样。青年作家付秀莹就是如此。
在付秀莹得到广泛关注的短篇小说《爱情到处流传》(《红豆》,2009年第10期)中,故乡悄然探出一角,到了中篇小说《旧院》(《十月》,2010年第1期)中,故乡毫无疑问占据了小说的主要篇幅,成为作者抒情、怀想的对象,也勾起了阅读者绵绵无尽的乡愁。
这乡愁首先是由乡村的景物引起的。在怀乡人眼里,没有什么能比故乡的风景更能牵引思绪了,于是,对风景的描写就有了不一样的意味。在对风景的选择上,必然是那些熟稔的,与记忆有关的事物率先跳跃到笔下。比如,枣树。当然,我们对枣树并不陌生。鲁迅先生在他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的“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早已在我们的记忆里生根发芽,枝繁叶茂。在《旧院》里,这棵枣树益发动人了。“院子里有一棵枣树,很老了。巨大的树冠几乎覆盖了半个房顶。春天,枣花开了,雪白的一树,很繁华了。到了秋天,累累的果实,在茂密的枝叶间,藏也藏不住。”这本是乡间院落里极为常见的一景。“老”暗示出枣树和旧院共同走过的岁月;从春天到秋天,仿佛蒙太奇式的勾勒手法,在景致上面就有了时间的痕迹。可不是么,远远站在时光的尽头的那一个,才是故乡呀。因为遥远,远得无法触及,就连记忆也摇荡起来,看不分明,所以,景致都如拉洋片似的,一帧一帧以无声的静态的方式呈现。意象罗列的写法就成了怀乡者写景的主要手法。小说描绘了一群姑娘坐在一处绣鞋垫的场景,阳光、微风、枣花、树影、麻雀、母鸡,可以想见,这场景是静谧的,安适的;与之类似的,还有“我”陪小姨谈恋爱时的场景,“春风沉醉的夜晚,庄稼的气息,虫鸣,月亮在天上,静静地走。”这样抒情的乡村,教人如何不怀念呢?
当然,不仅仅是景致,乡村吸引人的,还有在乡村的院落里独有的复杂的密如蛛网的人情伦理。用“吸引”一说,恐会引来许多质疑,曾几何时,这是我们沉重的负担,是我们的痼疾,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然而,在城市里生活得久了的人们还是会怀念,属于一个大家庭的复杂微妙的人际关系。说到底,《旧院》就是关于姥姥一大家子人的生活的。姥姥和姥爷,六个女儿的成长与婚恋,人与人之间的纠葛与命运,都在作者笔下得到审美的呈现。写的最精彩的,莫过于五姨的故事。因为一家子全是女儿,姥姥为五姨招了女婿上门,打那以后,母女关系变成婆媳关系,这份尴尬以及加诸五姨身上的痛苦,透过了岁月的毛玻璃片看去,颇有了动人的色彩。作者用赞赏的笔调写活了“我舅”这个人物。这是乡村生活里的一个典型人物,似乎每个村庄都有他的影子。他聪敏,精明,处事圆通,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眼就能看破;他有手艺,人缘好,村子里婚丧嫁娶,少不得请他帮忙,承他人情。这人情就变成了左邻右舍和睦的关系,以及家庭里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作者真是把乡村里的人情世故揣摩透了,人心的幽深、曲折,不是置身其间怕不能有如此圆通的理解。其实,理解的又何止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里面有几千年来乡土大地上厚重的文化沉淀,根本就是我们无法离开的生活世界。对于这份灵活、圆通,“我舅”也是颇有几分自得的,他享受人们对他手艺的这份敬重,直到时代的另一种风潮湮没了他。
这大概是令怀乡者眷恋不已的乡村的又一种魅力了。日益破败的乡村在现实生活里是不受待见的,但一旦挪到文学的世界里,这颓败就生出几分光泽来,旧院和“我舅”莫不如此。旧院是喧闹过的,“我的几个姨们,像一朵朵鲜花,有的正在盛期,有的含苞欲放。她们正处在一生中最光华的岁月。她们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回到家,她们凑在一处在灯下绣鞋垫。”此时的旧院,是生机勃勃的世界,人的光华给院落带来的是希望,以及更好未来即将到来的愿景。随着女儿们的挨个出嫁,旧院也便空了下来,“旧院是真的安静下来了。阳光静静地晒着,把枣树的枯枝画在地上,一笔一笔,很分明的样子。西墙上,挂着红薯的藤蔓,黑褐色,已经干透了。一只羊正在努力地拿嘴巴够着,却够不着。”在静物的临摹中,一种叫做寂寞的东西,在旧院里弥漫。人去院空,从来就是叫人伤感的呀,“这个旧院,寂寂的,让人空落落地疼。”更大的颓败还在后头。当“不一样的气息”流传到旧院时,当人们都“自顾自朝前冲去了”的时候,旧院被留了下来,世事变迁的悲哀,在旧院里,就分外触目了。好的时光总是要逝去的,好的世界总是在过去,我们对此感到愁绪满怀却又无从说起,在怀念中内心得到了些许满足与宽慰,因为我们据此识别出来,那就是主宰这个世界的无法抗拒的力量。
不能不提的,是怀乡者的视角。显然,文本是由两种目光交织成的,一种目光是属于儿童的,因为故乡总是与童年相伴的,每每忆起故乡,里面总是跳跃着一个小小的自己。由这儿童的眼光看来,故乡充满了天真的稚气与似懂非懂的懵懂。因此,这怀念里,不能不有几分童趣在。比如,“夏天的清晨,刚下过雨,我们相约着去河套里拾菌子。”,比如开会,一提起开会,“我”总会想到骑马,“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还有看露天电影,让我第一次感觉到男女之间“男女之间,竟然有那样一种莫名的东西,微妙、紧张、兴奋、不可言说,却有一种蚀骨的力量”,虽然,“我全不懂”。是不是只有在懂与不懂间,世界才格外开阔,格外浩大,让人总想探个究竟呢?可不可以说,怀乡者怀念的,不只是故乡,还有永远在故乡的土地上游荡的童心呢?还有一种目光,则是属于成年以后的怀乡者的,《旧院》里不时出现这样的句式,“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再不会想到……”、“多年以后,我依然记得……”。更让阅读者欣赏的,是那些对日常生活的光与影进行咀嚼的文字,比如,她说劳动,“劳动这个词,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了。它包含了很多,温暖,欢乐,有一种世俗的喜悦和欢腾。如果劳动这个词有颜色的话,我想,它一定是金色的,明亮,坦荡,热烈,像田野上空的太阳,有时候,你不得不把眼睛微微眯起来,它的明亮里有一种甜蜜的东西,让人莫名地忧伤。”没有历练,没有在人生这艘大船上迎风走浪之后依然相信美好,怕是说不出来这样的话吧。于是,我们看到,一道隔着迢迢时光的目光,在经历人生的种种后,依然难忘当年的美好,对当时不明白也无法明白的事情有了自己的解释。这两道目光互相指引,互相说明,蕴藏了多少说不清也道不明的东西,让这属于故乡的文字也粘稠、丰满起来。
至此,也许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叫做“旧院”了,正如桑塔格所说的,“我们不能没有旧,因为在旧事物中包含我们所有的过去,我们所有的智慧,我们所有的记忆,我们所有的悲伤,我们所有的现实感。”①在纸上重建一个故乡的努力,吸引了许多写作者。在付秀莹和她的旧院的前面,我们看到了汪曾祺和他的高邮,看到了萧红和她的呼兰河,看到了师陀和他的果园城,看到了沈从文和他的湘西。他们都是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里所说的修复型的怀旧者,旨在重建失去的家园和弥补记忆中的空缺,只是,这家园是用文字的一砖一瓦搭成的。
然而,还是让人生疑,我是说旧院。它太像我们每个人记忆中的那个故乡了,以至于失去了自己的“那一个”,宛如一幅烟云模糊的风俗画,让人看不真切。这么说的一层意思是,故乡也许是独属于一个人的,它的褶皱它的细节它的枝杈,都在每一个人内心里,表面上的像恰恰遮蔽了本质上的独特性。还有一层意思是,记忆都是不可靠的,在你以为完完全全还原了故乡的同时,你可能让怀旧的情感蒙上了真正认识故乡的心愿,阻挡了返乡的脚步。
二
于是,就有了另外一些怀乡者,他们也在乡村度过童年、少年时光,后来,外面的世界向他们敞开了,在某种机缘下,他们离开了故乡,来到了城市,让自己像一粒顽强的种子一样在城市里生存下来。故乡对于他们,也越来越陌生了。然而,突然某一天,他们强烈感受到自己与故乡的联系,他们不满足于建造一个故乡的幻象,而是拨开怀旧的面纱,勇敢地认识那个实实在在存在的故乡。在这些怀乡者中,我辨认出了梁鸿与乔叶的身影。
梁鸿的的确确生于乡土,长于乡土。我看到过同是生长于乡土的阎连科对她的一番说法,“我们,谁都无法了解、体悟一个乡野的女孩,把牧羊的鞭子挂在田头树下,或者把在田野累了一天的铁锨、锄头,倚靠在回家的门后,迅速捧起书本的那种感觉。无法体验因为劳动,使十指麻木胀大,握不住笔杆又必须像握住锄头样握住笔杆的那种感觉。我想,放下握锄头的双手,无间歇地迅速去握住笔杆,那大约如同拥抱了一天大地,在夕阳西照之时,又要迅速去拥抱一缕落日。”②这说法,是过分诗意了,但这里面透露出来的一个怀乡者对另一个怀乡者相惜的感情,是真挚的。2010年,梁鸿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怀乡者,是从她出版的那本《中国在梁庄》(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开始的。
梁鸿的返乡起源于她对目前生活的怀疑,她认为读书、写作的生活是“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于是,她“有种冲动,真正回到乡村,回到自己的村庄,以一种整体的眼光,调查、分析、审视当代乡村在中国历史变革和文化变革中的位置,并努力展示出具有内在性的广阔的乡村现实生活图景。”这是一个经过启蒙洗礼后的知识分子的语言,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不同的是,她深知改造乡村之虚妄,但在城市里习得的知识又时时提醒她,使她觉得有责任与义务将之运用于自己的故乡,尽管,这“运用”也只是“审视”,是不及物的。另一个怀乡者乔叶回到故乡的理由就更实际了,姐姐家遭遇了盖房子的困境吁请她这个“乡村叛逃者”返乡(《盖楼记》,《人民文学》2011年6期)。没错,乔叶称自己是“乡村的叛逃者”,这是“对乡村底子城市身份的人的统称”。与梁鸿不同的是,乔叶坦承她与乡村之间存在深深的沟壑,“无论是什么样的语言材料和语言品质,那道沟壑都很难填补。”为什么如此,原因也很简单,“我对乡村想要了解的欲望越来越淡。”“只要有路,只要有车,只要有盘缠,只要有体力,所有的叛逃者都只想越逃越远。”这两种看似大相径庭的态度其实并不矛盾。怀乡者大多如此,日日重复的生活让他们时时否定自己,希望重新接上与乡土的联系,但是,谁也不会将自己的根从城市的柏油马路上拔起,重新植进乡村的大地,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不管是因为什么,怀乡者踏上了返乡的道路,真实的而不是想象的“旧院”离她们越来越近了。起初都是揣着回忆的行囊,满怀诗情的。梁鸿甚至预先铺垫了美国自然文学作家亨利·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企盼在故乡的大地上和自然融为一体。她自然而然地回忆起少年时代曾经在一座桥上看到世界上最美的月亮的情景。回忆似月光,“恰如青春的哀愁,有着难以诉说的细致。”此刻,尚未抵达故乡的怀乡者们都如付秀莹们一样,展开了最诗意的想象。“沿河而行,河鸟在天空中盘旋,有时路边还有长长的沟渠,青翠的小草和各色的小野花在沟渠边蔓延,随着沟渠的形状高高低低一直延伸到蓝天深处,有着难以形容的清新与柔美。村庄掩映在路边的树木里,安静朴素,仿佛永恒。”这是梁鸿在抒情。“清流汩汩,明澈见底,水草丰茂,鱼蟹繁多,我摘金银花,恰薄荷叶,挖甜甜根,盘小泥鳅……那是我小小的童年天堂啊。”这是乔叶在回忆。显然,他们与修复型的怀乡者并无二致。
一旦接近故乡,怀乡者都亲身感受到了故乡的巨大变化,进而迷失在熟悉的故乡里。崭新而破败,熟悉而陌生,这是他们共同的感受。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怀乡者们的语调立刻发生了变化。蛰伏在梁鸿体内的研究者跳了出来,取代了先前的抒情者。梁鸿对自己的故乡——梁庄做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一个简单的结论是,“我记忆中的村庄与眼前的村庄相比,虽然地理位置没变,但其精神的存在依据却变可。”这个结论是作者通过大量的走访、调查,从家族与人口构成,地理环境,孩子、青年、成年的生存状态,乡村政治,道德、梦想等多个方面的状况得出来的。作者的语调更为冷静、理性,也更为严峻了,她与被访者对话的过程中,基于现代科学理性的知识决定了她追问的方向,人文知识分子的身份也在共同构成她叙述的过程。“村落结构的变化,背后是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变化。农耕文化的结构方式在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混杂的状态,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在中国的乡村进行着博弈,它们力量的悬殊是显而易见的。村庄,不再具有文化上的凝聚力,它只是一盘散沙,偶尔流落在一起,也会很快分开,不具有实际的文化功能。”此时,民族、国家等宏大叙事占据了她的中心视野,故乡反而消失不见了。“乡村,并不纯然是被改造的,或者,有许多东西可以保持,因为从中我们看到一个民族的深层情感,爱、善、纯厚、朴素、亲情等等,失去它们,我们将会失去很多很多。也许正是这顽固的乡村与农民根性的存在,民族的自信、民族独特的生命方式和情感方式才能有永恒的生命力。”这样的论述比比皆是。“中国在梁庄”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凸显出来。从怀乡者到离乡者,难道,抵达故乡的本体就会让人消弭怀旧之情,陷入到更为现实的问题中去了吗?
另一个怀乡者乔叶也差不多。她面临的是乡村目前最为迫切也最遭人诟病的问题——拆迁。小说家乔叶没有像梁鸿一样进入学者的理性思考里,而是从自己亲人的实际处境中将拆迁在基层农村的情况条分缕析,铺陈明白。乔叶的故乡乔庄在现代化进程中被列入了高新区,于是,农民与政府的博弈就此展开。农民想法设法地盖房子了,这盖,不是为了自己居住,而是等着政府拆迁,好得到赔偿款。看似简单的问题背后隐藏着多方利益,于是,乡村叛逃者也参与到整个事情的谋划、筹措过程中。盖楼就像一个黑洞,将人心的贪婪、算计赤裸裸地展示出来,乡村的人情伦理也完全蜕变成现代人的功利理性。乡村的变化也映衬出怀乡者的心绪,“作为一个从乡村走出来的孩子,我确实跟他们久违了。但是,我乡村的根儿还没死,离他们也就不算太远,于是不坐也就罢了,坐了很快就能坐在一起。”在融入乡村的过程中,那点诗情画意很快就在实际问题面前偃旗息鼓了。融入里面也有超脱,有居高临下的理解和同情,“他们的一切,无论是柴米油盐还是爱恨情仇,无论是精神根本还是物质源头,都与土地血肉同体,息息相关。”“一直是土地,始终是土地,土地就是他们的命。”注意,是他们,而不是我们。怀乡者已经不习惯乡村了,就像不习惯乡村的寒夜一样。
理性也好,功利也罢,情感却还在。用乔叶的话说,是“幽深难过”,在实际问题之后,怀乡者心里涌起了这样的感情。在再次离开故乡的时候,难过像幽灵一样,整个攫住了她。她一个人在灵泉河的遗址上陷入了对故乡更深沉更痛切的感情中去。“无数个这样的村庄都会这样消失——我忽然觉得无法想象。没有了村庄的大地,我无法想象。”大地,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大地抵达了她的情感深处,她突然想要听听大地的心跳。“一颗心律失常的心脏,一颗得了心脏病的心脏。”她对故乡的忧虑,对自己的怀疑全部浓缩在这个比喻里了。她以这种方式失去了自己的故乡。梁鸿的失去就更明白显近了。如果说,之前,当故乡以整体的、回忆的方式在她的心灵中存在时,她对故乡是时时怀念的,想回来的愿望也非常强烈;而现在,经过几个月深入肌理的分析与挖掘,故乡已经面目全非了。“所有的一切都成为功利的东西”,也毁掉了她的故乡。
三
重回故乡的震惊体验,在鲁迅那里与现在的怀乡者这里,差别似乎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般显著。时间之手让今日的乡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却并没有将怀乡者区别开,相反,他们迅速地识别出同类,在经典叙事模式下一再唱出自己的挽歌。对于这种情形,王德威有精准的认识,他说,“乡土论述竞相标榜写实/现实风格时,已经内蕴另一种神话。故乡之成为‘故’乡,必须透露似近实远,既亲且疏的浪漫想象魅力;闪烁其下的因此竟有一股‘异乡’情调。除此原乡主题不只述说时间流逝的故事而已;由过去找寻现在,就回忆敷衍现实,时序错置(anachronism)成为照映今与昔、传统与现代冲突间的必要手段。相对于此,空间位移(displacement)不只指明原乡作者的经验状况——‘故乡’意义的产生肇因于故乡的失落或改变,也尤其暗示原乡叙述行为的症结。叙述的本身即是一连串‘乡’之神话的移转、置换及再生。”③偏有怀乡者要打破这一神话。他们大约是博伊姆所说的反思型的怀旧者,“修复型的怀旧表现在对于过去的纪念碑的完整重建;而反思型的怀旧则是在废墟上徘徊,在时间和历史的斑斑锈迹上,在另外的地方和另外的时间的梦境中徘徊。”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魏微作为反思型的怀乡者的形象尤为特别。
《异乡》(《人民文学》,2004年第10期)在标题上就将“故乡”置换为“异乡”,对于“故乡神话”而言,不啻当头一击。从“故”到“异”,隐含了多少情感信息!“异乡”的“异”,起初,针对的是许子慧说的。好吧,得承认,我们都是许子慧,都是从一个小地方——有的是乡村,有的是小城镇到大城市来讨生活的人,可不是“异乡人”么。离乡,在现代中国是一个常态,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迁徙的加快,“从故土奔赴异乡,从异乡奔赴另一个异乡”。至于离乡的理由,魏微语带嘲讽,“他们怀着理想、热情,无数张脸被烧得通红扭曲,变了人形。”过上想象中更好的生活的愿望驱使他们离开故乡。对于子慧,“离开故土,流落异乡,其实并没有什么实在的理由,或许仅仅是为了离开。”这个前因,在其他怀乡者的文本那里,是隐匿不见的。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怀念故乡,却从来不说我们为什么离开了它,但只要一离开,故乡在我们心中就变得全然美好起来。离乡者子慧也时时想起,谈起她的故乡。在她的叙述里,故乡有了不同的版本,“跟同事用一个版本,跟小黄和李奶奶用另一个版本……版本多了,难免就会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有的时候,“吉安是这么一个地方:青石板小路,蜿蜒的石阶,老房子是青砖灰瓦的样式,尖尖的屋顶,白粉墙……一切都是静静的,有水墨画一般的意境。庭院里有樟树,槐树,榕树,推开后窗,就是清澈见底的小河,河水可以饮用,漂洗,夜里能听到流水的声音。”这时候的故乡,颇有点像付秀莹的旧院,也有些像梁鸿和乔叶记忆里的故乡,如此安稳,悠远。与其他怀乡者一样,她描述的吉安是二十年前的吉安,是过去时的。还有一种版本的吉安是她离家出走的三年前的吉安,“急促,庞大,慌张”,“整个城市就如一个大工场,推土机昼夜轰鸣,新楼房拔地而起,许多街道改向了,光天化日之下,人们变得迷茫紧张。”请注意,怀乡者的笔下第一次出现了两种时态的故乡,现在与过去并置,美好的与不那么美好的,都指向同一个对象,显然,后者很难再引发出怀乡者诗意的情感。这是魏微对于怀乡叙事的重要贡献,她戳破了古典的外衣,引入了现代维度,使故乡的形象有了历史的纵深。与此同时,怀乡者的感情也和过去的怀乡者不同了,“她喜欢她的家乡,同时又讨厌她的家乡”。无论是喜欢还是讨厌,一个不得不正视的事实是,“这些年来,故乡一直在她心里,虽然远隔千里,可是某种程度上,她从未离开它半步。”这或许是怀乡者更为真实的感情吧。
当她把离乡的经历比喻成一场梦游,一个寒冬以后,子慧终究也踏上了返乡的道路。当然,故乡也有太大的变化,这是无可避免的。有意味的是子慧的态度。对于变化,子慧并不像其他怀乡者那样震惊,相反,“子慧笑吟吟的,心里充满愉悦,故乡好像在哪儿见过。是啊,回家也不过如此,吉安既不很熟悉,也不太陌生,反正地球都成了一个村,中国变成一个城市也没什么了不起。”没有撕心裂肺的痛,只有无所谓的愉悦。她甚至有某种优越感,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偶尔路过此地的大城市的女子。”怀乡者的感情游离在城市与故乡之间,故乡固然有她温暖的记忆,可也让她陌生;城市的生活固然危险,倘若经济完全自足,也很“便当”。家已经没有了,更勿论什么归属感,这才是现代怀乡者的真实境遇。
陌生还在其次,故乡对她的冷漠与伤害接踵而至,这才是让子慧不寒而栗的地方。背后无数双像箭一样的眼睛,父母亲对她行李的检阅,令故乡“活”了起来。换句话说,故乡不再是一个被动的客体,等待着怀乡者去观察,去分析,去挖掘,去爱;故乡本身也是主体,对怀乡者施展力量。故乡之于子慧,是探究,是流言,是不信任。怀乡者被宣布是不受欢迎的人,故乡的大门对怀乡者封闭了。在梁鸿和乔叶那里,失去的还只是故乡;到了魏微这里,怀乡者整个被摧毁了。“异乡”的“异”方才敞开了它全部的意义空间。《回家》可以说是《异乡》的姊妹篇。同子慧一样,丹阳街发廊妹小凤回家以后发现“夏夜静谧的乡村竟有寒冬的阴冷;苍老安心的父亲神情悲悯哀伤,我和父母之间始终隔着一层,没滋没味的。”母亲鼓励小凤出去,同样意味着故乡对怀乡者的驱逐。表面上看,这驱逐是因为故乡出于伦理价值完整的需要,实际上,故乡本身也谈不上清白不清白(《异乡》里的吉安城不也出现了新的声色场所么),故乡对外在世界的敌意才是症结所在。
关于怀乡者,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了。有的人在纸上涂抹出记忆里的故乡;有的人勇敢地、大踏步地返回故乡,去发现自己丢失了故乡;有的人很悲观,他不相信存在一个更完美更理想的故乡,故乡永远在彼岸,没有船可以过河。这就是今天我们所在的位置。在我们身上,似乎所有怀乡者都占有一席之地,又似乎他们根本就不是我们。但是,对于故乡的怀想不会停止,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一代又一代的怀乡者将沿着漫长的无止境的道路,继续踽踽独行。
注释:
①苏珊·桑塔格:《文学就是自由》,载《同时》,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1月,第207页。
②阎连科:《梁鸿:行走在现实与学理之间》,参见《“灵光的消逝”》的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6月,第2页。
③王德威:《国族论述与乡土修辞》,《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台北麦田,1998年10月,第166页。
④(美)斯维特兰娜·博伊姆:《怀旧的未来》,杨德友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10月,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