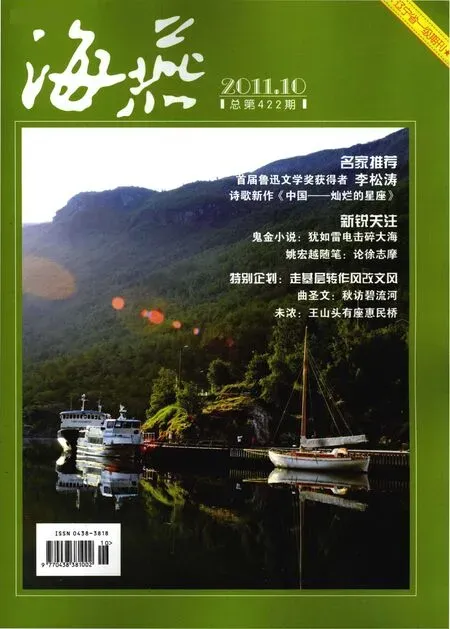出煞
文_王冠一
男子说:你来了!
一抹阳光跃过汤金色究竟顶直直地打在柳赞的脸上,她旋即别过脸去,却还是被这丰盛的阳光刺痛了眼睛。她站起来,发现陌生男子跪在蒲团上没有动亦没有看她,他只看佛。
这是水月庵,她怎么会在这儿?柳赞只记得昨夜摇摇晃晃走出圣地亚哥酒吧,张元伯立在门口说,我送你回去。柳赞略略摇头,送又如何?不送又如何?张元伯愣了一愣,伸出手环住了柳赞,你有身孕,不该喝这么多酒的。
这时一辆出租车驶过来,柳赞挣脱开他的怀抱,转身钻进车子里,重重关上门,门外的张元伯一脸惊愕又很委屈,抓住车门扶手好像要说些什么,但柳赞没有理会,她对司机说,走吧。司机迟疑,但还是发动了引擎……车子沿沥青马路奔驰,把城市抛向了远方,如弃婴。其实柳赞也不晓得为什么,连张元伯都接受,淡然了范聚亲的死,她却放不下。
柳赞望着这条漆黑的马路,似乎没有终点,又似乎已然走尽了……
见到范聚亲是在一个八月。
柳赞一眼便从人群中认出了他,跟平素想象的一样又不一样。他挺拔,穿深蓝色牛仔裤,白衬衫里面透出白色背心的轮廓,眉骨高所以显得眼睛格外深邃。他接过行李说,饿了吧,语气像许久未见的老朋友。柳赞竟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只听他又说,咱们先吃点东西。
她跟着他,穿过行色匆匆的陌生人。柳赞很喜欢看陌生人的脸,焦急,愉悦,慌张,平和……像新鲜而隐秘的故事,当他们转瞬而去,故事就留在了心底。她对范聚亲说,元伯跟我讲了你许多事。范聚亲摸摸后脖子露出大男孩般的笑容,呵!过去的事儿,倒是他记得清楚。说完,他目光沉了一下,又看向柳赞,元伯说他实在忙,让我好好照顾你。柳赞摆摆手走进了“来今雨轩”,一座古香古色的建筑。她坐在靠窗的红木椅子上,范聚亲似乎常来,直接点了枣泥山药糕,豌豆黄儿,又要了两碗冰糖燕窝粥。柳赞狐疑,这些菜名哪里见过?她没细想,便抬起眼说了句谢谢,正与范聚亲目光相撞。柳赞本能地要躲开,却来不及了,人生若只如初见。
这家的小菜很有特色,全是《红楼梦》里头的,清淡可口,我想你会喜欢的。柳赞恍然点点头,低声说了句,怪不得。
靡靡之曲萦绕着房间,忽然两个人都沉默,听着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柳赞心想自从认识元伯,她就知道了有范聚亲这么一个人,聚亲怎么给你形容呢?潇洒倜傥。他读了好些书。聚亲现在做什么图书编辑,咦?老婆,你不写了个小说吗,可以找他出版呀……起初柳赞还打趣,我看你们俩之间有爱情。张元伯拿起一张客户名单比比划划,他转移话题:唉!我得催催这几个客户,怎么还不交钱!后来柳赞一个人无聊时就想他,再后来想成了习惯,他是她遥远的一个幻象,如影随形。
去年他们结婚范聚亲本是要来的,但连续几日浓雾锁着大连,飞机不得降落,所以也就没有来。柳赞看出元伯失望的样子,她亦有点失望,莫名的。
听元伯说你是做……柳赞的话未完,范聚亲便道:这是昆曲《牡丹亭》里“皂罗袍”一折,我特别喜欢。这唱词每一个字填的都极妙,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一语道破了多少禅机。他夹起一块豌豆黄儿放到柳赞碗里。柳赞说,就好像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都应了那句人非物换,万境归空。
范聚亲一个激灵,都应了那句人非物换,万境归空。评得好!
柳赞不好意思起来,我胡乱讲的。
他们一句话说来一句话荡去,越谈越投机。范聚亲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他扬手加了一壶酒和一叠盐花生。如此良辰美景,没有酒怎么成呢?柳赞也没拒绝,端起来喝了一小口,顿时脸就红了。
元伯说你写了部长篇小说?出版了没有?
没有,现在出书比登天还要难。
或者考虑考虑网络发表。
这……柳赞顿了顿,网络太浮夸了,我做不来。范聚亲看着她,有一种静隐的美。他想在这个以金钱和富二代为价值取向的人群里,竟还有个她,他们着实很像。
其后范聚亲送柳赞到了酒店,明天我要有工作,后天再陪你逛逛。
柳赞说,你忙你的,不用麻烦,说着她转身上楼,动作有点刻意。
她走进浴室打开了龙头,让温水浇湿自己的身体,隔壁传来女子闪烁的呻吟声。她倚着描青花的瓷砖墙面,水雾弥漫了狭小的空间……上飞机之前张元伯急急地说,我不能跟你去北京了,突然有几单大生意。你好好玩,别怕花钱,老公我能赚。柳赞淡淡地问,你真的不去。他答:真的去不了!
傍晚,亮烈的火烧云泄于天边,她坐在窗台上,头发湿濡着。酒店下面有一群少年跳街舞,女孩拿着一捧衣服坐黑色摩托车上,舞者中最高的那个仿佛是她的男朋友,当他跳出高难动作,她都站起来呼喊……如果可以,柳赞愿意抛弃一切,永远都这样坐着,下雨时看雨,晴朗时观云,高兴了像那女孩一样大喊,悲伤了就睡去。她觉得她与张元伯之间有什么不对了,又说不出哪里不对。
柳赞沿着水月庵汉白玉莲花狮子雕栏走了一圈又回到原点,南边的禅院正装修,电钻声尖锐刺耳。
你有心事?
柳赞站在陌生男子后面,她身上还残着昨晚的酒气。没什么,她仿佛自语,只是想起了一个人。
如果当初没有相见,或许如今就不必“想起”了。
柳赞不由一惊,才认真看了看跪在蒲团上的陌生男子,觉得这个人轻飘飘的,在那儿又像没在那儿。她问道,你是谁?
你看,佛为什么低眉。男子并没有回答柳赞的问题。
柳赞望了望佛,佛眼低低的。
因为慈悲,佛不忍相看众生苦楚,所以垂下了眼帘,愿普度一切因缘,一切孽业,一切痴缠。
是吗?柳赞无端摸了摸小腹。电话响了,是元伯,语气很急,你在哪?她沉沉地说,水月庵。
好,我这就去接你。
柳赞合上电话,深深叹了一口气。
范聚亲把行李递给她,行李于两个人之间停顿了几秒,却仿佛一生一世那么长。嗯……你回去把小说发给我,或许我可以推荐给出版社。柳赞拖了长长的一个“好”字。范聚亲忽然指向她的衣领说,是没洗掉吗?柳赞看着自己衣领处那一块泥印,是她不肯洗,这泥印仿佛肌理大荒中的一抹灿烂,她穿着,便有了光明……那天他们在什刹海上泛舟,船夫戴硕大的草帽,撑一支杆子,皮肤黝黑。一见他们便说,你们俩很有夫妻相呀。范聚亲扶着柳赞上船,柳赞的心忽然一动。
小船在湖面缓缓而去,行过一片莲,粉白色的莲花与硕大幽绿的叶子相映成辉,在涟漪中摇摆。元伯是个好人,虽然跟我性格不大相同,但在大学这班同学里我们最要好,现在也是。
是啊!柳赞伸出手拢了拢水,水冰凉的,在手掌打了个漩流出去,坠进浅蓝的湖里。她想,元伯是个好人,也只是一个好人……或许生活就是这样,越想到达彼岸,却顺风顺水地来到了此岸,南辕北辙。
元伯一直跟我说结了婚真好。
小船上放着四脚方桌,桌上有茶,范聚亲把洗碧螺春的水倒掉,重新沏了一泡,顿时茶香四溢。柳赞的食指顺青釉茶杯口移动,几片叶子在杯中浮动,最后还是沉了下去,他什么都跟你讲?
也不是,比如你们怎么认识的,他就是不提。
柳赞饮下一口茶,想原来张元伯也有害羞的一面。这说来也巧,我们小时候做过邻居,但不大相熟,后来都搬走了。好像是毕业后的一个七夕节吧,我到邮局邮寄包裹,他在等邮件,就遇到了。后来,柳赞呵呵地摇了摇头。
范聚亲轻轻张开嘴,仿佛在说,是这样啊。
他知道那次,那次他给元伯邮了几家公司的材料,他想到北京去,元伯也想让他来。之后,元伯就没再提过去的事儿。
“小心”,范聚亲喊了一声,小船左右晃动,他旋即抓住柳赞的手。
一群野鸭没头没脑的游过来,吓得船夫迅速转向。野鸭丝毫不受他们的影响,游至船边忽然“嘎嘎嘎”彼此嬉戏打闹起来,溅得柳赞一身水。
你没事吧?范把小木凳子拖近她。柳赞一下子很紧张,手先垂在两侧又放到膝盖上,她觉得全身上下都不对,怎么做也都是错。范聚亲靠得更近,用纸巾认真地擦她身上的水渍。从衣角到领口延伸着,最后柳赞的下巴尖对着他脑顶儿,只要他再往上一点,就会戳上去。范聚亲说,这块带泥巴擦不掉了,柳赞没有做声,范聚亲才意识到他们离得太近,他的呼吸打在柳赞锁骨凹又扑回自己脸上还是热的……
登机的时间到了,柳赞向后撤了一步,头低低的,范聚亲却上前一步说,我跟元伯讲好了,过一阵子去大连看你们,仿佛这个“你”字发音很重。
柳赞点点头,上牙咬住下唇,咬得晕红仍旧没有抬头。我该走了,再见。
窗口人员核对完证件,让柳赞过安检。那一刻,她忽然转身,叫了声——范聚亲。她觉得声音很小很小,小到一粒沙尘中,沙尘随风飘散了,是她的微微世界。
范聚亲听见了,他在栏杆外引长脖子望向柳赞。柳赞远远地说,没什么,记得要来……
她想起昨夜出租车司机问她,女士您要去哪里?她半梦半醒间答:水月庵,有人在那里等我……柳赞扶着腥红的围墙跌跌撞撞走进庙门,陌生男子早已跪在佛前。他分明在说,是我,今天是七七四十九天的最后一日回魂,我赴约,来看你。
柳赞募地看向大殿下面,只有空空的蒲团。她唇角连着全身开始颤抖,是你吗?那蒲团在阳光下格外亮眼,柳赞慢慢移过去,你还是来了。此刻,众佛低眉看着她弥天盖地的悲伤,我为什么……忘不了你。柳赞一侧目,元伯从门口跑过来,究竟发生什么了?我是你丈夫,你跟我说我们一起解决。
柳赞在原地,静默了许久,许久,她苍白地说:“没什么,我们回家吧。”
张元伯有点琢磨不透他的妻,只好扶着她向庙外走去。几个女尼坐在大殿里念经,像山里的歌谣……最老的那个“当当当”敲起木鱼,空灵而悠远,声音盖住了装修的躁闹,柳赞高高地抬起头,她心中有一个客,沧海如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