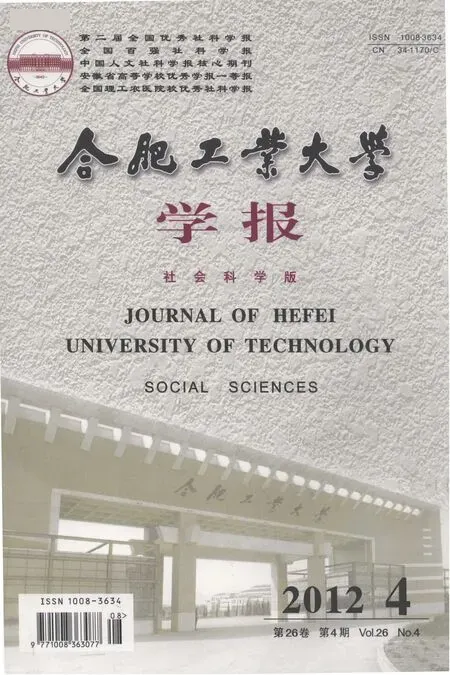近代报刊革命诗话的创作与传播
朱文华, 李德强
(1.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433;2.上海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444)
近代报刊革命诗话的创作与传播
朱文华1, 李德强2
(1.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433;2.上海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444)
清末民初,近代报刊出现了以宣传民主革命为己任的新型诗话,即革命诗话。它的产生和传播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文学产物。从其历史演变来看,近代报刊革命诗话以1911年为限,分为两个重要发展时期,并有着各自的诗学倾向。它的产生与传播一方面得益于报刊和文学的双向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国粹主义思潮推动的结果。这不但对中国诗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了重要的文化铺垫。
近代报刊;革命思想;诗话;传播
清末民初之际,随着报刊事业的发展和革命运动的高涨,部分文人开始通过报刊诗话宣传革命思想,这也刺激了一种新型报刊诗话——革命诗话的产生。不同于传统“封闭型”的诗话作品,此类诗话作品多直面近代社会文明,有着开放性的近代文学眼光,并成为近代革命文学的有益开端。据笔者统计,1870-1919年间,大约有三十种左右的革命诗话刊载出来。这些诗话集中于革命派创办的报刊中,其不但有放眼世界的革命豪情,亦多乱世英雄的慷慨悲歌,反映出那个时代先进人物的复杂文学心态。
一、近代报刊前期革命诗话的创作与传播
从具体创作和传播情况来看,近代报刊革命诗话以1911年为限,分为两个重要发展时期。民国成立之前,近代报刊中的革命诗话较为分散,内容也略显庞杂,有《寄轩诗话》、《粤西诗话》、《滇南诗话》、《旧民诗话》、《爱国庐诗话》、《华严阁诗话》、《旡生诗话》、《黍离诗话》等十几种作品出现,其中部分刊载于具有革命倾向的留学生报刊中。总体来看,此时期的革命诗话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明显特征。
首先,此类诗话多爱国之情,慷慨之音,并以新思想入旧风格中,具有明显“诗界革命”的特征,但比之维新派诗话作品激进许多,具有高调的民族主义倾向。正如《旧民诗话》小序所云:
诗之为道,感人最深,而最易入吟风咏月。骚人用以自遣,与民族之感官无与也。兹录古今人之诗辞,有关于种族之戚、国家之痛者,以笃吾民忧国爱种之心[1]。
不但如此,此类诗话还力图从民族文化中极力发掘新思想,为蓬勃发展的革命造势。从中也可见,革命派文人虽然反对文化专制,但却并不反对传统文化本身,且把它当作重要的文化资源以图触动国民的感情,达到宣传革命的目的。如《云南》发刊词曾明确的提出:
同等人抱此宗旨,誓竭诚效死,以输入之、传布之、提倡之、鼓吹之;或正论、或旁击、或演白话谋普及、或录事迹作例证。东鳞西爪,尽足勾稽;断简灵篇,亦寓深意[2]。
这也是这一时期的革命派对于报刊诗话的普遍态度,他们往往利用一切诗学资源为革命宣传服务,同时也推动了报刊诗话的传播;但把诗话绑在功利战车上进行高速运动,也难免会产生诸多不利影响。
其次,此类诗话重视诗品和气节,欣赏雄浑寄托之作。在诗话中,像民族英雄岳飞、戊戌六君子及诸多牺牲了的革命党人等的事迹及其相关诗作屡屡被提及,并以此来“振发国民精神”[3],其中最明显的诗学倾向即是对遗民诗人的推重。遗民诗人在鼎革之际经受住了道德的考验,其言传身教自然有着很强的示范作用和影响力,他们的高蹈姿态也具有了特殊的价值,这也与近代革命精神一气相通。在此类诗话中,像《黍离诗话》、《塞庵旧话》等作品都是以此来阐述对诗品和气节的重视。如《黍离诗话》开篇即通过前人诗歌来赞美陆秀夫的殉国行为,其云:
石田林景熙曾为陆秀夫事赋诗云:“紫宸黄阁共栖船,海气昏昏日月偏。平地已无行在所,丹心犹数中兴年。生藏鱼腹不见底,死抱龙髯直上天,板荡纯臣有如此,流芳千古更无前。”词严义正,洵足发明忠臣对心事[4]。
正是出于对“发明忠臣心事”的需要,作者不但对因民族大义而死的岳飞、曹大镐等人旌扬有加,也对遗民诗人汪元亮、程自修、徐世臣、徐波等多有颂扬。与此相应,此类作品往往重视有寄托的雄浑诗歌,以通过鼎革之际的黍离浩叹以唤醒汉民族蛰伏的痛楚,重新激发世人“驱除鞑虏”的革命情感,有着很强的革命意识。
最后,此类诗话往往以诗歌为战斗武器,具有明显的反满排清思想。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诗话也通过诗歌对清王朝对内大肆屠杀爱国志士,对外不惜以出卖主权来取媚敌国的行径作了深刻揭露,像《旡生诗话》、《迷阳庐新诗品》等作品都有此倾向。如《迷阳庐新诗品》对“维新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之诗情有独钟,并摘录其具有强烈战斗气息的《杂诗》二十首,如其十云:
妲己倾有商,褒姒灭宗周。天意信遐邈,女祸亦因由。慨当伐国日,献此美无俦。山川禀精气,民物含怨仇。并泄于一身,钟物岂非尤。方寸之祸水,胥溺及九州。颠倒怒笑间,因爱成仇雠。百物气相制,弱肉强相谋。谁谓伤人心,十世祸未休。片情累万族,念念泪交流[5]。
可见诗歌把矛头直接指向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表达出强烈的革命色彩。因而,此类诗话以复古为旗帜,又突破了“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以变雅之声为正音,这体现出革命派前期的诗论观。
二、近代报刊后期诗话的创作与传播
民国成立之后,革命呼声曾一度偃旗息鼓。但随着袁世凯政府的倒行逆施,又激起了部分革命文人的政治热情,并创作出十多种革命诗话。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革命诗话主要集中于进步刊物《民权素》和《民国日报》中。《民权素》的编辑都是倾向革命的进步文人,蒋箸超在其《序言》中曾云:
革命而后,朝益忌野,民权运命截焉,中斩同人等,冀有所表率。于是循文士之请,择其尤者,陆续都为书,此《民权素》之所由也。……上而国计,下而民生,不乏苦心孤诣,惨淡经营之作。惜乎血舌钳于市,谠言粪于野,遂令可歌可泣之文字淹没而不彰,转不若雕虫小技尤得重兴,天下人相见。究而言之,这锦心绣口者,可以遣晨夕、扶风月,于国事有何裨益焉?当传者,不敢传;于不必传者,而竟传之。世道人心,宁有底止与[6]?
从这段序言中我们可以觇见当时文学风气的变化及作者试图通过发扬传统精神来维系千年坠绪,唤起国民的爱国之心,维持民主革命的一线命脉。从中亦可见在民国初期,传统文化回归思潮的产生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正因如此,《民权素》自创刊后曾刊载出《绮霞轩诗话》、《抒怀斋诗话》、《清芬室诗话》、《秋爽斋诗话》、《琴心剑气楼诗话》等十一种革命诗话。相比而言,刊载于《国民日报》的《革命诗话》则直接通过为国捐躯的革命志士之诗来激发世人的革命斗志。其中既有“大好头颅向天掷,血中湛出自由花”的悲壮,也有“痛苦君亲恩太厚,百千万劫不能酬”的哀叹,亦有“大地秦关险/秋风易水寒/雪花歌一曲/听罢泪漫漫”[7]的凄苦之情,是那个时代的革命家心声的真实写照,具有很强的感染力。纵观此时期的革命诗话,他们的诗学风貌既承接前期革命诗话而来,又有新的开拓。
首先,此时的革命诗话多以复古为宗,普遍重视“言志”的诗学传统。同时,这些革命诗话多着眼于诗歌社会功效,对复古理论多有新的开拓,这也与革命派的文学宗旨是高度一致的。正如高旭《愿无尽庐诗话》所云;
诗贵乎复古,而固不刊之论也。然所谓复古者,在乎神似,不在乎形似。……今之作诗有二弊:其一病在背古;其二病在泥古。要之,二者均无当也。苟能深得古人之意境、神髓,虽已至新之词采点缀之,亦不为背古,谓真能复古可也。故诗界革命者,乃复古之美称[8]。
可见作者论诗虽然以复古思想为宗,力图通过继承和发扬诗歌的优秀传统来保存“国魂”,但实际上强调的是以复为变,有着鲜明的革命色彩。黄师霖先生曾指出:“高旭所要复之‘古’乃是指国之‘粹’,国之‘魂’实在即当时被理想化了的中国古代的优秀传统和民族精神。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指出创造'新意境、新理想、新感情'的诗界革命即是‘复古之美称’。换言之,文学界的‘革命’与‘复古’乃一而为二,二而为一,在精神上是完全相通的。因此这位高擎‘复古大旗’的南社主将,始终是革新诗歌的积极实践者和热情倡导者。”[9]471因而,这些革命诗话往往会走“以韵语发挥种族思想”[10]的路线,使得诗话本身所具有的诸多功能突破了诗歌的理论化形态,从而带有了更为复杂的社会和文学功能。
其次,此时期的革命诗话重视学问,倡养气,以不拘不涩为作诗之本。这些革命诗话不仅仅停留于浅层次的口号层面,而是对诗歌本身的探讨更加深入。因而这些诗话作品普遍主张以学问入之、以性灵出之的诗学途径,以达到“寄意远,而不失物情为贵”[11]的境界,像《抒怀斋诗话》、《鸣剑瘘诗话》、《愿无尽庐诗话》等对此都有精辟的论述。不但如此,这些革命诗话站在时代的高度,结合西方文艺理论对诗歌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风山诗话》所谓“融会古今、中外哲学家言,包含细人,锻炼琢磨,不蹈袭前人窠臼,以自铸伟词,别成一家,岂非诗界更新之雄杰。”[12]的理论在当时颇具代表性,有着兼收并蓄的世界眼光,也为诗歌在近代的新变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最后,此时期的革命诗话重诗歌的“用意”,具有开放性的诗学观。革命派前期的诗话作品多以复古为旗帜,力图通过诗歌来达到“为民国骚雅树先声”[13]的目的,像《旡生诗话》、《小奢摩室诗话》、《天风庐诗话》等都有此理论预设;后期的诗话作品在重视阐发思想的同时,则从多层面、多角度对诗歌的艺术进行探讨。《绿静轩诗话》所谓:“诗贵用意,尤贵自标新谛,不拾前人牙慧”[14],正是此时期革命诗话的艺术总结。这些革命诗话重视性情之笔,也欣赏多种艺术风格。他们对马君武诗的“豪放沉郁”,汪精卫诗的“凄婉悲慨”、吴绶卿诗的“俊逸雄杰”、唐常才诗的“浓艳清新”、吕惠如诗的“哀感沉挚”[10]都给予充分肯定。这种开放性诗学观不但与革命派诗人的宗旨相关,也是对传统诗学的延续和发展。因而,革命诗话的出现和传播也从侧面反映出了近代诗学风气的发展演变轨迹,其自有非常重要的社会和文学价值。当然,这些革命诗话或多或少都不能避免政治因素的影响,并以之为有力战斗武器,体现出较为明显的政治诗学形态。
三、近代报刊革命诗话的创作与传播成因
近代报刊革命诗话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文学产物,它的出现有主要两方面的原因:第一,革命诗话创作和传播,一方面得益于报刊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近代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晚晴时期,由于清廷“报禁”政策的打破,报刊数量也得到飞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899-1905年,全国新增报纸三百五十四种;1906-1911年,新增报刊八百零二种,报刊的出版地也几乎遍及全国[15]115。在民国成立后,更出现了“一时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16]211的局面。可见当时已经形成了全国性的报刊网络,并成为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如此,报刊文学尤其是诗话的创作和刊载,也出现了大发展的态势。
在此之际,传统文学的格局也发生了相应改变,尤其是梁启超提出了诗界、文界、小说界、戏曲界等系列的“革命”,也预示了文学革命时代的到来。在他的号召和倡导下,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的社会功用受到追捧,并有志于取代诗文的正宗地位。但“这些人之所以看重小说,不是为了表达,而是认为小说是在普通民众中实现启蒙的最有效的工具。归根结底,这其中仍隐藏着对小说体裁的轻视。”[17]306因而,传统诗话虽然受到一定冲击,却没有趋于消亡,而是借助现代传媒得到新的包装。报刊诗话作为特殊的文学形式,其作用亦得以显现。这些诗话的指向已经超出“话”诗本身,而具有了很强的象征意味。如刊载于《新民丛报》的《饮冰室诗话》,即是梁启超在维新变法失败后的重要作品。这部诗话的创作很大程度上乃是出于“志哀”的悲情,正如《平等阁诗话》所载女郎诗所云:“无计能醒我国民,丝丝情泪搵红巾。甘心异族欺凌惯,可有男儿愤不平?”[18]4在内忧外患中徘徊的近代知识阶层,对诗话的复杂心态已经超出了诗话本身,这其实已经为革命诗话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同维新派一样,近代革命派从开始就特别重视报刊的作用。1895年,革命派领袖孙中山即把“设报馆以开风气”(《兴中会宣言》)作为主要奋斗目标之一,这也对革命的成功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以至于孙中山后来曾很感慨地说:“此次革命事业,数十年间屡仆屡起,而卒观成于今日者,实报纸鼓吹之力。”[19]正因如此,革命派一直致力于报刊事业的发展。如1905-1911年,革命派仅在上海就创办了《国粹学报》、《竞业旬报》、《中国女报》、《神州日报》、《民呼报》、《民吁报》、《民立报》等十五家报刊,并以此来大力宣传革命思想。这些报纸为革命诗话的刊载创造了契机,像《寄轩诗话》、《呻吟庐诗话》、《爱国庐诗话》、《愿无尽庐诗话》等作品相继问世,以吸引知识阶层的关注。此后,革命诗话一直作为近代报刊重要的创作类型而长期存在。
第二,革命诗话的创作和传播,也是国粹主义思潮推动的结果。晚清以来,知识界的向西方学习,以挽救民族危亡的呼声越来越强烈。1902年2月,梁启超发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主张全面学习西方文明,公开与传统儒家道统决裂。但我们必须注意:这种社会思潮带来的最大影响并不是彻底打倒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而是突破了传统的对孔子的“一尊”态势,把孔子近代化和现世化。因为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革命派)虽然反对封建文明,但也往往把民族主义与爱国情怀联系起来,反对“见中国式微,则虽一石一华亦加轻薄”[20]的极端主义倾向。梁启超后来也承认“正惟倾心新学、新政,而愈感旧道德之可贵;亦正惟实践旧道德,而愈感新学、新政之不容已。”[21]68引进西方进化论的严复后来也认为“中国目前危难,全由人心之非,而异日一线命根,仍是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22]678把复古当做唯一救命稻草了。这种现象正是近代社会的文化异质,它不但造成了近代知识分子与传统文学无法割舍的关联,也注定了近代文学仍要在很大程度上延续着传统文学的轨迹发展。换而言之,反叛是近代文人的历史使命,复归则是他们的自觉生存状态。正是在这种文化反思下,近代国粹派应运而生。
近代国粹派的产生,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代表人物如邓实、陈去病、柳亚子、马叙伦等人多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成员。其主要成员如图所示:

注:此表根据郑师渠《晚清国粹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页)及王东杰《欧风美雨中的国学保存会》(《档案与史学》,1999年第5期)的相关人物加以整理制作
从表中可见,国学保存会成员多为革命党派,他们在治国理念上,主张暴力革命来推翻清政府;在文学观念中,又力倡保存和发扬国学,有着复杂的文化态度。因为晚晴以来,随着中国文明优势在西学东渐的风暴中渐渐丧失,这种文化焦虑也直接导致了文化信仰危机的产生。黄节在《国粹学报叙》中曾痛心疾首的说:
海波沸腾,宇内士夫痛时事之日亟,以为中国之变,古未有其变,中国之学,诚不足以救中国。于是醉心欧化,举一事,革一弊,至于风俗习惯之各不相侔者,靡不惟东西之学说是依[23]。
正因如此,他们试图“以西方学理为烛,照亮国学之精义”,即试图打通中西学术,以中证西来昌明国学,进而光大国学以存立国之本。与维新派一样,晚清国粹派也有着明显的复古思想理论预设。尽管他们有着不同的政治主张。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对国学的态度,而是在于其所代表的利益群体。正如黄霖先生所云:“这里区别不同性质的关键不在于重不重功利性,而在于将功利归于谁,换言之,也就是文学为谁服务的问题。”[9]7可以说,这种保存国粹的努力,乃是中国文化自我更新的最后尝试,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
近代报刊革命诗话的出现,正是国粹主义思潮高涨之际。这些革命诗话作品多从传统文学中发掘革命资源,通过“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24]来宣传民主革命思想。高旭在《南社启》中曾呼唤国魂的归来,他指出:
国有魂,则国存;国无魂,则国将从此亡矣!夫人莫哀于亡国,若一任国魂之飘荡失所,奚其可哉!然则国魂果何所寄?曰:寄于国学。欲存国魂,必自存国学始;而中国国学之尤为可贵者,端推文学[25]。
正是出于对国魂归来的呼喊,使得许多革命诗话得以产生和传播。通过继承和发扬古代诗歌的优秀传统来保存“国魂”,也是近代诗学领域的普遍态度。因而,此类革命诗话始终以复古为宗;但与传统复古理论不同的是,他们的复古理论乃是以复为变,有着鲜明的革命色彩。民国成立之后,以柳亚子为代表的革命派以相当高调的姿态力倡唐音,试图通过造就黄钟大吕之声来争取文化话语权,体现出这个时代文人对诗歌批评的要求。他打出的旗号仍是“一代有一代精华”的复古理论,其理论预设仍是诗运与国运相始终的路线。可见这种以复为变的诗学眼光,不但是资产阶级文学家对近代诗歌发展作出的有益探索,也是近代文人喜新恋旧文学观的诗学再现。它既发展了传统复古理论的思路,也整合了新时期复古理论的新方向,从而成就了近代报刊革命诗话的特殊风貌。
综上所述,近代报刊中革命大多都有浓厚的社会革命倾向,因而为革命呐喊成为其诗话的重要内容,体现出进步知识分子的心声。一方面,这些诗话作品从不同方面对诗歌的内容、风貌及创作规律予以理论上的探讨,不但丰富了中国诗话的理论成果,也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另一方面,这些诗话也受到时代、社会及作者等诸方面的影响,尤其重视通过诗话阐发革命精神,这也难免有肤浅和粗糙之病。此外,这些革命文人通过诗话的创作和传播极力发扬民族主义,鼓吹爱国主义,力图融中汇西,以实中华文明的意图,也使得近代报刊革命诗话往往呈现出“外之既不厚于世界文化之潮流,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26]的时代特征。这不但对中国诗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了重要的文化铺垫。
[1]旧 民.旧民诗话[J].汉帜,1907,(2):56-59.
[2]佚 名.发刊词[J].云南,1906,(10):1.
[3]于右任.本报四大宗旨[N].民呼日报,1909-10-5(1).
[4]振 公.黍离诗话旨[N].民立报,1911-7-27(4).
[5]景耀月.迷阳庐新诗品[N].民吁报,1909-11-7(4).
[6]蒋箸超.序言[J].民权素,1914,(1):1-3.
[7]瞿酲园.革命诗话[N].民国日报,1919-5-8(4).
[8]高 旭.愿无尽庐诗话[J].民权素,1915,(6):6-10.
[9]黄 霖.近代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0]韦秋梦.绮霞轩诗话[J].民权素,1914,(1-3):1-10.
[11]杨南村.抒怀斋诗话[J].民权素,1915,(12):9-12.
[12]周祥骏,风山诗话[N].生活报,1914-5-24(4).
[13]柳亚子.磨剑室杂拉话[N].民国日报,1917-8-13(4).
[14]噙 椒.绿静轩诗话[N].民立报,1911-7-17(4).
[15]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16]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三联书店,1955.
[17]马 睿.中国近代知识话语的嬗变[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18]梁启超.饮冰室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19]孙中山.民立报欢迎茶话会[N].民立报,1912-4-17:(1).
[20]鲁 迅.破恶声论[J].河南,1908,(8):16-31.
[2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2]严 复.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3]叶瑞昕.国学在新文化运动前的一场自救运动:论20世纪初的保存国粹思潮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价值[J].安徽大学学报,2002,(1):34-40.
[24]佚 名.扉页题词[J].汉声,1903:1.
[25]高 旭.南社启[N].民呼日报,1909-10-17(4).
[26]鲁 迅.文化偏至论[J].河南,1908,(7):1-18.
Cre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Revolutionary Poetry Theory Published by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n Modern Times
ZHU Wen-hua1, LI De-qiang2
(1.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2.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00444,China)
There was a new type of poetry theory,which tasked for propagating democratic revolution called revolutionary poetry theory,occurred in the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Its emergence and transmission was the special literary production of special period.The revolutionary poetry theory was divided into two development periods by the year of 1911in view of its historical evolvement,and there were different poetic trends in different periods.The cre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revolutionary poetry theory resulted from not only the bidirectional development of newspapers and literature,but the thoughts of the quint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The phenomenon had an important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poetry theory in China,and it laid a foundation for the“May Fourth”New Culture Movement.
newspaper and periodical in modern times;revolutionary ideology;poetry theory;transmission
I206.6
A
1008-3634(2012)04-0046-06
2012-06-0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0JJD75007)
朱文华(1949-),男,上海人,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蒋涛涌)